
朱湘诗全编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1.28 3.7折 ¥ 58 全新
库存4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朱湘 著;周良沛 编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41147326
出版时间2017-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201613070
上书时间2024-11-2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新诗形式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字子沅,祖籍安徽太湖,生于湖南沅陵。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回国后在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去职后,辗转漂泊,终因生活困窘愤懑,于1933年投江自杀。著有诗集《夏天》《草莽》《石门集》《永言集》;评论集《文学闲谈》《中书集》;译有《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等。
周良沛(1933- ),江西永新人。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枫叶集》《红豆集》《饮马集》《雪兆集》《雨窗集》《铁窗集》,散文集《白云深处》《流浪者》《香港香港》等。曾在新时期陆续编辑、编选了“五四”后及港、台、海外作家、诗人的全集、选集,有一百五十多位名家及新人的百多部书。历任靠前笔会中国中心成员,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委员,北京《诗刊》编委,香港《海岸线》执行编委等。
目录
夏天
自序
死
废园
迟耕
春
小河
黑夜纳凉
小河
忆西戍
宁静的夏晚
等了许久的春天
北地早春雨霁
寄一多基相
回忆
寄思潜
笼鸟歌
南归
春鸟
早晨
雪
我的心
快乐
鸟辞林
覆舟人
霁雪春阳颂
爆竹
鹅
草莽集
序诗·光明的一生
热情
答梦
饮酒
情歌
葬我
雌夜啼
摇篮歌
少年歌
婚歌
催妆曲
采莲曲
昭君出塞
晓朝曲
哭孙中山
残灰
春风
弹三弦的瞎子
有一座坟墓
雨景
有忆
日色
端阳
夏院
夏夜
雨前
当铺
秋
眼珠
猫诰
月游
还乡
王娇
尾声·梦
石门集
第一编
人生
花与鸟
歌
哭城
死之胜利
凤求凰
岁暮
生
恳求
冬
悲梦苇
招魂辞
泛海
洋
天上
那夏天
祷日
扪心
幸福
我的心
愚蒙
相信
希望
镜子
一个省城
动与静
雨
柳浪闻莺
误解
风推着树
夜歌
春歌
第二编
收魂
第三编
两行
四行
三叠令
回环调
巴俚曲
兜儿
十四行英体
十四行意体
第四编
散文诗
第五编
阴差阳错
永言集
序
寻
民意
残诗
尼语
戍卒
秋风
墓园
今宵
燕子
呼
慰元度
星文
儿歌
乞丐
问
我的诗
美之宫
回甘
小聚
西风
历史
断句
小诗三首
关外来的风
国魂
十四行
人性
神道
夏夜
兜儿
白
团头女婿
八百罗汉
新版附记
内容摘要
朱湘天赋诗才,一生孤高不肯随俗,穷困潦倒终至英年早逝,只留下不多的诗篇。朱湘著,周良沛编的《朱湘诗全编(精)》是现代文学目前的重要诗人朱湘的诗歌全编,集中了目前所能搜集的全部朱湘诗作。在白话新诗起步阶段,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诗歌在意象、格律、节奏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尤其在融会贯通旧诗词与新诗方面,为现代新诗留下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
精彩内容
序1不论怎么艰难,我们的文学,总是随着我们革命的事业在一道前进。胜利了的人民,回头去看现代文学史上的人事、是非,比之他们在被奴役的年代,更有权利,更具权威,可以加以评说。对于某些残缺、不确切、甚至被篡改了的史料,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问题越说越糊涂,以至于做出某些不确切评价的,我们自然有理清它的责任,客观地重新做出评价的问题。可是,我们的认识,决不是从“0”起步。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个完善的过程,即便针对完全陌生的问题,研究对象的陌生,也不能成为我们改换观点的理由。它的理论基础,是永远鲜活的奔流,忠于人民的基点,永立不败之地。新的时期新的思潮,可以活跃我们的思想,哪怕涌来浊流,也能在奔腾中白净。一场浩劫之后,百废待兴,拨乱反正。但乱了的,才拨正,并非乱与不乱的,都要翻个个儿,那样,“正”与“乱”之间,已无分界线,也无“拨”与“反”的必要。朱湘的诗集,就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推到面前来了。如果说,要给他翻案,那么,首先得问,他的原案是个什么样的案。如果说,要对他重新评价,那么,过去对他众说纷纭,有毁有誉,既是“重新评价”,纷纭之说中,首先要看我们自己认为哪种说法是能代表过去对诗人相对稳定的、总体的评价。有的说:朱湘曾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的济慈”。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鲁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由他来说朱湘为“中国的济慈”,非同一般。鲁迅的话,出自他的《通讯·致向培良》:“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鲁迅全集》的注释说:“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注文说“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是“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事实是,1923年,朱湘就加入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他的第一部新诗集正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新月》月刊是1928年3月办起来的,是徐志摩接掌《晨报副刊》也是在1925年10月,远在鲁迅《致向培良》之后。《副刊》改版《诗镌》,又在1926年4月1日,前后出了十一期,为期不到三个月。何况《诗镌》也不等于《新月》。那时,鲁迅既然认为“斥朱湘”的,“可以删去”,那么“似乎也已掉下去”是指什么,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明显的是:前者是借鲁迅的名义肯定朱湘,说他是“中国的济慈”;后者通过鲁迅著作的注释,得到的是另一种效果。朱湘在《南归》中说:许多朋友们一片好意,他们劝我复进玉琢的笼门,他们说带我去见济慈的莺儿,以纠正我尚未成调的歌声;殊不知我只是东方一只小鸟,我只想见荷花阴里的鸳鸯,我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我只想听九华山上的凤凰。诗人这段自白,从根本上否认了朱湘是否称得起“中国的济慈”之争的意义。济慈,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无疑是该肯定的。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只应该是:既不排外,也不媚外。任何一位真正的诗人,他只能立足于自己生根的土壤,就是同一土壤上的诗人,又得以各自的艺术个性相异于他人,才有各自诗的存在价值。因此,在诗坛一股崇洋之风兴风作浪时,对这位歌声“尚未成调”的朱湘,要朱湘去跟济慈的莺儿学舌,作为跃进龙门的手段,而诗人,只知自己“是东方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松间的白鹤”,又是怎样的一只东方鸟啊。对这样一位诗人,怎么评价他的创作成是另一回事,他这种追求,却不能不说是真正的诗的追求。这位诗人,很久很久,几十年都没人提起了,也许是被人遗忘,也许另有原因。诗人,生前未必被人认识;身后,有待我们认识。2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却没有到过太湖。1917上半年还在江苏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三年级读书,下半年就上南京工业学校,有志学实科。1919年秋,考上清华学校,插入中等科四年级。1924年即将毕业时,因为抵制斋务处在学生吃早餐时点名的制度,经常故意不到,记满三个大过被开除学籍,轰动全校。事后他写信给罗念生说:“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占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揉。”1925年3月,他在南京同刘霓君结婚,这是门当户对的人家,指腹为婚的亲事。代父行使家长职权的长兄要五弟行跪拜礼,弟弟只肯行新礼鞠躬。晚上哥哥大“闹”新房,把喜烛打成两截,新郎当即离去,搬到抚养他长大的、曾留学法国的二嫂薛琪英家。1924年,朱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他的译诗《路玛(罗马)尼亚民歌》、新诗创作《夏天》,也是以《文学研究会丛书》分别于1924年及翌年出版的。1926年,徐志摩办起了《诗镌》,它是以诗的名义吸引了作为诗人的朱湘。并由刘梦苇、闻一多、“清华四子”——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轮流编辑,徐志摩、闻一多出面负责。很快,因为诗人刘梦苇与杨子惠的逝世,朱湘看到《诗镌》没有很好地表示纪念,加上平日看不惯那些人的生活作风,就与徐志摩闹翻了,拂袖而去,以示他对亡友的义气。五年之后,他又写了《悼徐志摩》,为“《花间集》的后嗣”早逝而“酸辛”。也是出于同样的感情吧。因此,今天把他当年这番行为作为对“新月”的革命,大可不必。反过来,硬要把他跟“新月”捆在一起,也非事实。当时,他写的《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从某一个角度看,也许他对诗的形式、音律的要求,其唯美的色彩并不亚于徐、闻,可是,胸襟坦白,还不是结党营私之词。1927年8月,朱湘结伴柳无忌,由上海乘船赴美留学。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亚坡屯(Appleton)进劳伦斯大学(Lawrence College)四年级,选修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国文学。有一次,法文班上念法国作家都德(Léon Daudet 1867—1942)的游记,上面说中国人像猴子,学生听了哄堂大笑,朱湘当即退出课堂,尽管教师向他表示歉意,他还是愤然离开劳伦斯,转到芝加哥大学,念高级班德文和古希腊文。把辛弃疾与欧阳修的词译成英文诗;自己也用英文写诗,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后来,因为一位教员疑心他不曾将借用的书归还,可杀不可辱的诗人,又愤然离去,转到俄亥俄大学。旅美两年,总是伴着颓伤之情。1929年9月他回国,在安徽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他教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却常和夫人口角,生活也不愉快,除饶孟侃、谢文炳外,很少和同事们往来。1929年暑假,学校改组,因为欠薪半年有余,有人自动离去。朱湘对人热情、直爽,又倔强、暴烈,容易轻信于人,更不洞达人情世故,处处上当,得罪人太多,学校改组,他也没有接到聘书。出国前,有人认为他和闻一多、徐志摩关系好,可以找胡适上北大教书,他丝毫不予考虑:“找他们?犯不着!”好友柳无忌电报通知他上南开大学,他也不想去。离开安大,南北奔波,一直没有找到职业。在清华读书时,吃饭都是向厨房赊账,由罗念生担保付还,但他还要挤出钱来办一个只有二十个订户的刊物《新文》,在东安市场的一家旧书摊发行,出了两期就停了。自费印行,费神、亏本,他却很得意:“什么都是自己出的主意,那一股滋味真是说不出的那样钻心。”后来,钻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拿到钱时,还买些古玩、字画,夫妻吵架,又全给砸毁。学校欠薪时,这位系主任的幼子,不到一岁,因为没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被饿死。他离开安大后,更加狼狈。有时因为付不起房钱,人被旅馆扣留,竟要茶房押去找朋友解救。写诗译诗,实难糊口养家,何况人家说他的诗不如戏票值钱。而写稿,也得诗文刊出之后才付稿费,远水不解近渴。他,既无媚骨,也难随和。不太愿意找人帮忙,拿着稿费单也不愿抛头露面去取,既自傲,又自卑。他冷天身穿夹袍,妻子从邮局寄来的棉袍一到手却立即送进当铺。走投无路,贫寒难熬,他向寡嫂薛琪英借了二十元,买了三等船票,于1933年12月4日,由上海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6时,他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取出酒来喝了半瓶,倚着船舷,读着原文的海涅诗,当船过传说李白捞月的采石矶,纵身投江……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位孤高不肯随俗的诗人,蹈赴清流,寻其归宿。一位诗人的悲剧,一个悲剧性的诗人。自好难洁身,洁身难生存,诗人的悲剧,不是对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控诉么?一个诗人,在黑暗的旧社会,没有同人民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点,一同笑,一道哭,一起斗争,靠个人奋斗,凭个人意气,横冲直闯,头破血流,尽管磨难对他太多,他还是在磨难之中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尽管创作的成就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荣誉,他的傲慢、孤僻,仿佛胜利全在他的掌握中。后来这悲剧的果实,社会原因是种子,诗人自身的弱点,也不同样是酿成悲剧的因素之一么?凡此种种,对于今天的诗坛,它也提出了有益于我们思考的问题。3不仅今天的年轻人,就是中年人,对朱湘,也只知道他是一位“新月诗人”。“新月诗人”的雅号,是1931年二十一岁的陈梦家编选了《新月诗选》之后,人们奉送给入选的十八位诗人的。古代的、外国的例子不去说它,同是“五四”后的新诗,1922年出版了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的新诗合集《湖畔》之后,人们称他们为“湖畔诗人”。既然如此,那么,称前者为“新月诗人”,也就自然而然了。《新月诗选·序》说:“这诗选,打《北京晨报·诗镌》数到《新月》月刊以及最近出世的诗刊并各人的专集中,挑选出来的。”因此,目前有的同志为了回避谈“新月”,强说《诗镌》与《新月》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是不容混淆的界线,极不实事求是。《新月诗选·序》又说:“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仅仅一种方向,也不知道那目的离得我们多远!我们只是虔诚地朝着那一条希望的道上走。此外,态度的严正又是我们共同的信心。”海外有种说法,认为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以“格律诗派”统括“新月”,才名实相符。《新月诗选·序》却宣称:“但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又说:“技巧乃是从印象到表现的过渡,要准确适当,不使橘树过了河成了枳棘。”事实上,“新月”之中的有些诗人,对形式、技巧追求的固执,明显的是唯美与形式主义的,但在这序言中,对形式与技巧的看法,还没有陷入形而上学。一群诗友以追求“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作为他们“一致的方向”,不是遭人非议的理由。可是,“新月诗人”既不等同“新月社”,也不能说互无干系。“新月社”,既是文学,也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政治团体。约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1926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镌》(周刊),1927年在上海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核心人物是胡适、梁实秋、叶公超、陈源、闻一多、徐志摩、罗隆基等。他们当中,有诗人,也有政客、银行家、交际花。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又投靠国民党,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新月》月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阵地。鲁迅先生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讲到:“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可是梁实秋的文字里“我们”“我们”的,“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先生指明的正是这种情况。因此,“新月社”以它自身的活动,是作为革命文学运动的负面留存文学史中。而文学运动,也不是指文人在书斋里骚动的灵感,而是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映以及整个战场的一角,是和大革命前后的人民的命运相联的。撇开这样的历史背景,则会将当时论争的原则看作“学术问题”、“笔墨官司”。但“新月”的活动,长达十年之久。前后的成员,有很大的变动,各人的发展变化很不相同,有的向“左”,有的向右。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不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看“新月”,也不能不对“新月”的成员具体人做具体分析。当年,向《诗镌》《新月》投稿的年轻人,多数是不会参与“新月”诗之外的活动。如果把他们同“现代评论派”那些明目张胆地攻击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枪手相提并论,极不求实;但是,他们不少唯美、形式主义的抒情小诗,既是作为当时“新月”文艺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服务、壮大它声威的力量。这一点,是不以诗人创作的主观意图为转移的,于是,当我们看那些创作思想、美学原则的总体倾向,绝对无法点头苟同。无怪同情朱湘的人,希望今天不要再把他和“新月”扯在一起。4朱湘,如果是“新月诗人”又怎么样?朱湘,如果不是“新月诗人”又怎么样?闻一多,是伟大的民主斗士。可是,他早期确实是位道道地地的“新月”主将,且曾大力宣传国家主义。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的高压下,他“拍案而起”,站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前列,以自己的鲜血写出这位唯美主义者从未达到的美的诗篇。有的同志故意回避谈他曾是“新月诗人”,担心损害他的形象。用心虽好,却无必要。相反,他能从过去的信仰转到做出最后为人民战斗的选择,只能说明人民革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只能说明闻一多是多么曲折、艰难地攀登到他最后的人生高度。除此,还有什么呢?如果只是看“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是无法把“创造”的诗人视为革命者的。而郭沫若作为“创造”的主将,谁也无法否认他诗的革命。虽然,他以后自认为“标语人”、“口号人”,他在《女神》的各次版本上怎样能显示自己“革命”就怎样改动的做法,也是无法让人苟同。但《女神》时代的郭沫若,比起同时代的许多宣传“为人生而艺术”的诗人,他在诗行中表达出来的民主革命的思想,更强烈,更激进,也更艺术。为此,胡适的《尝试集》虽然是中国的第一本白话诗集,而新诗运动的奠基作品,却只能是《女神》。“新月”的闻一多同样是赞扬它的,“创造”的同人既赞扬它,也著文欣赏与郭沫若的创作倾向完全不同的王独清。就是同是革命作家的冯乃超、穆木天同志,在“创造”时,艺术上与郭沫若也不对路。所以,对那个时代的诗人,若以他参加的文学社团,“站队划线”,对其思想、艺术倾向以此定性,做终身鉴定,极不科学。这样来看朱湘,我们就不必花太大的精力考证他是不是“新月”诗人了。如果,作品选入《新月诗选》的诗人,可以泛称“新月诗人”,那么,称朱湘为“新月诗人”也不是名不正,言不顺;如果,把梁实秋之流攻击革命文学的劣迹与《新月诗选》中的作品混为一谈,结果,“新月”在事实上就成了一顶政治帽子,这样,在研究现代文学接触到这一诗歌流派时,不可能有个科学的态度。这十八位诗人,有的后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甚至是共产党人,要是笼统地给每人一顶这样的帽子,又会制造一些冤案啊!“新月诗人”四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若以某种利害关系来弄清它确切的含义,倒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前人一些是非,不是当事者,旁观者既更清醒,也可能难悉其中奥秘。但是,最能说明诗人本身的,还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他的宣言,他所参加的文学社团对他的影响,也是从他笔下表现出来。否则,闻一多不枉真诚的唯美、形式主义的文学宣言,若以“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样的诗句,想去印证他的某些宣言,就要乱套了。5时间的变化,会带来世间许多事物的变化,但成历史的作品,是变不了的。今天的人,只有掌握更先进的世界观来认识它,可以摆脱当年某些非诗的因素来看待。朱湘收在《新月诗选》中叫响的作品,怕数《当铺》了: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短短四行诗,隔行押了两个韵。一、三两行七字,二、四两行五字,两对音步,字数完全相等,格律严谨,外形漂亮。在很精致、考究的形式中,表达了人们为美所燃起的热情,只能随美而去而不复归的人生体验和叹息。美的追求是美好的感情,但是,此处的“美”,是没有具体内容、具体形象的,是抽象得什么人都可以接受的“美”。与空气一般,无从捉摸,亦不知抵抗,远望去一片青。落落展开在天上……狎弄它的要提防暴风来号令一切,凭它得到的权势兴隆,随了它毁灭。——《民意》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头脑清醒之际还知道人民是水、君王是舟的关系。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有“载舟覆舟,所宜深慎”之言。朱湘在《民意》中,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警句,而是以自己的艺术方式,表达了另一个时代的人的切身感受。显然,诗人是深感于民意受到践踏,但他却对反动的统治者说“凭它得到的权势兴隆,随了它毁灭”,从而显示出民意不可轻视,民不可侮的气概。朱湘在那时能呼出这样的声音,是可贵的。从这里,倒颇能体现他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因此,从“组织关系”(恕我借用一下这个现代用词),从创作倾向看,他当属“新月”,还是“文学研究会”?如果说《民意》,是诗人对逆民意而行者的警告,那么,《呼》就是直接形象地展示人民的力量了:谁能压得住火山不爆?就是岩石也无法提防,它取道去寻太阳。挡不住劲风,也不能叫松;要北风怒号,才会有松涛澎湃过黑云与紫电的长空这首写于1926年10月的诗,写得很有气势,写得形象动人。为了内容的表现的需要,对于有时还赖形式的雕凿、词藻的典雅来表现其诗的人,此时写得这等雄劲有力,挥洒自如,确是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这样的诗,恰恰是诗人跟“新月”闹翻了之后的作品。可惜,诗人生前顾忌它们是“讥讽世俗”的“骂世之作”,编进诗集又删去了。罗念生回忆朱湘的文章也说道,1927年,朱湘存了一小皮箱诗稿在他处,都在战事中失散了。对于当时已经成名的朱湘,当中肯定有不少都是当时拿不出来的“骂世之作”。它们在今天是最能说明朱湘的,可是,因为诗人当时拿不出来,今天就使我们少了很多能够为他说明真情的证词。这是一个悲剧。人们被剥夺了发言权,被扼死的声音,也是可悲于沉默的强音!这是一个悲剧,是诗人没有勇敢地面对惨淡的人生为大众呼号的悲剧,是个留给我们的警号,可他的悲剧依然是悲剧。有些诗,像《尼语》,无非是写点尼姑思凡之情,有什么可怕呢?封建的卫道者是何等顽固,要是怨诗人脆弱,看看它也够脆弱了。于是,诗人拿出来留到现在的作品,就多是当时的现实还允许他用心于技巧,精于音律之作了。今天有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小时候在课本上就有朱湘的《采莲曲》:小船呀轻飘杨柳呀风里颠摇;荷叶呀翠盖,荷花呀人样娇娆。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左行,右撑,莲舟上扬起歌声。菡萏呀半开,蜂蝶呀不许轻来,绿水呀相伴,清净呀不染尘埃。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拍紧,拍轻,桨声应答着歌声。…………写得甜美、和谐,表现细腻,气韵舒雅,音节婉转抑扬。在诗的形式上达到这么考究、精致的,真不多见。朱湘批评过闻一多用字的四个毛病:太文。太累。太晦。太怪。他用闻诗“是天仙的玉唾溅在天边”这一句为例,以为从“咳唾成珠玉”而演化为“玉唾”一词就太怪,“溅在天边”就没有“落在天边”准确。一般地说,能看到别人的毛病,并不等于自己没有同样的毛病,而在这些地方,朱湘还是很注意自己的。他寄信给彭基相说:“我们要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暂时借助于西方文化,这并不足为耻;西方从前也自曾舶去了我国的指南针、火药与印刷术。中国将来最大的恐慌便是怕产生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西方式文化,甚至也不换汤也不换药的纯粹西方文化。”诗人死后发表的《谈诗》,从《诗经》《楚辞》引了许多诗句赞叹“旧诗之丰富”后说:“旧诗之不可不读,正像西诗之不可不读那样;这是作新诗的人所应记住的。”朱湘既用英文写诗,也尝试了多种西体的格律诗。而他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有见地的。就像《采莲曲》,形式整齐却不豆腐干式的呆板,而是长短参差,错落有致,是有规律可循的变化。写得安详而细腻,将东方人,近乎古典式的、富丽的色彩与优雅的音乐融铸在诗行中。这完全是词曲式的格律,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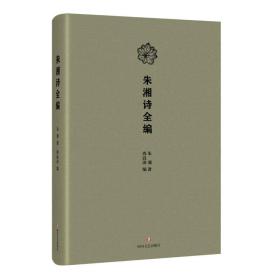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