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6.04 5.8折 ¥ 79 全新
库存80件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 著 田雷 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76403916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9元
货号1202634939
上书时间2024-11-1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年生,现为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席教授,创立并主持耶鲁农政研究中心。斯科特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至1998年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2020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将最高荣誉“阿尔伯特·赫希曼奖”授予斯科特,以表彰他“广博而卓越的跨学科研究”。其主要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弱者的武器》《支配与抵抗艺术》《国家的视角》《逃避统治的艺术》均有中译本,读者众多。
关于译者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法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耶鲁大学法学院,2008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近期出版专著《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译著《我们的孩子》《娇惯的心灵》《寒门子弟上大学》。“雅理”出版策划与主理人。
目录
前 言
导 论 一个支离破碎的叙事:那些我曾一无所知的
第一章 “驯化”的长历史:从用火、栽培植物、驯养动物,最终是……人类自己
第二章 世界的地景改造:先民的农庄系统
第三章 人畜共患病:流行病的"暴风雨"
第四章 谷物立国:早期国家的农业生态
第五章 人口控制:奴役与战争
第六章 早期国家的脆弱:形为崩溃,实为解体
第七章 蛮族人的流金岁月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带领读者穿越到人类早期文明国家形成的历史,著名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巴里·坎利夫爵士盛赞本书:“历史就应该这么写!”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家、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最新著作,全书以大历史的纵横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主要关注两河流域也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初民国家,必要时也纳入了对古埃及文明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分析。这是斯科特集毕生功力,综合考古学、生物学、环境史、人口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所写作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本书既有跨越数千年、游走多个人类早期文明的恢弘视野,同时又随处可见严谨、细致、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分析,对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个文明史的大问题,书中提出了若干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主编推荐
无政府主义者的视角、横跨多个学科、于细微处见真章,是贯穿斯科特所有著作的三大特点,宝刀不老的他在81岁时推出的这本书也不例外,满是智慧的闪光点。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由人类如何驯化谷类及动物,到早期国家形成而人类自己成为统治者的驯养动物,书名带有反讽意味的《作茧自缚》,描述的便是此一过程。这是作者斯科特继1970年代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80年代的《弱者的武器》之后,又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特别是许多国家皆在努力重振或拯救农村经济时,由人类文明与国家“根源”来反思此议题特别具有意义。
——王明珂 台湾“中研院”院士、“史语所”特聘研究员
人类学问的每一步前进,均得益于挣脱思想束缚的探索者。年过八旬的斯科特这次将目光从熟悉的现当代的东南亚投射到远古,跨到两河流域文明初期。这一步迈过了数千年、数千公里,他将国家相对化的思考让诸多遁入无思黑暗中的前提暴露在阳光下。本书与其说是两河流域的早期史,不如说是人类学家对农耕与国家关系的追问,是对国家初兴时状态的剖析。斯科特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颠覆了诸多既有的认识,是否能成定论,还需更多的验证;在旁人止步处继续前行,将思考踏袭的基石翻起来检验一番的勇气,最为可贵。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斯科特教授充满原创性的著作,历史就应该这么写!
——巴里·坎利夫 牛津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反政治叙事的当代大师,在此完成了一部论述文明起源的经典——话不多说,这是一本必读的书!
——大卫·温格罗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所教授
精彩内容
诸位在此将要读到的,是一份越界者的“勘探报告”。首先容我解释此中缘由。2011年,我接到邀请,要在哈佛大学举办两场塔纳系列讲座。收到邀请令我倍感荣幸,不过当时我刚刚完成一部耗费心力的书,正处在学术的休整期——“自由阅读”,眼前并无具体目标可言。四个月的时间,我究竟能做出什么有趣的东西呢?先要找到一个可以处理的主题,开动脑筋,我想到过去二十年来,在一门讨论农业社会的研究生课程中,我习惯用两讲作为课程的开场白。这两次课,内容涵盖了人类驯化动植物的历史以及初民国家的农业结构。虽然这两讲也曾不断更新调整,但我知道,其中内容可能早已过时。于是我想到,不妨让自己浸淫在讨论驯化问题以及初民国家的近期著述中,至少写出两篇讲稿,一方面跟进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能应对我课上那些目光如炬的学生。
接下来的经历,可说是一路惊奇!讲座的准备过程,颠覆了许多此前我自以为是的东西,也让我接触到一系列新的学术辩论和发现,由此我意识到,要适当地处理这个题目,我务必尽可能充实自己。故而,最终完成的塔纳两讲,充其量不过是表达出我自己的震惊——原来,需要彻底重审的老生常谈是如此之多,而距离真正开启重新检讨,尚有一段距离。讲座的主持人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教授,他为我精心挑选了三位敏锐的评议人——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和微依那·达斯(Veena Das)——在紧随讲座的研讨会上,他们让我心悦诚服:我的论证远远未到公开发表的程度。等到五年过后,我才拿出了一部书稿,自认为有理有据,且能激起学界的兴致。
因此,这本书反映了我尝试再挖深一些的努力。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仍是一位“外行”的作品。虽然我的名片上印着政治学家的头衔,且承蒙学界好意,也有人类学家和环境问题专家的名头,但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在史前史、考古学、古代史和人类学的交合处进行钻研。在上述这些领域内,我压根没有任何个人的专业知识,有鉴于此,我若被指责为狂妄自大,其实也并不为过。对于这次越界行径,我的辩护(可能谈不上正当理据)包括如下三重:第一,天真者亦有天真者的优势!不同于沉浸在各自领域的专家们,喋喋不休于针锋相对的论争,我的论述起始于大多数未经检视的理论预设——关于动植物的驯化,关于从迁徙到定居,关于早期人口中心,关于初民国家——若是未能跟踪过去二十年间的新知,这些预设就很容易被不假思索地奉为真理。就此而言,我的无知,以及在认清自己此前无知后的“大跌眼镜”,反而构成了某种优势,毕竟本书所预设的读者群想来可能也持有相同的误解。第二,作为一名“消费者”,我兢兢业业,凡同本书议题有涉,无论是生物学、流行病学、考古学、古代历史、人口学,以及环境史,我都设法去跟踪其中最新的学识和争论。第三,就我的学术背景而言,过去二十年来,我都致力于去理解现代国家权力的逻辑[参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以及非国家族群的诸多惯习,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那里的“化外民众”直至近期还在逃避国家的吸纳[参见《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所以说,本书是一个自觉的衍生项目。它并未开创出任何属于自己的新知,但仍怀有自身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将现存的知识“整合出新的图景”,以期带来或明或暗的启示。过去数十年间,我们的理解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从根本上修正甚或完全颠覆了我们此前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以及别处初民“文明”的认知。我们认为(至少大多数学者如此),动植物的驯化直接导向了初民的定居生活和定点农业。然而事实却证明,定居现象之存在,远远早于现已发现的动植物驯化之证据,而且要等到定居以及驯养动植物存在至少四千年后,才有了某种农业村落的出现。通说认为,从迁徙转向定居以及市镇的首次出现,乃是由于灌溉农事以及国家的作用。但事实却证明,两者通常都起因于湿地的丰富物产。我们曾经认为,定居以及作物栽培直接导向了国家的形成,然而事实却是,要等到定点农业出现许久过后,国家才突然间冒出头来。各种学说也通常设定,走向农业是人类向前迈出的伟大一步,无论福祉、营养,还是生活之闲适,都随之进步。但最初的历史情况却恰恰相反。国家以及早期文明经常被视为吸引力极强的中心,凭借其奢华、文化和种种机会,吸引人口归附。但事实上,早期国家却不得不动用奴役的手段,捕获人口并且控制其中的大部分,更何况,因居住拥挤,先民们还要承受流行病的肆虐。早期国家是脆弱的,且易于崩溃,但继之而起的“黑暗时代”却常常标志着人类福祉真切的改善。最终,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史实要予以正视,自外于国家的生活——也即“蛮族”的生活——就物质层面而言,常常过得更轻松,更自由,也更健康,至少相较于文明社会内的劳苦大众是如此。
当然,我很清醒,关于动植物驯化,关于早期国家形成,或者关于早期国家与其
相关推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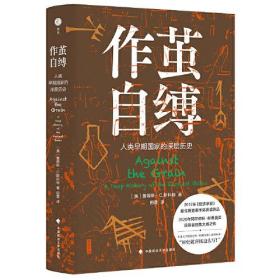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北京
¥ 49.0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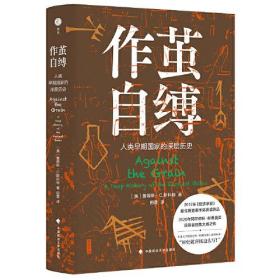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保定
¥ 52.00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南京
¥ 52.93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广州
¥ 46.04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广州
¥ 44.04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东莞
¥ 46.98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天津
¥ 45.34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广州
¥ 46.04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北京
¥ 53.90
-

作茧自缚 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全新广州
¥ 44.04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