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罪与罚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56.98 5.8折 ¥ 99 全新
库存45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出版社人民文学
ISBN9787020184934
出版时间2024-06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99元
货号1203300369
上书时间2024-07-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世界级心理描写大师,就国际影响力而言与列夫·托尔斯泰难分轩轾。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译者简介:臧仲伦(1931—2014),江苏武进人,著名文学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研究生班,历任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时数十年辛勤笔耕,臧仲伦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此外,他还译有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与巴金合译有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目录
目录
译本前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尾声
内容摘要
《罪与罚》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并为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小说主人公贫穷的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还顺带杀死了碰巧看到这一切的老太婆的妹妹。尽管有自己的一套杀人理论,他仍在自身罪恶感的折磨下,受尽痛苦。最后,他在索尼娅的规劝下投案自首,决心用人间的苦难来洗净自己的罪孽与灵魂。
精彩内容
译本前言
看看俄罗斯穷人的“自由”《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
这是一部催人泪下的社会悲剧。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哲理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要在这部小说中发掘一切问题”。问题很多,但问题的中心是“人”——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当时,由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实行了所谓的“农奴制改革”,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迅速瓦解,新的资本主义势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以十分野蛮的方式急遽发展;广大农民经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纷纷破产,逃亡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与原有的城市贫民一起,充斥着城市的穷街陋巷,过着啼饥号寒、衣食无着的悲惨生活。彼得堡的干草市场及其附近的大街小巷,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聚居着大批穷苦的工人、手艺人、小商贩、出身微贱的小官吏和穷大学生。这里是穷人的地狱,罪恶的渊薮。这里除了妓院外还充斥着各种酒馆。仅本书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居住的彼得堡木匠胡同,就有十八家大大小小的酒店。穷人除了干活就是到小酒店买醉。他们住在相当于我国北方大杂院的旧公寓楼里,那里又黑又脏,有如圣经中描写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和蛾摩拉。这里既有放印子钱的高利贷者和催逼房租的二房东,又有一无所有的穷人、醉汉、小偷、妓女、恶棍,甚至杀人犯。但是,君知否:在这表面的贫穷、犯罪和堕落后面,又有多少人间的苦难和难言的隐痛!
“一个人总要有条路可走啊!”“您明白吗,仁慈的先生,您明白什么叫走投无路吗?”这是穷公务员马尔梅拉多夫在丢掉工作之后斯文扫地、衣食无着、穷极无奈,只能借酒浇愁时的绝望哀鸣。
穷人在旧俄国走投无路——这就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人的命运”。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国,穷人面前只有三条绝路:一是啼饥号寒,冻馁而死;二是苟且偷生;三是铤而走险。
走第一条路的是绝大多数穷人。在当时的俄国,穷人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上不足以赡养父母,下不足以抚养妻儿弟妹。诚如索尼娅的父亲马尔梅拉多夫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所说:依足下之见,一个贫穷,但是清白的姑娘,靠诚实的劳动能挣多少钱呢?……如果她清清白白,但是没有特别的才能,即使她的两手不停地干活,先生,一天也挣不了十五个戈比啊!
而这点钱既不足以果腹,也不足以养家,他们“三天两头见不到一块面包”。
本书用浓重的笔触,使人扼腕三叹地描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悲惨遭遇。
酗酒,在俄国是一个古老而又现实的问题,数世纪以来,直至当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罪与罚》在作者构思之初即名《醉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6月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小说名为《醉汉》,它的内容与当前酗酒问题有关。”穷人酗酒的主要原因是穷——穷到走投无路,只能借酒浇愁。由于穷,由于走投无路,才酗酒;由于酗酒,就更穷,更走投无路。马尔梅拉多夫在他的浸透了血泪的自白中说道:贫穷不是罪过,这话不假。我也知道,酗酒并非美德,这话更对。但是一无所有,先生,一无所有却是罪过呀……对于一个一贫如洗的人,甚至不是用棍子把他从人类社会中赶出去,而是应该用扫帚把他扫出去,从而使他斯文扫地,无地自容。这样做是天公地道的,因为,当我穷到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就头一个愿意使自己蒙受奇耻大辱。街头买醉,即由此而来!
…………我喝酒,因为我想加倍痛苦!
不久,这部小说的构思逐渐发生变化。作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俄国的年青一代以及当时热烈争论的俄国发展道路问题上。原来构思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命运,成了《罪与罚》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尔梅拉多夫的自白,不仅是穷人悲苦的号泣,也是对俄国畸形社会的血泪控诉,是小说最优秀的篇章之一。
为生活所迫走第二条苟且偷生的路的,在当时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书中的女主人公索尼娅和杜尼娅。
索尼娅是马尔梅拉多夫的长女,年方十七。她为了养活自己的双亲和弟妹,不得不忍辱含垢,被迫为娼。杜尼娅是本书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妹妹,她先是在一个地主家当家庭教师。为了帮助自己的哥哥上大学,她向东家预支了一百卢布。可是偏巧赶上这家老爷是个色狼。为了还债,为了摆脱东家的性骚扰,更主要是为了哥哥,两害相权取其轻,她不得已同意嫁给一个她既不爱也不尊敬的市侩卢仁。名义上是妻子,实际上是买卖婚姻,用她哥哥的话说,“做他的合法的姘妇”。
同样为了亲人,一个被迫为娼,一个变相为娼。
对于仍旧保持着灵魂纯洁的索尼娅来说,她前面只有三条路:跳河,进疯人院,或者……最后,自甘堕落,头脑麻木,心如铁石。她之所以没有投河自尽,是因为她想到她的父母和弟妹。她死了,谁来养活他们?仅仅是把苦难留给了生者。如果说她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疯,那也只是时间问题。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曾自言自语地说再过两三个星期,她就要进疯人院了。他也曾当面对索尼娅说:“倘若你仍旧独自一人,你会受不了的,你会发疯的,像我一样。”那么,最终她将自甘堕落吗?不,她是灵魂圣洁的化身,也是人间苦难的化身。“这整个耻辱,显然,还只触及她的表面;真正的淫乱还没有一点一滴侵入她的内心。”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内心独白时曾经说过:“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索涅奇卡就是永存的!”这话一语双关:既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又是对索尼娅为他人牺牲自己、甘愿承受苦难,但又保持自己灵魂纯洁的赞美和讴歌。
杜尼娅是一个聪明、美丽而又高傲的姑娘,她“许多事都能忍,甚至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她也能处之泰然,坚贞不屈”。那她为什么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卢仁呢?是贫穷,是堕落,是贪图富贵吗?都不是。她“宁肯去给美国的农场主当黑奴,或者去给波罗的海东岸的德国人当拉脱维亚农奴,也决不肯玷污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道德情操,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永远委身于一个她既不尊重,而又丝毫合不来的人!哪怕卢仁先生是纯金打的,或者是一整块钻石做的,她也绝不会同意去做卢仁先生的合法的姘妇!那么为什么现在她又同意了呢?这是在玩什么鬼把戏呢?谜底究竟在哪里呢?事情很清楚:为了她自己,为了她自己的荣华富贵,哪怕为了救自己的命,她都不会出卖自己,可是为了别人她出卖了自己!”“为了哥哥,为了母亲,她可以出卖自己!一切都可以出卖!啊,必要时,我们甚至可以压制自己的道德感;把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一切都拿到旧货市场去拍卖。就让我的一生毁了吧,只要我们心爱的人能够幸福!”她们俩忍辱含垢,苟且偷生,不是道德沦丧,不是贪图富贵,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自己的亲人。
像她们一样陷入走投无路绝境的,还有本书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但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原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法律,但迫于贫困,不得不中途辍学,靠给商人子弟当家庭教师为生。他住在一间向二房东租来的棺材似的小屋里,后来连教书的事也丢了,衣食无着,债台高筑。他贫病交加,四顾茫然,决定铤而走险。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抢走了她的钱财。为了杀人灭口,他在杀死那个老太婆之后,还杀了刚好回到家里的老太婆的妹妹利扎韦塔。
蓄意杀人,是他苦苦思索的结果,是他的“理论”的产物。他炮制了一套“犯罪论”,或曰“杀人有理论”。他把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两类:平凡的人必须俯首帖耳,任人宰割,不敢触犯刑律;“而不平凡的人,正由于他们不平凡,有权干任何犯法的事,胡作非为,无视法律”。
这个理论是荒谬的,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总结,是强权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本来是一篇声讨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战斗檄文,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却把这一理论看成了绝对真理,看成了千古不移的法则: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他认为自己就是穆罕默德,就是拿破仑,是“超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美好的未来,他可以于心无愧地跨过尸体,跨过他人的血泊。他甚至欢呼:“从古到今永远打不完的战争万岁!”拉斯科利尼科夫走上犯罪道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一方面,他是被压迫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不甘心任人宰割,想反抗;另一方面,因为他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正确的信仰,他的反抗只能是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铤而走险,以恶抗恶,用豺狼哲学反对豺狼哲学。他心目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爱,不是平等,而是统治与被统治,即“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在他看来,只有拿破仑,只有穆罕默德,只有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人,其他人都是群氓,都是“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前写过一部小说,名曰《双重人格》(又译《同貌人》,1846),主人公叫高利亚德金。他是彼得堡的一名小公务员,地位低下,备受欺凌,而且性格怯懦,“胆小得像母鸡”。他也想阿谀奉承,投机钻营,攀龙附凤,成为“社会的宠儿”,但是他又顾虑重重,缺乏干无耻勾当的胆量和本领。他想往上爬,但又瞻前顾后,因而思想苦闷,产生了精神分裂: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幻化成另一个人,即小高利亚德金。这是个卑鄙无耻、八面玲珑、阴险狡诈的乞乞科夫式人物。小高利亚德金实际上是大高利亚德金的理想,是他想做而又不敢做或做不到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他的这一化身卑劣得使他感到可怕。他不敢正视这个化身,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发疯。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是理解《罪与罚》和作家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高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高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象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的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玛丽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
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双重性,首先表现在他的性格上。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在轮流起作用。正如他的好友拉祖米欣所说:“就好像他身上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人在交替出现。”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而且见义勇为,富有恻隐心。譬如,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曾帮助过一个患病的穷同学,维持这同学的生活达半年之久,这同学病故后,他又替他赡养年老多病的父亲,直至下葬。此外,他还从一座失火的房子里奋不顾身地救出两个孩子。最后,他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又倾其所有,为惨死于马蹄下的马尔梅拉多夫办理丧事。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犯。他不但杀害了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而且还殃及无辜,杀死了她的妹妹——一个善良而又备受欺凌的基督徒。
其次,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双重性还表现在他的犯罪动机上。他认为“这一切的原因是他的恶劣的境遇,他的贫穷和走投无路”。他杀人,一为母亲,二为妹妹,三为造福人类。但是转眼之间他又否认了上述说法:“这是胡扯!”“我只是简简单单地杀人;杀人,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一己的私利。”第一个动机说明,是社会把他逼上了犯罪道路。他杀人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他人的幸福,是为了造福人民。对于这样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不同意。除《罪与罚》外,作者在自己的小说中曾描写或提到过好几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案,作者通过书中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嘲笑过“杀人是因为穷”这一荒谬论点。正如《罪与罚》中的拉祖米欣说:“争论是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开始的……犯罪是对不正常的社会制度的抗议……他们把一切都归于‘环境作祟’——除此以外,就再没有什么了!这是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这里就可以直接得出:如果把社会安排好了,使之正常化,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也无须对什么提出抗议了,大家霎时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天性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天性被排除在外,天性是不应该有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拉祖米欣和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同学,两人的处境相同,同样穷,同样被迫辍学,同样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为什么拉祖米欣可以靠教课和翻译为生,拉斯科利尼科夫却偏偏走上杀人越货的犯罪道路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反对以暴易暴,以恶抗恶。他把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混为一谈。他把一切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统称为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在小说《白痴》中曾通过梅什金公爵之口异常激动地谈到社会主义者“不是用基督,而是用暴力来拯救人类!这也就是通过暴力来取得自由,这也就是通过剑与火来取得一统天下!‘不许信仰上帝,不许有私有财产,不许有个性,不是博爱,就是死亡,二百万颗头颅!’”不是博爱,就是死亡——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的口号,意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不赞成我们的革命口号,就让他灭亡。所谓“二百万颗头颅”——这是指一个名叫海因岑的共和党人说过的一句话:“只要在地球上排头砍去,砍掉二百万颗脑袋,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第二个动机说明,他身为被压迫者,却受到“不做牺牲者,就做刽子手”的资产阶级弱肉强食的豺狼哲学的影响。他渴望像拿破仑那样享有无限的“自由和权力”。“自由和权力,而主要是权力!统治一切发抖的畜生和芸芸众生的权力!”他的野心很大。他说:“我想做拿破仑,因此我才杀人……”杀人,不过是他的大计划中的一个小尝试。他认定,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就要敢于跨过尸体,涉过血泊。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来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他荒谬地认为:“谁的头脑和精神坚强有力,谁就是他们的主宰。谁胆大妄为,谁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对的。谁敢于唾弃更多的东西,谁就是他们的立法者,而谁敢于为他人之所不为,谁就最正确!从来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只有瞎子才看不清这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及其取向是敏感的,好像预见到了我们的今天。后来,帝国主义的政客们和思想家们,果然继承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衣钵,把他的“犯罪论”和“强权论”发展成法西斯主义和“超人”哲学。
第三,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双重性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罪行的认识上。良心和理智在他身上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行凶前的最后一刻,他还觉得杀人是一种十分丑恶、卑劣和荒唐的事;杀人后,他自惭形秽,经受着良心的痛苦折磨,觉得自己与人类一下子隔绝了,感到可怕的孤独。正如索尼娅所说:“啊,离开了人,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活下去呢?”这种因犯罪而感到自外于人民的下意识是自然的,也是深刻的。这是良心的法庭。他痛苦地对妹妹杜尼娅说:“你会走到这样的界限:不跨过去会不幸;跨过去呢——也许会更不幸……”这就是说,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固然不幸;但是视人命如草芥,对于一个人性还未完全泯灭的人来说,则是更大的不幸。他自己也承认:“难道我杀死的是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老太婆!……”但是,他在理智上又顽固地不肯认罪,理由是:为什么别人能杀人,那些所谓“伟人”能杀人,我就不能?“大家都在杀人流血,世界上,血,现在在流,过去也一直在流,像瀑布一样流,有人杀人就像开香槟酒一样,因为血流成河,人们居然在卡皮托利岗给他戴上桂冠,后来又尊称他为人类的恩主……如果我成功了,人们就会给我戴上桂冠,而现在,我只能束手就擒。”他感到懊恼的仅仅是他“懦弱无能”,他经受不住良心的审判和折磨,他跟大家一样也是一只不折不扣的“虱子”,因此犯案后没几天,他就去警察局自首了。
第四,拉斯科利尼科夫恨透了资产阶级市侩卢仁和人面兽心的色狼斯维德里盖洛夫。可是,他正是在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是他的“理论”的等而下之的体现者,是他的人格的市侩化和流氓化。卢仁拾人牙慧,伪装“进步”,宣传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哲学。正当他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牙慧,夸夸其谈的时候,拉斯科利尼科夫陡地打断他道:“按照您方才宣扬的,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必定是可以杀人……”他之所以贸然说出这样的话,正因为他看出他的理论与卢仁鼓吹的东西如出一辙。二者殊途同归:一个是抡起斧子,赤裸裸地杀人;一个是巧取豪夺,把人逼上死路。
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一个灵魂空虚、卑鄙无耻的恶霸地主。他设计暗害了自己的妻子,逼死了自己的用人,糟蹋了自己的侍女,又进而觊觎家庭女教师杜尼娅;而他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则是强奸幼女,使一个十四岁的少女投河自尽,含恨而死。这是一个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坏透了的人。但是,这个万恶之徒也居然做了一些好事:他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办理后事,并出资把她的遗孤送进孤儿院,又给了索尼娅三千卢布,使她能够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去西伯利亚。这人似乎没有是非观念,既能作恶,也能为善,也能真正地爱一个人。当他对杜尼娅的强烈的爱被拒绝之后,出乎我们意料,他没有对她强行非礼,施行强暴,而是觉得再这样活下去没意思,最后用自杀结束了生命。这人很聪明,性格也很豪爽,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有一定深度,拉斯科利尼科夫骂他是无耻之尤,斯维德里盖洛夫却说:“咱俩是一丘之貉。”他除了临死前在梦境中对自己一生的罪行恍恍惚惚地有所省悟以外,还对杜尼娅一针见血地剖析了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的根源:“说来话长,阿夫多季娅·罗曼诺芙娜。这事怎么跟您说才好呢,这也是一种理论吧,与我所见略同,比方说吧,如果主要目的是好的,即使做一两件坏事也是可以容许的。一件坏事可以换来一百件好事!对于一个卓尔不群和自尊心很强的年轻人来说,要是他知道,比方说吧,他只要有区区三千卢布,他人生目标中的整个前程、整个未来就会完全改观,而他却没有这区区三千卢布,这对于他当然是气人的。除此以外,再加上食不果腹,住房狭小,衣衫褴褛,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母亲和妹妹的处境不妙而产生的愤愤不平。最要命的是虚荣,骄傲和虚荣……拿破仑简直把他迷住了,就是说,使他特别着迷的是,有许多天才人物根本不在乎做一两件坏事,而是不假思索地就跨了过去。看来,他也以为自己也是天才……”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都是双重人格。一个是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再加上索尼娅和亲朋好友的爱滋润着他的心田,终于走上了新生的路。另一个则堕落太深,众叛亲离,没有爱,没有信仰,因此也就没有了希望。虽然也爆发出一星半点良心的火花,但终于四顾茫茫,不能自拔,只能开枪自杀,了此罪恶的一生。
拉斯科利尼科夫深恨卢仁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也正是深恨他自己。他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化身”。
能恨自己,能自惭形秽,正是新生的开始。卢仁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之所以执迷不悟,不可救药,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观不是恨,而是扬扬得意、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陀思妥耶夫斯基宣扬,只有爱和受苦受难的基督教精神,才能荡涤人世的罪恶,使人的道德更新。譬如:拉斯科利尼科夫曾向索尼娅下跪,索尼娅见状,大惊失色。他解释道:“我不是向你下跪,我是向整个人类的苦难下跪。”索尼娅在规劝拉斯科利尼科夫去投案自首时也说:“去受苦,用苦难来赎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引导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的是恨,对整个坏人当道、好人受苦的社会的恨。他由恨而起意杀人。而使他在道德上复活的是爱,索尼娅的爱。正因为有了爱,他才心甘情愿去受苦受难。“爱使他们复活了,一个人的心里蕴涵着滋润另一个人心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拉斯科利尼科夫从行凶杀人到心灵复活的过程,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含义。这是当时俄国社会两条道路之争的艺术体现。
俄国和欧洲,俄国道路和欧洲道路,是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条主轴。
什么是俄国道路,什么是欧洲道路呢?一言以蔽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道路就是博爱,欧洲道路就是权力和金钱。欧洲道路靠的是强权与暴力;俄国道路靠的是忍让、宽容与和平。欧洲道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如若不从,就排头砍去,即使“砍掉一亿颗脑袋”(《群魔》),也在所不惜;俄国道路则提倡从自己做起,以“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苦难中洗涤自己的灵魂,以求得道德的自我完善。换一种说法,欧洲道路主张暴力革命,俄国道路则主张和平过渡,主张改良。
《罪与罚》是这两条道路之争在一个人命运上的具象化:欧洲道路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路,因而受到良心惩罚。俄国道路则使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爱和良心的感召下幡然悔悟,走上新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1865年9月写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十分明显地表述了这一观点:这是一次犯罪的心理报告。故事发生在当代,在今年。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他出身小市民,生活极度贫苦,由于偏听、偏信和在理解问题上的左右摇摆,受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奇怪的“半瓶子醋”思想的影响,决心一举摆脱自己的糟糕处境。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九等文官的遗孀,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以后一辈子做一个好人,坚定而毫不动摇地履行他对人类的人道主义义务……(但是他在杀人之后)一些始料不及的感情折磨着他的心。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发生了作用,结果不得不去自首。……他在犯罪之后马上感觉到的与人类隔绝和分离的感情使他万分痛苦。真理的法则和人的天性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作用,内在的信念甚至没有遇到反抗。罪犯自己决定以承受苦难来赎自己的罪。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某些奇怪的‘半瓶子醋’思想”,就是指欧洲道路,也就是他一再在作品中攻击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当时流行于俄国和西欧的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罢了。而他所谓的“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法则”,也就是他一贯主张的所谓俄国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服苦役时期就开始构思一部忏悔录式的作品。他在1859年10月9日给哥哥的一封信中说:“早在服苦役期间……我就开始构思它了……这部忏悔录将会最终确立我的名声。”后来,他又说:“通过这一形象(指拉斯科利尼科夫),小说中要表达一种无比高傲、狂妄自大和蔑视整个社会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则笔记中写道:阿乐哥杀了人……他意识到他本人配不上他自己的最高理想,那种思想折磨着他的心。这就是罪与罚。 这段话弥足珍贵,它使我们懂得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一形象在俄国文学史上一脉相承的地位以及这一形象在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的典型性。《罪与罚》绝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情节的紧张、曲折取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对俄国当代社会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们从上面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阿乐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去世(1881年1月28日)半年多之前,曾在莫斯科发表过一篇论普希金的著名演说。他的演说引起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不同反响:有的欢呼,有的詈骂。
引起这场轩然大波的关键,就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篇演说中通过普希金的两部代表作《茨冈》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指出了当时存在于俄国社会中的两种人和两条道路之争。两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植根于人民中的俄罗斯人和欧洲化的俄罗斯人。欧洲化的俄罗斯人大都是出身贵族或平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受过欧化教育,不满现实,但是脱离人民,他们蔑视整个社会,四海漂泊,富有探索精神,到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这种人自视甚高,充满个人英雄主义。属于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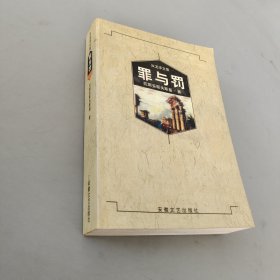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