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堡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5.43 1.1折 ¥ 49.8 全新
库存1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奥地利)弗兰兹·卡夫卡著,冷杉译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ISBN9787513930468
出版时间2020-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9.8元
货号1202349635
上书时间2024-06-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压轴之作著名翻译家冷杉德语直译,经典珍藏版本一本自我探索与救赎的现实主义佳作进退不得,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要面对的困境卡夫卡世界的荒诞折射的是现实世界的荒诞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异化和孤独感
卡夫卡被称为“作家中之作家”,《城堡》是其最具特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
小说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梦魇般的气氛;寓意深刻,令人回味无穷。
故事情节紧凑,冲突强烈,主人公卡勇敢、敏锐、颇具战斗力,堪称百折不挠,与卡夫卡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同。
《城堡》是卡夫卡的未竟遗作,其开放式的结局给了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
自出版以来,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被誉为“后世无法逾越,非读不可的小说经典”!
作者简介
弗兰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生于捷克首府布拉格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在保险公司任职,用德语写作,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代表作有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8
第三章 / 036
第四章 / 046
第五章 / 059
第六章 / 080
第七章 / 094
第八章 / 105
第九章 / 113
第十章 / 122
第十一章 / 128
第十二章 / 139
第十三章 / 147
第十四章 / 153
第十五章 / 170
第十六章 / 181
第十七章 / 190
第十八章 / 209
第十九章 / 219
第二十章 / 232
第二十一章 / 249
第二十二章 / 266
内容摘要
卡受聘到城堡当土地测量员。当他抵达城堡脚下时,却被告知自己的被聘是一个误会。为了确认自己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他想方设法接近城堡:他勾搭上城堡办公厅主任的情人,情人与主任决裂;寄希望于城堡的信差,却得知信差只能照章办事;求助于cun长,而cun长只是妻子的传声筒……卡感到十分无奈,似乎每向前迈一步,就会堵死一条去往城堡的路。在《城堡》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调叙述了一次绝望的挣扎,由此揭示世界的荒诞、异己和冷漠。
主编推荐
现代派文学鼻祖卡夫卡压轴之作
有名翻译家冷杉德语直译,经典珍藏版本
一本自我探索与救赎的现实主义佳作
进退不得,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要面对的困境
卡夫卡世界的荒诞
折射的是现实世界的荒诞
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异化和孤独感
精彩内容
第一章卡抵达时已是深夜了。整个村庄躺在厚厚的积雪中。浓雾和夜色完全笼罩了城堡坐落的那座山,连一丝灯光也没有。卡在通往村子的这座木桥上站了很久,望着眼前一片若隐若现的虚空,感到茫然。
然后卡便去寻找过夜的地方。一家客店里的老板还没睡,但这里已经没有空房可住了。店老板让卡睡在酒吧间的一个草垫子上,卡同意了这个安排。卡从阁楼上取出那个草垫子,摆在火炉近旁躺下。这里很暖和,有几个农民喝着闷酒,卡强睁倦眼打量着他们,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
没过多久,卡被人叫醒了。一个一身城里人打扮的小伙子正和店老板一起站在他旁边。那几个农民还没走,有几个把椅子转过来,想看得更真切些。这小伙子首先为叫醒了卡而很有礼貌地向他道歉,接着介绍自己是那座城堡的城守的儿子,然后说:“这个村庄是城堡的属地,没有伯爵批准,任何人都不能在这里居住或过夜。而您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批准,至少您还没有出示任何证明。”卡已经欠起了大半个身子,他梳理了一下头发,然后抬眼望着来人说:“我这是来到哪个村了?难道这儿还有座城堡吗?”“当然了,”小伙子回答,“是威斯特韦斯特伯爵先生的城堡。”“必须经他批准才能在这里过夜吗?”卡问道。
“一定要有他的许可证才行。”小伙子回答,然后用对卡很不屑的嘲笑口吻,朝着老板和其他客人问道,“怎么可能不经过他的同意呢?”“那我得去弄一张喽。”卡打着哈欠、掀开身上的毛毯说。
“没错,可是您找谁去弄呢?”小伙子问。
“当然是去找伯爵先生,”卡说,“除此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吗?半夜三更找伯爵先生要许可证?”小伙子惊呼。
“怎么,不行吗?”卡镇定地问,“那您半夜三更吵醒我干吗?”小伙子一下子撕掉了假斯文,嚷道:“瞧您这副德行!我要求您尊重伯爵的权威。我叫醒您是要通知您,您必须立刻离开伯爵的领地!”“戏演够了吧,”卡又躺下来,语气很平静地说,“年轻人,你有点过分了。明天我再跟您计较您的不良行为。如果需要的话,旅店老板和那几位先生会给我做目击证人的。另外告诉您,我就是伯爵派人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几名助手明天就带着工具坐马车过来。我本人不想错过在雪地里长途步行的机会,可不幸的是我迷了好几次路,所以才到得这么晚。我自己清楚去城堡报道已经太迟,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凑合过一夜。而您却那么不礼貌地烦扰我。我的解释到此为止。晚安,先生们!”卡说完翻过身去面朝火炉。
“土地测量员?”卡听见有人在他背后犹疑地问,接着是一阵沉默。小伙子很快恢复了镇定,压低声音对店老板说:“我要打电话核实一下。”怎么,在这乡下小客店里居然还有电话?他们设备还挺齐全的嘛。如果那小伙子非要打电话,就算他动机再好,也难免不打扰卡的睡眠。因此关键全在于卡是否让他打电话;卡决定不管了,随他打去。这样一来,装睡显然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卡又翻过身来仰着睡。厨房门敞开着,老板娘肥硕的身躯站在那儿把它堵得严严实实;客店老板蹑手蹑脚走过去向她汇报了情况,接着电话交谈就开始了。城堡的正城守睡觉去了,但还有几个副城守,其中一个叫弗里茨的还守在那边。小伙子先通报自己是施瓦策,接着讲了自己发现卡的经过:他是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穿得破破烂烂,脸上脏了吧唧,躺在一张破草垫上睡得正香,拿个小旅行背包当枕头,手边放着一根疙疙瘩瘩的手杖。这样一个人当然会让人起疑心;而且,既然店老板明显失了职,那么他,施瓦策,就有责任来对这事儿盘根问底。于是施瓦策叫醒了卡,盘问了他,并正当地严令他离开伯爵的领地。但是那人对此的回应相当粗鲁——也许施瓦策这样待那人不太公正,毕竟那人最后自称是伯爵招来的土地测量员。但是他,施瓦策,当然有责任核实那人的话是否属实。因此施瓦策请求弗里茨先生问一下中央局,是否真的派来一位土地测量员,并且马上把答复电话告诉他。
接下来屋里一片安静,弗里茨在电话那头查询,人们在这头等待答复。卡保持原样躺着,显得完全没有兴趣,目光仅瞅着眼前。施瓦策的讲述中混合着敌意和审慎,这让卡想到了字斟句酌的外交术;没想到在那座城堡里,连施瓦策这样的小人物也谙熟此术。中央局的人们也都够勤快,居然还有值夜班的。答复显然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弗里茨打电话过来了。这次通话似乎非常简短,施瓦策立刻便怒冲冲地挂上了听筒。“我说呢,”他叫道,“哪有什么土地测量员的影子!不过是个招摇撞骗的流浪汉罢了,可能比这还糟呢!”卡心想这下可完了,他们所有人,施瓦策,那几个农民,老板和老板娘,都会愤怒地朝他扑过来。为了躲过这一轮的攻击,他钻进被子缩成一团,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此时卡正慢慢探出头来张望,这铃声在他听来显得特别刺耳。施瓦策回到电话机前,听完对方好长一段解释后,缓和语气说道:“原来是搞错啦?这可让我太尴尬了。是局长亲自打来的电话?这可就怪了,太奇怪了。我该如何向土地测量员先生讲清这一切呢?”卡竖起耳朵听了个仔细。这么说来,城堡方面确认他这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喽。这从一方面来讲对他不利,因为这说明,城堡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所有关于他的必要信息,已经评估了他带来的压力,从而满怀信心地笑迎挑战。可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对他也有利,因为这说明他们低估了他的能力,从而给了他比一开始他所能指望的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假如那些人以为,承认他的测量员身份就能让他受宠若惊的话,那他们可就打错了算盘——尽管他们自以为高高在上垂怜了他,而他其实心里只不过战栗了一下,仅此而已。
施瓦策怯生生地朝卡走来,卡挥挥手把他打发走了。人们殷勤地请卡住到店老板的房间里去,被卡拒绝了;卡只从老板手中接过一杯安眠酒,从老板娘手里接过脸盆、毛巾、肥皂。不等卡要求,所有人便都扭脸冲出门去,生怕第二天被他认出来。然后灯熄灭了,他总算得到了清静。他一觉熟睡到第二天早上,只是偶然被窜过去的老鼠惊动了一下。
吃完早饭后,卡想立刻到村子里去;反正客店老板说啦,卡的早餐及全部膳宿费都由城堡方面负担。想到老板昨夜的不当行为,卡实在懒得跟他说话,但老板总是带着哀求的目光,默默跟在他屁股后头转,这让他又不得不可怜起老板来,就让老板在自己身边坐了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这位伯爵先生,”卡说,“他们说他优工优酬,干得好就加薪,是真的吗?像我这样离开妻儿远道而来的履职者,总得带回家去一点像样的东西吧。”“这方面先生您完全不用担心,从没听说有人抱怨这里工资给得少的。”“跟你这么说吧,”卡说,“我可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人,即使跟一个伯爵我也敢说出自己的意见。当然,能和这些贵人和平相处,是再好不过的了。”店老板坐在窗前座椅的边儿上,却不敢挪挪屁股让自己做得更舒服点,两只焦虑的眼睛始终紧盯着卡。起初他还想跟卡好好聊一聊,现在看来他只想溜走。难道他害怕人家向他了解伯爵的情况吗?还是他担心自己所见的这位卡“大人”不可靠?卡现在得给他台阶下了,就看了看钟表说:“哦,我的助手很快就要到了,你能安排一下他们的住宿吗?”“没问题,先生,”老板说,“可是他们不跟你一起在城堡里住吗?”难道他真的乐意把自己的顾客,尤其是卡,轻易给放走,转让给城堡吗?
“这个还没有定下来,”卡说,“我得先确定他们要我干什么工作。比如,我要是在下面工作的话,那我还不如住在这里的好。另外我还担心住城堡我不习惯。我喜欢一直自由自在地生活。”“你不了解城堡啊。”老板轻声说。
“没错,”卡说,“所以不该过早下结论。目前我对城堡的全部了解只有一点:他们很会挑选合适的土地测量员。可能那里还有其他不错的地方吧。”说完他站起身来,好让心神不安咬着嘴唇的老板得以解脱。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出去的时候,卡瞅见墙上一个黑画框里有一幅色调很暗的肖像画。“这是谁,”卡问客店老板,“是伯爵吗?”他站在画儿前审视着。“不是,”后者回答,“他是城堡的城守。”“这个城守可真英俊,”卡说,“可惜他的儿子很差劲。”“哪儿啊,”老板把卡拉到身旁,对他耳语道,“施瓦策昨天吹牛呢。他爸爸只是副城守之一,而且排在最后一个。”此时卡觉得老板真像个孩子。“瞧这事儿闹的。”卡哈哈大笑着说。可是店老板没有跟着笑,而是怯怯地说:“就连他爸爸也挺有势力呢。”“得了吧,”卡说,“你以为所有人都有权有势啊。你看我像不像有势力?”“你吗,”老板既胆怯又鼓足勇气说,“我可不觉得你有势力。”“嗯,完全正确,你很有眼力嘛,”卡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一点势力。所以我很可能和你一样敬畏那些有权势的人,只不过我不像你那么老实,总也不想承认罢了。”说完他拍拍老板的面颊。
店老板现在面露一点微笑了。他其实还是个青年人,脸还很软嫩,没长几根胡子。他怎么会娶了一个看起来比他老的胖女人为妻呢?透过一扇小窗子,可以看到她袖口挽得高高的,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卡不想再盘问他了,免得让他为难,把他好不容易逗引出来那点笑容赶跑。所以卡仅仅示意老板把门打开,然后自己步入这美丽的冬晨。
现在卡看到前方山上的城堡了,在晴朗的天空下它轮廓分明,皑皑白雪更让它光耀醒目。自然界的千姿百态统统银装素裹,但是山上下的雪好像比村子里的雪小得多。在村里,积雪一直堆到农舍的窗台,厚得几乎要压倒低矮的房顶;而在山坡上,万物还是那么轻盈,自由自在地矗立,起码从下面看上去是这样。
总体来讲,这座城堡远远看过去和卡预料的差不多,既非古老骑士的城池要塞,也非雄伟壮丽的新式建筑,而只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由几座二层楼房和许多紧密相拥的一层房屋组成。若不是事先知道这里是座城堡,卡肯定会以为来到了一座小镇呢。卡只看到了一座塔,但无法判定它是属于一座住宅,还是属于一所教堂。一群群乌鸦黑压压地绕着它飞。
卡盯着城堡,直奔它而去。待他走近时,他失望了,这个所谓的城堡只不过是一座寒碜的小镇,由许多村舍拼缀而成,唯一醒目的大概只有:一切都由石块砌成,但是泥灰油漆什么的早已剥落,石块似乎也在风化皲裂。一瞬间,卡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古镇,它毫不逊色于眼前这座所谓的城堡。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看看了。他心里开始比较家乡那座教堂的钟楼跟眼前这座城堡钟楼之间的差别。家乡那座教堂钟楼毫不犹豫地直线上升,直冲云霄,顶着一个红瓦的宽阔楼顶,是座能想象得出来的现世建筑,只不过比低矮的普通房屋更高一些,比乏味无聊的工作日更意义明确一些。反观眼前这座塔,现在看得很明显了,是属于一所住宅的,很可能是城堡主体的一部分。它从上至下圆圆的,式样单一,其中一部分被爬藤慈爱地遮掩住,露出些小小的窗口在阳光下闪烁,看上去像一些发疯的眼睛。塔顶有个露台,其雉堞参差不齐,也显得很脆弱,好像出自小孩子或着急或粗心的画笔,歪歪斜斜地呲向蓝天。它就如某个患抑郁症的居民,本该被锁在楼顶层最偏僻的房间里待着,却不知何故穿破房顶站了起来,向世人展示自己。
卡又站住了,仿佛立定能让他有更强的判断力似的,但是这样反而更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停下的地方紧挨着乡村教堂,在它后面是一所学校。这学校其实就是一座低矮的长条建筑,是老建筑的永久特征与将就凑合的临时性建筑的古怪结合体。一圈栅栏把它围了起来,它的花园现在是一片雪地。就在这时,一群孩子和他们的老师跑了出来。他们围着老师,个个睁大眼睛盯着教师,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小嘴巴说得飞快,卡简直跟不上他们的语速,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那个老师是个小伙子,矮个头,瘦肩膀,站得笔直,但还不显得可笑。眼见这样一个整肃威严的小个子老师站在面前,作为异乡人的卡赶紧主动上前打招呼:“老师您好。”突然一下子孩子们就都不说话了,似乎准备好了听老师回答似的,这让老师感到挺满意。“您在观看城堡吗?”老师问,语气比卡预料的温和,但是好像不赞成卡这样的行为。“是啊,”卡回答,“我昨天晚上刚到。”“您不喜欢这个城堡吧?”老师紧接着问。“怎么了?”卡反问,有点摸不着头脑,但随即放缓语气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说:“我不喜欢这个城堡?您凭什么认为我不喜欢?”“外来人都不喜欢。”老师回答。为了避免得罪老师,卡换了个话题问:“伯爵您肯定认识吧?”“不认识。”老师回答,然后打算转过身去不再理他。可是卡紧追不舍地又问:“您怎么会不认识伯爵呢?”“我怎么就不会不认识他呢?”老师先低声回答,然后用法语高声补充道,“请您注意,这儿有天真无邪的孩子在场。”卡正好借着这个理由问道:“老师先生,我能拜访您吗?我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感到有点孤立了,既没法儿和农民打成一片,恐怕也难以融进城堡。”“庄稼汉和城堡没啥区别。”老师说。“也许吧,”卡说,“但这也改变不了我的局面呀。哪天我能否去拜访您一下?”“我就住在天鹅街一个肉铺旁边。”这听起来更像是通报地址,而不是邀请,但卡还是说:“好,我一定去。”老师点点头,领着那群立刻又活跃起来的孩子继续前行。不久他们就消失在一条下坡很陡的小路上。
卡有些心烦意乱,他继续前进,可这段路竟也长得要命。他走的路是村里的主道,根本不通向城堡所在的那座山,而只是接近它,然后便像有意设计好似的拐弯儿了,虽然从不远离城堡,却也不朝它更近一步。卡一直期待这条路最终还是会拐到城堡那儿去,正是抱着这个期待他才坚持走下去。显然是出于疲倦,他才不愿意离开这条主路,但他也诧异这个村子怎么那么长,半天也走不到头,那些小村舍怎么翻来覆去地没完没了?最终他还是脱离了这条被他认准了的主道,拐进了一条窄巷子,这里的积雪更深,一脚踩下去再拔出来变得很费劲,让他出了一身大汗,接着突然就停下来迈不动步子了。
还好,他显然不是孤立无援,前后左右全是农舍。他攥了一个雪球朝一户窗子扔了过去。房门立刻打开了,这是他一路走来村里打开的第一扇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农民,穿着一件棕皮袄,头歪向一边,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很友善。“我能进屋歇一会儿吗?”卡问,“我快累趴下了。”老头儿说了什么他没听见,但见老头儿把一块木板朝自己搭了过来。卡很感激地从积雪里踏上木板,走了几步后便进到了屋子里。
这是个光线昏暗的大房间。卡刚从外面进来时跟睁眼儿瞎似的,被一个洗衣桶绊了一跤,一只女人的手扶住了他。从一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从另一个角落涌过来一股股水蒸气,使昏暗的房间变得更暗,卡傻傻地像是站在云中。“他肯定是喝醉了。”有人说。“你谁呀?”另一个声音蛮横地问,随后显然是冲着老头儿使厉害,“你干吗让他进来呀?难道要把每个街上的流浪汉都请到家里来吗?”“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卡说。“啊?你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的声音问,接着一片鸦雀无声。“怎么,你认识我?”卡问。“咋不认识呢?”同一个女声简短作答。不用自我介绍,他们好像都知道卡。
水蒸气总算消散了一点,卡渐渐能看清周围了。今天好像是个大清洗的日子。门旁边有人在洗衣服。水蒸气是从左侧角落冒出来的,那边有个大木桶,卡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木桶,足有两张床那么大,两个汉子正泡在里面热气腾腾地洗澡。然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右侧的角落,尽管他还说不清这惊讶的实质是什么。那边的后墙上有个唯一的大窗洞,从外面射进来耀眼的雪光,肯定是来自后院儿,把缎子般亮闪闪的一束光投射在一个女人的裙服上,那女人正疲惫地斜倚在屋角深处一张高背椅中给她的小婴儿喂奶。另几个孩子绕着她玩耍,一看就是农家孩子。但她却在这氛围中显得脱颖而出,大概病怏怏的样子有时也能让农家女显得像贵妇吧。
“你坐吧!”两汉子中的一个说。他满脸胡子拉碴,浓黑的唇须下露出张开的呼哧带喘的嘴巴,一只手从大木桶边儿上猛地伸出来,指着一个木箱子,带出一些热水溅了卡一脸——这可真是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木头箱子上已经坐着那个带卡进屋的老头儿了,正在起劲地打盹儿。卡高兴地心想,可坐下了,不容易啊。之后就没人再搭理他了。蹲在洗衣盆前的那个女人一头金发,年轻而丰满,边干活儿边哼着小调儿。两个汉子在桶里伸胳膊踹腿儿,稀里哗啦洗得痛快,孩子们想靠近凑热闹,却被阵阵飞溅的水花一次次击退,连卡也不能幸免,水花溅到他身上。那个靠在椅背上的女人有气无力地茫然盯着屋顶,连怀抱里的婴儿也不瞅一眼。
卡注视了这母婴俩很久,这幅凝然不变的凄美画面大概深深吸引了他;然后他大概就打起盹儿来,因为当他被一声大叫惊醒的时候,他的脑袋正靠在身旁那个老头儿的肩膀上。那两个男人已经洗完了澡,穿好衣服正站在卡面前;现在轮到孩子们在那个金发女人的照看下,钻到大澡桶里瞎扑腾了。看来,那个冲着卡吼的络腮大胡子是两个汉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另一个的个头不比这个更高,胡子却比这个少很多,他是个性格安静、脑子迟钝的人,体格比络腮大胡子壮,脸也方方宽宽的,总是低着头阴着脸。“测量员先生,”他发话了,“你不能待在这儿,恕我无礼。”“我本来也不想待在这儿,”卡说,“我只是想歇个脚喘口气。现在我没事了,可以走了。”“你可能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好客吧,”那人说,“是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待客的习惯。我们不需要客人来。”打了个盹儿后,卡脑子清醒了一些,耳朵也比先前好使多了,听那人说得这么坦率,卡很高兴。卡拄着拐杖,比较无拘束地到处走走,还接近过那个坐在靠椅里的女人,顺带看出来自己是这个屋子里身材最高大的人。
“也难怪,”卡说,“你们需要客人干啥用呢?不过有时候你们还是需要客人的,比如我这个土地测量员。”“这我就不清楚了,”那人缓缓地说,“既然有人唤你来,他们很可能需要你,这就另当别论了。反正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按老xi惯办事儿,你可不能怪俺们不懂礼数。”“不怪不怪,”卡说,“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你,还有这儿所有的人。”接着,让所有人都没料到,卡一个急转身站到那个女人面前。那女人睁着疲倦的蓝眼睛懒懒地瞅着卡,一条透明丝巾垂挂到她的眉宇间,那婴孩在她怀抱里睡着了。“你是何人啊?”卡问。不清楚是针对卡还是针对自己,她轻蔑地回答:“一个从城堡来的姑娘呗。”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汉子已经一左一右揪住了卡的胳膊,一言不发使劲把他押送出门,好像非此别无他法治他似招把那老头儿逗乐了,拍起巴掌来。那个洗衣女人也哈哈大笑,她旁边的那些孩子也突然起劲地折腾起来。
前后不出几秒钟,卡已经站在门外的街道上了,两条汉子站在门槛儿监视着他。雪又下起来了,尽管天色比刚才亮了一些。那个络腮大胡子不耐烦地嚷道:“你想去哪儿?这条路通城堡,那条路通村子。”卡没理他,而是把脸扭向另一个人,那人虽然很有年长者的威严,但给卡的印象却更和蔼可亲一点。卡问那人:“你是哪一位?请让我知道,我该感谢谁让我休息了这一会儿?”“我是制革匠拉泽曼,”那人回答,“不过你用不着感谢谁。”“那好吧,”卡说,“咱们也许哪天还会见面。”“我估计不会了。”那人说。就在这时,那个络腮胡子扬起手臂大叫:“早上好,阿图尔!早上好,耶雷米亚斯!”卡扭头去看,终于在这村子的街道上见到其他人了!从城堡那边走来两个年轻人,都是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头,穿着紧身的衣裤,而且长得很像,都是黑红的脸膛,醒目的黑山羊胡子。鉴于糟糕的路况,可以说他们走得够快的了,步伐整齐地迈着瘦腿儿。“你们这是咋啦?”那个络腮胡子大声问道。那两位走得那么急,一点也不想停下来,为了让他们听明白,那个络腮胡子只好冲他们大喊。“办公务。”那俩笑着大声回答。“去哪儿呀?”“去客店。”“我也正要去那儿呢。”卡也猛地大叫一声,这一嗓子比谁的都响。卡很想跟那俩人结伴而行——不考虑和他俩认识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而只是觉得他俩可能是好旅伴,能让他开心。可是,那两人虽然听到了卡的招呼,却只是点点头而已,然后一眨眼就没影了。
卡依然站在积雪中,不太想把脚从雪里拔出来,因为那样的话虽然能往前走一点,但也会陷得更深。那个制革匠师傅和他的伙伴总算把卡赶走了,这会儿正沾沾自喜,一边不断回头看卡,一边慢慢挤进只开了一条缝的房门走进屋里去,撇下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雪中。“假使我不是被人有意设计,而只是天定身陷此境的话,我还不至于那么绝望。”这是他此刻脑中闪过的念头。
这时,左侧一间农舍的一扇小窗子打开了。这窗子可真小,即使全开了也看不见里面探视人的整个脸,而只能看见一双眼睛,一双褐色的老眼。“他就站在这儿。”卡听见一个女人声音颤抖地说。“那个土地测量员。”一个男的声音接茬儿说。然后这个男的来到窗前问:“你在等谁呢?”口气倒不是不友好,但就像生怕自家门前的街上出事儿似的。“我在等一辆雪橇把我拉走。”卡回答。“这儿不通雪橇,”那人说,“这里没有车辆来往。”“可这儿是通向城堡的路呀,不是吗?”卡反诘道。“那又怎么样?”那人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即便如此,还是没有车辆来往。”之后两人都不吱声了。不过那男的显然还在考虑着什么,因为他并没有把窗子关上,烟不断从里面冒出来。“路况真糟糕!”卡打岔说,想换个话题。可对方只说:“没错,确实很糟。”不过,片刻后他又说:“你不嫌弃的话,我用我的雪橇带你去。”“那太好了。”卡喜出望外地说,“我付你多少钱?”“分文不取。”那人说。卡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你毕竟是土地测量员嘛,”那人解释道,“是城堡的人。要我送你去哪儿?”“去城堡。”卡马上说。“那我就不送你了。”那人也马上说。“可我是城堡的人呀!”卡说,学着那人的腔调。“就算是吧。”那人不屑地说,看来决心已定。“那就送我去客店好了。”卡说。“好的,”那人说,“我这就驾雪橇出来。”话里没透出多少友好的表示,反倒露出很强烈的自私和焦虑情绪,只想赶紧把卡从自家门前的街上请走。
很快,这家院门打开了,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一辆轻便雪橇出来了。后面跟着那个男人,年纪不算太大,可是很瘦弱,弯腰驼背,走路跛脚;一张发红的瘦脸五官集中,因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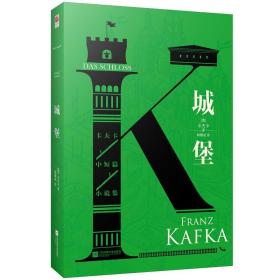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