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北方的小路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8.54 4.1折 ¥ 69 全新
库存14件
作者〔澳〕理查德?弗兰纳根|译者:张竝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ISBN9787573505125
出版时间2023-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9元
货号1203006876
上书时间2024-06-1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理查德·弗兰纳根
RichardFlanagan
澳大利亚作家。1961年生于塔斯马尼亚。1994年出版《河流引路人之死》,被《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为“澳大利亚文学ZUI有前途的首作之一”。2001年根据画家威廉·古尔德的经历写出《古尔德的鱼类图鉴》,获2002年英联邦作家奖。2013年出版《深入北方的小路》,次年即获布克奖,被《卫报》评为“大师之作”。弗兰纳根亦被《华盛顿邮报》誉为“当世ZUI伟大的作家之一”。2020年出版《幻梦中涌动的海》。
目录壹 一只蜂蜜/从牡丹花里/蹒跚而出。——松尾芭蕉
贰 暮色/从沙滩上那个女人/涌出,覆盖晚潮。——小林一茶
叁 露水的世界/每颗露珠中/都有一个挣扎的世界。——小林一茶
肆 这露水之世/仅是露水之世——然而。——小林一茶
伍 人生在世/行走于地狱的屋顶/凝望花朵。——小林一茶
内容摘要多里戈·埃文斯会活得很久,见证所有的变化。
铁路线崩塌了,就如所有的线路一样;它毫无意义,余下的也终将湮灭。孤独而平展的丛林绵延远去,在梦想与亡者之上,只剩下高高的荒草。
他想起人生中经历过的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他觉得自己是如此幸运,不仅能活下来,还知道有爱的存在。
如今,万事万物都大同小异,整洁有序的新世界正在来临。这是一个更加驯顺的世界,一个充斥着界限的世界,一切事物都被确知,任何体验都显得多余,甚至包括情感。人们谈论着自己的问题,为之命名,好像这样就能够描绘生活的神秘,或否认它的混沌。
如同一个垂死的世界里的漫长秋天,他觉得有些东西正在凋零。但他还是会活下去,他要比自己的时代活得更久。
《深入北方的小路》讲述了一个可怕历史事件中的爱情故事。战争是故事的中心内容,但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弗兰纳根关注的是爱本身和爱的救赎力量。小说充满了各种人性的晦暗和挣扎,但是结尾处一个令人振奋的世界出现了,不是充满戏剧性地突降临,而是自然而然地就出现在读者的眼前。——《纽约客》
精彩内容1
为什么万物之初总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记忆就是阳光在教堂的大厅内倾洒一地,他和母亲、祖母都在教堂里。木头结构的教堂大厅。炫目的光,他跌跌撞撞,来来回回,在这超然友好的光的沐浴下进进出出,投入两个女人的怀中。爱他的女人。好似步入大海,又返回海滩。一而再,再而三。
为你祝福,他母亲说着,搂住他,又让他离去,为你祝福,儿子。
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一五或一九一六年。他想必也就一两岁。阴影后来定格为上扬的前臂,黑色的轮廓在煤油灯油污的光下跳跃。杰基·马圭尔正坐在埃文斯夫妇家黑黢黢的小厨房里,哭泣着。那个时代,除了小婴儿没人哭。杰基·马圭尔是个老头子,也许有四十岁或者更老,他一直都在用手背从他那张麻子脸上擦去泪水。也说不定是在用手指抹眼泪?
唯有他的哭声定格在多里戈·埃文斯的记忆之中。就像是一种断裂的声音。渐缓的节奏令他想起了被套索勒住脖子的兔子用后腿踢腾地面的声响,这是他听过的唯一一种与之相似的声音。那时他九岁,进屋是想让母亲瞧瞧他大拇指上的血泡,他觉得没有一种声音能与马圭尔的哭声相比拟。之前,他就见过一次大人哭泣,那个场景令他震惊不已。当时他哥汤姆从法国的一战战场上回来,刚下火车,把军用背包往铁轨边滚烫的尘土中一抛,猛然间就哭了起来。
多里戈·埃文斯瞅着哥哥,心想究竟是什么会让一个成年男人哭泣。后来,哭成了对情感的简单确认,而情感成了生活唯一的指向。情感变得时尚,情绪成了剧场,人们作为演员,无从知晓下了舞台之后,自己究竟是谁。多里戈·埃文斯会活得很久,见证所有这些变化。他会记得有一段时间,人们都羞于哭泣,他们惧怕其中流露出的脆弱,脆弱会惹麻烦。而他会活下去,眼见人赞扬那些根本不值得赞扬的事物,只是因为真相使他们的情感难以承受。
汤姆回家的那天晚上,他们把德皇的相片投进篝火。关于他们听闻的战争、德国人、毒气、坦克、战壕,汤姆只字未提。他一言不发。一个人的情感并不总是和生活相等同。有时候,和任何东西都不等同。他只是定定地盯着火焰。
2
幸福的人没有过去,而不幸福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垂垂老矣的多里戈·埃文斯根本不知道这究竟是他读到的,还是他自己的杜撰。杜撰,混淆,破裂。持续不断地破裂。岩石成沙砾成尘土成烂泥成岩石,世界便是如此。母亲时常这么说。他常问母亲世界怎么会成为这样,成为那样,他要理由,要解释。世界便是如此,她会这么说,就是如此,儿子。为了搭一座堡垒,用来玩游戏,他一直在用力把石块从地表挖出来,而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却砸到了他的大拇指上,在指甲盖底下砸出了一大片瘀血,一抽一抽地疼。
母亲把多里戈抱到餐桌上,那里灯光最亮,她避开杰基·马圭尔怪异的眼神,抬起儿子的大拇指,探到灯光底下。杰基·马圭尔抽泣着说了些话。他老婆这个礼拜带小儿子坐火车去了朗塞斯顿,没回来。
多里戈的母亲抄起切肉刀。刀刃上凝了一层奶油般的羊脂。她把刀尖探入炉膛的煤块里。一小圈煤烟一跃而起,厨房便弥漫着炭烤羊肉的味儿。她把刀抽出,刀尖亮着红光,白炽滚烫的炭灰爆着火星,多里戈一瞬间觉得这景象既魔幻又恐怖。
别动。她说着,用力握住他的手,力道之大,把他吓了一跳。
杰基·马圭尔在说他是怎么坐上邮政列车去了朗塞斯顿,去那儿找她,但哪儿都没找到她。多里戈·埃文斯眼睁睁看着血红滚烫的刀尖触到他的指甲盖,母亲在指甲盖上烧穿了一个洞,冒起了烟。他听见杰基·马圭尔说——
她就这么人间蒸发了,埃文斯太太。
烟灭后,一股黑血从他的大拇指上汩汩流出,瘀血引起的疼痛和炽热的切肉刀引起的恐惧均已烟消云散。
走开,多里戈的母亲边说边把他从餐桌上往下推,快走开,儿子。
人间蒸发了!杰基·马圭尔说。
彼时世界仍然宽广,塔斯马尼亚岛仍是多里戈的整个世界。在岛上众多偏僻遥远、遭人遗忘的村落之中,没有哪座小村子能像克利夫兰那般被人忘得一干二净,那般偏远,而多里戈就生活在这座只有四十来口人的小村子里。以前,世道艰难的时候,这座关押犯人的村子一蹶不振,逸出了人们的记忆,如今存活下来,成了一条铁路支线,几栋乔治王朝时期的破落楼房,零零散散的几座设了门廊的木屋,供那些流放、迷失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人遮风挡雨。
背景处的森林里,拳曲的杏仁桉和银荆树沐浴着热浪,飘摇舞动,夏季炽热难熬,而冬季除了难熬还是难熬。没通电,没广播,当时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这里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没什么两样。如同一个垂死的世界里的漫长秋天。许多年后,对讽喻一窍不通的汤姆说—是对老之将至和行将就木的恐惧使他这样说的—生命只是一则比喻,真正的故事还在别处。多里戈当时是这样想的。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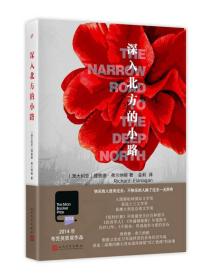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