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带(精)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4.44 5.1折 ¥ 48 全新
库存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日]小川糸著翟闪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ISBN9787229154356
出版时间2021-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31193281
上书时间2024-06-1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小川糸?,女,日本知名作家。处女作《蜗牛食堂》在日本畅销85万册,2010年被改编成电影,由知名演员柴崎幸主演。《蜗牛食堂》荣获2011年意大利书报亭文学奖,2013年法国欧仁妮.布拉泽大奖。另著有《山茶文具店》《喋喋喃喃》《趁热品尝》等多部作品。
译者简介:翟闪,女,汉族。安徽大学硕士,现为学校老师,主讲日语翻译、日语语法等课程。
内容摘要
少女云雀和祖母堇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祖孙,但是两人却意外投契,仿若朋友一般有着超越年龄的深厚情谊。祖母堇喜欢观察小鸟,平日就爱在露台上喝着甜咖啡,用望远镜观察家附近的各种鸟类,云雀受到影响,也和祖母一样喜欢小鸟。
某日,祖孙两人意外发现了三枚小小的鸟蛋,两人视为珍宝,决定把它们孵化出来。云雀和堇小心翼翼地照顾着鸟蛋,日夜不敢放松,最终,三枚鸟蛋中只有一枚孵化出了一只黄色的小鸟,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鹦鹉。云雀轻轻地将它捧在手心里,她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丝带。
后来,丝带渐渐长大,也越来越活泼可爱,云雀和堇非常喜爱它。谁知道有一天,堇在打扫房间时忘记了关好鸟笼和房门,长大的丝带就这样展翅高飞,离开了家,离开了这对好心的祖孙,故事也由此展开了……
精彩内容
堇特别喜欢鸟。
每当我去上学的时候,堇就会独自到家里二楼的露台上,躺在她喜欢的藤编摇椅上,一摇一摇地观察鸟儿。偶尔,也会一点一点地品尝着装在水壶里的甜咖啡。
我家的院子并不是很宽阔,堇之所以能在家观察鸟儿,是因为我家的房子是借景构造。房子内部已经成了老宅,从露台的位置看过去,恰好如浓密的森林一般。
去年夏天,我们在这样的“森林”里装了一个鸟巢。
当时,邻居家的树疯长,粗大的树枝都伸进我家院子来了,于是邻居家主人过来说想要砍掉。堇就毫不做作地直接跟人家交涉。
她说这点小事不用在意,还反过来问对方能不能让她在树枝上放个鸟巢。
当被堇那双眼睛凝视着时,只要不是心眼坏的或者意志特别坚定的人,都难以拒绝她的请求。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心心念念地等待着“客人”入住鸟巢。这棵以前被我们亲切地唤作“老爷爷”的大树上,曾偶尔飞来过几只野鸽子跟白脸山雀,堇拿着双筒望远镜从远处观察它们。近来,堇的手没力气了,视力也下降了,放个鸟巢在这里,恰是时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近距离地观察鸟儿们而不用再拿着望远镜了。
“老爷爷”四季景色不同。夏天,一树郁郁葱葱的绿叶;秋天,满树的叶子红黄尽染;冬天的时候,叶子们就被无情地吹落一地;可是一到春天,又会生出密密麻麻的小嫩叶,接下来到了夏天,又长满茂盛的叶子。
鸟巢就这样搁置了一年,又迎来了秋天。
不过和计划不同,这个鸟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偶尔有几只鸟飞来瞧瞧里面,却也没有在此常住下来,很快就又离开这个圆圆的洞,飞向外面的世界了。
即便如此,堇还是日复一日地盯着“老爷爷”看。
有时候,我也会跟堇一起观察鸟儿。
可是我因为受不了一直盯着等待,就很少长时间待在露台了。
说起来,还是堇给我取名叫云雀的。她说看到刚刚出生的小小的我时,那个名字就从天而降了。
堇平时极少表明自己主张,只有那次一反常态。她是第一个抢上前去,紧紧用双臂抱住包在崭新纱布包被里的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跟云雀是永远的朋友,我们一定能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那之后,尽管父母也商量过给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字,堇却一直坚持喊我“云雀”。
结果,虽然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也还是勉勉强强地把命名权让给了堇。就这样,我的名字就正式叫“云雀”了。后来,曾听母亲说她本来是想给我取一个带“子”字的名字的。
然而,当我懂事后,堇打开野鸟图鉴给我看“云雀”的图片时,说实话,我是相当失落的。画上的那个像麻雀一样土里土气的褐色的鸟,跟我所期待的红的、蓝的、黄的、彩色鲜艳的鸟完全不同,这让我总觉得有种被骗的感觉。
我心想,堇当时是怎么想的啊。
堇说:“云雀飞翔的姿态令人惊叹,像一条直线从天而降,没有片刻犹豫哦。很想让你成为云雀这样的女性啊。我无法再展翅高飞,只能一直仰望天空罢了。”至今,就像堇说的那样,我们是彼此独一无二的亲密朋友。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同学都觉得忘年交很奇怪,似乎他们都无法想象在同年级以外存在的友情。然而,我并不那么想,反而觉得太在意一岁两岁年龄差的人太可怜了。迄今为止,我从未有过“堇是老奶奶”的感觉。
刚进十月,一个晴朗的午后。
我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来,就直接去了二楼的露台,结果却不见堇的身影。心想着她会不会是去洗手间了,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见堇出现。这时,从邻居家的院子里传来淡淡的清香,是堇最喜欢的金桂的香味,乘着秋天的微风飘来了。我想和堇一起感受这样的感觉,就大声喊她。因为我的父母都在上班,这个时间,只有我和堇在家。
“堇——”我喊了好几声,堇才突然应声:“怎么啦?”我一看,她在楼梯下站着。明明是在家里,却戴了顶非常奢华的帽子。
“堇,金桂……”刚开口,堇就摆手制止了我。
我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下楼梯。母亲曾经一再提醒过我说这样下楼会弄坏地板,让我不要这样,可是现在家里只有堇,我就不用在意。我痛痛快快地跳下来,一着地,地板就像要裂成两半似的发出“吱——”的一声响。
“云雀,过来,过来。”堇扶着自己房间的隔扇门悄声说。
可是,我从来没有踏进过堇的房间一步。正犹豫着该怎么办时,堇又迅速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鼓起腮帮的堇的脸,简直就像是刚出锅的馒头。接着,听到堇一如平时那样轻声地说:“房间里很乱哦。”堇的房间是她的圣地,因此,虽然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许进她的房间,可是没有一个家人踏进去过。这是我们中里家的默契。
从出生到现在,我第一次来到堇的房间。屋子里有点暗,有种不可思议的味道。榻榻米上铺着绒毯,和式与西式的室内装饰混搭在一起,不过这确实是堇的风格。已经不用的小提琴上,放着穿和服的人偶,也有穿裙子的人偶,各占一隅。
房间正中间摆着张床,屋顶垂下来一块带状的布,像公主居住的城堡一样。
堇又关上房间的隔扇,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一定要保密哦。”堇的眼睛好美,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会沉迷其中。她的眼睛宛若所有的冒险家寻遍世界各个角落才发现的神秘的湖水那样,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片或浅或深的蓝色。
说着“保密”两个字时,堇下颌的两边紧紧地收起来。
她走向梳妆台。最近,她的膝盖好像不舒服,做什么都慢吞吞地,蹒跚着,慢镜头一样挪动,真像是位老奶奶一样在一步一步地前行了。
终于,堇走到梳妆台边,在坐上椅子的瞬间,她穿着的长裙裙摆蓬起,勾勒出一条起伏的波浪。我悄悄地站到她的身后。
透过梳妆台上的镜子看去,堇像是在看什么刺眼的东西一样,使劲儿地眯着眼睛。我从未见过堇发火。虽然她相貌普通,但不知怎的,看上去就像是一直在笑着。也许是因为她双眼的眼角像公园里的滑梯那样,有着缓缓的弧度。很可惜,我的眼睛没有那种滑梯式的弧度。
我也努力地对着镜子微笑。默不作声地把手放在堇的肩上。她的肩膀就像装满了奶油的袋子,总是软乎乎的,鼓鼓的。堇整个人都像是黏稠的鲜奶油那么柔软顺滑,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碰触她。
眼前的堇双手举到头部,伸手够到帽檐儿。她用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的手,轻轻地取下帽子。那是顶深红色、带花的很正式的帽子。
费了一番工夫后,堇取下帽子,头上露出束着的圆圆的发髻。
这是堇一贯的发型,从后面看,就跟过年时候装饰用的圆年糕一模一样。
她那满头白得匀称的发丝里,没有一根黑发,总能让人联想起过节时候小摊上卖的棉花糖。若是一直靠近盯着看的话,会莫名地淌口水,有种想要把它们放到舌头上尝尝的冲动。
可是,现在,堇却在我跟前,轻轻地往她的发髻中塞了样东西。我不停地眨巴眼睛确认,无论如何看那都是用来测温度的体温计。
我很惊讶,也很不安。难道堇发烧了吗?只是,据我所知,测量体温都是放在腋下或者舌头下面,放在头发里测量还是第一次见。的确,从昨天开始,就觉得堇哪里好像有些隐隐的奇怪。
“能不能帮我一下?”她开口道。
我将目光从体温计上移开,正好与镜子里的堇四目相对。她正直直地盯着我。
“云雀,我想让你看看,几度啊?”我按照堇的要求,注视着插进她发髻里的体温计。堇一只手一直拿着体温计,看上去有些费力,于是,我替她拿着了。堇把手放回膝上,像是等待重大结果一样,静静地闭着眼睛。或许是有些紧张吧,堇薄薄的眼睑像随风起伏的丝绸一样,在微微颤抖。
不会吧?
从刚才起,我就在努力驱走心中隐隐的不安。就在上周,跟堇同龄的老爷爷痴呆了,住进了养老院。但是,堇不会的……万一堇也那样了,我也要和她一起住进养老院去陪她。
我安抚着自己的情绪,一边静静地等待着插进堇发髻里的温度计数字停下来。在家以及学校的保健室里用的都是数码体温计,可是堇爱惜旧物,还在用老式的体温计。数码式体温计会发出声音通知我们,这种老式的就只能等它停下来了。确定水银停住了,才开始看泛着银光的刻度。
“36.9度。”“谢谢你啦,云雀。”堇不动声色却又郑重其事地跟我说。从她的声音里,我立刻知道刚才自己是想多了。堇没有生病。没错,我是最了解她的,这跟平时的堇一样。
堇就那样坐在椅子上,从发丝里取出体温计,用力地甩了甩。确认过刻度归零后,又把它放回原来的抽屉里。堇这种量体温的做法,或许是以前的方法吧。我也听说过给小孩子量体温的时候,有会把体温计从屁股里插进去测量的,也许还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体温测量方法吧。
我正想着,只见堇又把双手伸向头上的发髻,把它往两边拨开,尽量打开里面。
“你瞧。”里面到底会是什么呢?我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还是照着堇的话,稍稍探着身子,向堇的头顶看去,只见正好在她的发旋附近,放着一个淡红色的棉扑。
我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疑问。堇为什么要在那里放一个棉扑呢?堇一言不发,一只手缓缓地将它拿起来。所谓的棉扑,其实是夏天为了防止起痱子,洗完澡往身上扑痱子粉的时候用的,就是像棉花团一样的圆圆的软软的一个东西。乍一看像是稍大点儿的软奶糖,可是不知道到底叫什么,我和堇都把它叫作棉扑。
“嘿呀!”堇口中冒出了有点儿奇怪的声音。就像是嘴里衔着竖笛却痛痛快快地打喷嚏一样。
“好像是母鸟不孵了。”“孵?”我重复着堇刚刚说的词,有点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一看,在淡红色棉扑正下方,堇的发旋的正上方附近,放着一个小小的圆东西。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就像小猫一样,吭哧吭哧地用手揉了揉眼。然而,眨了又眨,无论怎么看,都觉得是蛋。
刚开始,那蛋跟堇自然的白发混为一体,看不很清楚,仔细一看,堇柔软的头发仿佛围成了一个巢,将蛋包围在里面。没有鸡蛋那么大,却也不像鹌鹑蛋有斑点。孩子们间曾经流行过这种形状的巧克力。我不经意间一闪念,说道:“巧克力做得真棒啊!”如果是巧克力,这样放着的话,也许会被堇的体温给熔化了。化了无所谓,我担心的是别把堇那罕见的白发给弄脏了。
“不是的,云雀,”堇说,语气就像名人[ 象棋、围棋里的最高等级。
]举起棋子喊“将”时那般自信、骄傲,“这个啊,可不是点心哦,是真——的鸟蛋呐。”她特意强调了“真的”两个字。
堇绝对没有撒谎。我立刻明白,那就是真真正正的鸟蛋。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上面粘着毛发,看不清楚。现在才发现居然共有三枚蛋。堇瞟了眼惊讶的我,莞尔一笑。不知为何,我之所以相信堇出身高贵,就是源自看到了她这种独特的微笑。
“是什么鸟呢?”我在想。
它们并不是像牛奶般纯白色,而是像鲜奶油那样浓郁的奶白色的鸟蛋。
“早些天,不是刮了很大的台风吗?母鸟似乎受到惊吓飞跑了。我从前天就一直守着鸟巢,母鸟好像是回不来了。今天早上开始就有乌鸦盯上它们了,所以我决定自己来负责照顾它们。这几枚蛋才产下几天,即便没有一直保温,也没关系,所以它们还有希望。”堇说的“希望”,大概是指孵出小鸟的可能吧。可是,在这样的小小的梦幻般的球体里充盈着将来能成为小鸟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最终也许还能长成真正的小鸟,对于这些,我实在难以想象。
结果,到最后堇都没有明确告诉我那些是什么鸟的蛋。或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吧。
默默地凝神看了会儿鸟蛋,堇再次打开梳妆台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彩色铅笔样的细长东西。也许是化妆时候的一种工具。
“云雀,能不能请你再帮个忙,用这支铅笔,在鸟蛋表面画上标记。如果三个能分别画不同的标识以便区分就更好了。今后的每一天,我都要转卵。”又一次从堇的口中跑出了闻所未闻的词儿。她说的“转卵”,是“展览会”的“展览”[ 日语“转卵”发音与“展览”发音相同。译者注。
]吧,可是总觉得不对劲儿。我正在琢磨着,又听到堇柔声说:“我说的‘转卵’,就是每天翻翻鸟蛋。要想让鸟蛋整体受热均匀,就要转换它们的方向。母鸟不也是经常翻动身体下面的鸟蛋嘛。只不过原本这是自然而然而为之,现在我来人工化了。”我照着堇的话,开始在鸟蛋的外壳上作画。然而,我稍一用力,蛋就差点儿出现裂痕,搞得我一直战战兢兢的,完全用不上力。指尖接触到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蛋的温热,心里莫名地有种柔软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用力碰触,终于拼尽全力,将三个鸟蛋全部都画上了记号。
第一个上面画的是“☆”,第二个画的“○”,第三个的时候,我犹豫了下。因为按照习惯,“○”后面应该是“×”的,但我觉得兆头不好,于是最后就画了个邮政标志“〒”。画完之后发现,或许是刚才一直紧张,手心里汗津津的。
“辛苦啦。”堇说着,又摸索着把棉扑放回原位,整理发髻。
堇整理好发髻,以免风吹进来,再戴上帽子。任谁也看不出那儿藏着鸟蛋。
就这样,我和堇开始了孵蛋的日子。
堇完全成了一个真正的母鸟,用头发筑成的巢守护着鸟蛋,而我则作为她的助手,尽最大能力协助她。孵出小鸟,是我们最大的使命。
孵卵、转卵到孵化,这些事情向我打开了一扇我从未了解过的多彩的鸟的世界。堇说,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是孵化成功至关重要的条件。
因此,自打那天开始,堇就干脆不再洗澡了。总之是尽可能地小心,不让鸟蛋感冒。我家是木质房屋,太阳一下山就会特别凉。于是堇就端出暖炉,在房间取暖,并且在上面放上水壶以确保湿度。
翻鸟蛋就成了我的任务。为了不让它们感冒,我决定洗完澡,身体暖和了的时候才去。
到了晚上,我洗完澡后就直接去了堇的房间,堇惬意地躺在那张观鸟的摇椅上。房间里暖和得如盛夏一般。我扫了一眼房间的温度计,已经27度了,比外面温度要高出十多度。堇圆圆的脸已经稍稍泛红了。
我一走近,堇就把帽子取下来,熟练地将头发围成的鸟巢左右分开。“把你刚才画上记号的那一面翻到下面去吧。”堇说。
我用拇指和食指小心地拿起蛋来,以免弄碎了,把带记号的一面转到下面之后,再放回原来的位置。
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才翻了一只,疲惫感就瞬间袭来。小小的鸟蛋,就像是镶嵌在戒指上的宝石那样,神圣而庄严。
终于完成了翻鸟蛋的任务,堇再次用手整理好发髻,盘成圆鼓鼓的漂亮发髻,然后,立即重新戴好帽子。
从那天开始,我的心片刻都没离开过鸟蛋。无论是睡觉还是醒着,都只想着它们。堇一直都和鸟蛋在一起,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她每天的生活,更是以鸟蛋为中心。她说不能让鸟蛋冻着,连最喜欢的观鸟都果断放弃了。反正保持身体温暖是最重要的,一整天都待在屋里不出门。
我一进堇的房间,就闻到一缕生姜糖的淡淡甜味。垃圾箱里也放着生姜糖的包装纸,这也是为了身体保暖吧。堇已经完全成了只母鸟了。
虽然堇以前就与众不同,但是自从成了鸟蛋们的守护者后,这种不同的程度就更甚了。吃饭的时候也好,上厕所的时候也好,帽子片刻不离身,就像是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似的。我除了帮忙翻翻鸟蛋,也一起坚守着这个秘密。
“堇,吃饭咯!”我冲着堇的房间喊道。
从孵蛋开始,已经过了一周了。
堇关着窗帘,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仔仔细细地整理着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堇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都会穿漂亮的裙子。那些都是堇还是香颂歌手的时候风靡一时的舞台服装。大都是袖子鼓鼓的,腰部紧紧收着,裙摆很长的晚礼服。堇是绝不浪费的人,很爱惜旧物,一直穿着舞台服装。
但,许是跟那时比身材变化了吧,后背的拉链经常只能拉到一半,腹部的装饰扣有时候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着实可爱。对这些,我们即便看到了,也假装没有看到一样。
我把堇要吃的面包卷放进微波炉,设置到100度,趁微波炉转着的时候,再把刚才做好的大酱汤重新加热一下。
“今天是土豆魔芋汤哦。”我用毛巾擦着湿湿的手,向堇望去。她今天穿了件暗红色的可爱公主裙,腰间系了个大丝带。当然,头上还是戴着帽子。
“谢谢云雀。”堇每次都必定会轻轻屈膝,表情温和地坐下来。
小菜是烤秋刀鱼,是母亲匆忙下班回来的路上,在超市里买的。上面还贴着半价标签。不过,分量只有父母和我三个人的。堇的位子上,白色汤碗里盛着的,只有大酱汤而已。我小心翼翼地把微波炉里加热的面包卷放进和酱汤碗配套的白色盘子里。
母亲把饭从电饭煲里盛出来,父亲也换上了居家服坐下来,我们一家四口终于都围坐在饭桌跟前了。整个家里都弥漫着秋刀鱼的香味。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吃饭模式的,我记事起,堇就一直和我们吃的不一样。是因为上了年纪,吃不了一般的食物,还是有其他的理由呢?我是小孩子,完全不懂。总之堇吃着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母亲重新进入职场。从那时起,堇的大酱汤就由我来做了。但是并不难。堇资助过的人们每周都会送来蔬菜,从中挑些对眼的,用高汤煮软了,再加入味噌溶化便可以了。
味噌汤旁边,再放上加热好的面包卷,堇的晚饭就做好了。面包卷通常是买好放在家里的。
对于在国外生活过的堇来说,大酱汤配面包,似乎并不怎么奇怪,很自然。
堇的早饭是水果和沙拉,午饭是饼干和咖啡。据说她还是香颂歌手的时候,曾经给福利院捐赠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当时受帮助的人们现在还会送来很多礼物。所以,堇的食物,基本上用他们送来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解决了。
父母亲和我都在埋头剔秋刀鱼的骨头,我用眼角余光看了下堇,她还在安静地喝着大酱汤。堇是用勺子而不是用筷子喝汤,海带也好,萝卜也好,都能妥妥地用勺子送进嘴里。每当看到她这样优雅的动作,我都看得出神,甚至会忘记吃饭。
我一次都没有见到堇把大酱汤洒到桌子上过。她也从没有像父亲那样,端碗咕咚咕咚地喝过,都是这样雅致地用勺子就能喝下去,而我,每次都要弄洒。并且,堇一定会等到其他家人都吃完的时候才把勺子放回去,绝对不会自己先吃完,或者自己一个人一直吃到最后。吃完后,她会往小玻璃杯里倒上白兰地,悠然地喝着,也会含上一小块苦巧克力,放在舌尖细细品味。
我暗自想,堇大概是日本,不,是全世界最后的贵妇人吧。
我的父母完全不理解这样的堇。对于只有极其普通想法的他们来说,堇从服装到吃饭、礼貌用语,全都像是外星人一样。因此在我家的餐桌上,几乎没有什么热闹的谈话。堇和我在一起也很健谈,可是一和我父母在一起,就突然沉默下来。
按照父亲的说法,堇是由小姑娘直接就变成了老奶奶。从社会关系来说,堇和我相当于是祖孙的关系,可实际上,我父亲并不是堇的亲生儿子。
关于堇,我所知道的是她出生于有着光辉历史的富裕家庭。然而,战后不久,地位、名誉、财产连同双亲都一并失去了。之后,她作为歌手开始谋生,却在步入正轨的时候患了场大病,突然唱不了歌了。那时候,她似乎历了很多难以言表的事情。
收我父亲为养子,是堇四十多岁的时候了。那时她已经能再次登上舞台歌唱,生活也终于安定下来,也不再有不能为人道的苦楚。于是堇收养了交通事故中失去双亲,在福利院生活着的我的父亲。
就这样,一直到父亲成年和母亲结婚后,一直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当然,我的父母并不是对堇冷漠或者有坏心眼,也没有要把她从家里赶出去这样的举动。只是,彼此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我以为正是这种相处方式,反倒让堇觉得自在吧。
第二天,一从学校回到家,我就听到家里罕见地响着音乐。我家很小,音乐声响彻整个院子,把“我回来啦”的声音也给淹没了。
我悄悄地看了一眼堇的房间,看到她跟平时一样整个身子都躺在摇椅里,正小憩呢。堇因为操心鸟蛋,就连夜里也一直都没怎么睡过。肯定睡眠不足了吧。
那是一个女人的歌声。听了有种苦涩的、令人怀念的、悲伤的感觉。总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却想不起到底是谁。有的调子是整体低沉的,有的调子又像是欢快地边跳边唱。听着听着,就有种在大海上随着波浪轻轻起伏的感觉。
我刚要打开背包,拉手咔嚓一声响,堇从睡梦中惊醒了。
“云雀?”堇有些惊讶,抬高了声音喊我。
“我回来啦,刚刚到家。”我小声说着,悄悄站到了堇的身旁。
“哎呀,我怎么完全睡着啦。”堇双手拍着她那软乎乎的圆圆的脸颊说道。接着,她似乎突然意识到了正放着的音乐,于是急忙从摇椅上站起来。她离开的瞬间,摇椅像是受到惊吓般摇晃着划出大大的弧形。
堇把唱片上的指针拿起的瞬间,家里顿时安静下来。原来很少见堇听音乐的。
我立刻开始了每天的必修课,给鸟蛋测体温。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任何语言,堇便心有灵犀地取下帽子。我从抽屉里拿出体温计,确认刻度甩下去之后,就轻轻地将前端插进堇的发髻中。
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都量不好。一想到体温计的头可能会把鸟蛋碰烂,我就觉得恐怖,总是无法把体温计放进去。无论如何都不能准确测到发髻里的温度。每次测量,我都感觉自己的眼睛像是长在体温计前端一样,摸索着找最合适的位置。这些天下来,终于能不再战战兢兢地测温度了。
“你很少在家听音乐呢。”我对刚才的唱片有些好奇,委婉地跟堇提起,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手里的体温计刻度缓缓上升。
这的确是少有的事。父母亲对卡拉OK很感兴趣,一有活动经常会带上我,可堇总是固执地拒绝,别说卡拉OK了,我甚至都没有听堇哼过歌。别说唱了,就连堇这样听着音乐的样子,我可能都是第一次见到。
然而,堇默不作声,完全就当我没有问过一样。体温计恰好停在了37度。
洗完澡后,我再次来到堇的房间,给鸟蛋翻翻个儿。我看到梳妆台上放着一本旧相册。寒冬已经逼近,堇穿着一双红毛线织的袜子,说是捐助者给织的,脖子上一层层地围着与之配套的毛线围脖。
顺利地结束了今天的任务后,就听到堇柔声对我说道:“云雀,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好吗?”我轻轻地坐到堇的床边。从孵鸟蛋以来,她的床上几乎就没有睡过的痕迹。堇环抱着相册,紧挨着我坐下了。软软的床摇晃了几下,我几乎要倒到堇身上去了。她一只胳膊搂着我,把相册放在膝盖上,开口道:“这是好久,好久以前的我。”堇翻着已经破破烂烂的相册衬纸,有些羞涩地说道。每翻一页,都像是打开古老的木窗一样,发出轻轻的吱吱呀呀的声音。衬纸颜色已经泛黄,照片也都像是在黑白底色上蒙上了一层雾气似的。
“虽然,我现在是这样一个老奶奶的样子,但我也年轻过啊,云雀。”照片上,是幼年时的堇。看起来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些。穿着漂亮的白色裙子,简直就像是堇房间里摆着的人偶一样。见到比我还年幼的堇,总觉得有点儿奇怪。
“好漂亮啊!”我对着其中一张照片,不由得小声感叹。
“这个啊,”堇接过话说,“是我成为一位著名声乐家的弟子之后,在老师家里住着,练习唱歌跟礼仪的时候的照片。现在想来,那时候也许是最惬意的吧。”盖着崭新桌布的圆桌旁,有个留着娃娃头的女孩,手里端着个咖啡杯。总觉得这女孩似乎就是堇。旁边还有一个明显年龄大些的女性。的确能看出来,堇是发自心底地感觉幸福,笑容里没有一丝阴郁。
就这样一页一页地回忆着,跟我说着,堇一张接一张地把这些深棕色的照片拿给我看。
其中,有张剪切下来的当时的报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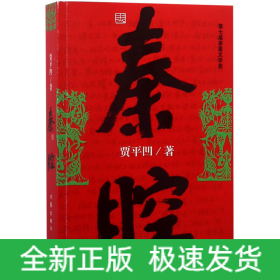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