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念的力量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4.91 6.0折 ¥ 75 全新
库存17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英] 以赛亚·伯林 胡自信 魏钊凌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69358
出版时间2019-04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5元
货号1201867857
上书时间2024-06-1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观念的演变解读历史的暗流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享誉东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观念史(亦称思想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伯林用强大的历史研究和叙事将观念史变成一门显学。他将人类观念的历史流变向读者和盘托出,不仅令读者更为全面、通透地把握处于历史演进中的人类观念,也揭示出观念乃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一股强大力量。
●囊括诸多经典伯林议题,了解20世纪思想潮流的入门佳作本书囊括诸多经典伯林议题,从俄国思想家、自由观念到以色列问题,还收录了伯林梳理自身学术道路的观念自述,无不以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切入我们所处时代核心的观念问题,为20世纪的现代世界提供观念的注脚,证明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而可怕的观念也可以给世人带来厄运和灾难。
●依据普林斯顿2013年修订版,新增名家前言,首刊伯林未出版文字本书依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升级整理,为伯林著作的最新定本,不仅注明早期版本中出处不明的引用,收录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阿维赛·马加利特的长篇前言,还增补了伯林此前从未出版的关于民主、教育和民族主义的三篇文章,乃是当前伯林著作的权威版本。
●全新“伯林文集”,典雅装帧,宜读宜藏全新推出的“伯林文集”囊括以赛亚·伯林的专著、文章和书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位20世纪著名知识分子的思想成就。文集采用方便易携带的小开本,典雅朴素而统一的装帧设计,美观疏朗的内文版面,既适合阅读,也适合收藏。
目录
参考文献说明
前言
编者前言
我的学术之路
哲学的目的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
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
俄国观念史
被神化的那个人
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
知识阶层的作用
自由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
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
以色列的起源
犹太人之被奴役与被解放
哈依姆·魏茨曼的领导艺术
寻找社会地位
欧洲浪漫主义的本质
梅尼克与历史相对主义
论通识教育
第二版附录
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
伍德罗·威尔逊论教育
论民族主义
索引
内容摘要
书斋里生长起来的观念,为何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观念的力量》收录伯林此前不曾集结成书的22篇文章,从伯林对自身学术道路的梳理,到令他成名的俄国思想家研究,再到令他享誉世界的自由论述,无不以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证明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而可怕的观念也可以给世人带来厄运和灾难。
精彩内容
我的学术之路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牛津哲学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我的哲学兴趣发端于此。那时,牛津大学的很多学生都上哲学课。我对哲学一直感兴趣,于是在1932年,我得到一份教哲学的工作;我那时的观点当然受到了牛津大学哲学同辈那些讨论的影响。哲学中虽然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返归经验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种观念已经开始主导英国哲学界,这主要是受到了G.E.摩尔与伯特兰·罗素这两位著名的剑桥哲学家的影响。
证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末期,我们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意义的本质——它与真理和错误的关系是什么,它与知识和意见的关系又是什么;尤其是意义的检验问题:它总是通过命题来表达,命题的可证实性也是一个问题。探索这个问题的动力来自维也纳学派,其成员都是罗素的弟子,深受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等思想家的影响。最流行的观点是,命题的意义就是它得以被证实的途径——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某句话,它就是一个无所谓真假的陈述,与事实无关;因此它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例如命令、愿望、想象型文学以及其他并未涉及经验真理的表达形式。
我受该学派影响:它所考虑的问题和提出的理论让我很感兴趣;但我绝非其信徒。我始终认为,各种陈述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可信的或不可信的,或许是有趣的;虽然它们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正是经验所感知的那样(从那时到现在,我从未以其他任何方式感知过世界),但是它们未必如维也纳学派及其追随者逻辑实证主义所宣称的那样,能通过某种简明而有力的标准证实。一开始我就认为,普遍命题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证实的。无论日常语言的陈述,抑或自然科学的陈述(这才是维也纳学派心目中的理想),都可以在无法严格得以证实的情况下拥有完整的意义。如果我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我绝不可能知道,我是不是对存在的所有天鹅都有此把握,或天鹅的数量是否无限;一只黑天鹅无疑能够推翻这一概括。可是在我看来,完全证实这个概括似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说这个概括毫无意义,就会显得荒唐可笑。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假言命题,尤其是未完成的假言命题。就后者而言,说经验观察能证明它们是对的或错的,显然是自相矛盾;然而这些假言命题显然是有意义的。
我想到很多类似的陈述,它们显然是有意义的,但其意义不符合以上所述严格标准,即直接的经验观察,或感官世界。因此我虽然积极参与这些讨论(后来被称为牛津哲学的那些观念,实际上起源于我家举办的那些晚间聚会,参加者包括后来成名的哲学家A.J.艾耶尔、J.L.奥斯汀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他们深受牛津经验主义的影响;牛津实在论也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外部世界独立于人类观察者)。我仍然是异端,不过是一个很友好的异端。我从未放弃那时就已形成的观点。我现在仍然认为,语词只能表达经验世界——此外并无其他实在,然而可证实性并非知识、观念或假设的唯一标准或最可信的标准。这是我毕生持有的观点,我的全部观念都带有这种色彩。
我让我的年轻同行加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如“这种粉红(色调)更像这种朱红色,而不像这种黑色”这类命题的属性。概而言之,任何经验都不可能推翻这个真理,这是显而易见的——肉眼可见的颜色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说该普遍命题是先验命题,因为它不是从形式上根据任何定义推导而来,因此它不是逻辑或数学之类的形式科学(formaldiscipline);先验命题(当时被看作同义反复)只属于形式科学。于是我们在经验世界发现了一个普遍真理。“粉红色”、“朱红色”或其他颜色的定义是什么?它们没有定义。这些颜色只能通过观看分辨,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的定义是一种伪装,我们不可能据此推导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很像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所讨论的那个老问题。一连数月,我们都在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深信,我那个命题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却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性;与其相对立的命题是不可理解的。我不知道我的同事们是否再次提出过这一问题,可是在当时,这是我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我的观点与《经验主义的界限》一文中罗素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
现象主义在我那个时代,人们讨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现象主义——问题如下:我们的经验是否以感觉经验为界,如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所言(密尔和罗素的一些文章也持这种观点)?是否有一种实在,独立于我们的感觉经验?有些哲学家,如洛克及其追随者,认为有这样一种实在,不过我们不能直接感知它——这种实在引发感觉经验,我们能够直接感知的就是这些感觉经验。另外一些哲学家认为,外部世界是一种物质实在,有时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它,有时我们会以错误的方式感知它:这种观点被称作实在论。与此相反的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完全是我们的理性、想象力之类的感觉和能力创造的——这种观点被称作唯心论,我从不相信这种观点。我从不相信任何形而上学真理——无论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极为不同的康德所谓的理性真理,抑或(客观)唯心论的真理,即费希特、谢林以及黑格尔所倡导的,至今仍不乏信仰者的那种真理,我一概不信。如上所述,意义、真理以及外部世界的本质,是我当时思考的一些问题;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它们写过些论文——有些观点已经发表。
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是,哲学家们都在寻找绝对确定性、毋庸置疑的解答或观念的绝对可靠性。一开始我就觉得这种寻找是虚幻的。某个结论或某种第一手资料,无论其基础多么牢固、内容多么广泛、逻辑多么严密、可信度多么“不证自明”,我们总是能够设想,某种东西可以改变甚至推翻它,即使现在我们还不能预见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我怀疑很多哲学都是建立在某种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种怀疑后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主导我的观念。
我一边教哲学,一边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撰写卡尔·马克思传。我当时从未觉得马克思的哲学十分新颖或有趣。然而研究他的观念却把我引向其先驱,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这是最早的有组织地反教条、反传统、反宗教、反迷信、反愚昧、反压迫的哲学团体。我开始钦佩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家们给自己制定的宏伟目标及其参与的伟大事业,他们要把全人类从教会、形而上学、政治等黑暗势力中解放出来。此后,我渐渐开始批评他们共同怀有的某些观念,可是我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启蒙运动始终心存钦佩与赞美。撇开其经验主义缺陷,我所批评的是它得出的一些逻辑结论与社会判断。我意识到,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那些教条,一定程度上起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所追求的那些确定性。
二观念史与政治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是英国军队的一名军官。当我回到牛津教哲学时,让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一元论——从柏拉图一直到现在,它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其次是自由这一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些问题。后来很多年,它们一直影响着我的观念。
一元论17—18世纪,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目不暇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尔、孔狄亚克,以及天才的宣传家伏尔泰和卢梭认为,如果发现了正确方法,我们就能找到社会、政治、道德以及个人生活的根本真理——在研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这种真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百科全书派坚信,科学方法是通向这种知识的唯一道路;卢梭等人相信,通过反思,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永恒真理。无论分歧多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相信,他们已经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个观点建立在一个具有更大普遍性的观点之上:所有正确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正确回答,其他回答都是错误的,否则这些问题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康庄大道必然存在,头脑清楚的思想家由此即可求得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自然科学如此,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领域亦如此,无论其方法是否相同。最深层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问题主导(或应当主导)人类的生活,把这些问题的所有正确答案集中起来,我们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诚然,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这些答案:人类可能太受感情困扰,可能太蠢、太笨或太不走运,不可能找到这些答案;它们也许很难,我们的方法也许不正确,求得它们的手段也许过于复杂,我们无能为力。无论哪种情况,只要问题正确,答案就必然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后代也许知道;古时的哲人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伊甸园中的亚当也许知道;如果他不知道,天使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也不知道,那么上帝一定知道——答案必然存在。
社会、道德以及政治问题的答案一旦被发现,那么既然知道它们是真理,人们就不可能不遵循,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要去选择其他方法。如此看来,尽善尽美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生活也许无法企及,但是原则上说,人们可以拥有这种观念——实际上求得这些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原则上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一种可能性。
诚然,不只启蒙运动思想家具有这种信念,尽管不同思想家提出的方法各不相同。柏拉图认为数学是通向真理的大道,亚里士多德也许认为生物学才是这样的大道;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圣经》中、在受圣灵感召的先知的解说或神秘主义者的直觉中寻找答案;有人认为实验和数学能解决问题;还有人如卢梭那样,认为只有纯洁的心灵、未被污染的孩子或质朴的农民才能认识这些真理——他们比社会上的人好,因为后者遭到文明的污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思想家也许认为,找到这种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前辈过于天真和乐观;但是他们都认为,人类可能——或说当时已经——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方法,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问题;根据这些真理,我们就能确立道德观念、安排社会生活、建立政治组织以及促进人际交流。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哲学——普通百姓与思想家,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改革家与革命者,都是其信徒。这是人类观念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生活两千年之久。如果那些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人们怎么会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许多世纪以来,这始终是欧洲理性主义及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人与人如此不同,文化与文化不同,人们的道德与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形形色色的理论、宗教、道德、观念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人类所关注的那些最深层问题的正确答案,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
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怀疑这个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观念,我就是不信它。也许性情使然,只好如此。
维柯阅读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著作,让我大吃一惊。在我看来,他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观念的哲学家。维柯想理解历史知识以及历史的本质:谈到外部世界,我们完全可以信赖自然科学,不过它们能给我们提供的,只是描述石头、桌子、星球或分子的运动。谈到过去,我们往往超越行动的范围,我们想知道人类是如何生活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动机、忧虑、希望、理想以及爱与恨——他们向谁祈祷,他们如何通过诗歌、艺术和宗教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能做这些,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我们能以这些方式来理解自己的内心生活。我们知道石头或桌子如何运动,因为我们首先观察其运动,然后提出假设,最后再证实这些假设。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块石头为什么想成为现在这副模样——其实我们并不认为它会有愿望或意识。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为什么是现在这样,我们追求什么,什么让我们失望,什么能够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观念。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远胜于我们对石头或河流的了解。
真知不仅会指出事物是什么,而且会解释它们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我们钻研得越深,就能越清楚地意识到,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所提出的问题,不同于罗马人所提出的问题;罗马人的问题又不同于基督教的中世纪、17世纪的科学文化以及维柯所在的18世纪提出的问题。问题不同,回答不同,抱负不同;语言的使用方法不同,符号的使用方法不同;某些问题的答案不能解释其他文化的问题,二者关系不大。当然,维柯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因此他相信只有教会能够提供这种答案。即使如此,他还是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念:文化与文化不同;在公元5世纪的希腊人看来很重要的事情,在印第安人、中国人或置身于18世纪实验室的科学家看来,其意义会大不相同;因此他们观点各异,他们那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当然,人性是共通的,否则这个时代的人就不能理解另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或法律,维柯是法学家,他很清楚这一点。这并不是要否认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化体验,一种活动在同一文化中,与另一种活动有关;但是这种活动与另一文化中相应的活动之间,就没有这样的紧密联系。
赫尔德后来我了解到一位更重要的思想家,即德国哲学家兼诗人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他还不是第一个反驳其同时代法国思想家的人(获此殊荣的是他的老师约翰·格奥尔格·哈曼)。这些思想家认为,有些真理是普遍的、永恒的、毋庸置疑的,无论对谁,亦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是真理;偏差来自错误和幻觉,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普遍的——“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任何人都相信的那些真理。”。赫尔德认为,不同文化对各自核心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他感兴趣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文学科,人的精神世界;他深信,葡萄牙人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在波斯人看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孟德斯鸠早已开始发表这种看法,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他称环境为“气候”。可是到头来,他还是一个普遍论者——他认为,那些转瞬即逝的小问题的答案也许各不相同,主要真理却是永恒的。
赫尔德明确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参照系;这些文化没有任何理由互相攻击——普遍的宽容一定是可能的——但是统一必然导致毁灭。帝国主义是最坏的选择。罗马镇压小亚细亚的民族文化,以造就统一的罗马文化,这是犯罪行为。世界是一个大花园,奇花异草在这里生长,它们习性不同,其要求、权利、过去和未来各不相同。由此看来,无论人类有哪些共同之处(再重复一遍,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特征),普遍有效的正确答案,既适用于这种文化,又适用于那种文化的正确答案,根本不存在。
赫尔德是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政治上,他并非民族主义者(在他那个时代,政治民族主义尚未出现),但是他相信,文化具有独立性,人们必须维护不同文化的独特性。他认为,文化能把一群人、一个区域或一个民族团结起来,属于某种文化的愿望是人类的基本需求,根深蒂固,一如他们对饮食或自由的需求。他们希望属于某个社会,在这里,你能听懂别人的话,你有行动自由,你不仅建立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而且编织了情感的纽带;这种需求是成熟的人类生活之基础。赫尔德不是相对主义者(虽然人们经常这样描述他),他认为,人类拥有一些基本目标和行为准则,但是在不同文化中,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尽管这些目标和准则彼此相似,一种文化可以理解另一种文化,但是我们绝不能把不同的文化混为一谈——人类不是一,而是多;问题的答案是多,不过它们可能都有某个重要特征,这是统一的。
浪漫主义及其发展这种观念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一些崭新的,却令人不安的观点:理想不是客观真理,写在天上,要求人们理解、模仿或实践;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价值观念不是人类发现的,而是他们创造的——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确这样认为,以反对肤浅的法国人所提倡的客观主义和普遍化倾向。独特性至关重要。德国诗人用德语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创造了这种语言:他不仅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德国艺术家创造了德国的油画、诗歌与舞蹈——其他文化概莫能外。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提过这样的问题:“人们唱某首歌以前,它在哪里?”究竟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哪里都不在”——人们在唱歌的时候、在谱曲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生活也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生活过的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对道德与生活的美学阐述,不是对永恒真理模式的套用。创造就是一切。
各种思潮由此发端——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英雄崇拜。我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也许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此外,“我”是谁?对拜伦式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我”实际上是一个个体、局外人、探险者或亡命徒,他公然反抗社会及其公认的价值观念,只信奉自己的价值观——这也许让他在劫难逃,却胜于盲目服从或沦为平庸的奴隶。别的思想家认为,“我”具有很浓的形而上学色彩。它是一个集体——一个民族、教会、党派或阶级,或是一座大楼,我只是它的一块奠基石;或是一个有机体,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微生物。集体是创世主;只有当我隶属于一个运动、种族、民族、阶级或教会时,我才有重要性;我的生命本来就与这个超人密切相关,对他来说,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体。德国民族主义应运而生:我做某事,不是因为它是一件好事,也不是因为它合乎正义,更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代存在主义也应运而生——我做某事,因为我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我不是由任何事物创造的;我做某事,不是因为那是一种我必须遵守的客观秩序,或者因为我必须遵守某些普遍准则;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我就是我,我给自己指明方向,我对自己负责。否认普遍的价值观,强调人首先是超我的一个元素,应当忠于超我;回顾欧洲历史,强调这一点是很危险的,它已经导致现代很多具有毁灭性的邪恶事件的发生。追根溯源,它正是发端于最早的德国浪漫主义政治观念和理论及其在法国和世界各地的信徒。
我从未接受关于超我的这些观念,但是我很清楚它们在现代观念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不是我,而是党”,“不是我,而是教会”,“我的祖国,无论对错,毕竟是我的祖国”,如上所述,这类口号已经伤害到人类观念的主要信念——真理是普遍的、永恒的,适用于所有时间的所有人——这种伤害至今没有消失。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一种不停地运动的精神,能够自我创造和自我推动;是一部自我编排的多幕戏剧,马克思认为,其结局将是某种尽善尽美的状态——这一切均起源于那场浪漫主义革命。我坚决反对关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宏伟的形而上学解释——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但是我承认,这种解释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产生了影响。
多元论我认识到,理想是多种多样的,一如文化与性格。我不是相对主义者,我不会说:“我喜欢加了牛奶的咖啡,你喜欢不加牛奶的咖啡;我喜欢善良,你喜欢集中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压倒或整合某一方。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我坚持认为,有多种价值观念是人类能够寻找,而且正在寻找的,这是一些不同的观念。其数量并非无限多:人类的价值观念,当我保持人类的相貌与性格时,我可以追求的价值观念,其数量是有限的,我们可以说它是74或122或26;无论多少,它总是有限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在于,如果某人追求某个观念,那么我虽不追求此观念,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在他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去追求该观念,将会是怎样。因此人类的互相理解是可能的。
我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换言之,它们的本质以及对它们的追求,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重要条件,这是一种客观要素。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他们不是狗或猫,也不是桌子或椅子,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包含这样一种要素:某些价值观念是存在的,如果人依然是人,他们只能追求这些观念。如果我是一个具有足够想象力的(我确实需要这种能力)男人或女人,我就可以进入某种价值体系,这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我能设想有人会追求它,并且他们依然是人,依然是我能和他们沟通的一种生物,我和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因为人类必然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否则他们就不再是人类;他们也必然拥有一些不同的价值观,否则他们就没有任何区别;实际上他们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多元论并非相对论的原因——多种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要素,而非其主观想象力的创造。当然,如果我追求某一价值体系,我可能厌恶另一种价值体系;我可能认为,对我自己和其他人来说,它有损于我能践行或容忍的唯一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攻击它;在极端情况下,我甚至会发动战争。但我还是承认,它是一种人类追求。我厌恶纳粹的价值观,但是我明白,如果有许许多多的误导以及许许多多的错误观念,人们就会相信,它们是唯一的救世良方。当然,我们必须反对它们,如果需要,我们还得发动战争;但是我不同意像某些人那样,认为纳粹实际上是一种病态或精神失常,他们只是大错特错,完全被误导了,举例来说,他们认为有些人低人一等,种族至关重要,只有日耳曼民族具备真正的创造力,等等。我认识到,接受了足够的错误教育以及足够广泛的错误观念与谬误,人虽然还是人,却会相信这些,犯下滔天大罪。
如果多元论具有充分的根据,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只有一种价值体系是正确的,其他皆错),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我的价值观念是我的,你的价值观念是你的;如果我们发生冲突,那可糟透了,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的政治多元论是我研读维柯与赫尔德的结果,也是我追溯浪漫主义起源的结果;极端而病态形式的浪漫主义肆无忌惮,容不得人类的宽容。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隶属于某个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其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应批评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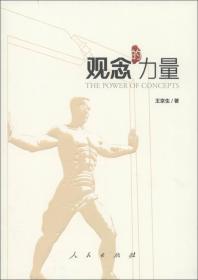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