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的绝命之旅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5.17 3.8折 ¥ 66 全新
库存4件
作者(沙特阿拉伯)阿齐兹·穆罕默德|责编:曹晴|译者:蔡伟良//王安琪
出版社上海文艺
ISBN9787532181179
出版时间2022-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6元
货号1202672218
上书时间2024-06-1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沙特阿拉伯青年作家阿齐兹·穆罕默德生于1987年,曾经发表过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K.的绝命之旅》于2017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次年便入围阿拉伯国际小说奖(亦称阿拉伯布克奖)短名单。阿齐兹·穆罕默德也因此成为该奖项创办以来最年轻的入围作家,而《K.的绝命之旅》也成为该奖项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处女作入围短名单的作品。
《K.的绝命之旅》入围短名单后,许多媒体都对作者进行了采访,在被问到小说主人公K.与奥地利著名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颇为相似,是否在写作上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时,阿齐兹·穆罕默德坦言,他确实喜欢卡夫卡,但是“喜欢一个作家,并不能说明写作中必然会受其影响”。尽管如此,读者在读完《K.的绝命之旅》后很可能会认为作者或多或少受到了《变形记》的影响,而这在小说第一章中的几处表述中亦可得到证明,如“这几天在卡夫卡日记中读到的一句话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或许我还依然受着卡夫卡日记的影响”。
实际上,影响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作品在主题、情节、语言等小说艺术要素上是否做到了极致,或者至少能吸引读者,能引起心灵的互动,引发对相关问题的批判性思考。我想阿齐兹·穆罕默德应该是竭尽努力了,其效果也是出众的,对此作者自己回忆道,对得奖(包括提名)他并不感到意外,在小说还未出版前,出版商就对它抱有极大的期待,并决定推荐参与评奖,且相信获奖的可能性极大。
出版商之所以如此自信绝对有其道理,原因是小说构思的不同一般,主人公处境的非同寻常,以及主人公(抑或是作者)面对现实的无奈而引发的深邃思考。(译序,节选)
【书摘与插画】一觉醒来,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艰难地呼吸,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盯着枕头,枕头上有一块污渍。从此刻自己的呼吸感受判断,这八成是鼻血。我左半撇胡子上的血已经干了,但鼻孔里的血倒是还湿着。我猛然惊醒,抬起头,转瞬间脉搏恢复了平稳。透过窗看到外面太阳的位置,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索性翻了个身躺到枕头的另一边,再次合上眼。
入睡之前,也就是凌晨时分,我记得自己是在看一本书,再往前,在洗热水澡。我曾在书里读到,洗热水澡招人犯困。洗澡前我吃了晚饭,抽了支烟,在几个房间里踱来踱去,把灯开了又关,上了床又下来,起坐漫无目的,与人们每天晚上醒着的时候做的事情相差无几。或许我选今天来只睡两个小时是错误的,但只睡两小时,选在哪天都不对。
乱七八糟的床头柜上的闹钟叫个不停,那尖锐的声音仿佛一根钉子戳进脑袋。
花了几分钟我终于从床上起来,不疾不徐地在脑中回顾自己起得太晚这一事实。小解之后,根据尿液的颜色我估摸着身体是缺水了。我开始刷牙,一直刷到牙龈作痛,以至于都不能确定刷了多久。我又洗了把脸,洗去睡意,也洗掉胡子上和鼻孔里的血迹。我咒骂着那熟悉的铁锈味儿,它像是陈旧回忆燃起的火种,涌入喉咙。
小时候,流鼻血是家常便饭。那时,鼻血滴落到衣服、脚上之前,我可以感受到一股温暖的血液在呼吸道里轻缓地流动。尽管并不疼,但是刚见到鼻血的那一瞬间总是有点害怕。流鼻血这个毛病总是让我在放学后无缘与其他小孩一起玩耍,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尽管我懂得一些止住鼻血的方法,比如在鼻子上端放冰块,或是用一根手指从外面按住偾张的血管,但这片土地上空对我怀有恶意的太阳总有办法让我的鼻血再次流淌。
可现在是冬季,通过窗外的景色我可以肯定。刚刚下过雨,窗玻璃在雨水的作用下折射着阳光。我飞快地穿上衣服,一如往常,这是我对自己起床太晚仅有的补救。刚一出门,又下大雨了。
上车,我转动车钥匙,音乐立马聒噪起来。我像早晨拍床头柜上的闹钟那样使劲地给了收音机一巴掌,让它不再发声。这一路上我脑中一片空白,挡风玻璃上两个雨刷左右摆动,像上了发条的催眠仪器。猛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停车场,这里几乎停满了车,回了回神,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处何方,车停得有些远,我不得不加快脚步。天气寒冷,好似在催我再走快些。
通往塔楼的这漫长几分钟里,我抬起头再三打量,这是一幢很显眼的建筑,从哪个方向都可以很容易地走近它,但入口却十分隐蔽,得找寻一番才能抵达,甚至会让人有那样的感觉:越接近这栋楼越觉得永远都无法进去。
一切都与昨日别无二致,但心中却萌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一切又和昨日截然不同。
刚走到侧门,浓重的油漆味扑面而来,走廊通风不佳,这种味道常年都有。走廊尽头有一部自动扶梯,站在第一级望不到最后一级,它不间断地向高处运行着,仿佛能载你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人们大多不喜欢乘自动扶梯,而径直走向电梯厅,在那儿等乘电梯。早晨快过去了,电梯厅只有我一个人,可无论人多人少,等电梯的时长都一样。
能透过电梯间的大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空地:一个无人游玩的花园,几把木椅,抽烟的人总是坐在那里。根据外面抽烟的人数我可以推断出自己迟到了多久。谁也不会一到这里就下来抽烟,一定得先上去露个脸,证明他已经来了。说不定这儿的玻璃窗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让等电梯的人能看到楼下的那些景象。之后,电梯一到,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里面挤,似乎连再多看一秒窗外的风景都无法忍受。
我走进电梯,按下“10楼”,电梯门保持了一会儿打开状态便自动关闭了。我看了下表,又确认了一下裤链是否拉好——我时常忘记拉它,然后像是第一次关注自己的穿着一般,从上到下自我打量了一番。
十楼到了,我立刻双手插兜,试图表现出一副对自己上班时间底气十足的样子。我保持着这副姿态穿过大理石走廊,推开科室的玻璃门,之后,在一排排办公桌之间狭窄的过道里穿行,尽量不撞到任何一张桌子,也避免同人打招呼,最后终于在电脑前坐了下来,从显示屏上撕下那张黄色便笺,我根本不需要看就知道上面的字是谁写的。随后向坐在我旁边的老头问了声早安,我乏力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猥琐。这几天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的一句话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场突如其来的谈话展开时口水从嘴中飞溅而出,像是凶兆。”这时我听到一个苍白的声音回应我的问早,便意识到这又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工作日,我这才发现,从睡醒一直到现在,我好像刚刚回过神来。
一看屏幕我就感到一阵恶心,或许我依然受着卡夫卡日记的影响。沉迷卡夫卡会让你摊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一直以来,无数个清晨里我都会或轻或重地感到恶心乏力。记得我刚步入青春期时就有这种感觉了,它就像一位常客,或许有些事情总在起初时更明显。
上六年级的时候,早晨我被叫起来去上学,那时我总会在卫生间待上好几分钟,脑袋靠着马桶的抽水箱,刚要打盹,母亲催我赶公交的粗暴敲门声就会把我惊醒。当时,为了不去上学我找来各种借口搪塞她,虽然我撒谎时母亲从我的语气中就能听出我在瞎编,但恶心和乏力却不可能全是装出来的。“你就忍一下吧。”母亲答道,因为她当时坚决而机械地重复着“忍”这个词,所以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时候,我总得不断地向母亲述说我的病症,才能不让她觉得我没有什么实际病症就向她告饶,或让她以为我没有尽力去忍。
到了上中学的第一年,有一次,家里人一致同意带我去看医生。当时是父亲陪我一起去的,诊室很小,至少当时在我看来是这样。医生的一双手又大又糙,他一言不发地用双手检查我的身体,说一切都很正常,然后神经质地洗手,擦干。好像他对于诸如此类的病症一没时间,二没兴趣。随后医生绕过办公桌,打算坐下,白大褂蹭过墙时发出恼人的沙沙声,比一般情况下衣服擦过墙的声音重得多。
我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和我父亲坐在两张相对的椅子上,脚几乎要碰到一起。鸦雀无声,我们只听得见医生重重的落笔声,他在病历本上写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情况无须就医。突然父亲把他的脚往回收了收。若非当时父亲同我一道去看了医生,这次就医经历是不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
“一切都很正常。”医生重复道,语气似在暗示因为我浪费了他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有时间也有兴致来惩罚我了。“他现在这个年龄,细胞在生长期,分裂得要比成年人快,这才使身体能够不断成长。”随后医生放下笔,将一只手搁在另一只上面,仿佛以此来表达他的嫌恶。“如果每个青少年都因为有些恶心或者乏力就来看病,诊室会被挤满,我们就不能去诊治重病患者了。”在他眼中我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男孩,有一点小毛病就叫苦不迭,说不定他已经看出长大以后的我会是一个对自己的职业牢骚满腹的人了吧。
医生继续说着,刚劲有力的前臂在桌上蹭来蹭去,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正克制着某些更使劲的动作。至于父亲,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走神,一副男人得知自己精子活力不足之后的表情。不知医生说到哪儿的时候,他看也不看我就表示同意说:“是的,是他夸张了。”这就是父亲说的唯一一句话,语气极为平静,你甚至会觉得就算我得了什么大病他也无所谓。
它的控制。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人会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之后意识到,痛苦就是痛苦,一旦第一次悟出这个事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商品简介“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绝症患者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模式,其思其言纵然有悖常理也该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
罹患绝症的年轻人K.讲述着得病三十九周以来自身和周遭发生的一切,描画病人与病态,其身染重病却流露出更为复杂的思绪,以此映射出同辈人内心深处的怨、恨和无奈……
小说对沙特阿拉伯社会作了精准细致的多角度解剖,呈现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青年一代强烈的主体意识。
作者简介
阿齐兹·穆罕默德(1987—)沙特阿拉伯作家。以诗歌和短篇小说开启文学创作生涯。首部长篇小说《K.的绝命之旅》使他成为阿拉伯布克奖(又称阿拉伯国际小说奖)最年轻的短名单入围者,亦是第一部入围的处女作。
目录
《K.的绝命之旅》无目录
内容摘要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绝症患者的生命进入倒计时模式,其思其言纵然有悖常理也该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
罹患绝症的年轻人K.讲述着得病三十九周以来自身和周遭发生的一切,描画病人与病态,其身染重病却流露出更为复杂的思绪,以此映射出同辈人内心深处的怨、恨和无奈……小说对沙特阿拉伯社会作了精准细致的多角度解剖,呈现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青年一代强烈的主体意识。
主编推荐
··穆罕默德——阿拉伯语文学新势力代表,阿拉伯布克奖短名单最年轻入围者
·首部入围阿拉伯布克奖短名单的处女作
·被誉为阿拉伯当代的《变形记》
·全景式解剖社会弊病,多方面刻画社会生活
·穿插作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欧内斯特·海明威、苏珊·桑塔格、村上春树、谷崎润一郎等名家作品的独到观点,与主人公的心境完美融合
·生动描绘年轻人内心的躁动,呈现出伴随着互联网和新技术成长的青年一代强烈的独立意识
·趣味盎然又感人肺腑,反讽中展现作家的悲悯
·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前会长蔡伟良教授倾力打造译本
精彩内容
一觉醒来,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艰难地呼吸,揉了揉眼睛,睡眼惺忪地盯着枕头,枕头上有一块污渍。从此刻自己的呼吸感受判断,这八成是鼻血。我左半撇胡子上的血已经干了,但鼻孔里的血倒是还湿着。我猛然惊醒,抬起头,转瞬间脉搏恢复了平稳。透过窗看到外面太阳的位置,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索性翻了个身躺到枕头的另一边,再次合上眼。
入睡之前,也就是凌晨时分,我记得自己是在看一本书,再往前,在洗热水澡。我曾在书里读到,洗热水澡招人犯困。洗澡前我吃了晚饭,抽了支烟,在几个房间里踱来踱去,把灯开了又关,上了床又下来,起坐漫无目的,与人们每天晚上醒着的时候做的事情相差无几。或许我选今天来只睡两个小时是错误的,但只睡两小时,选在哪天都不对。
乱七八糟的床头柜上的闹钟叫个不停,那尖锐的声音仿佛一根钉子戳进脑袋。
花了几分钟我终于从床上起来,不疾不徐地在脑中回顾自己起得太晚这一事实。小解之后,根据尿液的颜色我估摸着身体是缺水了。我开始刷牙,一直刷到牙龈作痛,以至于都不能确定刷了多久。我又洗了把脸,洗去睡意,也洗掉胡子上和鼻孔里的血迹。我咒骂着那熟悉的铁锈味儿,它像是陈旧回忆燃起的火种,涌入喉咙。
小时候,流鼻血是家常便饭。那时,鼻血滴落到衣服、脚上之前,我可以感受到一股温暖的血液在呼吸道里轻缓地流动。尽管并不疼,但是刚见到鼻血的那一瞬间总是有点害怕。流鼻血这个毛病总是让我在放学后无缘与其他小孩一起玩耍,在烈日炎炎的日子里更是如此。尽管我懂得一些止住鼻血的方法,比如在鼻子上端放冰块,或是用一根手指从外面按住偾张的血管,但这片土地上空对我怀有恶意的太阳总有办法让我的鼻血再次流淌。
可现在是冬季,通过窗外的景色我可以肯定。刚刚下过雨,窗玻璃在雨水的作用下折射着阳光。我飞快地穿上衣服,一如往常,这是我对自己起床太晚仅有的补救。刚一出门,又下大雨了。
上车,我转动车钥匙,音乐立马聒噪起来。我像早晨拍床头柜上的闹钟那样使劲地给了收音机一巴掌,让它不再发声。这一路上我脑中一片空白,挡风玻璃上两个雨刷左右摆动,像上了发条的催眠仪器。猛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停车场,这里几乎停满了车,回了回神,我才反应过来自己身处何方,车停得有些远,我不得不加快脚步。天气寒冷,好似在催我再走快些。
通往塔楼的这漫长几分钟里,我抬起头再三打量,这是一幢很显眼的建筑,从哪个方向都可以很容易地走近它,但入口却十分隐蔽,得找寻一番才能抵达,甚至会让人有那样的感觉:越接近这栋楼越觉得永远都无法进去。
一切都与昨日别无二致,但心中却萌生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一切又和昨日截然不同。
刚走到侧门,浓重的油漆味扑面而来,走廊通风不佳,这种味道常年都有。走廊尽头有一部自动扶梯,站在第一级望不到最后一级,它不间断地向高处运行着,仿佛能载你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人们大多不喜欢乘自动扶梯,而径直走向电梯厅,在那儿等乘电梯。早晨快过去了,电梯厅只有我一个人,可无论人多人少,等电梯的时长都一样。
能透过电梯间的大玻璃窗俯瞰着外面的空地:一个无人游玩的花园,几把木椅,抽烟的人总是坐在那里。根据外面抽烟的人数我可以推断出自己迟到了多久。谁也不会一到这里就下来抽烟,一定得先上去露个脸,证明他已经来了。说不定这儿的玻璃窗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让等电梯的人能看到楼下的那些景象。之后,电梯一到,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里面挤,似乎连再多看一秒窗外的风景都无法忍受。
我走进电梯,按下“10楼”,电梯门保持了一会儿打开状态便自动关闭了。我看了下表,又确认了一下裤链是否拉好——我时常忘记拉它,然后像是第一次关注自己的穿着一般,从上到下自我打量了一番。
十楼到了,我立刻双手插兜,试图表现出一副对自己上班时间底气十足的样子。我保持着这副姿态穿过大理石走廊,推开科室的玻璃门,之后,在一排排办公桌之间狭窄的过道里穿行,尽量不撞到任何一张桌子,也避免同人打招呼,最后终于在电脑前坐了下来,从显示屏上撕下那张黄色便笺,我根本不需要看就知道上面的字是谁写的。随后向坐在我旁边的老头问了声早安,我乏力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猥琐。这几天在卡夫卡的日记中读到的一句话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一场突如其来的谈话展开时口水从嘴中飞溅而出,像是凶兆。”这时我听到一个苍白的声音回应我的问早,便意识到这又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工作日,我这才发现,从睡醒一直到现在,我好像刚刚回过神来。
一看屏幕我就感到一阵恶心,或许我依然受着卡夫卡日记的影响。沉迷卡夫卡会让你摊上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过一直以来,无数个清晨里我都会或轻或重地感到恶心乏力。记得我刚步入青春期时就有这种感觉了,它就像一位常客,或许有些事情总在起初时更明显。
上六年级的时候,早晨我被叫起来去上学,那时我总会在卫生间待上好几分钟,脑袋靠着马桶的抽水箱,刚要打盹,母亲催我赶公交的粗暴敲门声就会把我惊醒。当时,为了不去上学我找来各种借口搪塞她,虽然我撒谎时母亲从我的语气中就能听出我在瞎编,但恶心和乏力却不可能全是装出来的。“你就忍一下吧。”母亲答道,因为她当时坚决而机械地重复着“忍”这个词,所以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时候,我总得不断地向母亲述说我的病症,才能不让她觉得我没有什么实际病症就向她告饶,或让她以为我没有尽力去忍。
到了上中学的第一年,有一次,家里人一致同意带我去看医生。当时是父亲陪我一起去的,诊室很小,至少当时在我看来是这样。医生的一双手又大又糙,他一言不发地用双手检查我的身体,说一切都很正常,然后神经质地洗手,擦干。好像他对于诸如此类的病症一没时间,二没兴趣。随后医生绕过办公桌,打算坐下,白大褂蹭过墙时发出恼人的沙沙声,比一般情况下衣服擦过墙的声音重得多。
我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我和我父亲坐在两张相对的椅子上,脚几乎要碰到一起。鸦雀无声,我们只听得见医生重重的落笔声,他在病历本上写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我的情况无须就医。突然父亲把他的脚往回收了收。若非当时父亲同我一道去看了医生,这次就医经历是不会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的。
“一切都很正常。”医生重复道,语气似在暗示因为我浪费了他的时间,所以他现在有时间也有兴致来惩罚我了。“他现在这个年龄,细胞在生长期,分裂得要比成年人快,这才使身体能够不断成长。”随后医生放下笔,将一只手搁在另一只上面,仿佛以此来表达他的嫌恶。“如果每个青少年都因为有些恶心或者乏力就来看病,诊室会被挤满,我们就不能去诊治重病患者了。”在他眼中我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小男孩,有一点小毛病就叫苦不迭,说不定他已经看出长大以后的我会是一个对自己的职业牢骚满腹的人了吧。
医生继续说着,刚劲有力的前臂在桌上蹭来蹭去,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正克制着某些更使劲的动作。至于父亲,则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走神,一副男人得知自己精子活力不足之后的表情。不知医生说到哪儿的时候,他看也不看我就表示同意说:“是的,是他夸张了。”这就是父亲说的唯一一句话,语气极为平静,你甚至会觉得就算我得了什么大病他也无所谓。
它的控制。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人会在一个极其普通的时刻之后意识到,痛苦就是痛苦,一旦第一次悟出这个事实,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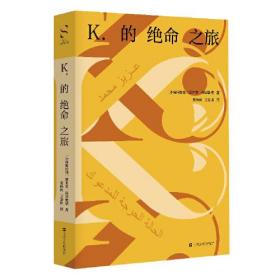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