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土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8.83 2.8折 ¥ 68 全新
库存5件
作者戴寅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
ISBN9787530220924
出版时间2021-06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68元
货号1202387015
上书时间2024-06-0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商品简介
《中土》是清史学者戴寅的长篇历史小说新作。本书以历史时间为叙事轴线,书写了晚清七十年中土儿女御侮图强的民族史诗。自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至奕?、曾李左张等主持洋务运动,自北洋海*军的创建与覆灭,至刘铭传、唐景崧等保卫台湾家园,当古老的中国在苍茫无际的暗夜中蹒跚前行时,士人报国之心从未泯灭。本书尤其以浓墨重彩的篇幅回望近代中国海防的艰辛草创与苦难命运。中*华海*军,南洋、北洋,数十年血泪之凝聚,毁于一旦。士大夫救国,三十年奋发,三十年艰辛,三十年坚忍,两代人,前亡后替,摧而不折,孤而不拔,辛苦经营,瞬间湮灭。然中土犹存,中*华文明犹存,中国人的精神犹存……
作者简介
戴寅,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后就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并留校任教。1987-1990年就读西澳大利亚莫铎大学博士研究生,后在海外任教和工作。2004年至今,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
目录
《中土》无目录
内容摘要
《中土》是清史学者戴寅的长篇历史小说新作。本书以历史时间为叙事轴线,书写了晚清七十年中土儿女御侮图强的民族史诗。自林则徐领导虎门销烟,至奕?、曾李左张等主持洋务运动,自北洋海*军的创建与覆灭,至刘铭传、唐景崧等保卫台湾家园,当古老的中国在苍茫无际的暗夜中蹒跚前行时,士人报国之心从未泯灭。本书尤其以浓墨重彩的篇幅回望近代中国海防的艰辛草创与苦难命运。中*华海*军,南洋、北洋,数十年血泪之凝聚,毁于一旦。士大夫救国,三十年奋发,三十年艰辛,三十年坚忍,两代人,前亡后替,摧而不折,孤而不拔,辛苦经营,瞬间湮灭。然中土犹存,中*华文明犹存,中国人的精神犹存……
主编推荐
清史学者戴寅长篇历史小说新作
一部晚清七十年中土儿女御侮图强的民族史诗
回望近代中国海防的艰辛草创与苦难命运
山河破碎的斑斑青史里,高昂着中国人的精神
“国可灭,天下不可灭。中土不是地,是东方古代遗存,中国不以王朝维系,不以哪个民族维系,只以自身文明维系。”
精彩内容67
西太后慈禧的六十大寿是光绪二十年阴历十月十日,西历1894年11月7日。
仗要打,生日也要过,沿街戏台、彩舫、花亭、牌楼从东华门修到颐和园。不过,西太后心里是真别扭,好端端一个节庆,宣了战,过什么过!
西太后一直不想打这场仗,紧着让李鸿章中外调停,但没管用。东洋日本着实可气,挑这个时候,非要打。
慈禧原来担心打仗冲了生日,现在已经打了,又担心战局。北边,日本人从高丽国渡鸭绿江过来了;南边,日本人从海上过来了,外面的局势很不妙。
她问醇亲王:“月前水师打了场恶战,现在还在海里吗?”
醇亲王说:“回禀皇太后,水师现在不在海里头,正在港内修理军舰。”
慈禧问:“东洋的水师在海里吗?”
“在。”
慈禧说:“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恶战,船都打坏了,它们能出来,咱们怎么就不能出来呢?”
醇亲王说:“日本有厂子,修得快,修了五日,给修好了。我们机器不全,单只修理打坏的巨舰船锚,就已太费事,要两个月才成。”
慈禧听明白了,点点头,说:“说了归齐,还是技不如人哪。七王爷,我看这水师一时半会儿出不去,要是东洋日本没人拦着,在大沽口一上岸,可就离咱们北京城不远了。”
“太后所虑极是。”
“唉。”慈禧叹口气,没说什么。
慈禧说不出来什么,她在想以后。大沽口离北京不到三百里,洋人以前不是没来过,进了北京烧了圆明园,这次来的是东洋人,这甲午年的事情,闹大了。
那天白日,没有多说,慈禧想了一天。到了晚上,她对着储秀宫掌案的李莲英说出一句话:“这东洋人,他究竟想问大清要什么?”
李莲英不知道,心想:八成什么都想要。
国家大事,他不敢吱声儿。
慈禧其实没有问他,是在问自己,又问:“要不,找个人去问问?”
李莲英何等机灵,得,老佛爷想停战。
这件事,一直没有再提。到了来年二月,大过年的,威海卫被日本人占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领兵的全自尽了。紫禁城里突然气氛阴沉,乾清宫和储秀宫里面好像都出了事,太监和宫女们都不愿意往那边去,里面出来办事的全都低着头,好像谁也不认识了,问话,一言不发,战战兢兢,脸色死灰,必是全都受了惊吓。
皇上和太后打起来了。
那天过午,李莲英正往太后屋里端漱口水,刚要掀帘子进门,皇上忽然驾到,急匆匆迈大步进了门,直奔太后那屋。李莲英吓得赶紧跪,光绪没看见他,直接进了太后的屋。李莲英不敢进屋,端着漱口水在外面跪着,心想坏了,皇上圣驾,事前无人来通告,自己径直来了,这还得了!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里面太后高声训斥:
“迁都!社稷所在,国本所在,我朝根基所在,说迁都就迁都!反了你了,你迁得了吗?我朝开国,明朝就迁都,它迁了再迁,有何用处,结果怎样?祖宗的基业就在这北京城。你们都走,我就守着这片繁华,守着大清,哪儿也不去!”
太后天威震怒,李莲英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当晚,翁同龢奉诏乾清宫议事。到了宫里,他看见皇上脸色铁青,迈大步在大殿里转,从这头再转到那头,再往回转,一边走一边高声痛骂,转来转去,骂来骂去,突然泪流满面,失声号啕。见了翁同龢,他抬起手,却说不出来话。翁同龢见光绪这样,很悲痛,跪在地上跟着皇上哭,说:“皇上啊,皇上,龙体要紧。”
师生二人哭了半天。光绪哭的是王朝的气数,太后偏执,正在把国家断送,自己眼看着,却只能干着急;翁同龢猜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哭的是皇上抗战的苦心。
太后的心思,主战的朝臣们早就看出来了。翁同龢进宫之前已经想好,趁太后还没有动静,劝皇上赶快离京西去,坐镇长安,把战争打下去,留得青山在,不怕丢北京。削弱了倭寇,赶出去,再图中兴。可是现在看来已经晚了。翁同龢接着哭,哭国运在劫难逃,天违人愿。当夜,乾清宫里,君臣痛哭,哭声是王朝末路的哀鸣。大清立国二百多年,一时断送。
太后坚决不离开北京城。二月初,已经派人去日本试探媾和。当国者既无定见,又无恒心,既为保国而战,怎能想停就停,实在可悲。一人心性,其他全然不顾,怕了日本,难道不怕国内士人百姓吗?有此断送,自此以后,你的朝,你的国,在中土,还立得住、留得住吗?
消息传出,辽东、辽南为山河奋战之士一片哀鸣,恨声遍野。
1895年4月,清廷遣使去日本谈判议和。日本不谈,指名必须枢臣,李鸿章或者翁同龢去谈。
翁同龢是坚决不去,死也不去。
李鸿章奉旨议和,不动声色,谢过了皇恩,把钦差亲送出门。华、洋幕僚在后院里站了一大群,都在等他。
李鸿章回来,见了众人,说天快黑了,大家先回去歇着,一切明日再说。
魏经见中堂在书房里半天没出来,端一碗热汤面进屋去瞧瞧,见李鸿章坐在屋正中,闭着眼,垂着头,衣襟上湿一片。魏经吓一跳,这是睡着了还是……
李鸿章没睡觉,知道是魏经,问他:“金陵大小姐和姑爷有信函吗?”
“有有,前日来信,说少奶奶又有喜了。”
“好,好,好。这才好。老魏,你把门掩上,我跟你说个事情。”
魏经关门,心里嘀咕,这是怎么了,跟我单独说事情。李鸿章让魏经搬把椅子也坐下,又把魏经吓一跳,以前没在这屋坐过。魏经坐在椅子沿上,仍然是上身直立垂手,还是平时服侍主人的样子。几十年来,他头一次在中堂面前坐,不习惯。
李鸿章说:“先给你讲个故事。”
魏经听了直出汗,老大人今天关上门,要给我魏经一个人讲个故事。刚才钦差来过,然后中堂独自坐在书房,衣襟是湿的,这是出了什么事呀?
李鸿章对他说的是一段陈年的旧事:
江苏阳湖有个人,是个有本事的,有本事却中不了举,就去曾国藩那里帮忙。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正在和太平军打仗,此人初入幕府,没人把他放在眼里,就让他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人在南昌一带转了一圈儿,回来了,跟曾国藩说,湘军主力周凤山不会打仗,换人吧。曾国藩平素最讨厌的就是书生自大,空口议论,不以为意。不到十天,周凤山兵败,曾国藩赶紧把人家请来求教。那人讲了一番道理,曾国藩心服口服。自此,言听计从,重用了他。
咸丰六年(1856)七月二十一日,暑天溽热,蝉声彻夜,曾国藩在正房里睡觉,那人睡在厢房。初鼓之后,都睡不着,二人同时起身,去到庭院里散步。深更半夜,黑咕隆咚,两人碰了面,都吓一跳。巧遇,也不能在大半夜自家的院子里巧遇呀,于是两人同声发问:“有什么事吗?”
他们没事,就坐在外面的石凳上夤夜闲谈,没想到谈出一段惊天的话。曾国藩当时是两江总督,那天他很担忧,对那人说:“京中来人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说的是北京城里现在太乱,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困苦,北京怕是要出事。
那个人也很担忧,他担忧的不是京城,是大清国。
李鸿章说到这里,看着魏经,见他僵直坐在椅子边儿上,就说:“老魏,你坐好了,下面的话要坐好听,不然会掉下来。”
“老大人,我坐好了。”
李鸿章接着讲。
那个人对曾国藩说:“天下治安久矣,然合久必分。纵然当今皇上是明主,一时还不会土崩瓦解,但不出五十年,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天下大乱。”
曾国藩不相信,说:“我朝君王皆英主,不至于如此吧。”那个人说:“君王固然英才天纵,然我朝创业,太过于容易,天下,是随手捡来的,机运巧合而已,又杀戮太重,好事盖不住坏事,只要做过恶,天道就不容。后世君王德泽也不能扭转。”
曾国藩听他这样讲,就说:“那我还是早死好,别见到那天。”
曾文正公过世二十年后,那个人也死了,赶在前年,甲午开战前一年。
李鸿章的故事讲完了。魏经早从椅子上站立起来,汗如雨下。
“中堂!咸丰六年距今四十年,您是说,大清的气数快……”
李鸿章说:“老魏,本爵活了这把年纪,没看见天道,你见过吗?”
魏经紧摇头,说:“在下也没瞧见过。”
李鸿章说:“也实在不知何为气数。朝廷自有为自己造就的前路,不敢揣测。何为天道,老夫寻求半生,尚未见到。或许天道绵长,非一世可见,故只由史家论说。无论怎样,九州中土,人在地在人心在,世代不灭。这个,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倒是让我看到了。今日朝廷下旨,要我去办一趟差,这趟差是我的末路。任事者不能人人善终,你跟着我,从今往后没有好处。多年以来,我没有厚待你,你也从无怨言,我让人在你的老家置些田产,修了一座院子,你回家去好好过生活吧。”
魏经走出书房让大风吹出一脸眼泪,心想:中堂以后也许可以过几天清静日子了。
魏经没有回家乡,这些年,一直想回的家乡早已清冷无人,陌生之地,回不去了。
1901年1月17日,李鸿章在贤良寺临死之前,已经给穿上了寿衣,眼睛却睁着,直视庭宇,张着嘴却说不出来话。匆忙赶来的周馥见状痛哭失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心不下,不忍离去呀?未了的事我等可以办,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目张口动,眼中有泪。这回,连魏经也猜不出他想要说什么。
张佩纶败军之将、戍边之徒,见状悲愤交加,自己也有所领悟:
唐景崧给恭亲王看的扇面,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无定见,复少恒心,说的是国人的短处,入木三分,其深其透,超乎国人的所知,连中堂和自己,都不能免。当初看到这句话,中堂出了一身冷汗,说:“切中其要,愧疚欲死。”但还是没有悟到,刚与柔,不是术,是道。一国一人,风骨正气,是大道,得道者昌,失道者灭。瞻前顾后,避小害而丧大义,一味遇刚则柔,反会招来人心离散王朝崩塌之大害,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以为身担国运,要做不怕世人非议的忠臣,逼得就剩下一条拼命的路,却还不去走,不知道一国垂死,要拼死一争,以死战养民气,或可复生的道理,以至于后来人心不固,国事离析。
中法之战,无定见,战不战,和不和;中日之战,无恒心,可再战,而不战,不可和而求和,以至于亡朝鲜,割台湾。之前,琉球一事,一步失足,以至于此。不救琉球,就是连自己都不想救。从此中土离心,外国轻贱,清朝的气数,在那一刻,就已经尽了。在后来的战争中,民气和铁甲,不知民气是铁甲中的铁甲,这虚与实之间的奇正,全都错乱。败,不是败在谓之“实”的铁甲和利炮,而是败在了国人自己的手里。
中堂事后不会不去想这一生,临终弥留的此时,一定幡然醒悟,哭都哭不出来此生的遗恨。
张佩纶想到此处,走上前,弯身附在李鸿章耳边轻声说:
“老大人一世,以身许国,持风雨飘摇之政,小心翼翼,一味忍让。背书骂名仍不敢轻动,卧薪尝胆,步步退让,怕的是灭国,图建东山之起,只有琉球一次机会,却未能举国奋力一击,一步之差,乃至如今。此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马关之约,国之奇耻,代西宫受过,当世英名,亦随国运崩坏,非百年以后不能脱干系。此为英雄之劫,报国之士,多不能免。国难之中,前史多有,后世不绝,非一人可自持之所能。中堂此生,上可对天,下可照土,何必对人?此去,大江东去浩荡,已无所憾!”
李鸿章耳闻知音,立刻流下一行清泪,内心明澈,已入化境,闭目气绝。
当初清廷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割,血淋淋。唐景崧立即在台湾宣布独立,建立台湾民主国,摆脱条约的限制就可以继续对日战争,年号“永清”。
“永清”二字,既痛彻,也迷茫,永世大清国何在?
然而,国可灭,中土不可灭。
台民宣示公议:“民主国尊奉正朔,遥作屏藩。现在代表天下,不代表朝廷,坚持对日战争。”
唐景崧任大总统,全台筹建义军,丘逢甲总办全台民兵,刘永福统领台南,吴汤兴统领台北,全民成军,保卫台湾。
林朝栋在中法战争中毁家卫国死战,族人无分老少男女,多有战殁者,刘铭传把台湾的樟脑生意交给林家去做,雾峰林氏已成巨贾。此时,他在乡里再募义军,宅院的里里外外、四周园林,放满煤油桶,准备打到最后关头,点火焚烧家园,率军进山。
日本近卫师团去接管台湾的同时,台湾民主国发布宣言,公告中土:“今已无天可吁,无兵来援,台民只有独自死战一途。事平之后,请命中土,再做办理。”
话,说得清楚,你们不打,我们打,打完了再回归。
随即台湾爆发全面抗日战争。
台湾民众,举家迁往大陆的很多,他们在轮船上看见,时有大陆的船只东行。商船民船向台湾航行,船上布衣韦带青年,身背长弓,凛然站立船头,海风吹起衣裾,破浪而去。
乘客目送背影,知道,这是大陆人去台湾参战,令人不禁追忆汉高祖大风之歌。
台湾抗战,从1895年打到20世纪初,从旧时代打到新时代。
唐景崧书生报国,慷慨激切,在战场上却没有打过胜仗,注定不得不败、不得不逃。日本占领台湾,他又往广西老家跑,怏怏渡海归乡。清廷把眼一闭,不追究他自立国家的大罪,随他自去安度余年。走下传奇人生舞台,他又成一介书生。
此人一生,注定不会寂寞,他别出心裁,在桂林榕湖搭起个戏班子,叫“桂林春班”,唱一种没有人听过的戏,是他给自己新造的,把桂北的地方戏、皮黄腔和桂林话一混、一掺、一变、一编、一写,创立出一个剧种——桂剧。从此,终日默然,写戏听戏了。其内心深处,无人可知。不过,家园五美堂中有座“听棋亭”,上刻一副自书的对联:
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
多少棋中妙手何堪束手让人先
后世亭前一年四季,常有观者流连体味,猜度此中的壮烈与迷离。
士人报国,已尽心力,生平之志或有不能遂,已无话可说,飘然遁去自造小蓬莱一隅,遗世独立做个看客。旧日英雄以此谢幕,天下舞台,让给新生后进。
西风吹过中土,挟带崭新的学问更新世界,文明的利刃划破邦国,越南、朝鲜、中国,在西风中个个烽烟四起,王朝覆灭,南北分国,陆岛离析,众生各寻前路。
国可灭,天下不可灭。中土不是地,是东方古代遗存,中国不以王朝维系,只以自身文明维系。文明,是根本,深埋于其土,西风焕新物貌,吹它不散,只在自我遗忘中消亡。
当年,北洋海军覆灭的消息传到恭亲王府,他已经是个闲人,天快黑了,还在庭院廊下斗蛐蛐。
暮光之中,他站起身,背起手看看天,天上出现星月,又望着地上正德年间的蛐蛐罐,自问:中华海军,南洋、北洋,数十年血泪之凝聚,毁于一旦。士大夫救国,三十年奋发,三十年艰辛,三十年坚忍,两代人,前亡后替,摧而不折,孤而不拔,辛苦经营,瞬间湮灭。此中旧事,后日无所知。既然败,都是错,或可讥,或可忘,前人已去,何虑人言。一百年后,西风浩荡,物是人非,此星此月之下,中土人人或已奋发?天下立身者,可担当激烈如是?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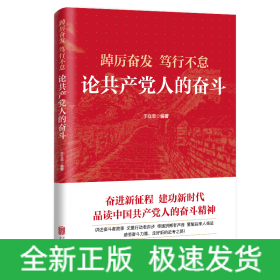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