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求高贵的修辞术——柏拉图《高尔吉亚》讲疏(1957)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1.83 4.8折 ¥ 8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责编:李安琴|总主编:刘小枫|译者:王江涛|口述:(美)施特劳斯|整理:(美)斯托弗
出版社华夏
ISBN9787522204185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88元
货号31679455
上书时间2024-06-0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施特劳斯(LeoStrauss),犹太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政治哲人,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曾获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施特劳斯是由德至美的流亡哲人,在美国学术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20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死后却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的重要哲人。施特劳斯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他不仅以自己的学述对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前人的深刻解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即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这一点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西方学界的未来走向。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将整个西方思想史纳入其学问织体中,展开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身后的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并在学界引发了激烈的政治争议。自本世纪初开始,刘小枫教授陆续将施特劳斯的作品引入中国,久积而成规模,继影响北美学界之后,又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学界的学问方向:绎读经典在某些学人当中已蔚然成风。
目录
目 录
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英文编者前言
编订说明
第 一 讲 导论
第 二 讲 高尔吉亚部分(447a-452d)
第 三 讲 高尔吉亚部分(452d-458e)
第 四 讲 珀洛斯部分(458e-468e)
第 五 讲 珀洛斯部分(468e-480d)
第 六 讲 珀洛斯、卡利克勒斯部分(480d-486d)
第 七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6d-488a)
第 八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88a-493d)
第 九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4a-d)
第 十 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4e-499b)
第十一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499b-505e)
第十二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5b-513d)
第十三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08c-516c)
第十四讲 卡利克勒斯部分(516d-520e)
第十五讲 高尔吉亚神话(521至结束)
内容摘要
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讲授过两次柏拉图《高尔吉亚》研讨课,第一次是在1957年冬季学期,第二次是在1963年秋季学期。1963年讲稿的中译本业已问世,与之相比,这本1957年的讲稿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更完整,讲完了整篇对话,而1963年讲稿不包括《高尔吉亚》结尾的神话部分。第二,1963年讲稿的基本问题意识是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挑战下,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而1957年讲稿则以教条主义与怀疑主义为背景,探讨柏拉图如何思考哲学本身的意义。第三,施特劳斯在两次讲稿中对卡利克勒斯性格的分析有巨大差异。卡利克勒斯这一人物形象,充分说明修辞术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如果说整部《高尔吉亚》可以看作对修辞术的审查,那么,这一审查不仅批评了智术式的修辞术,还指向一种哲学式的修辞术,它可以沟通、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从而为哲学提供了真正的辩护。
精彩内容
第一讲导论[节选]所有的哲学思考都始于这种洞穴意识。它是唯一不武断的哲学开端。笛卡尔以普遍的怀疑为开端,它派生于真正的和绝对的开端。因为笛卡尔必须证明,我们关于天空和大地的知识不可靠。但是,假如要证明这一点,你就得以别的东西为前提:以关于天空、大地以及二者之间事物的所谓的知识为前提。这样,以洞穴为开端就是唯一显而易见的开端,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所有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天空、大地以及二者之间的事物被普遍永恒地给予。它们对我们而言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它们并非真正显而易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人的处境会像这样。这个开端对我们而言不可回避,而且是唯一不武断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绝对的开端,但这个开端并未指示绝对知识或关于绝对之物的知识。它只是无可逃脱。柏拉图为此又发明了一个词。我们把洞穴看作天空、大地以及二者之间的东西,柏拉图把我们的这一洞穴意识称为pistis,希腊文的意思是信念(trust)——盲目的、不可避免的信念。我们生活在派生的、有条件的、就其自身而言并非可理解的世界之中。我们十分肯定地知道一棵树是一棵树;但为什么它是一棵树,这是一棵树意味着什么——困难从这里开始。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它使最终被给予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但这个世界本身比被给予的东西更难认识。我们仿佛上下颠倒地生活着。关于我们处境的每一个说明(explanation),或关于我们处境的每一种解释(interpretation),都缺乏我们对该处境本身的意识所拥有的那种强制力。
但是,我们生活在洞穴之中这一事实并未充分说明人的处境。察觉到我们生活在洞穴之中才是哲学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并非总是得到满足。察觉到我们生活在洞穴之中要求我们付出某种努力。首先,我们生活在相信(belief)中,相信那些关于整全的种种可疑意见是真实的;我们生活在相信中,相信那些声称能解答整全之谜的种种意见是真实的。这些相信不具有信念(trust)的性质,不是盲目的、必然的信念。我们不是被迫接受这些“相信”,它们缺乏那种初始信念所特有的强制力。这些意见值得怀疑。换言之,我们首先生活在——再用个柏拉图的术语——信念和影像的混合体之中。你们记得线喻(thedividedline)及其四种知识类型。我现在谈的只是较低的两段,其中一段被称作信念,另一段被称作影像。影像不像信念具有强制力。例如,假如人们说“白色神牛”,那么牛是否神圣乃是可怀疑的,而牛是白色的这一点却不用怀疑,除非是在教室里。这就是柏拉图通过区分不同知识类型所表达的含义。哲学的开端就是意识到这一初始信念与影像的基本差异;[7]哲学的开端就是决心严肃地对待这一差异——事实上,如此之严肃,以至于我们打算将其运用到所有事物上。
但是,怎么可能生活在这一基础上呢,即在如下看似合理的假设的基础上:问题总是比解答更显而易见?难道好人的问题不总是比这问题的解答更显而易见吗?也许可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兴许无知之知,按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意思,暗示了——不,构成了——关于好生活的问题的答案。基于人的处境,基于我们都是派生的并且生活在派生的世界之中,除了寻求非派生之物,或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那么我们必定变得自吹自擂、自以为是,变成那种自称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的人,要不然就轻率浮躁、有失稳重,对待严肃的事物不严肃认真。可倘若如此,倘若哲学显然由人的处境所规定,那么,这对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以及社会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试着说,那的确是柏拉图《王制》的主要功能:展示哲学的必然性会对个人的和群体的人类生活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换言之,政治哲学,包括道德哲学在内,可能会导向那些原则上的终极答案,即便关于整全的宇宙论或问题也许不允许有终极答案。无论如何,这似乎就是柏拉图的主张。我们可以把这观点表述如下:种种哲学问题通过我们作为人类的处境强加给我们。但是,没有哪个哲学问题像关于好生活的问题、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那样,如此深刻地根植于我们作为人类的需求之中。
这个问题总是在被我们从属的社会提出之前就得到了回答。我们所有人从小到大都被告知要这样做、要那样做,等等。这些社会的答案其实从不清楚明白,也不令人满意。想想今天“民主”的含义吧。就我们试图表现正派、保持自重而言,我们在行动上遵守了社会的标准。然而,我们同时却察觉到,这些共同理解的标准是成问题的,因此,我们被迫朝着更正派而非相反的方向超越这些标准。然而,好生活在于哲学思考,或者德性就是知识,这样的论点绝非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被迫追问:为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把哲学本身召唤到哲学之外的一个审判台(atribunalotherthanphilosophy)前。此审判台主要指要求我们付出忠诚或忠心的社会,而这样要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政治社会同样属于那种首先、永久且普遍地被给定的东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存在,他们都是服从者,不一定是服从国王们,但肯定要服从社会。不难看到,这不是由于孩童般的禁忌,而只是我们需要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关心我们的社会,而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心我们的社会是好社会。
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好社会,因为社会给予的答案不一定为真。于是,我们对社会的关心会立刻将我们引向政治哲学,我们大可以说,政治哲学并不仅仅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还是哲学的自然开端。这再次使人联想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哲学是对整全知识的探求,但认识整全意味着认识它的部分。哲学[8]因此变成了对整全的诸部分的研究。但是,除非将部分当作整全中的部分,否则部分不可能被真正认识。除非根据整全来认识部分,否则部分不可能被真正认识。在柏拉图看来,这是哲学的根本性难题。然而,整全有一个部分就其自身而言也是一个整全,它是特殊的整全,是最易接近的整全,这一整全受人天生追求的诸目的所限定。这一整全是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的处理对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凭借其自身得到理解,至少对于实践的目的而言可以得到充分理解。
哲学,按照柏拉图的理解,在本质上是探究的、好奇的。哲学的开端就是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洞穴之中,意识到我们被社会强加的正统意见所束缚。假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这样的意识必须被唤醒。首先,我们生活在公认的意见之中,仿佛这些意见就是真理。我们一开始并不相信我们生活在洞穴中。必须有某个人向我们表明,我们生活在洞穴中。他必须解放我们。这是柏拉图写作对话的一个理由。他用对话向我们表明,有一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他试图通过以下方式来解放其他人:一是让他们相信,他们生活在洞穴中,而非生活在自由的空气中;二是向他们指出走出洞穴的道路。于是,对话就不是展示某种哲学学说的武断形式,而是柏拉图理解哲学的方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柏拉图教授的不是某一哲学学说,而是如何进行哲学思考。
关于哲学的出发点,让我们再稍微讲得精确一些。我们生活在洞穴中而不自知。我们相信,有人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所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相信这一点。或者说,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自己的洞穴中。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在原则上是因人而异的。哲学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从每一个个体的个别情形开始,它必须(must)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依据个别的情形,从个体关心的个别需要开始。没有关于个别需要的伟大智慧;每一位教师都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点。解放人们的方式有无限多种。因此,柏拉图没法在他的对话中充分展示这种解放,因为不可能穷尽这无限多种方式。不过幸运的是,人类和人类境况的无限多样性可以被概括为一定数量的类型。所以人类的解放可以用为数不多的几篇对话呈现出来。在每一篇对话中,都有一些个别的人物,这意味着他们有专门的名字和性情——他们可以秃顶,也可以肥胖,以及拥有所有其他的品质。换言之,对话人物不是一个叫甲或乙的家伙,就像霍布斯在他写作的对话中称呼他们那样。a他们彼此称呼对方为“亲爱的甲”和“亲爱的乙”。但这不是柏拉图的风格——柏拉图对话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人。所以在每一篇对话中,都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专门的名字,生活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对话就发生在他们中间。而选择这些人,为的是考察他们的典型性格。
这是我们的开场白,它对于在座的某些人来说可能不言自明,而对于另一些人可能又太难理解。我承认,刚才说过的一些东西,对于一个刚开始阅读柏拉图的人来说并非显而易见。而我们一定要从开端、从事物的表面出发。让我们言归正传,真正从表面出发。我们从一个确定的事实出发,那就是我们很困惑(如果有人不想被列入困惑者之列,那也行),我们不仅困惑,而且需要[9]指引。进而,我们从如下偏见或曰合理的假设出发,即我们可以获得来自柏拉图的某些指引。柏拉图写作了许多品,但他并未告诉我们应当从哪一篇读起。因此,任何开端,从任何一篇柏拉图对话开始都完全合理。适当的开端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只要真正开始阅读柏拉图,而非阅读研究柏拉图的文献。我们[不]应当把任何关于柏拉图的假说当真,我们唯一应当接受的就是柏拉图的文本,流传至今的柏拉图文本。我们或许不该对抄写员的错误表示惊讶。毕竟柏拉图与我们相隔两千三百年呢。但是,若对传统文本缺乏一种谨慎的信任,我们便没有任何机会接近柏拉图。我们丝毫也不关心那些聪明人告诉我们的说法,比如像《高尔吉亚》写作的时间和背景什么的。我们只考虑柏拉图本人在对话中提到的时间和其他背景。起初,我们甚至不知道柏拉图为什么写作这些对话。起初,假如[我们]有理智的话,这些对话只是柏拉图的奇特造物——奇特,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词:美丽。起初,我们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对话是不是哲学著作;那只是一个重大的假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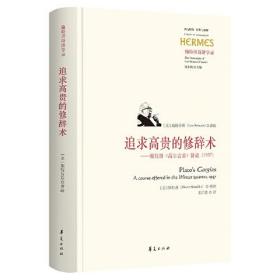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