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民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4.42 3.8折 ¥ 3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阮清越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83236
出版时间2020-04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1202066072
上书时间2024-05-3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阮清越(1971-) Viet Thanh Nguyen 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 2017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 生于越南邦美蜀。1975年随父母从越南逃难至美国,在难民营度过一段时日后,全家定居加州圣何塞。 1997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英语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至今,现为英美研究和民族学、比较文学教授。 2016年凭借长篇小说处女作《同情者》一举拿下诸多靠前大奖,包括00届普利策小说奖,实属罕见。同年,其非虚构族裔研究作品《从未逝去:越南和战争的回忆》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7年,阮清越获麦克阿瑟天才奖,被认可为未来拥有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颠覆了大众对越战的认知,深描因战争失去家园的人的生活状态”。 2018年,阮清越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同为该院院士的有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麦克尤恩、米兰·昆德拉、奥尔罕·帕慕克、爱丽丝·门罗等。
目录
\\\\\\\\\\\\\\\\\\\\\\\\\\\\\\\"【目录】
黑眸女人 / 1
另一个男人 / 23
移植 / 49
我想要你爱我 / 75
美国人 / 101
别人 / 127
祖国 / 157
鸣谢 / 181\\\\\\\\\\\\\\\\\\\\\\\\\\\\\\\"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难民》是阮清越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共由7个短篇故事组成。与《同情者》相比,《难民》的题材更为日常,没有思想体系和国家命运的沉重叙事,多为在美国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牵绊。故事人物与情节迥异,如《黑眸女人》讲述了一位捉刀手撞鬼的故事,《祖国》则讲述了二代移民重回越南故土的经历。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阮清越的成长经历,也能看到他在移民身份认知等方面十多年的田野研究成果,每一篇作品都是赤裸的揭示、克制表达的复杂情感,审视了战争创伤、自我认知的危机以及记忆的珍贵与脆弱。整体看来,《难民》中的人物大多身处“不适之地”,想要表达的情感非常复杂,有追忆故土的乡愁,有大难不死的幸与不幸,有夫妻、恋人间的温情,有强烈的文化冲突……但作者的文字较为克制,时常用自嘲的语气讲述同为难民的不同经历。
\\\\\\\\\\\\\\\\\\\\\\\\\\\\\\\"
精彩内容
《难民》节选黑眸女人有些可以让人出名的事,大脑健全者是不愿其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但总会有人撞上,比如,遭绑票囚禁几年,或因性丑闻遭受屈辱,或死里逃生。这些事的经历者需要人帮着写下这些经历,以作回忆录。他们的代理人寻来觅去,十有八九最终会找上我。“好在你写什么都没挂名。”母亲有次说道。我说,书后面的致谢辞里如果要提我的名字,我也不反对。听这话,母亲说道:“让我给你说个故事吧。”她的这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但之后就再没少听。“在我们老家,”她继续道,“有个记者,写东西指控政府虐待犯人。于是,政府就拿他指控他们虐待犯人的手段,一样不差地虐待他。他被政府关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从此就再没了踪影。写东西的人要是挂名,就是这种结局呀。”因此,我也就安于做个替人捉刀而不求署名的写书人了。这么一段时间后,维克多·德沃托选中了我,他的代理人给他看了一本我写的但署名者是一个男孩的父亲的书,男孩在读书的学校开枪杀了几个人。“我与这位父亲有同样的负罪感。”维克多告诉我。原来,他经历了一场空难。空难导致一百七十三人遇难,其中有他的太太和一双儿女,唯有他幸免于难,但他身体的多个部位均已残损。残损的他出现在各种谈话节目里。他声音柔和,没有抑扬顿挫;一双眼睛难得抬起,偶尔为之,里面布满吊丧人似的黑影。计划为他出书的人说,趁人们没忘了空难,得赶紧将他的经历写成书才行。我接下了这单活。这天,我正写着他的回忆录,死去的哥找我来了。
母亲叫醒我时,屋外仍一片漆黑。她说道:“别害怕。”我卧室的门开着,过道里的灯照进来,很是刺眼。“我怕什么呀?”她说了哥的名字,我一时竟没跟哥联系起来。他很久前就死了。我闭着眼应道,说不认得叫这个名字的人。她不依不饶。“他来这里,看我们来了。”她说着话,掀去被子,将睡眼惺忪的我拽了起来。母亲六十三岁,中度健忘。因此,她领我到客厅,嚷着“咦,他刚才就在这里呀”,并没让我吃惊。她跪下,摸着镶花摇椅旁的地毯。“还湿着呢。”穿着棉质睡衣的她沿地毯上的水印,爬着摸到门口。我摸摸地毯,确实湿。有那么一会,我信了母亲的话,怵得打了个冷颤。此时,凌晨四点,屋里静悄悄的,阴森诡异。不过很快,我听到排水沟里的雨声,让脖颈发紧的恐惧因此减轻了不少。准是母亲先前开门出去过,淋湿了身子,又回到屋里。母亲蹲在门边,握着门把。我走到她旁边跪下,说道:“都是你的幻觉哩。”“我没瞎没昏,确实看到他了。”她一把拨开我搭在她肩上的手,站了起来。她的两只原本黝黑的眼睛,因为生气而放出光。“我看见他在走。我听见他说话。他想见你。”“可是,他在哪呀,妈?我什么也没看到啊。”“你当然看不到。”她叹道,好像我是那种连明摆着的道理都不懂的人,“他是鬼,是不是?”自几年前父亲过世,母亲和我一起生活,相敬如宾。我们都特别喜欢话语。不同的是,她爱说个不停,我好静静地将要说的话写出来。她老往我耳朵里灌道听途说,但我只爱听跟年轻时的父亲有关的事。她说,父亲那时是乐天派。说完父亲,母亲少不了说起诸如记者遭遇之类令人发怵的故事,想要教育我:生活如警察,时不时给人一击,且乐此不疲。说到最后,她会说起她最喜欢的鬼故事。她知道很多鬼故事,其中有些还是她亲历过的。
“六姨七十六岁时,发心脏病死了。”她一次,两次,或许三次告诉我。来回地重复成了她的习惯。我从没把她的故事当真。“那时,她家在头顿,我们家在芽庄。有天我端菜上桌,竟然见六姨穿着睡衣坐在餐桌旁。她又白又长的头发,平时盘成髻,这回竟然散着,披在肩上,遮住了脸。我当时差点把端的菜碟掉到地上。我问她来这做什么。她不言不语,只是微笑,站起身,亲亲我,随后把我往厨房推。等我再转身看她时,她没了影。我见到的是她的魂。我随后给她家打电话,六姨父接的,说那天早上,她在自己的床上去世了。”照母亲的说法,六姨得了个好死:一是死在自己家里,二是有家人送终。她的魂到处走走,不为别的,就跟大家道个别。母亲言之凿凿说看到了我哥、她的儿子的那天早上,我和她坐在餐桌旁,她又说起六姨的事。我为她泡了壶绿茶,不顾她反对,给她量了体温。体温计如她所料,显示正常。她边朝我扬着体温计边说,你哥来了没一会就不见了,准是累了;毕竟,刚从太平洋那头过来,可是几千英里啊。
“那他是怎么过来的?”“泅水呀。”她可怜地看我一眼,“所以,他全身湿了嘛。”“那他还真是一等一的游泳高手。”我调侃道,“他什么样?”“一点没变。”“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竟然一点没变?”“人死时什么样,他的鬼就永远那个样。”我记得哥死的样子,心里若还有幽默,幽默也因此烟消云散。当时,他的表情像被怔住,双眼圆睁,就是破碎的船板顶着他脸,也一眨不眨——如果真见鬼,我也不想再见到他。母亲到美甲店上班去后,我想补觉,可无法睡着。我每每合眼,便感觉哥直愣愣地看着我。只有此刻,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想他了。我一直努力想忘了他,可在这个世界或在我脑海一拐弯,我总能撞见他,我最好的伙伴。时间虽过了很久,我仍记得他在屋外唤我名字,叫我跟他去玩。我跟着他,避开被炸得七零八落的棕榈树与满地弹坑,经村巷,走阡陌,过木菠萝林、芒果林,去到坝上、田间。当时的童年生活大抵如此。
回想一下,可以这么说,我们度过童年的乡村是个多鬼的地方。父亲被征入伍。全家人担心他一去便再也不能回来。出征前,他在家旁挖了个掩体,掩体用沙袋加固,顶上用木头隔挡。里面很热,像没空气,湿气也重,散发出泥腥味,到处蠕动着虫子。即便如此,哥和我毕竟是孩子,常下到掩体嬉耍。大些后,我们上了学,学会了讲故事。在学校,我是最好的学生,好到老师放了学还愿教我英语,我学后再教哥。作为回报,他给我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民谣,或是道听途说的东西。每次飞机在头顶呼啸,我们和母亲挤在掩体里;他在我耳边悄悄讲鬼故事,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过,他始终认为他讲的不是鬼故事,而是过往确实发生的事。给他讲这些事的人可信,她们是一大把年纪的干瘪老妪。她们蹲在集市上,照看一个个煤炉或一篮篮货物,嚼着槟榔,啐出给槟榔汁染红的唾沫。她们声称,在我们那块地方有群赶不走的“居民”,比如被地雷炸死的韩国中尉,炸剩的上半身挂在一棵橡胶树树枝上;被剥了头皮的美国黑人士兵,尸体浮在小溪里,不远处是他那被击落的直升机,他的一双眼睛与露着脑髓的半月形脑袋冒出水面,闪着冷光;被砍头的日本下等兵,在木薯丛里四处找自己的头。老妪们说,那些侵略者想征服我们,如今永远也回不了家。她们边说边咯咯笑,露出黑得上了漆似的牙。反正,哥那么描述。掩体里黑黢黢的,我听哥转述那些黑眸老妪讲的故事,又开心又害怕,身体抖个不停。当时,我想自己该一辈子不会讲那样的故事。
那么,我现在竟做着代人捉刀的营生[原文为ghostwriter,本意为捉刀手,此处又可理解为写鬼的人,一语双关。],也是讽刺,对吧?时间到了中午,我仍躺在床上,问了自己这个问题。牙齿漆黑、眼睛漆黑的老妪们听到了我的问题。“你把你如今做的事也叫营生?”她们磕着牙讥笑我。我往上扯盖在身上的被子,只露出半个脑袋。到美国后的最初几年,我每听到走廊或屋外有东西在动,便用被子这样蒙住自己。那时,每每有人敲门,父母会先透过客厅窗帘往外看个仔细,他们很怕自己年少的同胞,那些男孩伴着战争长大,学会了暴力。“别给生人开门。”母亲一次、两次、三次地告诫我,“我们家可别像那家一样,给枪逼着,被绑了起来。绑他们的人用烟头烫婴儿,直到婴儿的母亲说出藏钱的地方,这才罢手。”我在美国度过的青春期,满耳都是这类让人苦不堪言的事。所有这些证明,母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属于这里,没人保护我们。在这个国家,决定一切的是人所拥有的东西;除了故事,我们一无所有。
我被敲门声敲醒。天色已黑,手表显示傍晚六点三十五分。敲门声再次响起,很轻,很犹豫。我不想朝那方面想,可心里清楚是他。我早就给卧室门下了锁。我用被子兜头盖脑蒙住自己,心脏狂跳。我巴不得他离开,可他反倒卡拉卡拉扭动门把,我知道非得起床不可。他在用劲扭晃着门把,我看着一颤一颤的门把,根根寒毛竖起。但我同时跟自己说,他可是为我才丢了命。我虽不能为他做别的,总该给他开门。
他被水泡涨,了无血色,头发蓬乱,皮肤暗沉,下身一条黑色短裤,上身一件破烂灰色T恤,一双胳膊与两条腿皮包骨样。他生前留给我的最后印象是高我一头;如今,我们的个头正好相反。他叫我名字,声音嘶哑尖细,完全没了他年少时的亢亮。眼睛和两片嘴唇,倒一如从前,感觉想探究什么,后者微张,像随时要说点什么。左太阳穴的伤口紫里透黑,闪着亮光,我记得伤口有血,如今却不见了,该是被海水和暴风雨冲洗掉了。没下雨,但他湿得精透。身上散发出海水气味,更难闻的是只有沤久了人汗和排泄物的船才有的气味。
听他叫我名字,我一打冷颤,但这是我爱的人的鬼,是母亲说的那种不会伤害我的鬼。“进来吧。”我招呼道。这似乎是我此刻能说的最勇敢的话了。但他没动,而是低头看脚下地毯,身上的水滴在上面。我给他取来干净T恤、短裤和毛巾,他若有所盼地望着我,我明白他的意思,转过身,不看他更衣换裤。我给了他我的最小号T恤和短裤,即便这样,他穿着还是太大:短裤裤管长到膝盖,T恤晃里晃荡。我示意他进到我的房里,这回他听从了我。他坐在我被窝凌乱的床上,可不愿与我目光相接。看样子,我怕他,他更怕我哩。他仍十五岁,我却已三十八岁。我不再是有使不完劲的疯癫假小子,也轻易不愿说话。不过,为了谋事,比如采访维克多,我会说话的。写书人,三流也好,四流也罢,有一套规矩,我自然能照这套规矩行事。可是跟一个鬼能说什么呢?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我怕听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于是改问:“怎么这么久才来呀?”他低头看着我没涂指甲油的裸露的脚趾。或许,他觉察到我不擅长同孩子打交道。母亲般的爱意柔情对我来说委实太难,同样难的还有超过一晚的亲密关系。
“你得泅水。泅这么远,要花很长时间,是吧?”“嗯。”他的嘴还是张着,像要继续说话,却又把不准该说什么、如何说出来。母亲看我婚也不结,无儿无女,认为我性格乖悖;眼前的鬼兴许便是我的乖悖招致的第一件事情。他兴许不是鬼,而是我做错了什么事的兆示,就如要了父亲性命的癌。说到父亲的死,母亲说,也是好死,在家里有家人送终,不像她儿子也不像我差点遭遇的那样。我心底深处,如一口像被我用混凝土封死的深不见底的井,腾涌着恐慌。就在这时,客厅那边传来开门声,我松了口气。“母亲很想见你呢。”我说道,“你在这等着。我马上回来。”待我领母亲回到房间,我们看到的只有他换下的湿衣、湿裤与用过的湿毛巾。母亲拿起灰色T恤,哥在船头两侧各画有一只红色眼睛的蓝色船上,穿的也是这件。
“你现在知道了吧?”母亲说道,“永远别背朝鬼。”黑色短裤,灰色T恤,逸出难闻的海水气味,湿沉沉的,但沉的不只是水。我拿着他的衣服去到厨房,衣服的重量是往事的重量。在很多场合,我见过他穿这件T恤、这条短裤。我记得,当时的短裤不是现在的乌黑,而是干净的蓝色;T恤也不像现在这样灰不溜秋、破破烂烂,而是纯白整洁的。“你现在信了吧?”母亲掀开洗衣机盖,问道。我不知如何应答。有些人称,他们若信什么,那种信燃烧似火,而我开始信的东西却寒气逼人。“嗯,”我答道,“我信。”母亲和我坐在餐桌旁吃晚饭,背后的洗衣机嗡嗡响。空气里飘漾着浓浓的茴香与姜的香味。“所以他过这么多年才到这里。”母亲边吹热汤,边答道。没什么能吓得她丢了胃口或伤得了她铸铁的胃,就连当年船上的遭遇和如今儿子的鬼来访也不能。“他可是一路泅过来的呀。”“六姨当时住得离我们家几百英里远呢,你在她死的当天也见着她了。”“鬼跟我们活人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鬼与鬼也不同。有好鬼,有坏鬼,有幸福鬼,有悲伤鬼,有老死的鬼,有早死的鬼,还有婴儿鬼。你认为,婴儿鬼会与爷爷鬼外公鬼一样行事吗?”我对鬼一无所知。我之前不信有鬼,我认识的人,除了母亲和维克多,也不信有鬼。说到维克多,他自己就看似鬼,悲伤将他烧得了无血色、几近透明;他仅有的色彩来自那头蓬乱且久未梳理的红发。就是他也只有两次跟我说起鬼,一次在电话里,一次在他家客厅。他家里的一切还保持着他和太太、儿女离家去机场那天的样子,没动过,连上面可悲的灰尘都没掸过。我的印象是,他家所有窗户自那天起便一直闭着,仿佛要将太太、儿女留在屋里的已稀的气息封存起来。她们没得好死,死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死的人继续走动。”他蜷在摇椅上,两手置于腿间,说道,“可我们活的人,只待在这里。”他这话用在了我为他写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的开头。母亲睡后,我下到地下室里写这一章。地下室亮着几管日光灯。我写下一句,停下笔,听听是否有敲门声或下到地下室的台阶上是否有脚步声。一个晚上就是这种节奏:写写,停停,听听动静。但始终一片静寂。第二天整个白天,节奏依旧,只是写写停停听听的次数更多。维克多的回忆录即将收尾,这时,母亲从美甲店下班回来,拎回在唐人街买的两袋东西,一袋是吃的家用的,另一袋是内衣、内裤、一套睡衣裤、一条蓝色牛仔裤、一件斜纹粗呢布夹克、一包短袜、一副针织手套以及一顶棒球帽。哥自己的短裤、T恤已晾干熨好。母亲将新买的东西堆在它们旁边,说道:“外面冷,他穿着你给的衣裤在外头晃,像个流浪汉,像个偷渡客,不成啊。”我说我可不这么想。我对鬼需要什么一无所知,让她不快,她哼了我一声。直到晚饭后,她方才开始释然。她心情变好,因为那晚我没像平常饭后下到地下室里,而是留在上面,陪她看她租来的一堆韩国肥皂剧。肥皂剧里尽是靓女俊男,他们陷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里。“要是越南没打仗,”看着韩剧,她说道。她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让我觉得有趣,坐得又靠近些她。“我们现在不也像韩国人不是。西贡也会像首尔。你父亲呢,活着。你呢,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呢,不用做修甲美甲这活,做个退休的家庭主妇。”她的头上夹了一头卷发夹,大腿上搁着一碗西瓜子。“我每天去看看朋友,朋友也来我这坐坐。我死了,参加追悼会的不得上百人。可在这里,我的追悼会到时由你操办,有二十个人能来就谢天谢地了。我可是最怕出现这种场面。你甚至记不起要倒垃圾要付水电费,就连出门买个吃的用的,也不愿意。”“可我不会忘了为你守灵哩。”“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该为我守灵?什么时候该给我过祭日?你又该说些什么?”“你替我写下来呀。”我说道,“把我该说的替我写下来不就得了。”“你哥可是知道该做什么。”她说道,“生儿子就是为这些事备着的。”听她这话,我无言以对。
到了夜里十一点,他依然没来,于是母亲睡觉去了。我又下到地下室,想着写完维克多的回忆录。写书如同进入浓雾,凭感觉找到一条路,经由这条路,从现实世界到达一个由文字构成的与现实迥然不同的世界;这样的路,有时好找,有时难寻。我于浓雾中跌跌撞撞摸索前行时,一只看不见但确实栖在我一边肩上的鹦鹉问着:我怎么活着?哥怎么就死了呢?我年龄比哥小,身体比哥弱,可被葬的却是他。他被葬时身上没裹一点死人该裹的东西,我没向着他说半个字。就这样,木板上的他被抛入大海。我想起母亲的恸哭、父亲的抽咽。当时,他们的眼泪没冲走我的沉默。如今,我该说点什么,该唤他回来,他也一准等我这么做呢。可是,我竟不知该说什么。就在我以为又一个晚上过去了、他又不会来时,我听到他在台阶上头敲门。我告诉自己,要信他。我信他永远都不会伤害我。
“别敲了。”我打开门,说道,“这也是你的家。”他只是盯着我。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陷入了沉默。还是他先说话:“谢谢。”他的音色亮了许多,几近我记忆的那种亮,而且这回,他没别过眼去。他穿的仍是我的T恤、短裤。我给他看母亲为他买的帽子、衣裤、袜子,他却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可你穿的还是我上次给你的衣裤。”他没应我。这样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定没听见我的话。
“我们是为活的人穿衣服,”他终于吱声了,“不是为自己。”我领他坐到沙发上。“你说的我们指的是鬼吗?”他挨我坐下,想了想我问的话,这才回答。
“我俩过去就一直相信有鬼的。”他说道。
“我过去可不怎么信呐。”我握着他手,“你为什么回来?”他一直盯着我,盯得我周身难受。他的眼睛一次没眨过。
“我不是回来,”他说道,“我是上这来。”“这么说,你还没离开这个世界?”他点点头。
“为什么还不离开呢?”他又缄默不语,过了很久,这才问道:“你说为什么?”我望向别处,“我一直想忘了过去。”“可你没忘。”“我忘不了。”我没忘记当时坐的没名没号的蓝色的船。它也没忘记我:船头两侧各画有一只红色眼睛,一直居高临下盯着我。当时,连着四天,海上风平浪静,白昼天空碧蓝,夜间天空澄静,一切平安无事。四天后,我们终于见到遥远地平线上的岛影。岛影如缝在天际的一道道黑色针脚。就在那时,远方冒出一条船,奔我们而来。对方船疾,我们船慢。我们的渔船,只能载有限的船员和他们捕后冷藏的鲭鱼,却载了一百多个难民,怎么快得起来。哥领我进到逼仄的轮机舱。发动机轰轰在转。他用小刀割短我的长发,把它变成参差的男孩短发发式。我至今还留这种发式。“别开口。”他叮嘱道。那一年,他十五岁,我十三岁。“你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女孩。快,把外面衣服脱了。”我向来听他的。脱衣服让我难为情,虽然他几乎没瞅我一眼,只顾将我外衣撕成布条。他用布条将我的远说不上发育的两个乳房束紧,接着,脱下自己的外衣给我穿上,将它扣实。他的上身仅剩件破烂T恤。他又往我脸上涂抹机油。我们这才相拥着蜷在暗处。海盗们跳上我们的船。也是渔民的海盗,与我们、兄弟没两样,一身精肉,棕色皮肤。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挥着砍刀,有的端着机枪。他们缴走了我们的金子、手表、耳环、结婚手镯以及玉器,掳走了所有少妇与少女,共计十二人,枪杀了阻拦他们的一位父亲和一位丈夫。没人敢再吱声,只有被拖拽到海盗船上的少女少妇们尖叫哀嚎。女孩们来自别的村子,我一个不认识,因此说不上多同情。我紧紧倚住哥的胳膊,求天主佑护我别跟她们一样,被海盗掳去。直到最后一个女孩被扔上海盗船,海盗们也撤离了我们的船,我这才敢出口大气。
最后一个撤离的海盗经过我和哥时,瞥了我一眼。他与父亲年纪相仿,鼻子像一只让烈日炙烤过的猪蹄,身上逸出的气味里有汗味也有鱼的肠肚味,精瘦矮小,能说几句我们的话。他走到我跟前,托起我的下巴。“挺俊一个男孩嘛。”他说道。哥握着小刀猛地刺了过去。之后,我们三个怔住了;六只眼睛盯着刀刃,刃尖染血。一时无声。很快,小个子男人痛得嚎叫起来,抡起机枪,用枪把照哥的头砸了下去。咔嚓——这声音至今在我耳边响着。血自哥的眉骨汩汩淌了出来。哥重重仆倒,下颌骨和一边太阳穴咚地撞在木甲板上。可怕的撞击声也至今留存在我记忆里啊。
我轻摸他受伤的地方。“还疼吗?”“不再疼了。你还疼吗?”我即刻可回答他的问题,不过,还是故作思考状。“疼。”我终于答道。当时,小个子男人将我掼倒在甲板上,我摔伤了后脑。他撕去我的衣服,锋利的指甲在我身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我别过脸,看见母亲父亲叫喊,可是,我的耳膜似已破裂,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叫喊,却只感觉嘴一张一合,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天地像被什么死死捂住,一片死寂。从那往后,母亲、父亲和我在这件事上只字不提。他们与我在这事上的缄默不语,其实一次次割伤我。但是,最让我心痛的还不是这点,也不是压在我身上的那些男人,而是当时射入我的没有光的眼睛的光。我当时将目光投向天上,太阳像天主吸的烟卷的燃烧的烟头,悬在天庭,但随即无情地灼烫着我的皮肉。
自那以后,我躲着白天,躲着阳光。就是哥也注意到我因此发生的变化。他抬起一条小臂,与我的一条小臂并在一块,让我看,我的肤色可是比他的白。我们当年在掩体里也对比肤色,在眼前张开各自的手,看手在暗里能否显出形来。每次轰炸后,土筛过一般落到身上,我们蒙着尘土确认彼此还在不在;想到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我仍簌簌发抖。第一次听到飞机声,哥在我耳边悄声教我别怕。它们不过是鬼怪[Phantoms,美军使用的鬼怪战斗机。]罢了。
“你知道我那时最喜欢什么吗?”他晃着头。我们坐在沙发上。已是十一月,我办公用的地下室比客厅暖和许多。“每次轰炸完,我们出到掩体外,你攥着我的手;我们站在太阳底下,眼睛给刺得眨个不停。我喜欢躲在黑暗中后迎来阳光的感觉,还有轰轰炸完后的那种静。”他由晃头改为点头,但眼睛仍一眨不眨。和我一样,他也在沙发上蜷起身子。我们膝盖碰着膝盖。自打将哥葬入海里便一直栖在我肩上的鹦鹉,又开始扰我。看来若要赶走它,只有让它开口说话。
“告诉我,”它问,“为什么我活着而你死了?”他打量着我,眼睛不管睁多久,里面满是水。母亲没说对。其实他变了,证明他变的是他的眼睛,它们在海水里浸泡太久,永远合不上了。
“你也死了,”他说道,“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我记起与维克多的一次对话。那是一天晚上,已是十一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急于知道答案,也知道他当时没睡,便给他打了个电话。“是的,我信有鬼。”他听了我的问题,并不惊讶,答道。我想见得到,电话那头的他蜷在椅子上,烛蜡般的身体顶着一颗火红的脑袋,仿佛点燃他的是那场夺走他家人生命的空难的记忆。我问他是否真见过鬼。他应道:“一直都见的。我一合上眼,我的太太,我的两个孩子,就会浮现,看上去跟在世时一模一样。我一睁开眼,余光总能看到他们。他们动得很快,没等我看清,就不见了。我还能闻出来。我太太走过时,留下了她的香水味;我女儿留下了她的洗发香波味;我儿子留下了运动衣里的汗味。我还能感觉他们。我儿子用手拂着我的手;我太太像以前在床上睡在我身边那样,呼出的气撩着我的脖子;我女儿贴着我的两个膝盖。而且,鬼会说话,人听得见的。我太太叮嘱我出门别忘了带钥匙;我女儿提醒我别烤焦了面包;我儿子叫我把院里的树叶耙成一堆,好从树上往叶子堆里跳。他们还一起为我唱《生日快乐》。”两周前是维克多的生日。我想象,他的生日是怎样的景象——他该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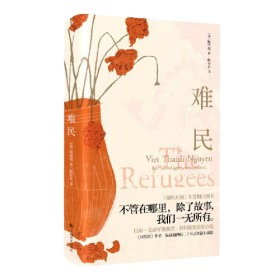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