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静海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2.59 3.9折 ¥ 58 全新
库存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匈)巴尔提斯`阿蒂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9677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436441
上书时间2024-05-2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序言
宁静海
译后记
内容摘要
“什么时候回来儿子?”“你去哪儿了儿子?”三十六岁的作家儿子和话剧演员母亲共同生活在一间公寓里。十五年间,他每次出门、进门,都要回答母亲同样的问题,编织不同的谎言;十五年间,他模仿叛逃的姐姐的口气用左手给母亲写信,以朗诵会的名义不断离开家,遇到爱人尤迪特,又遇到女编辑乔尔丹,了解到父亲曾经作为秘密警察的真相;十五年间,在无数次“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昼夜交替,四季更迭,政治剧变,东欧解体,窗外的世界早已变换,窗内的囚笼依然存在。
在浓烈、大胆、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描述中,巴尔提斯以母与子近乎疯癫的人生,呈现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疯狂,以及它们压抑人的力量。人人都是人性的囚徒,都试图在极致的爱恋与极端的情欲中寻找内心的宁静,犹如月球上的那片宁静海。
主编推荐
“米兰·昆德拉的继承人”巴尔提斯·阿蒂拉代表作,比肩诺奖得主耶利内克《钢琴教师》当代欧洲文坛zui先锋、zui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米兰·昆德拉的继承人”。德国评论家安德里阿斯·布列登斯坦认为,《宁静海》承继了米兰·昆德拉早期小说的传统,将“冷嘲与忧郁、现实批评与形而上学、情色与俗世生存沉重地交织在一起”。诺奖得主耶利内克盛赞有加,认为《宁静海》比《钢琴教师》更能反映人性的幽暗,更能体现历史的深度。《宁静海》德文版在德国被评为zui佳图书;英文版曾获美国zui佳翻译小说奖。母与子:共同编织的憎恨与依恋之网母子关系:照顾与逃离 & 逃离与回来;监视与反监视 & 控制与被控制;反抗与被反抗 & 纠缠与被纠缠。儿子痛恨母亲的监视,但又疼惜母亲的境遇,不但每日帮她购买日常用品,还伪装成姐姐,用左手给母亲写信。他只能借助于写作进行内心的逃亡,明知母亲偷偷用小刀割开他的手稿,甘愿让她成为个读者。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怎么逃,都逃不出母子俩共同编织的憎恨与依恋之网。斑驳衰朽的历史、禁色分明的爱欲、沉重堕落的肉身这是一本关于真实与谎言,欺骗与真相,热爱与憎恨的杰作。以母与子近乎疯癫的人生,呈现一个时代的荒谬与疯狂,以及对人性的巨大伤害。巴尔提斯将繁多凌乱的生活细节嵌入东欧巨变的时代背景中,将几代人的个体命运置于显微镜下进行剖解,既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的残忍,也看到了时代风暴中卑微如蚁的众生命运。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挫败 & 征服:男作家和女性的关系的熔岩之河。女性群像:母亲、孪生的姐姐、情人、女演员、女编辑、女审查官等。巴尔提斯将身体、性与身份置于显微镜下,将世界描绘成一个让人类身体相互连接的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复杂体系。身体是圣殿,也是地狱:身体的相互影响、相互诱惑、相互渴望和相互折磨。虽然巴尔提斯是写身体,但绝不止于身体,而是身体对历史、家族、经历和关系的记忆。精致小巧的装帧,特邀typo_d工作室整体设计,小开本软精装,以轻盈呈现“不能沉重的生命之轻”以抽象意象的提取作为设计的源点,以网状的线条寓意时代对人性的压抑和对自由的束缚,烘托作品的主基调与氛围,隐喻人人都是人性的囚徒,都试图在很好的爱恋与特别的情欲中寻找内心的宁静,犹如月球上的那片宁静海。精选森罗万象杰尼雅和长谊棉玥作为用材;封面银墨为奔驰专属的艾卡银。
精彩内容
葬礼是在星期六上午十一点举行的,尽管我很想再拖几天,希望艾丝特能来,无奈办公室的女接待员告诉我,由于现在有新的规定,他们不能继续为尸体冷藏提供半价优惠,她问我为什么不火化,那样不仅便宜一些,而且也很实际,我们可以选一个对全家人都合适的日子举办葬礼。我只应了一句,我不能把我母亲烧掉。既然如此,那就定在星期六吧。我预付了三天的尸体保管费,她为我开好发票,并且登记到运尸簿上,704号—装棺—星期六—凯莱佩什,随后递给我几张公文纸,用圆珠笔指点着,告诉我该在哪里签字。
要知道,当办公室里的女接待员向我建议火化时,我全身骤然抖了一下,因为我想起母亲歇斯底里的体操表演。“你看,他们都这么坐起来。”她边说边撑着床旁边的扶手椅向我模仿死人怎么在焚尸炉里坐起来,因为几个月前她在一个科普节目里看到过这一场景,从那以后几乎每天清晨她都心有余悸。事实上我早就跟她说过:“您就放心吧,妈,您不会被火化的。小心!杯子里的茶要洒出来了。”但是没过几天,又旧戏重演,她说火化是对上帝的不敬,我知道她担心被火化了的人不能复活,按理说,她该喜欢火化,因为她这辈子从来没有信过上帝。她去世前还要我发誓,决不会把她送进焚尸炉,她不能容忍自己死后被烧掉。我回答说,我不想发任何的誓,好在她还能够走动,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份公证,写明她死后不可以火化。这一招很灵,她不再为这个折腾了,因为她恐惧出门已经十五年了。
就这样,有片刻的幻觉让我好像从高空看到了她,只是她现在不是抓着扶手椅,随后我想起艾丝特,她要是能回来该有多好,因为我很想让她看到我母亲那副萎缩的躯体、在最后一夜咬秃了的指甲和戴在痉挛手指上的七枚纪念戒指,从“朱丽叶戏剧表演奖纪念戒”、“诗歌之友纪念戒”到“莫斯科艺术节纪念戒”,戒指上的镀金早已磨掉,由于铜制或铝制的质地不同,把她的手指根染成绿色或黑色。我很想让艾丝特看到我母亲那因喷了太多摩丝而变得黏腻的焦黄枯发,由于染发膏涂得一年比一年更不均匀,隐约露出头皮的烟灰色,尸体的僵硬使她的胸脯重又变得紧绷起来,想当初她刚刚喂奶一个半月,就开始在自己的乳房上抹盐,生怕乳头会被叼长。我最想让艾丝特看的是死人的眼神,居然跟活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那永不瞑目的碧蓝色目光,将从星期六开始照亮已经空等了十五年的墓穴深处。
没有发布讣告的必要,想来她已经十五年没有熟人了,更何况除了艾丝特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来凯莱佩什公墓。事实上我憎恨讣告,在我母亲的抽屉里至少攒了有三十张。由于在某些单位的联系人名单上,人们忘了删掉她的名字,就在前年,邮递员还送来过一份,那张讣告让她读了整整一天。“可怜的温克勒,他扮演阿巴贡非常出色,唉,生活真是冷酷无情,连这样杰出的演员也难逃一死,太可怕了。简直太可怕了。你永远别忘了,儿子,今天死的是温克勒,明天就要轮到我了。这个没有宽恕可言。”有时,她把所有的讣告从不同的抽屉里掏出来,像玩扑克牌似的并排摆在桌面上。由于用手捏的次数太多,纸已变得油渍麻花,就像吉卜赛女巫用来算命的纸牌,只是那些纸上写的信息更为详细,可以读出死亡时间,还有猝死或长期受到病魔折磨的具体死因。她一摆弄那些黑乎乎的纸片就是几个小时,根据死亡时间,根据死亡年龄,或根据所属的派别将它们分组摆好,一边摆弄,一边喝茶。
“新教徒的寿命比我们平均短六年半。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儿子,这种事不可能是偶然的。”她说。
“您说得对,妈,可是现在我得工作了。”我说。她回到自己房间,又开始计算谁活得最长。
上星期天我去外地参加作品朗读会。我之所以接受这类邀请,并不全是为了挣钱,主要想出去透透气。我出去采购,做好饭菜,然后锁上房门,钥匙在锁眼里转第二圈时,我听到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尽量早点回来,妈,最迟明天晚上,汤我放在冰箱里了,喝之前别忘了热一下,夜里想着把电视关上。”我反复叮嘱。门上装的是双保险的门锁,她还要挂上两条防盗门链,从某种角度说,她并非无缘无故地在房间里备有灭火栓、消毒剂和保险柜,也并非心血来潮地一连几周都要我替她拆开信件,因为她在电视里看到过有一位总理或市长拆信后的下场。
“血肉横飞,儿子,我在电视里看到,写字台的四周血肉横飞。”话音未落,她着急忙慌地进了厕所,好像她之所以让我替她拆信,是因为她急着想去小便。后来,有一天深夜,她窸窸窣窣地摸到我房间,站在门口,我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进我的房间,她问我是不是想熏死她。我说:“我马上打开窗户,换换空气,妈。”她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门口。
“您怎么了,妈?”我问。
“你心里很清楚。不许你偷看我的信。这是我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你听懂了没有?”“好吧,以后我不再拆信了,但您现在必须得去睡觉了,已经凌晨三点了。”另外,在最后几个月里,我已经不再给她写信。
我步行去的火车站,路上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而且不用紧赶慢赶,我很需要这样的散步。我不管去哪儿,哪怕是去商店买东西,也要先在博物馆花园里或在拥挤的楼群中间散一会儿步,直到我对不是以“妈”字结尾的语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么讲也不是非常准确。我不仅要对另外一种语句,而且要对另外一种动作、另外一种呼吸做好思想准备。在刚开始的几分钟里,我总感觉像是在穿越无人区,要知道,在十五年中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四季交替,多瑙河泛滥,一个令人蒙羞的帝国分崩离析。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经纪人建立起各种宗教,善于做收支平衡表的会计们改写《约翰福音》,用女歌手的名字命名飓风,用政治家的名字命名地震,十五个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同样多的老妇人划着小船逃离世界上最后一座麻风病岛。仅仅在一次“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就诞生了三项社会福利法案,发射了三百颗人造地球卫星,在亚洲有三种语言被宣布为死亡语言,在智利有三千名政治犯在人为的矿难中销声匿迹。在“你什么时候回来”和“你去哪儿了”之间,离我家最近的那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倒闭关门,假冒的收费员在街区内神出鬼没,老邮递员喝走私的伏特加酒喝瞎了眼睛,管道里的所有污垢灌满了烧开水的锅炉。不过,同样在这两句问话之间,楼长把胎儿从亲生女儿的肚子里踢了出来,因为十四岁的艾米凯真的很爱那位教体育的叔叔,死活不肯去打胎,当母亲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时,女孩的父亲刚朝女儿踢第一脚,等我从艾丝特那里回家并骗母亲说“去听了一场音乐会”时,艾米凯已经做完了第一次手术。
我已经盘算好了,既然答应参加这次朗读会,那就应该耐心、认真地坚持到底,毕竟我是自愿去的。如果有人提问,我就耐心回答,人家之所以请我去一个小村子里的图书馆,就是要我回答这类问题:您为什么写作?您在写什么新书呢?您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满不满意?您是否抱有更多的希望?我甚至在一张小纸条上事先写好了几个问题的答案,省得在现场抓耳挠腮,因为我的反应相当迟钝,一般来说我的即兴回答总是很笨拙。有一次,我应邀参加一家电视台的直播访谈,简直羞窘得无地自容。女主持人总共请到了三位作家,轮到我时,我本来应该讲自己为什么写作,可是我的脑海中只有一种场景:我母亲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喝着薄荷茶,等我一进家门,她就会问:“你去哪儿了儿子?”就是在那次节目里,我说“写作就是怯懦者的自杀”,话刚出口我就立即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说,女主持人立刻打断了我,说她随口就能列出一串已被写进百科全书的作家名字,对他们来说,上吊或卧轨才是自杀。从那之后,她只跟另外两位作家继续交谈,因为他们的回答谨慎从容,机智得体。我在聚光灯下一声不吭地坐了半个小时,仿佛是坐在审判席上,仅仅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我一进家门,母亲就问我:“你去哪儿了儿子?你把我一个人扔下半天了,电视也坏了。”我很清楚,我们家的电视没任何毛病,是她看完节目后故意将天线转了个方向,好像她什么都没能看到。
我后来已经养成了习惯,凡是遇到这种场合,总会先想好回答的措辞,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要求记者们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我提问,然后花上一两个晚上咬文嚼字,直到对那几个为什么的回答准备得周密得体,以求满足文学报刊或女性杂志读者的好奇心。这些回答看上去并不显得殚精竭虑,实际上它们与事实相去甚远,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或者连我自己都想弄明白,不过,这样的回答至少显得很合理、很聪明,使我不必为此感到羞惭。好啦,不说这个了,总之我已经盘算好了,等一会儿我要尽量满足读者们的期望,事实上他们的期望也合情合理。假如朗读会后备有白菜肉卷和水果白酒,那么我也要喝几盅,那样我就可以不必逢场作戏,就跟半年前一样,当时我为了逃避跟小镇镇长及其同僚们共进晚餐,跑到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那出戏我演得非常成功,从那之后我就上了瘾。
媒体评论
巴尔提斯·阿蒂拉将冷嘲与忧郁、现实批评与形而上学、情色与俗世生存的沉重交织在一起。自米兰·昆德拉的早期小说之后,我再没有读到这样的作品。—— 德国评论家安德里阿斯·布列登斯坦因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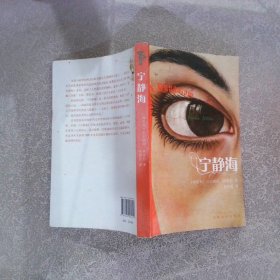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