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广芩文集 状元媒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9.27 6.3折 ¥ 78 全新
库存3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叶广芩 著 叶广芩 编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0218006
出版时间2022-0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1202577067
上书时间2024-11-2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院长。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曾任陕西省人*大第十一届常*委会委员,西安市第九、第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全家福》《青木川》《状元媒》等;散文集《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老县城》等;中短篇小说集多部;电影、话剧、电视剧剧本等多部;儿童文学《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土狗老黑惹祸了》。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好书奖、柳青文学奖、萧红文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奖项。
目录
跳加官(代序)
第一章 状元媒
第二章 大登殿
第三章 三岔口
第四章 逍遥津
第五章 三击掌
第六章 拾玉镯
第七章 豆汁记
第八章 小放牛
第九章 盗御马
第十章 玉堂春
第十一章 凤还巢
后记
内容摘要
《状元媒》是京味文学大家叶广芩家族系列作品的代表之作,讲述了清朝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做媒,促成了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婚姻,由此引发了金家大宅门里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
作品以小格格“我”的视角为轴线,冠以十一部京剧戏名写成。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跳跃性地写出了背景百年的人物众生相、北京百姓的价值观念、北京社会的风土人情。那些个细节,那些个欢乐,那些个拾掇不起来的零碎,如同一瓶陈放多年的佳酿,夜静时慢慢品来悠远绵长,回味无穷。
叶广芩动用了她独特、难忘、熟悉的生活素材,构思精巧、精心创作。她对传统文化的直接体验与研习、对世事交变的敏锐感知,以及自身修养所具有的学识与胸襟,加之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都赋予了这部作品非比寻常的魅力。
主编推荐
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旗手叶广芩
书写故乡北京与中国家族故事的集大成之作
“北京的家是残存在我心深处可望不可即的情愫”
叶广芩的作品中那种既投入又清醒、既细致生动又从容舒展的叙述,哀婉深沉、悠远悲凉的情调,总能将人们引入一种特殊的氛围,随之领略自己所不熟悉的那样一个特殊人群的悲欢离合和生存状态,深入体味那曲折复杂的人生况味。
精彩内容
第一章 状元媒
好一位吕状元颇有预见,论计谋称得起诸葛一般。
——京剧《状元媒》八贤王唱段
一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宋王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作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57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的相似,如出一辙的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80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头脑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成一片大楼。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模样来了。推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缺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锔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洇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空气中飘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锔大缸》里的戏词,说的是走街串巷的锔大缸的匠人跟胡同大姐调情,唱“砸了你的旧缸换新缸”,大姐接下来唱“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捌了又捌,说不出一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揉着,一块儿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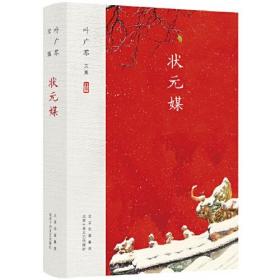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