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先的村庄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6.87 4.0折 ¥ 42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席星荃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52505
出版时间2020-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2元
货号31022322
上书时间2024-06-3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席星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教育》“新作快评”专栏主持人,《高校招生》特约理事。写作以散文为主,兼及小说、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和评论三百五十余篇,两百余万字。出版散文集《沧桑风景》《记忆与游走》,长篇小说《风马牛》等。作品入选《1998中国散文精选》《2008中国散文排行榜》《中国当代人文读本(哲理卷)》等。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优秀奖、世界华人游记征文大赛优胜奖等二十多项文学大奖。
目录
序/001
祖先的村庄/001
在当下的槐树畈游走/002
远眺中的村北田野/016
古道、寺庙:遗址与当年风俗/024
人、神、鬼共居的村庄/037
门楼上的幻象/043
大门前,槐树下/044
物候里萌发的灵感/048
兜兜上的口号/051
古老的门匾/055
在草房子里高声朗读/060
课文里的黑暗与惊悚/065
心一直跳,一直跳/070
门楼上的幻影/075
少年离开了故乡/079
祠堂、桃花和诗篇/080
五分钟的相遇/085
在风景里幻想另外的风景/090
忽然到了武昌东湖/094
蛇山上的省图书馆/097
菜肴和《史记》/102
一道河湾,另一道河湾/106
少年回到了故乡/111
好像在沙漠里寻找绿荫/112
舅舅/117
人跟人不同,就像书跟书不同/121
在街头报栏前独自伤心/127
忽然见到个老马同志/131
孤独的午后,有女来访/135
不要失望,也不要幻想/140
姑娘们/143
男孩长大了/144
有个姑娘叫季三儿/148
这个姑娘叫春枝儿/152
一个姑娘不知名儿/158
又一个姑娘不知名儿/161
乡村的甜味、咸味及其他/165
父亲成为祖先/187
婶娘/209
后记/258
内容摘要
这是一部融入作者对故土浓郁怀旧情愫的长篇散文集,书中追忆了20世纪古楚原乡某个家族人、事与时代的沧桑之变,饱含着作者独有的思考与感悟。
鬼魅的传说、古老的祭祀、神秘的巫医、繁重的劳动等几代家族祖先的生存境况,农民宿命以及苦难中坚强的人,苦涩的自尊、执着的精神追求,如此种种本真的生命样态,在古朴、苍茫、雄浑的氛围中,在作者对日趋边缘化的乡村回望中一一生动呈现。
主编推荐
初春时节,绿遍天涯,原野空旷安宁,我是它上面一个孤独的人影——在熟悉的故乡失落了道路,也失落了情感的家园,只能在记忆中游走寻找,百转千回,内心的天地荆棘丛生、榛莽遍地。这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人跟人不同,就像书与书不同。书就是人,是人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凭着坚硬的文学爱好与理想,对浪漫的精神追求永葆向往,用仁慈的文字重新营构家园,塑造家园的精神品格。不断前行却是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
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远方,我们只能一直在路上。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作序,倾情推荐。
精彩内容
祖先的村庄在当下的槐树畈游走多么茂盛蓬勃的植物啊,而这却是村子的中心!
心里想,一个村庄,要是它的植物——杂树、蒿草和荆棘——太茂盛了,那么,人就不会茂盛。
满眼是成堆的恣意自由的植物,而耳朵承受着静的压力——耳畔太静了,似乎听得见风丝吹过耳廓的声响,而身边的一切:树木,房屋,水坑,蒿草,一切都凝滞了。这岑寂,这静,不像是真实的人间。可这明明是我的村庄,我站立之地就是我家老屋的门前,这,绝不会弄错。
物象与气氛高度默契,或者说静寂的气氛由周遭的事物辐射而生——是的,它无声,也无形,却是一种存在。
面前是三座稍稍前后错落、废弃多年的房舍:东边两座,红砖红瓦,三开间平房;西边一座,稍稍靠后一点,二层水泥楼房。三座房前后已被杂树野蒿拥堵包围,无法靠近。不见一鸡一狗,也不见猫的影子。阒寂无声,静得可怕。只有阳光似乎依然炽烈,却也孤独。我不禁想起《聊斋志异》里鬼狐妖魅的世界。
然而我到底不能承认这是那个世界;因为这是我的村庄、我的老家、我的祖宅……近年来,我一年总要回村一趟,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外面讨生活的人,这不算太少。所有的归来,都只是回到村子前头大弟的家,有时会到老屋前来看看;有时在村里走走。现在我就站在老屋前,情景又有演进,它更破败更荒凉了,杂树蒿草蹿得更高,简直插不进脚去,竟然无来由地长出了两三丛荆棘,也不知是打哪里来的种子,鸟雀衔来的?大风吹来的?反正与人无关。这景象不独我家老屋,你在村里走,偌大的村子,废弃的房屋很多,却很少看到人。杂树、野蒿和荆棘疯狂生长,它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野蛮生长、共同繁荣,大有让村庄返回原始荒野的雄心;是的,它们得天独厚,人类已经给它们制造了这样的千古难逢的机遇。
站在这些弃屋前,我感觉到凉气森森——我在心里自问:植物们有了得以复兴的机遇;而曾经活跃,后来遁逃的鬼神狐妖是否也得到了重新登场的机会呢?
面前这三座房,东边的一座是我堂叔的。堂叔是二爷的小儿子,他孤身一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在城里捡破烂、拉三轮,后来又开电麻木,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屋顶多处塌陷,门已朽坏,荆棘封门。当中的一座就是我家的。早先,这里是一座三进的深宅大院,有彩绘的门楼和青石砌的天井。百年前西横屋分给了三曾祖,三曾祖拆了西横屋,在原址另盖了三间面朝南的正屋,老院子从此破了相。我小的时候,院子、门楼和二道厅已经消失,但石门枋和前院墙残存着,“耕读传家”的砖匾依旧清晰可辨。那时候,东横屋住的是二奶奶家,正屋堂间和西梢间住的是我家,正屋东梢间住的是小爹家,这都是大家族不断分家的结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二奶奶拆了东横屋,用原木料砖瓦在东边另盖了两间,就是现在东边小叔这房。小爹拆了老正屋东梢间,在前边另盖了两间新房(后来再拆了这房在后边另盖三间,逐渐演变成现在的二层楼房)。天井、石门枋和残墙也拆的拆、塌的塌,数百年的老宅彻底完结。那时候父亲在老正屋的地基上翻盖了红砖红瓦的平房,算来已经有了四十年的沧桑。自从父母去世,这屋就没人住了(我和三弟在城里生活,二弟在村前另盖了新房),它被岁月摧折,被风雨剥蚀,显得颓唐、矮小、破败不堪。门已经开裂变形,门锁锈死,窗户朽断。我站在它跟前,想找回一点昔日老院的形迹,却仿佛站在一个陌生的人家前。
西边这座二层红砖楼房的前身也是一座二进的四合院,主人麻大爷跟我爷是堂兄弟。现在的红砖楼房是刘家兄弟的。刘家三兄弟四十年前就全部离开村庄,有当兵转业在城里落户的,有出赘的,有在城里打工的,谁也不清楚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也从不回村,简直像失踪了一样。只有这封闭多年的房屋标志着村里有过这户人家。
向后走去,又是一排房屋。当年可没这一排楼房;当年这里是村后的水田,田野的起点,水田一块接一块,绵延出旷远的田野,以及更远的田野之外的村庄——童年时,我曾经遥望那些村庄之外的远方的天空,想象北京城的雄伟与繁华,想象天安门;在想象里感觉生在人间的幸福和人生遐想的无限美妙。
可惜,童年逝去,这样的想象永不再来,而这样的幸福永不重现。不仅仅是我家的老院,整个村庄也根本改变了模样,想找到一点当年的痕迹完全没有可能。
这是陌生的老家。
那一年,我七八岁,西边的四合院还十分完整,青砖青瓦,正屋、横屋和门楼严整结合,屋脊两端是高翘的鸱吻,在乡土气息浓厚的村子里保持着不合时宜的旧时威严。后来,麻大爷迁居别的村庄,四合院分给别人居住。据说四合院后边原来是带围墙的后园,但这时候只是一块平庸的隙地,长着一棵枣树,隔几步还有一棵枣树。土场边缘隆起一道坎,那就是后园的旧墙基。旧墙基下就是水田了,是村北田野的起点。
那个午后突然起了一场暴风雨,雷鸣电闪,风狂雨猛。我们赶紧躲进家里,父亲插上门闩,狂暴的风摇得门哐哐乱响,像一头野兽发了疯要扑进屋。院子里雨水倾盆而下,风雨声和霹雳声震耳欲聋,声势吓人。但一眨眼工夫风息雨止,雨后的乡村青天如碧,凉爽清新,村里村外满眼翠绿。这是当年乡村的普通风景,也是消失了的风景。大自然是风景里绝对的主体,村庄是小的,房屋是小的。人类行为弄出来的一切痕迹微不足道,仅仅是这浑然博大风景的点缀而已。
那时候村里有很多枣树,正是阴历七月初,枣子红了屁股。暴风雨才一歇,我就提着小筐跑到屋后去捡枣。刘家屋后已有三两个孩子,各自在东一摊西一摊的积水和残枝碎叶里匆匆寻找落枣儿,忽听得一个孩子大叫:“看,快看!”大家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村北碧绿的田野上,在小堰和北大堰之间,有一个红色的影子慢慢移动着……“鬼——!”谁大叫了一声,大家扭头就跑。父亲跟几个大人在远处谈论暴雨和庄稼,听了我们的说道,也抬眼去看,奇怪,竟然什么也看不见,蓝天白云下,漠漠的原野空旷无边,新鲜而寂寥……议论纷纷,有人说那是矮傩子,我们小孩子听了惊悚不已,心里半天不能平静。
“矮傩子”大概是自古以来东乡葫芦湖就有的传说,“矮傩子”在人们言语里出现的频率很高,是谈话的兴奋点,类似于今天演艺明星的八卦。我听得多了,知道它并不多可怕,不过是一种无害而矮小的鬼魅。有一回我听见黄嬷嬷跟我妈闲聊,说当年她家住在村东梢的时候,一天傍晚,她端着筲箕到门前的钟家大堰去洗菜,快到堰边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矮傩子正从菜园篱笆下往堰里走去,很矮,人形,像一个小孩儿,走不快,挨着地面向前挪呀挪呀,但也很快走入水里不见了。她说那个矮傩子腿短,一身黑衣裳。黄嬷嬷讲完,韩舅母也插进来讲了,说是有一回她起早去东冲割麦,天刚麻麻亮,走到小堰上头的水沟,看见沟外的麦田边有一个矮傩子。矮傩子也看见了韩舅母,立刻向麦地深处走去,一走一拐的,走不快,但一眨眼就消逝在麦棵里不见了。她们谈得那么逼真生动,我听得津津有味,但心里是有点憷的。我知道,这东西毕竟是鬼魅而不是人类,虽然它对人类并没有危害。是的,现在想来,这个奇特的“矮傩子”算得上鬼怪世界里的一个例外,它从来不与人发生纠葛,不干扰人类的生活,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它仿佛是鬼神世界的隐士,与世无争,乡下普普通通的池塘、麦田和溪水就是它的桃花源。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不能轻易否定黄嬷嬷和韩舅母的话,她们说那是她们亲眼所见;但是对我而言,又只是耳听的。那么,她们的陈述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当年的我在信与不信间左右为难,现在的我就肯定了吗?不,我仍然左右为难。只不过比当年多了一些疑惑:言说的真实性在哪里?如何才能让人的言说取信于听者?言说者、听者和言说对象之间究竟能否达到同一?
也许还是相信黄嬷嬷和韩舅母的好,一个人、鬼、神共存的世界多么有意思啊;再说,这样的世界和人间,不是让一生受苦的人们多出了一点对未来的希望,至少是多出了一点安慰吗?哪怕是多出一点麻醉也好啊。至少至少,在当年的乡下人的梦境里,比当今的人多出了一些与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惊悚;而这种并非关乎生计的惊悚不也是一种人生滋味吗?大家不是都在说,现在的人生,太实际了,就像一块生铁块子、一片干抹布和一部拙劣至极的烂片。
那时候,槐树畈的人相信身边有许多鬼神。更早些,乡下人的生活里处处可见与鬼神相关的物象,比如庙宇、道观和坟场。这些鬼神生活的场所与槐树畈人的生存空间相杂错,难分界线。据说我家后园墙外的东北角曾有一个土地庙。我家跟麻大爷家是一个高祖,两座院子相邻,后园的围墙也相连。那时候,一般的村庄都有土地庙,是一个村庄公有的祭祀场所,而这个土地庙却是我们家专有的。那时候我的祖宗是村里的“大户”,有钱有地位,属于乡绅之流。也许是要虔诚地感谢土地爷的关照与厚爱,也许是希望土地爷赐予更多的财富,也许是显示乡绅与众不同的地位,我的祖先就给自家建了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据说庙是极小的,矮矮的不过五尺之高,只能供土地爷土地奶奶两个塑像,前面放一只小香炉。祖先们上香礼拜的时候,一拱手就触碰到它的瓦檐。但再小的庙,其供奉的神灵也是法力广大的,只能虔敬小心、敬奉如仪,不可存轻慢之心。代一代,我的祖先们就这样站在土地庙前,拱手上香,顶礼膜拜。小时候我常常独立在传说中的土地庙遗址前,寻找祖先留在地上的脚印。我看见地上生长出茂盛的植物根蔸,它生生不息,年年发出新枝。我怀疑它就是祖先的脚印所化,我毫不怀疑脚印也是有灵性的,人死了,留下的脚印不死,传递着人的精神和愿望,变化为这样的植物,借以向后人表达他们的灵魂与精神。站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祖先的身影,他们的祝祷之声在时空延续、飘荡。
后来我们家人口繁衍很快,一棵大树不断地分杈再分杈,枝杈越来越细瘦。后来渐渐穷了;既然穷了,土地庙的香火就不再旺。但这土地庙坚持了很久,穷过来的后人们把它当作一种荣光,也当作一种祖传的精神咬牙坚守,正是所谓“穷不舍志”的标志。但终于坚守不住,六十年前那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到来了,这是国运大势,不会顾忌到你一个偏僻乡村某户人家的土地小庙。我家的土地庙很快颓败,而后消失。
从我有记忆开始,屋后就是一块隙地(这是祖先们当年的后园),叔叔在隙地左边开辟了一块窄长的小菜园子,园子边长着一棵枣树。婶娘栽了木槿作为篱笆,秋天木槿盛开蓝紫色的花朵,静静地伫立在清淡温煦的秋日阳光下。后园的旧墙基做了菜园子的北边缘,另一段旧墙基上长着一丛孤独的枳树,树丛上攀爬着一棵瘦瘦的野蔷薇。春天野蔷薇开粉红的花,枳树开洁白的花,都比别处的清瘦,连带吹过的春风也带了些微的凉意。到秋天野蔷薇结出珊瑚珠似的小红果儿,枳树则结几个橙黄的橘子似的果子,挂在秋风里。这一切都暗示着某种往昔岁月,如果你的心够敏感,就会感觉到它呈现出的没落意味。这意味曾使我年幼的心备觉苍凉和哀伤。我在旧墙基上寻找土地庙的痕迹,臆想祖先们敬神的情景,我知道那是一定有传统程式和礼仪的——关于季节和时刻,关于香烛祭品,关于着装盥洗,关于身姿和手势……土地庙的消失与湮灭有一个过程,香火也是逐渐冷清下来的,其中必有许多的细节,包括人的心理演化,也许还有神的哀伤和退走过程——如果真的有神,那么神如何看待人类对他/她的冷淡与遗忘?
我们无法得知答案。一切都消逝在时间中,永无重现的可能。
作为一个有历史的村子,槐树畈的坟场是很多的。那些零散的坟包大多散布在村外庄稼地里,有些坟包年代久远,地处偏僻,人迹罕至,坟上青草茂盛,阴气森森,孩子们割草时望而生畏,不敢走近。这样的地方却正是小动物们的家园,草丛下藏着洞穴,是野兔、狐狸和猪獾们的府邸。
家族墓地竖着丛林似的墓碑。村前大路左边是我们家族的坟地,埋葬着我的历代祖先,我六七岁时亲历了曾祖母棺材下葬的场面。那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乡村保持着旧的丧葬习俗,下葬前一晚请了陈瞎*在天井院里唱孝歌,他一边敲着架子鼓一边唱,咚咚咚,咚咚咚,曲调苍凉而悲伤。四周站满了村里的老少,一律的神情庄重而沉思。翌日送葬,亲戚们送的是灵屋子,那是一座纸扎的花花绿绿的宫殿,楼台参差,檐角高耸;还有纸扎的童男童女,画着深黛的眉眼,裙裾飘飘。颜色是分外的鲜艳,形象也非常的生动;只是我感觉有一点阴气,森森的叫人害怕。灵屋子最后都被一把火烧了,噼噼啪啪,火焰熊熊,宫殿楼阁和纸人纸马在烈焰中倒塌、焚烧,化为青烟和灰烬(而后来就流行送花圈了,近年也有纸扎的电视机和汽车等,这也是与时俱进)。东冈脚下的坡地上也有一大片坟墓,也有林立的墓碑,那是本村陈氏家族的墓地,也是我们放牛的好牧场。我一一看过那些石碑,都是清朝的,什么“嘉庆”“道光”“光绪”,尚未见到有民国以后的。也许民国以后国民都穷了,再也买不起一块石碑了;或者是自民国以来社会动乱频繁,人心不古,把千年遗传下来的传统丢到了脑后?
村里也有老坟场与人家相杂处。村子后边有一座大坟,小时候我和伙伴们在坟上跑上跑下,冲冲打打,高喊着:“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坟边长着一棵大枣树,秋天结了满枝玛瑙似的枣子,我常常站在坟包上一砖头扔上去,树枝被击中,摇晃着落下枣子来。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座无主孤坟,直到前几年,有一回跟八十岁的堂叔席道甫闲谈,才知道那就是我们家族开山祖的坟。我竟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都不知道里面躺着我十二代以前的祖宗!连那坟前的石碑也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扳倒,后来就失散了。后来出生的子孙就以为这是座无主野坟。后来之后的后来,坟包渐渐矮下去,成为平地,被新盖的楼房紧紧挤在当中,邻近的一家在上面盖了猪圈,坟包完全消失了。而猪圈的主人就是始祖的第十一代后裔……前几年修建始祖墓园,想找那块碑,怎么也找不到了,只好另刻了一块新的。其他那些村里村外的坟墓遭遇也差不多,坟都平掉种了庄稼或建了房屋,石碑都拉倒了,有的支了野桥,有的被凿成牛槽摆进了生产队的牛栏。集体解散之后,这些面目全非的石碑再次流散,不知落脚何处。
族兄兴斌说,他小时候坟上的草长得好,他常在这里放牛。这使我忽然明白,当初村里人口少,房屋稀,这块地方属于村外的空旷之地;后来子孙繁衍,人家就与坟墓为邻了。
不错,就是这样,我家东南边隔着一块窄地也有两三座老坟,这些坟上长着厚厚的稨草,秋凉草黄的时候,我的外婆就到坟上来铲草。坟边有一条二尺宽的小路,人们从这条小路到井上挑水。有一回,程奶奶梦见自己在这条小路上走,迎面碰见两三个提着烟袋、穿着长袄的白胡子老头,程奶奶没见过他们。一个老头对同伴说,这是某某家的媳妇。白天程奶奶说给本家老爷子们听,老爷子们说那是老坟里的祖宗啊,你不认得他们,他们认得你哩。原来这片老坟里埋着程奶奶这一支派的先辈。
表哥其宏说,有一回他给生产队看仓库,半夜梦见两个白胡子老头进了仓库,一个老头弯腰看了看睡觉的他,对另一个老头说,这是席家的外甥,莫惊动他。表兄觉得奇怪,说给舅舅听,舅舅哈哈一笑,说,你不晓得仓库后头的坟场里埋的都是席家先人吗?那两个老头就是坟里的祖宗啊。
那时候人们梦见死去的祖宗是很寻常的事,大家不以为怪,并且多半当了真,以为那是当然的。人们通过梦境与鬼神共同生存,在梦境里产生希冀,受到惊吓或生出恐慌;但多数时候得到的是精神慰藉。这样的生活虚实相杂,既是近前的实在,也是玄远的梦幻。
一些深宅大院的陈年老屋也是传说中的精怪之窟。人们一直说,麻大爷这座四合院当年有一个皮狐子精。一天,麻大爷的爹从外面回来,进了门楼,穿过天井院子,登上台阶,推开大门进了堂屋,忽然觉得异常,一抬头,看见迎面的横梁上垂下一条竹扫帚似的大尾巴,循着尾巴往上看去,梁上坐着一个毛茸茸的怪物,绿莹莹的两只眼睛正盯着他看呢。麻大爷的爹吓得一个趔趄,转身就跑,然后喊了众人小心翼翼地回来,探头进屋去看,那怪物已无影无踪……听了这个传说后,少年的我再不敢独自一人进那院子里去,平时想一想这传说就会眉毛直跳,那幽深的大屋成了我少年时期最恐惧的去处。而我很弄不懂麻大爷一家三代人是如何在这充满危险的大屋里过日子的。也许这皮狐子精并不危害人类,除非不得已,它不会在人前显形;它与宅子的主人相安无事,自得其乐,算是一对好邻居吧?
麻大爷浓眉方脸,矮个儿,身板结实,脸上有大点大点的黑麻子。他和大奶奶都是脾气极好的老人,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年正月初一我和两三个本家的孩子都到那野外长渠边的草房子去拜年。麻大爷见了我们来,高兴得不行,笑呵呵的,亲热地叫着我们的小名,问这问那,大奶奶则颠着一双小脚端出爆米花、花生和荸荠,叫我们尽情地吃,然后弄一桌“九大碗”酒席,肥肉块子切得又厚又大,热腾腾的,满满地盛了两大碗;麻大爷怕我们客气,不断往我们碗里夹肥肉,每一回都让我们吃个够。他的儿子是人民教师,拿国家工资,比一般人家富裕,过年待客的酒肉很充足。所以每年正月初一给麻大爷拜年雷打不动,成为我少年时代最高兴的事情;即使刮风下雪、冰天雪地,我和本家的兄弟们都不会耽误。
麻大爷的老屋里有皮狐子精,院子后面的大椿树却住着许多鸟。父亲生前给我讲,那椿树不高,却有水缸那么粗,分了无数的枝杈,树冠浓密繁茂,老鹳们在树上筑了一百二十多个窝。每天早晨老鹳醒来后外出觅食,傍晚从外面归来,都会在树顶盘旋一阵,黑压压地乱飞,叫声响彻村庄,传到很远的野外。有一回暴风雨之后,树下落了许多雏鸟。这棵大椿树在我的童年已经不存在了,替代它的是两棵枣树;暴风雨过后没有雏鹳掉落,只有落枣。但我想,地上的残枝败叶和积水应该是一样的。另外,我们见到了村北田野上的怪影。有人说那是矮傩子。
老鹳这种鸟我小时候是见过的。大舅家跟我家隔着两三座坟包、一块菜园子和一条水沟。大舅门前就有一棵大椿树,树干笔直而高,树皮光滑,枝叶繁茂,其中就有好多老鹳的窝。老鹳是大型鸟,模样极像鹤,羽毛却是灰黑色。我常常仰面看着老鹳在树顶环绕飞翔,慢慢落到窝里,听它们的一片聒噪,这样的聒噪使村庄显得分外有生气,分外温暖。村里只有这棵树上栖息着老鹳。那老鹳大约也有几十只吧,它们集中在这棵大椿树上做巢,这棵大椿树算得上老鹳的“村庄”了。后来这棵椿树被砍倒,残枝碎叶中混杂着老鹳的摔碎的巢。那个傍晚老鹳失去了家园,无处安身,在倒下的大椿树上空盘旋悲鸣,久久不肯离去,从此后村里再也没见到老鹳的影子。那是我们村,也是我们葫芦湖乡,甚至整个鄂西北地区最后所见的老鹳。
人跟老鹳也差不多,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麻大爷这座祖宅大院,前后住了三代人。麻大爷离开祖宅迁居别处之后,曾厚英住进了这座大房子。但她在这屋里住了四五年之后,竟然抛弃了这座全村最好的大瓦房,搬到别处去住了。那个村子是她的老家,但因为离开太久,到底人地生疏,住不下去,几年后再次搬家,却没回槐树畈,而是落户在上面的村子双庙畈,盖了两间低矮简陋的土坯草房。她这一番折腾是一个难解的谜,其中必有难言之隐。
曾厚英算我的远房亲戚,跟我妈非常要好,搬走后她每年总要回槐树畈一二趟,来了必然到我家,跟我妈亲热地说上半天话。我对这个母亲的好友印象很好。但是她生前缄口不提搬家的原因,即使对我母亲也不提。或者说过吧,但那只会是托词,不会是真正的原因。如今曾厚英过世多年,个中缘故就更无从知道了。
曾厚英搬走后这两间大正屋归了生产队,空了两年,只做临时开会使用。空了几年之后,刘支书看中了,就拿村西自家的房子作了交换搬过来住,成了我家邻居。刘支书的老婆吴奶奶个子高大,面皮黧黑,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你跟她对面站着,她的微笑比她的话要多很多。她跟我妈也很要好。不幸的是刘家搬来后也没有好运,先是吴奶奶得了乳腺癌,到了晚期,人十分虚弱;刘支书因种种变故抛下患病的老婆和四个孩子上吊死了。奇特的是刘支书上吊不是在屋梁上,而是在东横屋的红薯窖里。刘支书个子矮小,他在窖口横一根木杠,系上绳,把自己挂上去,就这样吊死了。这样的上吊法也是一种创造,起码,没有惊动病入膏肓的老婆吴奶奶,也没有吓着他的孩子们。吴奶奶也很快死了,于是刘家的孩子们成了孤儿,年年生产队照顾他们的口粮。刘家的孩子们成人之后,把旧房换成二层红砖楼房,然后一个个离开了村子,三十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踏进一步。
当年,老宅院子门前的场子上有绿茸茸的青草地,那是鸡群的乐园。草地外是几口相连的清水池塘,岸边浅水中丛生的石菖蒲有姜一样的根和肉棒似的花穗。柳枝垂在水上,莼菜开着黄绸般的花朵。初夏时节,麦芒小鱼成群地游,倏而浮在水面,倏而沉入水下。塘边各家菜园,春夏是苋菜、茄子和辣椒,冬天是白菜和萝卜。摘了菜,在塘边洗净,端进厨房炒了上桌。
这草地、池塘和菜园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初。后来清水塘被一点点地填掉,上面盖了两三户人家的房屋,香蒲、莼草和小鱼们渐渐失去家园。那时候我还在村里当青年社员。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污水坑,被人倒了红白黑赤的现代垃圾,散发着怪味。盖在水塘上的房屋也塌了,人不知到了哪里。
站在少年时站过的地方回想往昔,虽然也看见许多明亮的贴着马赛克的楼房,我却感到陌生和荒凉。一切都已远逝。
媒体评论
席星荃具有现代观念,特别对散文观念有一种突破的渴望,超越一般的写作者。这一本新作继续写他的故乡槐树畈,历史的场景前后延展百余年,比他之前的文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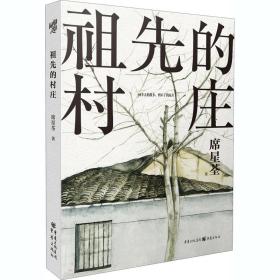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