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雅明传(艺文志·人物系列)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73.69 5.1折 ¥ 145 全新
库存9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霍华德·艾兰,(美)迈克尔·詹宁斯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2923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145元
货号31497600
上书时间2024-06-0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霍华德•艾兰Howard Eiland
耶鲁大学文学博士,曾执教于耶鲁大学、波士顿学院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出版社四卷本《本雅明文集》编者与译者。
迈克尔•詹宁斯Michael Jennings
弗吉尼亚大学文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文学教授。哈佛大学出版社四卷本《本雅明文集》编者与译者,另著有Dialectical Images: Walter Benjamin’s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译者简介
王璞,美国布兰代斯大学副教授、比较文学项目主任。北京大学文学学士(2003)、文学硕士(2006),纽约大学比较文学博士(2012)。曾游学巴黎(2008),参与翻译本雅明《拱廊街计划》手稿,并任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研究员(2020)。出版有诗集《宝塔及其他》《新诗•王璞专辑:序章和杂咏》,学术专著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另发表有关于现代诗歌、国际左翼、批评理论和“全球六十年代”等主题的一系列文章。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柏林童年:1892—1912
第二章 青年形而上学:柏林和弗莱堡,1912—1914
第三章 批评的概念:柏林、慕尼黑、伯尔尼,1915—1919
第四章 亲合力:柏林和海德堡,1920—1922
第五章 学术游牧民:法兰克福、柏林、卡普里,1923—1925
第六章 魏玛知识分子:柏林和莫斯科,1925—1928
第七章 毁灭性人格:柏林、巴黎、伊维萨岛,1929—1932
第八章 流亡:巴黎和伊维萨岛,1933—1934 479
第九章 巴黎拱廊街:巴黎、圣雷莫、斯科福斯堡海岸,1935—1937 590
第十章 波德莱尔与巴黎街道:巴黎、圣雷莫、斯科福斯堡海岸,1938—1939
第十一章 历史的天使:巴黎、讷韦尔、马赛、波尔特沃,1939—1940
尾 声
缩略书名表
参考文献选
致 谢
索 引
译后记:评传的可能性
本雅明著作中译目录
内容摘要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是20世纪上半叶至为重要的思想家,其观点与思想异常迷人,却也捉摸不定,对整个20世纪的人文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本雅明学术兴趣广泛,横跨哲学、文学、艺术、摄影、电影、建筑、翻译等,却从未被限定在某个现代学术领域、某种写作文体和某类思想范式之中。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本雅明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发现某种形式,在其中,一种可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媲美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能够通过直接动人心魄且让人过目难忘的文采,发出回响”。
本书是一部杰出的、里程碑式的本雅明传记。两位资深的本雅明研究者兼本雅明文集编者、英译者艾兰和詹宁斯以900页之巨的篇幅,全景地描绘了本雅明的一生,以及20世纪初那个从昨日世界走向两次大战间的恢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版图。同时,本传记并非简单的生平编年,还梳理了本雅明几大重要作品的写作过程,阐发了他的主要文本,是指引我们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可靠地图。原书2014年甫一出版,便获得读者的好评与学界的肯定,并于2020年被翻译成本雅明的母语德语由苏尔坎普出版。
主编推荐
★ 长达900页的大部头传记,权威、材料丰富,全面地梳理本雅明的生平经历:从家乡柏林的成长求学到精神故乡巴黎的困顿流亡;从谋求学院一席之地失败到积极活跃于报刊、广播,立意成为德语世界的一流批评家;从始终孤独、复杂纠缠的亲密关系到几段同等重要但极为不同的友谊。
★ 本传记将本雅明放置于他所属的时代背景——魏玛共和国、一战、西班牙流感、纳粹德国、苏联成立,清晰地展现他是如何被身处的欧洲历史所塑造。
★ 本书涉及同时代思想文化人物众多,施米特、海德格尔、布莱希特、阿伦特、阿多诺、霍克海默、布洛赫、克拉考尔、肖勒姆、纪德、巴塔耶,等等,提供了一幅20世纪初德法知识分子群像,让本雅明在时代的智识星丛中绽放光芒。
★ 思想、文本是本雅明一生活动最璀璨的结晶,本传记不仅提供完备的编年历史,也细致梳理了本雅明的主要作品,敏锐、精巧地分析了本雅明的哲学思想,因而是指引读者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可靠地图。
★ 本书作者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雅明选集英译本的编者与译者,是当前很好的本雅明研究学者,传记的可靠性与学术性有保证,并已被翻译引入本雅明的祖国德国。
精彩内容
导 言
德国犹太批评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现在被普遍认为是欧洲现代性最重要的见证之一。尽管他的写作生涯相对短暂——他的生命在逃离纳粹途中,于西班牙边境过早地终结——但他身后留下了在深度和丰富程度上都令人震惊的作品。在他所谓的“德语文学的学徒期”,他做出了关于浪漫主义批评、歌德和巴洛克悲悼剧(Trauerspiel)的不朽研究,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苏联激进文化和支配巴黎文坛的极端现代主义的独具慧眼的倡导者。在20年代后半期,他处在现今以“魏玛文化”为人所知的诸多发展的中心。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拉斯洛?莫霍伊-纳吉(LászlóMoholy-Nagy)这些友人一道,他参与构建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一种先锋现实主义——当时这种新方式正在挣脱塑造了威廉帝国时期德国文艺的那种文绉绉的现代主义。这一时期,随着写作赢得认可,本雅明产生了一个并非不切实际的希望,他想成为“德语文学的首要批评家”。同时,他和朋友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将大众文化变成严肃研究的对象:本雅明所作的论文涉及儿童文学、玩具、赌博、笔迹学、色情物品、旅游、民间艺术、被排斥群体(比如精神病人)的艺术、饮食,并讨论到各种不同的媒体,诸如电影、广播、摄影和插图出版业。他一生中的最后十年基本上是在流亡中度过,其间相当一部分的写作为《拱廊街计划》(TheArcadeProject)的衍生品,这一“计划”是他对19世纪中叶法国都市商品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做的文化史研究。虽然“拱廊街计划”只留下一座巨大的未完成的“躯干雕塑”,但贯穿其中的探索和思考激发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比如写于1936年的著名论战文章《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TheWorkofArtintheAgeofItsTechnologicalReproducibility”)和那几篇将波德莱尔定位为现代性代表作家的论文。但本雅明并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批评家和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家,他还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介乎虚构、纪实报道、文化分析和回忆录之间的作品。他1928年的“蒙太奇之书”《单行道》(One-WayStreet),尤其还有生前未发表的《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BerlinChildhoodaround1900),都可谓现代杰作。最后,本雅明的大量作品拒绝文体分类。在或长或短的散文作品中,有专著,论文,评论,哲学、历史编纂学和自传片段的结集,广播稿,书信和其他文学-历史材料的编辑、短篇小说、日记。他的作品还有诗歌、法语散文和诗歌的翻译、各类篇幅和重要性不一的随想片段。
在这些作品中被召唤出的种种浓缩的“意象世界”,显影了20世纪里最为动荡的一些年代。生长在1900年前后柏林一个归化的富裕犹太家庭,本雅明是德意志帝国之子:他的回忆录充满了对皇帝热衷的那些纪念性建筑的追想。但他同时也是爆炸式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子;到1900年,柏林已是欧洲最现代的城市,新兴技术四处迅猛发展。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曾反对德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因此在瑞士度过了大部分战时岁月——但战争的“灭绝之夜”的图景弥漫于他的作品之中。在魏玛共和国存在的那十四年间,本雅明首先经历了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的血的冲突,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早期毁灭性的恶性通货膨胀,最后经历了20年代后期令国家陷入瘫痪的政治纷争,正是这种局面导致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在1933年夺权。和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本雅明在1933年春逃离了这个国家,再没有回来。他人生中的最后七年在巴黎流亡,这段岁月他孤立、贫穷,出版渠道相对缺乏。他永远不能忘记,“在有些地方我可以挣到最低收入,在有些地方我可以靠最低收入过活,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他事业的最后阶段见证了即将来临的战争阴影蔓延整个欧洲。
为什么本雅明的作品在其去世七十年后仍对学者和一般读者都富有感召力呢?首先是观点的力量:关于许多重要作家、关于写作本身的可能性、关于技术媒介的潜能和隐患、关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欧洲现代性境况,他的作品都重塑了我们的理解。
但是如果人们忽略了他那独特地蚀刻出来的语言媒介——也即诡异(uncanny)的本雅明风格——那么就无法全面领会他的影响力。仅仅作为句子的工匠,本雅明就足以和他那个时代最灵活和最深刻的作家比肩,而且他还是一个先锋的形式创新者:他最有特色的作品是以他称作“思想图像”(Denkbild)的东西为基础的。这个名称来自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指一种格言式的散文形式,它将哲学分析融于具体意象,产生出标志性的批判性摹仿(criticalmimesis)。即便是他看起来完全论说性的文章,也时常由这些一针见血的“思想图像”按照先锋派蒙太奇原则隐秘地编排而成。本雅明的天才就在于,他能发现某种形式,在其中,一种可与同时代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媲美的深刻性和复杂性,通过直接动人心魄且让人过目难忘的文采,发出回响。因此,阅读他既是一种智识体验,也是一种感官体验。就像是对浸了茶的玛德琳蛋糕的第一口品尝:朦胧间忆起的世界在想象中盛大绽放。当语句徘徊,聚集成星丛,又开始变换排列,它们就微妙地和一种正在生成的重新组合的逻辑构成同调,慢慢释放出它们的破坏潜能。
然而,相对于本雅明作品强烈的直接性,本雅明其人始终难以把握。正如其作品的多面性一样,他的个人信念也组成了他所谓的“矛盾而流动的整体”。这一贴切的说法,含有对耐心读者的召唤,也体现了其心智的富于变化且多中心的构型。但本雅明的不可捉摸,还显示出一种自觉的努力,试图在其周围保持一些封闭的用于试验的空间。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W.Adorno)曾评价,他这位朋友是“很少亮出底牌”的人,而这种深深的保留,借由面具和其他周旋策略所组成的武器库,用于守护内在生活的深井。于是就有了所有人都提到的他的极度礼貌——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复杂机制。于是就有了他的思想生活中每个阶段都表现出的成熟持重,这种沉重感让他在闲谈中也会说出神谕似的话来。于是就有了他声明过的“政策”:要竭力避免和友人过多的接触,最好把每个个人和群体都保持为他的思想的参谋。
在这一不断漂移的操作空间中,本雅明从早年起就这样为人处世,以便实现“内在于[他自己]的多种存在模式”。如果说尼采把自我看作由许多意志构成的一个社会结构,那么本雅明就把自我视为“从这分钟到下一分钟的一系列纯粹的即兴表演”。正是与一种险峭的内在辩证法相一致,个人教条主义的完全缺乏才会和一种绝对的,有时甚至无情的判断共同存在。因为瓦尔特?本雅明作为现象的多重性并不排除一种内在系统性或本质一致性的可能,正如阿多诺说他朋友的意识世界是非凡的“离心”统一体,这一意识世界通过分散为多样而构成其自身。
而调和这一麻烦的性格复杂性的,是心智绝对而炫目的卓越。朋友和故旧留下的关于本雅明其人的记录不可避免地都开始并结束于对这种力量的证明。他们也强调了他无所不在的超拔智性和他在他人面前奇特的非肉身的存在。皮埃尔?米萨克(PierreMissac)很晚才认识他,说本雅明甚至不能忍受诸如朋友把手搭在他肩膀上的举动。还有他的拉脱维亚恋人,阿西娅?拉西斯(AsjaLacis),曾说他给人以刚刚从另一颗行星赶来的印象。本雅明不断把自己称为僧侣;在每个他单独生活过的房间里—他爱说那是他的“修室”—他都挂上圣徒的画像。这表明了沉思在他毕生事业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在这种无肉身的灵气之下,却又充溢着一种活跃的有时甚至暴烈的感官能量,这一点见诸本雅明在性爱上的冒险主义,见诸他对迷幻类药物的兴趣,也见诸他对赌博的激情。
在这方面,他也还是一个矛盾体。他既向往孤独又抱怨寂寞;他经常寻求共同体,有时甚至自己去创造共同体,但也同样经常地厌恶加入任何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中,他曾担任德国青年运动(GermanYouthMovement)的积极组织者,之后他基本上退出了直接的公共参与。这种在实践层面上的退避,唯一的例外——他力图通过作品发挥重要作用的努力不算——便是他在三个相隔甚久的时机尝试创办刊物;虽然这些计划中的导 言刊物都没能面世,而每次搁浅的缘由又全然不同,但渴望会聚(symposium)——让志趣相投的思想家和作家聚在一起——是他的哲学感性中无法消除的倾向。
有一点值得特别强调。虽然本雅明身体素质平平,是一个时常显得笨拙的角色,但见过他的人首先回忆起来的,却并不是这些特征;相反他们记住的是他的勇敢。是的,按我们今天的说法,他赌博成瘾。但那也是意志的集中表达,表明他敢于用生命冒险,敢于违抗常规,敢于站在那些张力和悖论已经到达绝境的智识立场之上。瓦尔特?本雅明追求文人生涯之日,正是这种生活类型从欧洲舞台消逝之时。他弃绝了舒适、安全和荣誉,以便保持智识上的自由,保持阅读、思考及写作的时间和空间。和克拉考尔一样,他分析过威胁到他本人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存在的那些情况。所以,不仅他的方法论,而且他的全部存在似乎都遵循一种控制着一场永恒赌局的辩证节律。他的外貌和生理特征,包括他富有表现力的手势,乌龟般断断续续腾挪的步态,悠扬的嗓音,以及说话时的字正腔圆;他在书写的体力劳动中、在等待的过程中或在强迫性的收藏和游荡中所获得的快感;他的自我仪式化的怪异趣味;还有他文雅到有些乖僻的迷人气质—这一切都证实着一种旧世界式的、爱好古物的性格倾向,仿佛他是从19世纪移植过来的。(在瓦尔特?本雅明的照片中,很少有他不是穿着大衣、系着领带,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的。)而与此同时,他对像电影和广播这样的新兴技术媒体以及包括达达主义、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在内的先锋派运动都抱有强烈兴趣。这种激进的心智构造使得他和那些决意从一张白板(tabularasa)重新开始的先锋派形成了对话关系。同样,由于他尖锐的深刻、难以捉摸的思想方式与智识生活所储备的无尽幽暗,他的举止就必然否决晚期世纪高等布尔乔亚的舒适惬意,而青睐于创新。他写下的关于波德莱尔的文字也是一种自我写照:“夏尔?波德莱尔是一名潜伏特务——是他的阶级对自身统治的隐秘不满的代理人。”抛开主题和对象不谈,有三个关切始终存在于本雅明的作品中——而每一个都在传统哲学的问题中有其根基。从最初到最后,他都关注经验、历史记忆,还有这两者的显要媒介——艺术。根据它们在感知理论中的起源,这三个主题指向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而在对它们的富有流动感的阐释中,它们又带着尼采的酒神式生命哲学的印迹;作为学生的本雅明曾沉浸于这两套体系之中。正是尼采对实体的古典原则的批判——对统一性、连续性和因果律的批判——以及他激进的历史事件主义(eventism)——其中强调了“现在”在所有历史阐释中的特殊地位—为在“一战”前艺术大爆发那几年间刚刚成年的一代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根基(可以说是无根基的根基)。本雅明后来从未回避这样一种挑战:同时在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律背反之中和之外进行思考。他也从未放弃过这样阐释现实:将之看作各种力量汇聚的时空海洋,深邃而充满转变的潮涌。不过,在寻求对现代都市的面相学理解中,他最终转移到了不论对唯心主义还是对浪漫派的经验观来说都同样陌生的领域,大海的意象与迷宫建筑或拼图谜题的意象轮番出现,谜题即使不能解开也要被商讨——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需要解读的文本,是多面向的语言。
所有那些热烈的沉浸除外,这就绝然是一种与政治合拍的工作,虽然它的运作方式与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本雅明早先将政治行动定义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艺术,后来他又对政治目标的概念本身产生了怀疑。但不论怎样,政治的问题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变得更加紧迫,而当时,在那个和自身毁灭玩火的世界中,幸福的理念和救赎的理念似乎已经密不可分。他在给某些友人的信中谈论过“共产主义”(由他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演变而来),并公开宣扬无产阶级的权利,但同时他又崇尚由一个从歌德到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Keller)的漫长资产阶级文化人传统所代表的“真正的人性”和有益的道德怀疑主义。他对苏维埃俄国的巨型社会试验的热情,在托洛茨基被放逐之后实际上就消失了,虽然他继续提到革命之于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各方面与布莱希特如出一辙地列举作家的政治-教育责任。这些责任,他试图不仅通过出版作品,而且通过创办刊物——包括一份和布莱希特共同编辑的刊物——来实现。作为他战前学生运动的理论延伸,带着他不严谨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信条,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基于他对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广泛阅读,包括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鼓动者诸如傅立叶(Fourier)、圣西门(Saint-Simon)、蒲鲁东(Proudhon)和布朗基(Blanqui)。不论早期还是晚期,他与其说是一位强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不如说是一个富于幻想的起义者。也许我们可以说,对本雅明本人而言,作为一名不守规矩的“左翼局外人”,政治的问题可归结为一组体现在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矛盾。政治和神学之间、虚无主义和弥赛亚主义之间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都无法在自身中得到调和。同时也无法绕开这些相互冲突的主张。他的存在——总是在十字路口,如他曾说过的——始终横跨这些不可通约的事物,不断押下赌注。不过,如果本雅明最深的信念(convictions)依旧无法探明,那么很难质疑的是,在1924年以后,本雅明成功地将自己的哲学使命(commitments)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统一了起来,因为后者关系到商品文化在西方的地位问题。在写作关于悲悼剧研究的专著时,他就展开了和匈牙利理论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的内部辩论,他在1924年阅读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马克思的更局部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卢卡奇的表述中变成一种把社会看作“第二自然”的全景化视角——它揭示出通过商品交流过程构建起来的社会机器,人们在其中活动就好像它是确定的和自然的。因此,甚至在采用马克思式修辞之前,本雅明已经可以说他的著作是辩证的,虽然未必是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的最后一步则是这样完成的,本雅明——还有同他一道的阿多诺——把第二自然的观念加以延伸,将之定义为“幻景”(phantasmagoria),这个词来自18世纪的一种光学装置。依据这一视角,社会整体是一部机器,投影出具有内在意义和连贯性的自身形象。赋予本雅明早期写作以生命的种种哲学关切在这一思考形式中得到实现。因为,在现代商品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幻景”的观念要求承认一种内置的含混性和无法决断性,于此,我们所谓的“人”被一步步去自然化。本雅明认为,如果一种真正的经验和历史记忆在这样的条件下仍是可能的,那么艺术作品将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用他自己的激进说法,一种新的“身体空间”(bodyspace)的浮现,是和一种新的“意象空间”(imagespace)的准备相关联的。只有通过时空经验的转化,一种新的人类集体形态才可能出现。
***本雅明去世时,他庞杂的写作产出星散四处,隐匿无踪,以至于其中很大一部分看起来将无法找回。虽然他的作品许多曾经发表过,但至少同样多的作品从未在其生前发表,并以草稿、清样和片段的形态保留在他的一些友人手中,而这些友人又遍布德国、法国、巴勒斯坦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中,他的许多作品被重新找到,有些甚至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发现,有些藏身于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莫斯科的苏联档案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隐秘角落。随着本雅明作品集和书信的完整版本的出版,他的大多数文字现在都已印行。我们对其个性和人生故事的描述,主要依靠这一问世的记录。
此外,对本雅明生平和思想的各种回溯性叙述已由他的友人和同伴们发表,其中,最早监督其作品集的整理工作的人士提供得最翔实,比如格肖姆?肖勒姆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恩斯特?布洛赫、皮埃尔?米萨克和让?塞尔兹(JeanSelz)以及其他一些人士,他们大多写于本雅明的身后声名在1955年开始上升之后,而本雅明的名字从1933年起一度几乎被遗忘。我们的工作站在过去六十年间曾经研究过本雅明的生平和思想,并从中汲取灵感的几千位人士的肩膀之上。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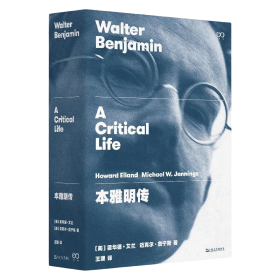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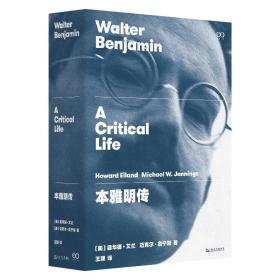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