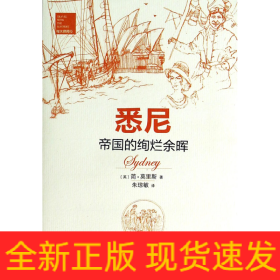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2.91 3.7折 ¥ 35 全新
仅1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英)简·莫里斯|译者:朱琼敏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ISBN9787547306468
出版时间2014-01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5元
货号2797221
上书时间2024-05-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简·莫里斯的旅行文学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国内已经出版的有《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也是其旅游文学作品之一,作者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描绘了悉尼这一澳大利亚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国际著名旅游城市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变迁。
作者简介
简·莫里斯(JanMorris),诗人、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192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曾担任《泰晤士报》和《卫报》记者多年,后专事写作。其著作超过30部,包括小说、历史与旅行文学作品。除了名作《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外,还有关于悉尼、牛津、香港、威尼斯、曼哈顿、威尔士、西班牙和加拿大等的记述。其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LettersfromHav)曾入围布克文学奖。2008年,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
目录
开篇掠影
悉尼创世纪
悉尼的外观
悉尼的风格
悉尼人
悉尼的自娱精神
悉尼的城市抱负
悉尼的帝国情结
尾声回望
致谢
内容摘要
悉尼当为此感到荣幸。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选择其作为最近的写作主题,她笔下的画面并不是一张起源卑微、简单美观的明信片。而是展现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复杂特性……几乎没有几个悉尼人对自己城市的历史与轶事的了解比得上她。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这本书的写作,有时候就像是海上冲浪;她笔下的句子如滔天巨浪,不曾因为失去平衡而喷涌而散。狂喜之情或由洞察力。有时又或是由鄙夷之心克制着……简·莫里斯用它的历史令人信服地阐释了现代悉尼。
《悉尼:帝国的绚烂余晖》是一幅人类历史全景图。你可以看到一个野蛮趋向文明的自然走势。收获了成熟窖智,也失去了野性的生猛鲜活。
精彩内容
人们依然乐意指出,澳大利亚是在加里波利的战场上成为一个国家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的悉尼也脱胎换骨——认识到自己是澳洲的一个城市,而不再是英国的一个移植城市,从此,悉尼有了自己的城市性格。尽管它的市民中仍然有98%是英国人出身,但现在他们无论是外貌、口音还是衣着都已经截然不同。让我们最后来看一看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他们,那段时间里,每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着经济大萧条,悉尼也不例外。城市里的每一处景象都折射出这场经济动荡——棚户区和施粥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寄宿公园、火车站、摇摇晃晃的船屋,母亲们带着孩子在海岸漂流货物中拾荒。共产主义兴盛,有组织的犯罪猖獗。大战后的伤残士兵在城市街道上游走,厚着脸皮沿路乞讨。在这样的不幸中,这个城市的个性达到了某种高潮,而这种性格到现在更强大至一百万倍。
在这整个世纪,经济都或多或少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个城市的规模已经延伸至郊区,这里已经远离市政厅:在西面,跨过帕拉马塔河,直抵蓝山;南面到达博特尼海湾;北面则与古老的霍克斯伯里河流放地相接。同时,沙滩文化也蓬勃发展——悉尼有着充裕的阳光、沙滩及海浪,这在明亮的近郊海岸住宅区、在救生员们壮观的竞争场面中都能充分感
受到。这个城市比19世纪80年代时感觉更有南半球的特色,也
更富太平洋风格,仿佛它正在有意改变方向。甚至在建筑方面也不再像50年前那么盲从于英国,而是发展并融入了额外的亚热带风格——屋檐、悬壁、拱廊、游廊和人行道上由铁索拉着用于遮阳的顶棚,这些都成为澳大利亚城市风格的主要特色。
经过几代的阳光照耀和物产丰足之后,人们自身也发生了突变。女性高大强健,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粗俗、
呆滞、随和但步态有力——这一度成为他们的标志。这真是纯正澳洲人的全盛时期——宽边软帽下的澳洲小伙,穿着长短裤和及膝袜,在酒吧的老地方,而他的姑娘正在房间尽头和一群女孩闲聊。
这是一个爷们儿、俗气又骄傲自大的悉尼,或者就像诗人肯尼
斯·斯莱塞(KennethSlessor)所写的,“煤气灯,稻草帽,香蕉串,坐在电车上的悉尼城”。“在一切所思所想中,”悉尼漫画家威
尔·戴森(WillDyson)在1929年宣告,“我们展示着如一个乡村老妇一样的精神。”这里是悉尼,它的地方性,真实可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地方还半念想着自己仍然是帝国大都市,并在帝国志得意满的作品中被粉饰为帝国的第二大城市。但它真的不能被如此归类。尽管它依然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但也只是自治的澳大利亚六大州府中的一个,而这个国家的联邦首都则落在180公里外的堪培拉。它的统治阶级,总体上还保持着可笑的忠诚与保守,但劳动阶层则大抵对其与英国的联系无感,并常常对共和传统无感,更无感于悲悯天下的共产主义者。
按国际标准来说,悉尼并不那么重要。它维多利亚式的地标和乔治时代风格的遗迹早在琐碎平凡的商业发展中被吞没。
在它的郊区,树木被残忍砍倒,大多数地方都变得非常讨人嫌。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几乎没有兴建过一座公共大楼,也
没有地方让人驻足观赏或者在未来数十年后有保护的价值。骄傲自大,很可能只是自卑的表现,我想公平地说,20世纪30年代是悉尼的低潮期。这个城市在回顾它肮脏的开端时,仍然记恨在心;它被病态的帝国忠诚和骚动的独立之心撕扯着。考察
它的粗俗褊狭和仇恨之心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在另一个50年里,它会在后帝国时代,一跃而成蓬勃发展的奇迹——_稍后,本书将一一描述。
两年过后,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以一种奇妙狂喜之态,悉尼开通了它的海港大桥,后者成为世界上的建筑奇迹之一,也是当时澳洲大陆上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在那个时刻,我想悉尼的当代史开始了——或者说悉尼就此定型。经过另一场世界大战,经济繁荣与萧条交替循环之后,悉尼的经济地位也随之确立。大英帝国的式微改变了它对世界的看法,欧亚大陆移民的如潮涌入改变了它的旧俗。随着18英尺帆船风驰电掣般驶过布莱德雷海角,随着摩天大楼在海岸上熠熠闪光,我们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周日午后”。
悉尼人总说他们的城市缺乏历史感,就此我不敢苟同。我发现悉尼的“过去”比其他大多数城市都更易追溯,我们对这片新大陆的开拓者如此熟悉——或知道他们的名字,又或对他们仅有泛泛的印象,我们对早期一幕幕场景的想象何其容易。
如今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念碑依然伫立,象征着维多利亚式的辉煌。大卫-琼斯已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商店”,而皮特街上的W.H.Soul药店提供“灵魂色彩”快速胶片冲印服务;财政部的内院如今是洲际酒店的咖啡馆;土地部大楼的壁龛还在等待另外25位英雄的到来。在乔治街北端附近有个急转弯,是为了避开原来政府造船厂——它的界标早已不见;而当街道转向东面,又回到市政厅旁边时,是为了躲避第一个城市墓园,在这里猪欺负过羊群。悉尼市中心这种出人意料的街道形状部分还是因为菲利普声名狼藉的小宅。坦克溪,偶尔会波澜汹涌,依然在环形码头六号码头边流入悉尼港。那里的涂鸦,从首批船舰到访时就存在了。我常常在夜晚,看到港口附近坐在岩石上的人影,似乎正在孤独冥想,一如许久之前的原住民一样。
夜幕降临后,小渔船的锚灯在水面上掠过,很容易就让人期待其中会有艘小舟驶离黑夜,它的船尾会站着一个裸体的黑女人,而船腹正升起袅袅炊烟。
灌木丛依然旺盛生长。我们将对如今的野生世界投以一瞥,以此作为对旧悉尼回顾的收尾。这里不但是城市中的乡村(rusinurbe),更是不可毁灭的自然力量。我们站在北方郊区的一座路桥上,俯身下望,看到人行道下方是一处沟谷,布满了杂乱的灌木。黄昏已至,满月徐升,三三两两的人群开始陆陆续续地在桥上聚集起来。车流畅通,夜色迷人,树丛间星
星点点的房子看不到人迹。而我们足下,河流在巨大的蕨类植物间波涛起伏。一个前臂文身的年轻人随手向桥下扔了个烟头,它闪烁
着微弱的火花,随着水流漂进了树丛。一群小孩比赛奔跑,在人行道上上下下,乐此不疲。我们在等待悉尼果蝠——就是那体型巨大的狐蝠,它们在附近某处成百上千地聚居,据说还会散发一种特有的蝙蝠味,让人惊惧。每个夜晚,它们就会离开
丛林里的栖息地,去城市搜寻,它们会飞过整个北部郊区,更会飞越港口。它们路过公寓窗口,身影扑朔迷离,人们经常能感觉到它们,却很少能看得真切。它们是地球上最南面的果蝠之一,是悉尼规模最大的“居住群”,它们逃过了所
有历史造成的劫数,如今,已经收获了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我曾经参加过保护协会的一个会议,协会地处这条路前方富有的戈登郊区内,这群人对果蝠的热情甚至让果蝠自己也会大吃一惊——那里有各个年龄层的蝙蝠爱好者,佩戴蝙蝠徽章,身穿有蝙蝠形象装饰的T恤衫,聆听热情洋溢的关于蝙蝠的讲座,认真检
视玻璃盒子里的蝙蝠骨架,并以传教士的热情派发关于蝙蝠的传单。
夜幕降临,一小群观众挤到了栏杆边,从蓊蓊郁
郁又朦朦胧胧的灌木丛里飞出一只孤单的灰首狐蝠,越过我们的头顶,又朝着港口的方向南飞而去。一两分钟后,又出现了两只,接着又出现了一小群。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散漫无序的过程,孩子们早已消磨了兴致,又开始在人行道上下奔跑起来。
“就这样了吗?”一个女孩儿问她年轻的爱人。“他妈的,”那个文身的小伙叫道。但是,又几分钟过去后,果蝠出现的速度戏剧化地加快了,它们三五成群地出现;接着,又成批出现;然后,一大群一大群地出现;最后,是一队一队地出现,直到漆黑的夜空全是它们的身影。它们川流不息地从灌木丛中倾泻而出,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就像是一次声势浩大、愤怒异常的霸权复辟。
片刻之后,它们延伸至夜空的冗长路线变得有些枯燥。等不到最后一只果蝠飞越桥面,孩子们就看够了,喊着
要回家。
P28-32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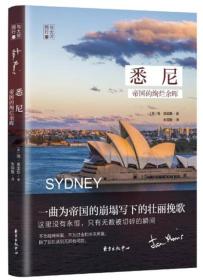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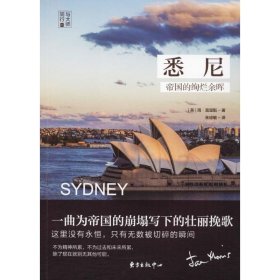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