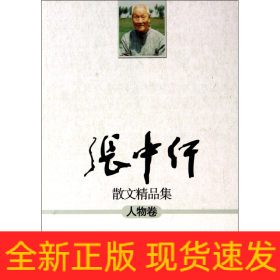
张中行散文精品集(人物卷)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10.74 4.1折 ¥ 26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张中行
出版社北方文艺
ISBN9787531726289
出版时间2011-08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26元
货号2035615
上书时间2024-05-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张中行散文平实朴拙、散淡冲荡,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记人,他勾魂摄魄,写出人物文化内涵与精神品格;状物,他机智洒脱,常发出智慧之音;言理,他冷静超脱,化高深的学理为平实的意识,充满哲学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宁静邃远之美。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流畅,文笔精妙,较好地体现了作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读来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本书《张中行散文精品集(人生卷)》收录的就是他的人物散文,记录了作者与一系列名人的故事。
作者简介
张中行(一九○九年一月~二○○六二月),曾用名张球,著名语文学家、散文家。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一九三一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三五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教中学、大学,编期刊。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辑、特约编审。著作先后出版有《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和白话》《负暄续话》《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顺生论》《谈文论语集》《负暄三话》《说梦楼谈屑》《横议集》《说书集》《流年碎影》《说梦草》《散简集存》等。
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治学严谨,其著述,谈学问以探赜索隐的知识性见长,书杂感以揆情度理的哲理性取胜,均以其真情、真知、真见,有益于世道人心,因而颇为学术界和读书界的人们所喜好,并成为当代杂体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一见。
目录
章太炎
黄晦闻
马幼渔
马一浮
邓之诚
熊十力
马叙伦
胡博士
苦雨斋
刘半农
刘叔雅
朱自清
温源宁
顾羡季
周叔迦
废名
叶恭绰
张伯驹
刘舅爷
刘佛谛
辜鸿铭
梁漱溟
叶圣陶
俞平伯
嘶位奖学家
诗人南星
祖父张伦
杨舅爷
怪物老爷
启功
季羡林
老温德
刘慎之
王世襄
凌大嫂
故园人影
内容摘要
张中行,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人称“文坛老旋风”。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本书《张中行散文精品集(人生卷)》收录的就是他的人物散文作品,共计36篇,包括:《章太炎》、《熊十力》、《苦雨斋》、《辜鸿铭》等。
精彩内容
马幼渔马幼渔先生名裕藻,是我的双重老师。30年代初我考入北京大学,选定念中国语言文学系,他是系主任,依旧说,我应该以门生礼谒见。上学时期
听过他一年课,讲的是文字学中的音韵部分。马先生虽然是宁波人,风范却没有一点精干善于拨算盘珠的样子。口才也不见佳,因而讲课的效果是平庸沉闷,甚至使人思睡,专就这一点说,颇像我的中学老师兼训育主任陈朽木先生。总之是,因为看不出他在学术以及行事方面有什么突出之点,同学们对他总是毫无惧意,甚至缺乏敬意。他早年在日本,也是听过章太炎先生讲学的。因而以太炎先生为引线,关于马先生就有个颇为不好听的评语,是某某人得其(代太炎先生)什么,某某人得其什么,马先生列在最后,是得其糊涂。
说糊涂,是近于开玩笑,难免过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马先生不过是好好先生而已。好好先生有可取和不可取的两面,可取的是不伤人,不可取的是不办事。不办事而能多年充当系主任,这或者正是北京大学容忍精神的一种表现吧?不过无论如何,他总是系主任,依照帅比将高的惯例,他就不能不出名。出名还有另外的原因,都是来自家门的。其一是有几个弟弟,其中两位在学术界相当有名:一位是马叔平(衡),金石学家,写过《石鼓文为秦刻石考》,受到门内汉的赞许,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位是马隅卿(廉),有大成就的小说学家。其二是有一位贤内助。怎么个贤法,家门之外的人自然不得详知,但马先生有时似乎愿意泄漏一点消息,于是曾因此而受到女学生的嘲弄。其三,就是这位贤内助生了个赫赫有名的女儿,名马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我在校时期,全校学生公推为校花。校花,闺门待字,其在男学生群里的地位、印象以及白日之梦等等可不言而喻,这且不管;马先生却因此而受到株连,这也不是什么过大的伤害,只是间或,当然是背地里,戏呼为老丈人。
这好好先生的印象又不只是在学生群里。大概是1933年暑期吧,整顿之风吹来,触及中文系(当时简称国文系)的也颇有一些,其大者是胡适之以文学院院长的显位兼任中文系主任,稍次是去教师之不称职者,开刀祭旗的人物是林公铎。马先生退为只算教授了,后来像是也不再讲什么课,总之是名存实亡了。
在校时期,多数人心目中的马先生不过如此,这印象即使够不上大错,也总是模糊。是30年代末,北京沦陷了,马先生因为年近花甲,没有随着学校往昆明。他原来住在景山西街(旧名西板桥),也许为了隐姓埋名,迁到王府井大街大阮府胡同,与刘半农先生(已故)的夫人住前后院(马前刘后)。其时我和同系同学李君也住在北京,寂寞,很怀念旧日的师友,而师友星散,所以有时就到马先生那里坐坐。我们发现,马先生也很寂寞,更怀念红楼中的相识,于是渐渐,我们就把到马先生那里去当做后辈的义务。
这样,日久天长,我们才明白,在校时期对马先生的认识其实并不对。
他通达,识大体,以忠恕之道待人,并非庸庸碌碌。旧日有些印象像是沾点边,也是似是而非,比如好好先生,这是我们把他的宽厚看做无原则的迁就。其实,他律己很严,对人的迁就也仅限于礼让。在这方面,可记的事情颇不少,随便举一些。还是任系主任时候,他家的某一个年轻人报考北京大学,有一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在马先生面前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今年国文会出哪类题。”马先生大怒,骂道:“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诉你考题吗?”又,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做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
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
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他爱国,有时爱到近于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我们每次去,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为了安慰老人,我们总是把消息挑选一下,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报喜不报忧。——我们确是有个忧,是马先生有个羊角疯的病根,几年反复一次,而且,据说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后会不会有意外呢?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们有些日子没去,忽然传来消息,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灯灭,早晚难免这一关,所谓达人知命,也就罢了。遗憾的是,他朝夕盼望胜利之来,七年多过去了,终于没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见的,真的胜利了,“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还能听见吗?
P6-8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