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书:一个人的地理志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3.92 4.1折 ¥ 59 全新
库存18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乔丽
出版社作家
ISBN9787521226300
出版时间2024-0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9元
货号31972590
上书时间2024-05-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乔丽,傣族,云南瑞丽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理事、云南省作协注册文艺志愿者、德宏州政协常委、瑞丽市政协常委。
目录
序 美文如玉 白庚胜_001
雾起之地_001
被月光祝福的我们_035
在故乡里生活的他们_080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两则)_099
半江渔火,一枕清霜_126
存在与消失_153
匍匐大地_182
探访宾川鸡足山_246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两则)_257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_264
我赞美家乡,但不承认我是罪人_283
附 时而行走,时而潜泳 蔡晓龄_290
后记 我的民族书写及自我描摹_293
内容摘要
《西南书》是傣族作家乔丽以中国西南地区为视角撰写的一部散文集。在本书中,作者频频回望故乡,反复吟咏着和她有关的一切:水墨画般的云南德宏与它的历史;从云南文山走到国际视野的楚图南;与友人一起探访临沧双江的茶山;在梅里雪山开启的转山之旅;探访徐霞客久驻的宾川鸡足山;触摸宣威可渡古镇的摩崖石刻……区别于口号标语式的民族书写,乔丽是以诗人的口吻,在记述个人成长的同时,重新认识和探索自己身上藏匿着的傣族基因和文化。
精彩内容
雾起之地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
在这块土地上,流传着大家耳熟能详的“云南十八怪”,“裹着毯子谈恋爱”就是其中一怪。听起来确实很奇怪,但这其实是一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他们习惯用一块大大的毛毯披在身上用以御寒,同时也有装饰之美,用法亦同汉族的披肩,平日里出门就随手披上了。
这块土地就是“勐卯”,一个来自傣族语言的音译,意即“有雾的地方”。
我喜欢称之为“雾起之地”。
1云南,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毋庸置疑地拥有着别具一格的南方气质。或许是个人的偏爱,我总觉得它不像沿海那些“南方”,不管从哪方面说,这几个“南方”都太热了。云南是彩云之南,温润但不潮湿,热情但又带着绵软的清凉,有着大家闺秀的大方和端庄,又有小家碧玉的亲和与羞涩——不要责怪我的偏心,因为我就是这块土地上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对它有着不需要解释的天然爱恋。
而瑞丽,则完美地浓缩了云南的美——粗犷与细腻毫无违和感地融合,就好像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和傣族、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这些少数民族世代混居,几种文化的交融与依存、发展,呈现出来的趣味性和魅力,因为多棱角而光芒四射。
瑞丽城地处坝子,但丝毫不觉得逼仄,因为远山足够远,麦田足够辽阔,倒像是中国水墨画里那些层层叠叠的灰黑。大片大片辽远的稻田,仿佛将落日最后的辉煌吸收殆尽,于是在星夜降临前,每一阵风来,那黄金般的尊贵便奔腾在大地上。
这样的画面,或凝固,或流动,我觉得极美。
而且我总觉得在之后的某天,它们一定会成为某位画家笔下的另一幅不亚于凡·高《乌鸦群飞的麦田》的佳作。
这块土地上有长达169.8公里的边境线,中国与缅甸作为边境线的标志有山峦、田埂、小路,或某条小河。虽说有国与国的分别,但两国的边民们宛如同一个村寨的村民。藤蔓生在中国,果实却调皮地跑到了国外;缅甸的鸡光明正大地跑到中国来,下一个蛋再回缅甸;性子贪吃的猪牛们也会趁主人一个不留神,便偷越国境吃庄稼,有时是水稻,有时是苞谷,有时是豌豆尖、蚕豆荚。主人发现后,或气急败坏地吵架,或无可奈何地付之一笑……但是到最后,都会化干戈为玉帛,毕竟大家语言相通,是文化相同的同宗同族,攀扯起来,都有着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
一位诗人曾这样写过:小河很浅,窄处,仅仅两三米。
我坐在小河边的石头上。
我看到,一只中国的白鹭,没有办任何手续,堂而皇之地飞出国境,到缅甸的竹林中消失。
这样的文字,也没有办任何手续,就堂而皇之地住进我的心里了。
从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听到有关我们中缅两国的“胞波”情,这“胞波”情从何而来呢?
我无意中发现,1995年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伊洛瓦底江两岸》里有这样的传说:远古的时候,上帝降下了两个儿子在世上,都落在伊洛瓦底江上,后来江水上涨,哥哥冲到了北方,弟弟冲到了南方,哥哥和北方的凤凰结婚,他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中国!弟弟和南方的孔雀结婚,他的后代就是今天的缅甸,这就是中国和缅甸称为“胞波”(亲戚)的缘由。
——这是作者在旅缅途中听到的民间传说,所以无论这里说“上帝降下了两个儿子”有多可疑,但中缅互称“胞波”至今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瑞丽其实不叫“瑞丽”,而叫“勐卯”,这是一个傣族名字,直译是“有雾的地方”;但如果意译的话,你就可以发挥足够的联想,译为“雾蒙蒙的地方”“雾起之地”等,或者你甚至可以译成“雾城”,这样忽然之间就有了点《雾都孤儿》的味道。
少数民族起名字都很直接,眼睛看到什么,就会起什么。譬如“大等喊”是“金水湖”,虽然这个寨子里现在已经看不见哪怕一平方米的湖水了,但通过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若干年以前,那里曾有一个拥抱晨光与夕阳的金灿灿的湖。“勐卯”这个名字的来源,确实就是因为瑞丽坝子常年有雾,尤以秋后为甚。每年冬至,浓雾便施施然驾到,将整条瑞丽江、整个坝子,一股脑地收进水袖里了。若是站在高高的勐秀山上,俯瞰瑞丽坝子,是一种不真实的空灵之美。
“勐卯”可算是德宏州境内最古老的地名之一,因为傣族曾经是这块土地上的王者。其间,元明两朝官方曾将其称为“麓川”,而明中期三征麓川后,这个名字逐渐湮灭,又恢复了“勐卯”。现在被瑞丽人称为“老城子”的傣族寨子就是当年的平麓古城。我在寨子里曾经找到两块残缺的石碑。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岁月漫长又短暂,艰难又轻易地走到了现代。而我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的很多人不知道“勐卯”这个名字,就算知道也难明其意,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那“勐卯”是什么时候悄悄地变成了“瑞丽”呢?
得从1931年8月开始说起,当时“云南王”龙云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自小生活在汉地的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显然还略为匮乏,所以他对“勐卯”这个名字无法理解,觉得这个名字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又是当地的土话译音。原话是这样说的:“不但毫无意义,且系土名译音,亟应更改,以垂永久。”上级都这么说了,那下属们只好绞尽脑汁构思一些既洋气又能名垂千古的名字了。先是勐卯行政委员丁芝庭呈报了“固边”一名,龙云不满意,说“意义广漠,碍难采用”;勐卯行政委员李典章随后想出了“鼎新”“瑞丽”“西屏”三个名字。“鼎新”和“西屏”自不待言,一取“革故鼎新”,一取“西陲屏障”之义。对于“瑞丽”这个新名字,龙云倒很喜欢,因为有根据有来历,“取义于瑞丽江,既有根据,词复雅驯”,所以,从1932年5月起,“勐卯”就成了曾用名。
这些年,随着我们的身量渐高,和我们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瑞丽江,及它身边的一切。从简易板房,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黄泥巴路,朽当当的瑞丽江竹桥,到现在林立的豪宅大院,多条车道,以及宽阔的跨江大桥。
那些消失不见了的,也就慢慢淡出了瑞丽人的记忆。
比如夕阳下,系着筒裙在江水里嬉戏的傣族少女少妇们,那油画一般动人的景色,和那些逝去的江水一起流成了历史,再不复见。那座看上去就像百岁老人一样颤巍巍的竹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不见了。
但无论是起高楼,架长桥,还是将车道扩得有原来的若干倍宽敞,道路永远不够用,房子永远不够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约而同地涌入这个昔日的荒蛮之地。
在道路、思想、经济都达到高度连接的时代,神秘与陌生都被消灭,少数民族和汉族大量通婚,民族文化被稀释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汉地的文化、观念、生活方式。而同时,在此生活的汉族人民,也被少数民族浓郁独特的文化所吸引,这些互相吸引和欣赏的具体细节表现在饮食和节庆上。少数民族爱上了四川的老火锅,辣辣的湘菜,营养丰富的粤菜,而汉族同胞们则毫不犹豫地喜欢上了这里的手抓饭、酸扒菜、撒撇、牛扒呼。
20世纪90年代,瑞丽的繁华一度达到了巅峰状态。因为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瑞丽从最偏远狭滞的西南角忽然一夜之间来了一个大转身,变成了面朝南亚、东南亚的大门。那些和我们肤色、长相不一样的人们蜂拥而入,带来了斯里兰卡五颜六色的宝石和缅甸绿莹莹的翡翠,摆在地上,放在简陋的铁皮柜上,一时之间,商贾群至,甚嚣尘上,成为中国最高调、最昂贵的“地摊货”。小小的瑞丽瞬间蒸发出腾腾的热气,这些热气来自熙熙攘攘的人群,来自进口或出口的货物,来自热辣辣交换的财富。
有趣的是,发财的大多是外地人,而本地人仍旧不紧不慢地生活着,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脚下的生存资源被分了一杯羹而焦急上火,这就是瑞丽人。
不得不承认,整个瑞丽富庶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太好了,山和水,都同样养人。
满山满坡的野菜,龙胞衣、杜鹃、螃蟹尖、鸡 、苦藤、刷把菜、鱼腥草、刺五加……没有化学污染,还多有药之效用;在动物保护法出台以前,这里满山跑的麂子、马鹿、草豹子,还有那望之令人脊背发凉的各种蛇,都是当地人的美食。所以,就是在以前最艰苦的年代,瑞丽人的日子也过得很安稳。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或者是90年代,瑞丽开始错错落落地建起了一些楼房。三层、四层、五层……高层,许多本地人和定居在此的外地人陆陆续续地拥有了在现代堪称“豪华”的自建房,房间多到住不完,这不刚好,外地人多,租给他们呗。于是本地人最常见的职业是“包租公”“包租婆”,不会大富大贵,但小日子也过得细水长流,很是滋润。
在这里,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他们对某个地名的称呼。譬如我们要说去某个地方碰头时,或某个地方位于哪个位置时,本地人最常用的表达是这样的:在老百货大楼旁边,在老电影院旁边,在老如意食堂那里,诸如此类;而外地人则会准确地说出街道名。
这些街道有名字基本是近几年的事,我们则习惯了这个城市以前没有被命名的路和残存的老建筑们。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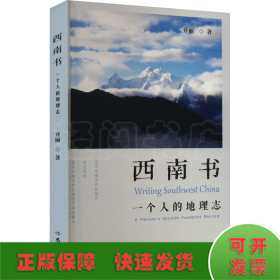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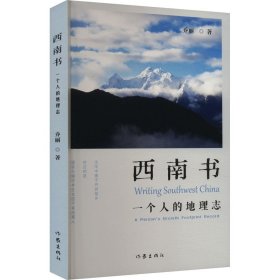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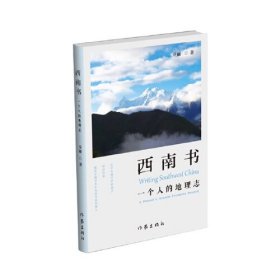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