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为了什么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8.01 2.9折 ¥ 28 全新
库存16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以马内利修女 著 华宇 译
出版社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ISBN9787807091547
出版时间2008-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28元
货号11202092
上书时间2024-12-1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可敬可爱的以马内利修女
活着,为了什么
关于帕斯卡
前言 对意义的焦虑
第一章 思想与物质
第二章 吊诡的理智
第三章 享受
第四章 解放
第五章 爱的行动
第六章 “一切是一,每一个都在另一个之中”
结语 泡沫与永恒
贫穷的富裕
前言 贫穷与富裕的吊诡
第一章 贫穷的丑闻
第二章 与穷人一起
第三章 贫穷的富裕
第四章 选择贫穷
第五章 与贫穷的基督相遇
第六章 神的选择
第七章 生命的喜悦
内容摘要
本书为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分别于2002年与2004年出版的以马内利修女的《贫穷的富裕》和《活着,为了什么?》的合集。
在《活着,为了什么?》中,作者以法国天才数学家、物理学家、思想家帕斯卡的《沉思录》为主轴,深入探讨了人生存的意义。在以马内利看来,帕斯卡的思想分为三个范畴——物质的范畴、精神的范畴和心灵的范畴,而帕斯卡思想以及人类历程的高峰,是在心灵的范畴即爱的范畴里。正是爱,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和永恒的重量;只有爱,能够让我们带着我们的伟大和可悲,继续生活在喜乐之中。
而在《贫穷的富裕》中,以马内利修女则分享了她对真正富裕的发现——施予和接受大量的爱,以及获得幸福的步骤——抛却外在的富裕,接受匮乏的生活;走出空洞的自我,以便走向他人。以马内利修女自己正是抛却物质而让生命获得全面绽放的最具说服力的证人。
作者简介
在2004年法国举行的最受喜爱女性评选活动中,出人意料,法国人心中最受喜爱的女性,既不是美丽的苏菲·玛索,也不是法国宝贝朱丽叶·比诺什,而是已经95岁高龄的以马内利修女。
以马内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原名玛德莲?桑刚,1908年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1928年正式宣誓成为修女。正如以马内利的名字一样,以马内利修女一生践行着“神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的旨意,几乎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穷苦人士。尤其是1971年在她即将退休之际,由于目睹开罗拾垃圾者的艰苦生活条件并为之震动,决定从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1993年,她以85岁的高龄被迫“退休”回到法国后,继续为贫穷人士奔走,她的事迹开始逐渐传播开来,成为继特蕾莎修女之后,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女性。
主编推荐
继特蕾莎修女之后,又一位令世界感动的女性,以她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向我们娓娓道来:物质的消费无法解除生命的焦虑,精神的思维也无法克服存在的孤寂,唯有爱的行动,在关切、付出和分享当中,生命才得以完整,人类灵性的光芒才得以晶莹绽放。
精彩内容
第一章 思想与物质
1923年的一个秋夜,我即将与帕斯卡发生关联。当时,我快满15岁。我并不知道那一年恰巧是这位思想家诞生300周年纪念。我也没料到,他会在我的人格发展上扮演关键角色。我会是今天这副模样,一个偶尔举止有些怪异的人,部分原因得归功于他。要阐述生命中这个重要经验,自然得提到帕斯卡思想的第一个范畴,也就是物质的范畴,以及人心中高涨的觊觎之情。
我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
那个时候的我,正值年少轻狂的发育期,四肢不断抽长,脸上长满了痘痘,一头乱发,噘着嘴巴,一副已经看透一切的样子。我对一切不满,凡事都成为我批评的对象。我已经开始体验到在我一生中透过各种不同方式不断折磨我的感觉:感到自己老是气愤挥拳,老是在撞墙,老是在各项事物上被迫面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我和家人住在布鲁塞尔的一栋楼房里。一楼是母亲的办公室,她在父亲过世后接管内衣工厂。二楼饭厅隔壁的房间则是我和弟弟做功课的地方。一天,我认为弟弟对我干扰太大,决定将书桌搬到三楼空间宽大的浴室窗户旁边,也因此躲过家庭老师露西小姐的控制。我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监督。生性懒惰的我(至今依然如此),经常偷看一些不入流的爱情小说。
我还有另外两大消遣:一面大镜子让我可以尽情畅快地欣赏自己,我总是对自己长得不够美丽深感懊恼。隔着窗户,我还看到一位男孩的身影,他和我一样,也是埋头在教科书堆里。很不幸,他离我太远,我没法跟他打招呼。但他仍让我开启了一箩筐的奇思幻想:他英俊吗?脸长什么样子?他几岁?叫什么?还有,他有过哪些奇特经历?我的想象力不断地、尽情地奔驰着。
我发出哀怨的叹息,打开塞得鼓胀的书包,先抽出一本,哦,是法文翻译成希腊文的练习!简直无聊之极,晚一点再来弄吧。另外一本,是将《伊利亚特》(Ilid,也译《木马屠城记》)从希腊文翻译成法文的作业——有趣多了。事实上,我运气很好,治理学校的“马利亚姐妹会”为女学生们开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课程。这在比利时堪称创举,因为那个时候,只有男生可以学习这门学科——尽管如此,上大学仍旧是男孩子拥有的特权。因此,我有许多年的时间接触了像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年至前19年,古罗马伟大诗人,曾写作田园诗与巨著《伊利亚特》,但丁在《神曲》中以他为人类智慧的代表)、荷马和柏拉图这样的天才,他们对于善与美的教导(也就是希腊文kalos kagathos,美的与好的人,亦即完美之人),是我每天的精神食粮。我喜欢遵照福列松老师要求的,用优雅、严谨的法文来翻译尤利西斯的冒险故事。我感觉这个练习促进了我智力和精神的发展。我有时会很有成就感,发现自己能将每个字词忠实地翻译出来,不因个人诠释而改变、扭曲原意。当翻译作业一完成,我从书包抽出第三本书。这会儿又是什么呢?有一页文学作品要读。希望不会太枯燥!
我打开中古世纪到现代文学选集的厚书,深呼吸一口气后,开始读起来: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柔弱的东西。
嘿,终于有个人讲些还算有意思的话!还有什么东西比芦苇更柔弱呢?一丝微风都能让它弯腰折枝。人是一根芦苇,我是一根芦苇。我不敢大声承认,可怜的玛德莲…,我其实是多么脆弱啊!我有时会大发脾气,丝毫不能掌控情绪,也无法敦促自己做事持久不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可以让我气馁,比方说一个我无法立即抓住字义的拉丁文或希腊文,一页稍微困难一点儿的物理,一篇题目说教意味浓厚的作文等,简而言之,都是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和所有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工作、烦恼还没有多到让焦虑变得麻痹的青少年一样,我也被难以解决的问题所困扰、纠缠。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一点意义也没有。读书为了什么?总之以后得工作。人到世间走一遭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一条堵塞的死路,不仅乏味得不得了,甚至蠢极了。
我看着窗外,对面屋顶上,一只大黑猫正慵懒地伸了个懒腰,将头埋在手脚当中,白色的胡须在风中微微颤抖着。它正恣意地享受黄昏时分依旧暖和的阳光。当猫咪多好!尽情享受当下,满足感官。没有烦恼,只要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睡就好。至于猫妈妈,只要能够感觉到小猫咪靠拢在它身边吸着奶,就心满意足,根本不用管什么上学念书!
我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来,回到帕斯卡的文章上:
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柔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
我大大地震惊。人是柔弱的,没错,可是他却能够思维。霎时,我眼前涌出一道光:那只猫,不会思维!我内心蠢蠢欲动。我不是动物,而是人。是的,我像猫一样会呼吸,但我是能思维的人。我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我能够思维。
我用一般少女特有的反应方式,让这个发现变得惊天动地,仿佛这是个怪异的新发明:我的生命赋有这个奇妙的能力,也就是“思维”。我重复着这个词,思维!它让我整个身体和灵魂都灼热起来。顿时之间,我感到自己的价值比猫咪要高千万倍。动物终归是动物,人呢,则会思考!我天真地雀跃欢呼:我不是猫咪,我因思维而存在!
这一次,我充满渴望地重新拿起书本继续阅读下去:
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置他于死地。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比置他于死地的宇宙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终将死亡,也知道宇宙比自己更具有优势,然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什么?与浩瀚的宇宙相比,我这根可怜微小的芦苇,尽管软弱、狭隘,仍旧拥有无可限量的价值与高贵。我像喝了酒一样愈来愈陶醉。我以前认为愚蠢极了的生命如今有了意义:突然之间,我逃过了黑洞,逃过了我徒劳对抗的困境。是的,我要活着。活着,来发展我那会思维而且超越宇宙界限的生命。我顿时感受到,我的生命不仅没有因为我的软弱与无能而一无是处,相反的,它的价值和高贵就在我的生命本身,以及它让人获得解放的能力之中。我因自己此刻站在让人意想不到、能够开启新视野的大门门槛前而神魂荡漾。诚如我将在稍后加以说明的,我预感到人虽然软弱,却能够成为这个轻易就能把人毁于一旦的宇宙的主宰。啊,我逃脱了!
我继续读完这段文字: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帕斯卡要引导我们到哪儿去呢?他从芦苇说起,最后谈到了道德!这是一个多么冷漠、多么令人扫兴的词啊!就像是在我激昂的热情上头浇了沁凉的冰水一样。我已经提过,我不能忍受任何义务和约束。我早在“六八运动”…开始之前就服膺了他们著名的口号:“禁止去禁止!”道德象征了钳制你的枷锁,阻止你朝想去的方向跑,阻止你抓住眼前的欢乐,一言以蔽之,阻止你有任何的享乐。说到底,最吸引人的反而是被禁止的东西。每当禁止我做某件事时,我皮而感到一股难以遏止的欲望,更想尽快去做。“禁止”就像盐巴、辣椒一样,让食物变得有味道,让舌头有刺激感,让人感到兴奋。相反的,举凡任何美德之事,都让人心生厌烦。人只活一次,应该尽情享受所有果实的滋味。“有教养”好女孩的理想典范让我感到憎恶。“这不是有教养的女孩会做的”之类的话会让我立刻起反感。对此,我总是回以“我嘛,就偏要做”这种放肆鲁莽的话,还会傲慢地加上一句:“而且,以后就会有人跟着这么做。”我这种态度是打哪儿来的?毫无疑问,我想自己做判断善恶的唯一法官,不受任何约束的羁绊。人们通常会把嚼子套在动物的嘴巴上来控制它。我是一头野兽,还是一个自由的女人?
帕斯卡到底想说什么呢?他不是那种“严厉斥责”型的人,而是邀请我好好思考。因此,我要寻求的不是一个具约束力的规则,而是一个具建设性的思想,能够让我在“高贵”中茁壮成长。那么,难道这就是“道德”:力图赋予自我更多的人性、增长属于人性的尊严、成为一个具有“会思维的芦苇”特质的人,并且就此进入一种具开放性的道德,一种能够解放任何狭隘平庸事物的道德之中?我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局限在我的自我意识之中,只关心我自己的感受。这样的生命,说穿了,是令人厌烦而悲哀的。
青少年——我今天对青少年问题尤感关切——有时会有灵感闪现的时候,会在某个瞬间领悟到一套生命哲学。说来可能令人震惊,但在我的生活圈里,没有人了解我的不快乐、我的疑问、那条我感觉被囚禁其中的幽暗隧道,以及我那总是充满矛盾的性格。事实上,我的生活平坦顺利,和家人过着相当安逸的日子,可是,为什么我对一切如此百般刁难、总是不高兴呢?读到帕斯卡的书时,我终于隐约感觉到,自己正跑在一条宽敞的道路上,终于有个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如果道德能够不建立在一些命定规则的基础上,而是在良善思维的原则上的话,因为思维理当是自由自在的,那么道德就只能是自由的、扩张的、充满喜乐的。因此,“真正的道德会嘲笑道德”。
太阳开始隐没,屋顶上看不见猫咪的踪影了。当夜晚降临时,我由阅读帕斯卡,展开了漫长的旅程:日复一日地奋力抗拒,让自己这根柔弱的芦苇不随风摆动;借着思维的力量来发现和谐、平衡生命的泉源。关于这个平衡,拉丁格言中的“在合宜健全的身体里头的合宜健全的精神”(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是非常贴切的描述。小心!这条路上可是布满荆棘。不论是合宜地使用身体或是合宜地使用精神,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
首先,邪恶思维俯拾皆是。各式各样的极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灰暗和极端的例子。以某个假理想的名义,人们竟然屠杀数千甚至数百万人。有人甚至把自己的死当作获得荣耀的工具。有些人以自杀作为摧毁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性命的方法,他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在支持他的人眼里也是一号人物,是为某个神圣使命殉难的“烈士”。对他来说,他所从事的是非常伟大的行动,他对这个行动完全不抱任何怀疑。不论是在政治的领域(如希特勒),或是宗教的领域(如某些误入歧途的教徒),崇拜偶像经常是思维偏差的根源:人们把某个思想变成了神。自此,此善不仅胜过众善,同时将某恶转变为一种“超善”。人们被催眠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
然而,根据我刚才引述的格言,精神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神圣化必然会影响到其与身体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在纳粹意识形态体系里,有一个纯洁的优等种族,借由血缘说和自然法则说被加以神化。对某一优等种族的神圣化,连带地把“种族净化”的行为合理化了。换言之,消灭人类社会中所谓的不纯部分,首当其冲的就是犹太人。对自命为“教徒”的恐怖分子来说,人先天就是不纯净的,然而,当他为某个神圣理由自我牺牲一切时,他将获得净化和升华,并因而上天堂。因此,他们会透过一项死前的礼拜仪式,先把自己的身体准备好。在献祭的仪式中,即将殉难的烈士会除去身上所有毛发,再洒上香水。面对这样一种思想的败坏,我们会恐惧得直打哆嗦,它的信徒却是充满仰慕地颤抖。的确,神圣会使人产生一种强大感,远远超过人不过是一根芦苇——即便是一根能思维的芦苇——的体认。
在达到这个噩梦般的极端之前,每个人不都应该留意自己的推论所可能产生的偏差吗?因为推论很容易就将某个思想变成绝对、完美的思想。我们只消偶尔听听自己的言谈就可以知道——我们所迷恋的是,我们的言论能够反映出自己的强大形象,但对相反意见中所存在的真理却视而不见,更遑论对支持这些相反意见的人。
在另一个对立面上,不管在哪一个社会,人要摆脱对身体、对肉体之美的沉溺,要摆脱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同样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点上,帕斯卡依然是我的灯塔:他承认物质的确有诱人之处,但也有局限性,他进一步指出了我们和物质之间该有的适切合宜的关系。
思索物质
在帕斯卡眼里,物质乃是一切不属于“精神”的东西。我们可能会以为,生活在17世纪的帕斯卡,会将一切与智性无关的东再都视为微不足道。对我来说,最具深长意味的并不是因为帕斯卡是数学家、物理天才,而是作为一位思想家,他一点也不蔑视物质。他写道:
让人去思索整个自然界的崇高与宏伟吧……让地球在他眼中,比起太阳所描绘的巨大轨道,就像是一个小点吧;让他震惊于那个巨大轨道本身,比起苍穹中运转的恒星所环绕的轨道来,也只不过是一个十分细微的小点罢了。
宇宙的浩瀚与壮丽既吸引了帕斯卡,又叫他困惑不已!大自然把原始面貌展现在人的面前:天地的雄伟和广大让人感到渺小,近乎卑微。相较于数亿的星斗与星系,人不过是一个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的点!
这还不算什么。人不只在抬头仰望天空时,看到宇宙的浩瀚无垠,同时,脚下也裂开许许多多无限微小的深渊。因此,人天生就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间项”。当然,无限大对人来说是立即可见的,而现代物理也早让我们习惯在有如原子大小的尺寸里面看到:
浩瀚宇宙之中,每一个宇宙都有自己的苍穹、自己的行星、自己的地球,其比例与这个可见的世界是一样的。
人就这样失在这两个同样令人眩晕的无限之间。犹有甚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认清它们。
……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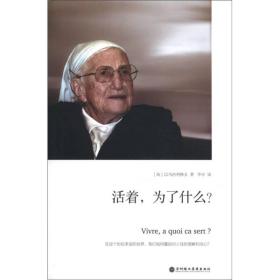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