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的海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2.68 5.0折 ¥ 45 全新
仅1件
作者李砚青|责编:史佳丽//李亚梓
出版社作家
ISBN9787521214703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5元
货号1202653001
上书时间2024-06-1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商品简介
《小的海》收录了李砚青在各大期刊发表的九部中短篇小说。《寻找张蓝》是有关记忆的小说,十八岁的“我”高考落榜回到小镇上,子承母业干起了卖凉菜的活,面对现实生活的世俗与艰辛,主人公深感失落、无奈,张蓝是主人公小学同学,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的人,同时也是符号,承载了主人公“我”少年梦想与未来期盼的符号,是一个精神领地,寻找张蓝似乎是一项永远也不能完成的任务;《钝刀》写的中国南方工厂里的“青工”群体,从一个工人跳楼事件抽丝剥茧,真实地还原了青年一代的工厂生活,资本的压迫、生活的无序、情感的混乱,理想幻灭的背后有挣扎、有反抗、也有种种不妥协的力量;《小的海》写的是青年进入城市,在富人家庭当司机的一段经历,在多重欲望的建构下勘测人心,追索生存本相,刻画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分裂的众生图……
作者简介
李砚青,1992年生,湖南永州人,湖南省小说学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高研班学员,在《民族文学》《大家》《芙蓉》《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百花洲》《青年作家》等刊发表作品三十余万字。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
目录
总序袁 鹰/1
序 构筑精神之岛的价值所在梁鸿鹰/5
寻找张蓝1
钝刀31
保证书85
杏香街112
远方树叶129
流动的夜晚146
呆鹰岭黎明时刻193
良夜201
小的海209
内容摘要
《小的海》是李砚青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作者10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小的海》写的是青年进入城市,在富人家庭当司机的一段经历,在多重欲望的建构下勘测人心,追索生存本相,刻画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分裂的众生图画。
主编推荐
李砚青的小说有湖湘文化的烟火气,以及冷眼打量世界的冷峻气质,行文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相反,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对复杂生活中的人的剖析,很具有一些过来人的沧桑感,可以说,他用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将人间百态、世上沧桑,化作笔底风云的时候,甚至显出了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作为一个年轻小说家,李砚青处理生活、整合生活的能力,已经在他的文本里,在其构筑的艺术世界里,在表达的独特性上显现出来了。这是颇为令人欣慰的。
精彩内容
寻找张蓝一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了十字街。六年前,我拉着一个崭新的行李箱、一张嫩青得像打过蜡似的竹席以及一把包装完整的天堂牌雨伞离开了这里。六年后,箱子破烂,竹席乌黑,雨伞几乎报废。中巴车极富节奏地往前突冲了三次后在十字街东口缓缓停下,我被焦灼的人群卷裹着下了车,我听见行李箱在野蛮的拼挤中发出痛苦的呻吟,一股无名火在我胸中升起,我刚张嘴要嚷,发现身边的人早已如潮水般退去,不见了踪影。我立在原地苦笑,一场夏雨接近尾声,小街在雨后出现的宁静冲淡着我的愤怒。
狭长的街道上泥坑遍布,垃圾漂浮,我艰难地行进。想着那条传说中要铺过来的高速公路和我的梦想有着同一个特点——遥远。事实上,我的梦想已经破碎了,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有的人见了我然后避之不及,有的人则心怀慈悲加入到我的队伍。不久,我身后的队伍便浩浩荡荡。我从众多的面孔中敏锐地找到了母亲,也许我有意识地忽略掉了寻找的过程,我一仰头就望见了她。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体上的暴力推搡全然不觉,随着人流在警戒线边上小心翼翼地涌动,那警戒线仿佛带了电一般,让人畏惧。我的母亲头发散乱,脸部扭曲,嘴大张着,露出那口暗黄的牙齿,迎接了我。我的表情代替了我所有的语言,同样,母亲也用她的沉默表明了她的宽恕。六年前别人对她说:“你儿子考上了县一中,省重点呢,一只脚就跨进大学的门槛啦!”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句话,母亲毅然决然地出租了老宅把家搬到了城里,她的这个决定甚至都没跟在广东的父亲通气,就更不用说我了。一向办事拖沓的母亲仅用半天时间就在一中附近租到了房子。她苦心孤诣地要把我的另外一只脚也抬进去。
但是她失败了。
罪魁祸首是我。
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继续在城里待下去,以前我们觉得它喧闹、拥挤以及种种的不尽如人意,现在,我们自觉地打包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并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从这儿消失。之前母亲虽然还在县里一个纺织厂上着班,可每天也就是白耗着日子,挣的钱刚够房租和水电。高考那一个月母亲就已经把工作辞了。说不上辞,结清工资,走了就走了。我和母亲前后脚走进了出租屋,她抓住一张矮凳满目狐疑地摇晃了几下,在确认它是结实牢固的才坐了上去。我轻轻掩上门,两步便走到了客厅中央,短暂的停顿之后我手足无措。
“大木,明天我们回十字街吧!”母亲如释重负地说。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出了她对原先的职业的无限怀念。在十字街,做凉拌菜的有两家,一家是西口的杨慈秀,在斤两上给人缺少得厉害,可生意一直红火。有人说她大度,舍得往菜里放油。另一家是北门场的李水英,李水英就是我的母亲。她在斤两上也给人缺少,但不厉害,多年来生意温温的,像她的脾气一样。母亲说杨慈秀往菜里放的那种油我们家也有,不过她很少用。
无论从哪方面看,回十字街重操旧业都是明智之举,所以我没有提出异议,只是恳请母亲准许我晚回去几天。我说我还要回学校去收拾东西,还要跟一些朋友道别等等。整理好所有东西后,母亲从汽车站叫来了一辆人力板车,物件堆上去,母亲关切地迈着碎步跟在后边儿随时注意着。后来那些物件上了一辆没挂牌照的三轮车。母亲坐在那堆物件上回到了十字街。
那几天我缩在宿舍楼里哪儿也没去。宿舍楼已经是一座空城,前后有几批人进来搜刮过之后就再也无人光顾。耗子横行。我白天不停地喝水、洗澡、发呆,晚上便把凉席和枕头搬去天台睡觉,如果太阳不是很毒的话,我会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到第三天的时候情况有些不妙了,我居然患上了失眠症,这个名词于我而言显然是一种奢侈。就像一头耕牛说自己不能耕田了,一只母鸡说自己不能下蛋了,这些都太矫情。一开始我毫不在意,强迫着自己往床上躺,到后来只要身体一挨着凉席心里就慌,白天如此,晚上亦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回十字街了。
对于未来我并非没有细密的考虑,那几天的时间里我甚至把自己已经度过的三分之一的一生回忆了一遍。我今年十八岁,算二十,我理想中的人生长度是六十,六十挺好。以前我总想活个一百来岁,后来想想觉得那实在漫长得可怕,人老了就只剩下吃饭、拉屎、睡觉了。甚至连放个屁都拖拖拉拉、要死不活的。每当夜晚降临,县城南边一个背靠着一座小矮山的广场上就会坐满了老人。一只流浪的猫走过,他们会注视很久,我走过,他们也会注视很久,像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两种动物。哦,对了,差点儿忘记交代了,我们学校校长和教务处主任的母亲以及办公室主任和后勤处副主任的父亲都在来宿舍楼搜刮人员名单之上。短柄的牙刷、缺齿的梳子、一只满是窟窿眼的运动袜、一个掏耳勺都是他们眼中的抢手货。
回忆有个好处,那就是有助于我们梳理出自己人生的大致走向。在去县里上学之前我从未走出过十字街,到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离街三里多路的“长兴”冥纸厂。母亲经营着一个小店,除了有一次将一个小学生的肚子辣痛,最后上了医院,其他时候再无风波。父亲在外打工,不在工厂,也不在工地,在他的小学同学经营的废品收购站里帮手,一帮就是十多年。平均一年回来两到三次。我呢,先后从十字街中心幼儿园和十字街中心小学毕业。坏事不沾边,没拔过螳螂腿,也没有抓过四脚蛇。好事没少做,捡到东西上交,义务打扫粮站。出格的事我倒做过一件,至于是不是坏事我也是到了现在才逐渐有了评判。那件事已经超出“坏”很远上升到罪恶了。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个叫李月梅的塞了一张小纸条在我课本里,上面写着“大木,我喜欢你”。正好我看到的时候旁边的几个伙伴也偷瞄了,他们“嗷嗷”地叫着,我羞愧得无地自容,风驰电掣地跑到李月梅桌旁,把纸条砸在她脸上,具体地说是左边颧骨靠下来一点点的地方,然后一脚踢在她的小腿肚上,骂了一句“不要脸”。在这件事后不久我就去了县里,又听说李月梅在十字街中学念到初二便辍学去广东进了厂。我们再没见过。容我废话一句,那时候她的同桌就是张蓝。
谁也没料到我会考上县一中。那一年,整条十字街上考上的也就四个。分别是北门场的我的邻居王新初,他家开着一个卤粉店,我们两家经常换着东西吃;还有南口的胡大宝,他家开着一个猪肉铺,胡大宝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体重就达到了一百二十斤,一步三喘,绰号“大太太”;再有街中央的李能武,他家开着我们街上规模最大的服装店,所以他身上穿的永远是最潮流的,跟他站在一起,我们都是土包子。他跟我们说,其实不是你们穿得土,而是你们的思想土,你们压根儿没想过拿掉这个帽子是不是?是不是?在那个年纪他就跟我们谈“思想”这种高深的东西,我们都觉得他投错了胎,他应该生在美国,至少也得是香港。我和李能武的关系开始挺好,后面不好了。他是李月梅的堂哥。
李能武骂我们几个是土包子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等到了县里,我们站在了那些衣着光鲜的城里同学中间,我们手心发烫、耳腮通红,身上的每一个关节都像装了发条,随便一动就嘎吱嘎吱响。而李能武不仅站在他们中间谈笑自若,居然还能吸引不少女生往他身上瞅。回到寝室后我们几个果断地逼他交出了箱柜钥匙。
六年的城里时光说长不长,一切恍如昨天。说短也不短,我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男汉子。既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一天又一天,我吃在家里,睡在学校。每天走过同样的街道,开始你会觉得街道上每天充斥着不一样的人,久了,你会发现其实还是一样。记得在校门口右手边有一位满脸胡楂、长着酒糟鼻的摩的司机,初一的时候我坐过一次他的车,原因已经记不清了。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打的”,兴奋得跟坐飞机似的,双手抓住后架、看着他落满白色头屑的衬衣、绞尽脑汁地想要跟他搭上话,可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只是稍微点点头,我怀疑哪怕我从车上掉下去他也不会有多么在意。于是我记住了他。六年后我急着去民政局盖个戳,第二次在同一个街角坐上了他的车,他的衬衣上依旧落满头屑,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懒得甚至是不屑于同他讲话啦!到了目的地后我给了他一张五块的,他居然还找了我两块,而上回车费也是三块。我说你们的车费难道一直没涨?我这话的前提是肉价由原来的四块多一斤涨到了现在的十二块钱一斤。估计他还从未碰见我这样嫌价钱便宜的乘客。他有些腼腆地挠着后脑勺说不敢涨,涨了就拉不到客啦。我看到雪白的头屑纷纷落下。
与我的平淡恰恰相反,我的伙伴们乘风破浪、大干快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生高潮。先说说李能武,他在初二的时候就交了第一个女朋友。要知道,在那时,我们刚刚明确了男生女生在性别上的具体差异,都羞于和女生说话,和女生的交流几乎为零。那女孩个儿高,皮肤红润,瓜子脸,城里人,听说家里开着一家鲜花店。倒数第二条显然是重点。李能武就是这样让我们一直仰视着,就在我们快要累断了脖子的时候,他转到了市一中。我们以为他肯定把那个城里女孩也带走了,他们都在食堂里相互喂过饭了。可后来我们竟然在学校里碰见了她,我们没有在她脸上看到我们想要的情绪。因为她身边已经站了另外一个男生。那男生的眼神狠狠的,好像跟谁都有仇。再见到他们,我们就学乖了,装作路人,大摇大摆地走过去。王新初说,我们本来不就是路人吗?众人才恍然大悟。高一军训结束的时候李能武回来看我们,我们谁都想跟他说这事儿,然后邀功求赏,但是谁也没敢。
都说粉里边含有明矾,吃多了人会变笨,这个常理却没有在王新初身上发生作用。王新初不是天才,但他身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他的与众不同。他习惯于把每一个问题反复地考量后再做出具体行动,一旦发现不对,便立马刹住、折回,不辞辛劳。客观地说他的这个习惯在学习上给他帮了大忙。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尽量把整张试卷扫荡干净,就是胡编乱造,也要把卷子涂满。而王新初总是不紧不慢地思考着,这样做的结果是只要做了,就没有错的,做不完没关系,他老早就够本了。以至于后来我们的年级组长把他当成了典型大肆宣传,一开始要他自己上台介绍经验,但第一次登台王新初就差点儿紧张得昏厥过去。这本与我没有一点关联,可当天晚上我遭了殃,半夜的时候我被冷醒了,一摸,肚腹处的被子湿透。王新初睡我上铺。这事儿打死也不能说。我们几个里边只有王新初每个月放月假都回十字街,六年间,他源源不断地把十字街的消息带给我们。那时一定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大太太”胡大宝的人生精彩和李能武、王新初的不一样。无论谁第一次见着胡大宝都会说他长得一脸的富贵相。事实也正是如此。他爹胡屠户没有上来陪读,但他的大弟弟也就是胡大宝的亲叔叔是县水利局一位不小的官儿。我们见过这个官儿,困扰我们的不是他和胡大宝为何长得如此神似,而是我们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县城的日西河也就五米来宽,哪儿来的水利供他管呢?在我们贫瘠的知识系统里只有像三峡那样的大家伙才称得上水利。胡大宝入学不到一个月就买了一辆八百多的山地自行车,在让我们瞠目咋舌的同时,也让我们为那辆自行车揪痛了心。人的运气来了真真是门板也挡不住。胡大宝后来不仅做了学校纪律稽查部(主管查抓食堂插队、随地乱扔垃圾等违纪行为的部门)的干事,手臂上套个红箍箍往人跟前一站,简直是威风无限。后来他又一路顺风顺水地升到了部长。由此胡大宝“大太太”这一绰号就不知不觉改成了“胡部长”。究竟是哪个没出息的开的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然而,“胡部长”这个叫法终究是改不过来了。
小地方来的人往往具有心眼小的特点,在“大太太”胡大宝成了“胡部长”之后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便有些疏远了,不知是我们因为妒忌从而疏远了他还是他在心里故意撇清了我们。总之,和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安静。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件事情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虚伪而是应该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做都已经做了,还有什么难为情的?而且不仅做了,用李能武的话说(当时他还没有转去市一中),“没看出来,大木这小子还藏得挺深”,说完这句之后他还觉着不过瘾,偏又煞有介事地对着众人加了一句“知道为什么说咬人的狗不叫了吧”。这句话让我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发誓再也不跟他们一起胡来了。但一到了周末,我还是会极其猥琐地勾上他们的肩膀。
都怪胡大宝这小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总觉得他也是为了拉近与我们的关系才无意之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漩涡。那是在初三下学期开始没多久的时候,一天,“胡部长”神秘兮兮地问我们要不要跟他一起去看个好东西。看他那副样子好像捡到了宝贝似的,我们能有幸目睹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们问他究竟是什么好东西,他死咬着不松口,只说等你们见了就知道了,嘿嘿……在灰尘弥漫的街道上,我们几个跟随着“胡部长”的山地自行车一路小跑着来到了县教育局对面的一家小网吧,连像李能武那样见多识广的人都惊呼:“胡部长!你带我们来网吧呀!未成年人不准进入你不知道吗?”“胡部长”肥手一挥鄙夷地说:“乱弹琴,我都带你们来了你们还不相信我?去吧!兄弟们!今天我请客。”说着,他麻利地开好了四台机器。这期间一个精瘦精瘦的中年男子一直笑脸看着他。不用说,他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
我们几个站在门边上一动不动,呼吸紧促,完全就是考试作弊时的心情。李能武为了挽回刚才失去的威严,神情镇定地大步走向了那张大红色软椅。王新初如有所思、步态僵硬地跟了过去。当门边只剩下我的时候,我居然有种想哭的冲动。我又留下一个笑柄。
大家坐定之后,“胡部长”轻车熟路地引导我们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界面。我们先打开了桌面上的“电视休闲”。然后打开了“本地电影”。再然后打开了“最新电影”。最后我们到达了终点——“成人电影专区”。
在那个天气异常炎热的下午,我们在洪水般的汗水中经历着惊心动魄的生理冲击。我们在那个小网吧从下午三点待到了晚上八点。走出推拉门的时候,除了“胡部长”,我们其他几个人都几乎瘫软在地。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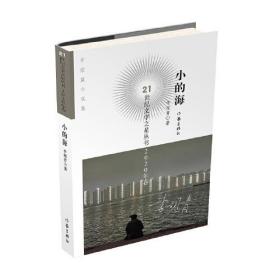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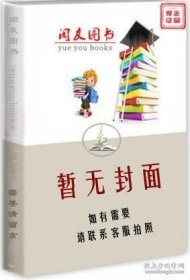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