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35.16 4.0折 ¥ 88 全新
库存3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芭丝谢芭·德穆思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90789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88元
货号31437038
上书时间2024-06-12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芭丝谢芭•德穆思(Bathsheba Demuth),美国布朗大学环境与社会史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北极地区的能源史与气候史。她曾在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各地的北极社区生活多年,其性格形成期就是在白令陆桥度过的,亲身经历了与迁徙动物比邻而居的生活。
目录
前言?关于地名
序曲?北迁
第一部分?大海,1848—1900
第一章 鲸鱼的国度
第二章 鲸落的消逝
第二部分?海岸,1870—1960
第三章?浮动的海岸
第四章?行走的海冰
第三部分?陆地,1880—1970
第五章?变动的苔原
第六章?气候的变化
第四部分?地下,1900—1980
第七章?不安的地球
第八章?救赎的元素
第五部分?大洋,1920—1990
第九章?热量的价值
第十章?觉醒的物种
尾声?物质的转换
致 谢
资料来源注释
注 释
内容摘要
浮动的海岸》是首部关于白令海峡——从俄罗斯到加拿大的北极陆地和海域——的综合性历史著作。自19世纪以来,人类在白令陆桥这片极北之地开启了一场极具现代意识形态的试验。作者通过讲述白令陆桥动物和矿产资源的历史,揭示了一百五十多年来人类如何将这一偏远地区的生态财富转化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力量的过程。作为一部讲述人类开发与北极生态之间关系的开创性著作,《浮动的海岸》打破了以往人们所熟悉的环境史叙事,而以一种新鲜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白令陆桥这一被忽视的景观。
在本书中,德穆思根据自己与当地人一起生活的经历,并利用对当地人的采访资料及相关档案,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深刻而迷人的故事,揭示了人类的巨大需求与野心给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带来的且将继续带来的动态变化和无法预见的后果。与许多环境史学者一样,面对人类对地球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德穆思不再认同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观点,即自然和人类必须拥有不同的历史。在德穆思的笔下,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是相互交织的,人类及其观念与地域、动植物、矿藏资源等非人类部分彼此互动,相映成趣。
主编推荐
《浮动的海岸》是关于白令陆桥的首部综合性环境史著作。芭丝谢芭•德穆思根据自己与该地区原住民一起生活与采访的经历,并结合丰富的档案资料,展现了在这一有限的空间中所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环境的冲突。作者通过自然界的透镜,将人类的生活与经济视为基本的能量循环,从而为人类历史的书写提供了新鲜而富有远见的视角。 本书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图书馆杂志》、《科克斯书评》、《自然》杂志年度☆佳图书,获得了美国环境史学会☆佳环境史图书奖、西方历史学会哈尔·K.罗斯曼图书奖、西方历史学会W.图伦汀·杰克逊奖、美国历史学会约翰·H.邓宁奖、埃里克·岑西生态经济学奖、乔治·珀金斯·马什奖、茱莉亚·沃德·豪奖、威廉·米尔斯奖等奖项。
精彩内容
第一章:鲸鱼的国度18世纪末的某一天,一头弓头鲸宝宝出生了。时值深冬,数月以来太阳低照,温度也很低,使得白令海远至南部的海面也结上了冰。鲸鱼妈妈找到浮冰上一块开阔的空间用以分娩。在倒转的蓝色晶莹的冰层间有一块是空心的,灰白色的宝宝被鲸鱼妈妈放在上面,呼吸了它的第一口空气。沿着这块浮冰薄薄的边缘,其他的弓头鲸妈妈也产下了它们的宝宝。伴随着一股血流,鲸鱼妈妈安静地产下了宝宝,小鲸鱼游入了海中,这片海是两万多头鲸鱼的家园。
在春日暖阳下,白令海表面的冰层向北漂移。鲸群也跟随着冰层向北迁徙,穿过了白令海峡,鲸鱼宝宝一会儿自己游,一会儿趴在妈妈的背上休息。海洋里不时有浮冰融化成水,它们与其他小弓头鲸群相会合,头鲸一路上吐出串串水泡,引领着鲸群。到了6月,鲸鱼妈妈、鲸鱼宝宝和它们的鲸群,一起向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的波弗特海游去,其穿行的脊背标示着海冰的下缘。在没有夜晚的漫长慵懒的日子里,鲸鱼妈妈给宝宝喂食,宝宝嬉戏玩耍,有时短暂地游散开去,然后成环形向前游。夏日渐去,进入9月和10月,鲸鱼又一次向西游入楚科奇海,鲸鱼宝宝游动时抓紧妈妈的鳍。初冬的寒冷黑暗使浮冰加厚了很多,海洋中的哺乳动物有缺氧而呼吸困难的危险,这时候鲸鱼会游向南方。此时,鲸鱼宝宝已经出生半年多了,它更加勇敢,能够在更深的地方潜水,在水面呼吸的时间也更长了。
从海面上看,白令海显得空旷苍凉—夏季蓝灰色的海面不时会有风暴,不见太阳的冬日里,海上覆盖的是厚厚的冰层。然而,白令海峡是世界深海环流的终点。源于北大西洋的水流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白令海,在此汇集了大江大河冲刷而来的营养物质。在海峡处,两个大陆向彼此靠拢,由于风和海底地形,产生了涡流。温暖的海水和冰冷的海水汇流,将铁、氮、磷等元素带到海洋表层。在海洋表面,这些元素遇到了夏日充足的太阳能,遇到了大气中的碳元素,形成了有机生命体。海水接触了空气,加上太阳的照射,二百多种光合浮游生物成形了。这些浮游生物和藻类是白令海最原始的生命形式。亿万的浮游生物和藻类就这样在这片世界上最为丰饶的海洋生态系统安家了。
浮游生物所做的事情是所有生命体都会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断繁殖。它们不断地将太阳光转化为淀粉组织,使海洋充满能量,这些卡路里需要供养三百多种脂肪丰厚、成群成堆的浮游动物,它们形色各异,从小虾、仔稚鱼到神话的缩影——水螅、触角怪以及由体刺、液囊和胶状组织构成的生物。鲸鱼的任务是把这些分散的能量聚集起来,以此供养其上百吨的巨大身体。嘴巴是它们的工具,它们有着和小船一样长的下巴和薄板状的胡须,它们的胡须比牙齿还多,进食时能够帮助它们从水中过滤出来磷虾。在浮游生物密集的地区,鲸鱼能在六周时间吃下去一个季度需要的食物。弓头鲸妈妈也就是这样用十四个月的时间在体内孕育出一个一吨重的宝宝。宝宝出生后,妈妈还要劳累一年多,捕食海洋生物,产出滋养宝宝的奶水。鲸鱼无不如此。在二百多年前,鲸鱼吃掉了白令海里一半的初级生物。
正是因为汲取了海洋中的能量,鲸鱼具有了自己的力量。弓头鲸在海洋世界里能做好多事情,其中之一便是和其他鲸鱼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独自遨游时,它们的歌声也时而轻快、时而婉转、时而低沉,有时刺耳如咯咯吱吱的铰链作声,有时是低沉的轰隆声,有时如鸟鸣一样高昂。当它们发现成群的磷虾时,它们会唱歌示意其他鲸鱼,一小群鲸鱼会像大雁一样形成V字队形,它们一边向前游,一边张开大嘴捕捉成群的桡脚类动物。它们的语言只有自己同类能明白,其他物种是无法理解的。
能够跨越物种分野的是能量。弓头鲸也用它们的肉体供养着其他生物。一些小鲸鱼宝宝成为虎鲸的口中之物。一些鲸鱼也成为人类的食材。每磅弓头鲸的肉比任何其他北极陆地或海洋的物种所含的卡路里都要高。连一头一岁的小弓头鲸都够一个村庄吃半年的。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以及沿岸的楚科奇人是最早捕猎小鲸鱼的人。
对鲸鱼的捕猎一直存在着。弓头鲸能活到二百多岁,当这头鲸鱼宝宝出生时,美国还没有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沙皇俄国也未曾拥有阿拉斯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刚刚问世几十年,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将在五十多年后出版。在小鲸鱼的一生中,它将见证人类如何梦想乌托邦的到来,如何发展核能招来灾祸,人类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技术力量来重塑世界。
小鲸鱼能幸存下来是令人惊叹的,并不只是因为二百年对于哺乳动物的生存来讲确实很长。鲸鱼是将工业革命及其意识形态吸引至白令陆桥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类对能量的控制利用。商业捕鲸船就是其中的先锋军,船上所载的未必是革命者,而是意图将鲸鱼的躯体变为商品来获取利益的人们。他们杀戮鲸鱼,获取利润,是基于市场在不断增长的预期。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鲸鱼不是用来贩卖的,而是被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看作生灵。这些人也捕猎鲸鱼,但是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转世轮回,万物难以久长。在商业捕鲸船出现后的几年中,鲸鱼自己也认识到了美国船只的危险,并学会了一些行为来躲避这些捕鲸船,以对抗商业对它们的渴求。
一
1852年的9月底,两个捕鲸团队在楚科奇东北海岸相遇了。一对白令本地的捕猎者在他们帐篷附近的海边搜寻时,发现了三十三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跨过苔原向东南方向缓缓前行。一开始,本地捕猎者并没有接近这些人。他们人数众多,而且语言也不通。然而,北极的绝望境地超越了语言。船员们打捞的物资—饼干、朗姆酒、糖浆、面粉、宠物猪的残粮和临时帐篷—不足以让他们熬过已从群山之中呼啸而来的冬季。本地捕猎者经过观察和思考,选择了怜悯。
本地捕猎者对外来者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在其冬季村庄的海象皮帐篷中分成不同家庭。俄国探险者谢苗·德兹涅夫曾在1648年路过此地。八年后,维图斯·白令率领他的队伍在辛哈克沿岸登陆。詹姆斯·库克和约瑟夫·比林斯在18世纪末带着大英帝国的重托探索了这片海峡。分别由奥托·冯·科策布和米哈伊尔·瓦西列夫率领的两支俄国队伍在19世纪初来到这里。哥萨克商贾在更远的西边的奥斯特罗夫诺聚集点做着生意。在过去的几个夏季里,更多的船只经过这片海岸,他们的出现就好像海市蜃楼一样神奇。但是,这些遭遇了海难的水手面色苍白、行动缓慢,他们既不想与本地人开战,也不想做交易。他们蹲坐在自己的冬季帐篷里,行动古怪。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刮胡子。他们不喜欢本地人有着狂野手势的仪式活动。他们的歌声很滑稽。村里的女人需要帮他们缝皮衣,教他们如何穿皮衣。他们带来的糖浆和饼干很好吃,但是快不够了。村民们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衣服,还把村庄里的食物分给他们吃,这食物便是鲸鱼肉。
这些人是遭遇海难的“市民”号的幸存者。“市民”号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出发,赶着第五个商业捕鲸季而来。对招待他们的村民,船员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船长托马斯·诺顿后来这样描述村民:“当我们孤立无援、处境艰难时,他们出乎意料地给予我们很多同情和帮助,这让我们始料未及。”但是,感激之情也不能让这些船员喜欢上鲸鱼的味道。美国船员难以忍受滑滑的且嚼不烂的肉,特别是当生吃的时候,“即使时间长了也还是无法适应这讨厌的东西”。就像他不会与村民们分享他对洗浴、性、所有权、衣服和宗教的看法一样,诺顿船长没有告诉村民们他对鲸鱼肉的反感。诺顿和他的船员们在村民的住所度过了冬日幽暗的日子,透过海豹油灯冒出的烟雾,他们相互审视着对方,由此也开始了一段博弈,博弈的中心就是,白令人的生活应受何种价值观的引导。
从新英格兰来的捕鲸者与白令本地的捕鲸者价值观相异,并不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同,他们都是靠捕杀鲸鱼为生。他们的差异在于对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什么是人?什么是鲸鱼?鲸鱼的价值在哪里?未来会怎样?诺顿将鲸鱼看作供养村民们的“食材”,但对其他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鲸鱼的语言。
栖身于自己帐篷里的诺顿,也不知道在白令陆桥生活要面对不断的变化。某一年,大雁群没有来到它们经常栖息的湖里。某个冬天,风暴潮将海洋上的冰块卷起,把它们带入几百英尺外的内陆,所经之处一切尽毁。某一时刻,一个蹲在冰面上等海豹上浮喘气的猎人却意外地遇到了北极熊。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中生活,尤皮克人、因纽皮亚特人和楚科奇人认为,世界是没有固定形态的,鲜有东西能一成不变,但是大多数东西都有灵魂。就像未来可能被突然侵袭陆地的海洋冰块改变一样,灵魂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土地。萨满可以变成鲸鱼,再变成人;人最开始可以是一头海象,然后慢慢长成一个男孩;一个强大的咒语可以让人在五天里变为一只北极熊;驯鹿可以有人类的面孔。人和其他事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土地和海洋是鲜活地存在着的,有感觉和判断力,也会一时兴起做出危险的事情。在这个充满各种意志的世界里,生存依赖于相互合作。
弓头鲸和人类的合作需要经历一种特殊的变化,它们需要奉献出生命。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因纽皮亚特人阿萨特查克在八十年后说:“鲸鱼从自己的国度观察着人们。鲸鱼会说,‘我们游向照顾穷人和老人的人们,我们把自己的肉身奉献给他们’。”它们会根据捕猎者的道德品行以及在仪式上对鲸鱼的重视来决定是否献身。女人们会通过一些安静的仪式来和鲸鱼对话,仪式上有魔力的萨满的舌头会变成鲸鱼的尾巴。在斯乌卡克,尤皮克人会把肉带到海里,一边喂给一直用身体供养人类的弓头鲸,一边低声歌唱。倘若没有这些仪式,鲸鱼会告诉彼此,人类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不足以让它们为之献身。它们不愿为不值得的人而死,它们宁愿留在自己的国度。
如果鲸鱼离开了自己的国度,它们会在春天游弋于阿拉斯加附近,春秋季节活动于楚科奇海滩和岬角附近,一些楚科奇的村民在夏天也会捕猎灰鲸。在鲸鱼出没的季节,船员们准备好能装载六到八个人的海象皮小船,小船漂荡在冰冷的海上。每条船上都有一位船长,这位船长一般和他的妻子一样,能够和鲸鱼进行灵魂上的沟通,同时还具有熟练的捕鲸技巧。他还得确保鱼叉、绳子、浮标及鱼枪等都是干净洁白的,那是鲸鱼们最喜欢的颜色。然后,船员们开始在冰的边缘观察鲸鱼。有人需要一直盯着水面,以便发现突然露出水面的黑色脊背。一队人可能会观察几周的时间。他们不但不能点火,也不能多说话。每个船员都穿着崭新的浅色衣服,这样水下面的鲸鱼就会以为看到的是天空和冰面。在斯乌卡克,女人们送丈夫们去海里捕猎时,会祈祷“猎手们就像透明人一般,人过不留影”。
鲸鱼靠近的时候,捕猎者们只有几分甚至几秒的时间做出反应。他们知道弓头鲸的听力很敏锐,所以轻手轻脚、不声不响。有经验的船长可能会等到鲸鱼呼气喷出的水花声掩盖住船和冰面的摩擦声再做出行动。当船只偷偷接近鲸鱼时,尤皮克猎人会观察鲸鱼的肢体动作,人们相信通过它们转身和下潜的方式可以预测出船长的寿命,以及鲸鱼是否愿意献身于人。当鲸鱼将要再一次潜入水中时,捕猎者开始行动了。20世纪30年代,从小就在斯乌卡克以捕鲸为生的保罗·萨鲁克描绘道,船长“呼喊着船员们的名字,让他们到鲸鱼前面拦住鲸鱼”。因纽皮亚特猎手一边放出鱼叉,一边歌唱。
如果他们距离一只大鲸鱼很近,船长会等到它上来水面呼吸,露出侧脊时再行动。猛然一击,每个鱼叉的曲形后钩都在弓头鲸皮肤下面的肉里扎出一个深深的口子。人们把这些鱼叉用粗绳绑在海象皮小船的浮板上,几十个鱼叉一起将鲸鱼挣扎的身体拖出水面,鲸鱼越想挣扎逃脱,钩子陷入其心脏和脊椎的位置越深。杀掉抓到的鲸鱼需要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周围是冰冷的水和热血形成的泡沫。这是很危险的工作。大鲸鱼会从船底跃起将船掀翻,把船上所载全部抛入冰冷的水中。楚科奇猎人所捕猎的灰鲸个头很小却很危险。所以猎人们会捕猎一岁的灰鲸,以及弓头鲸和灰鲸的幼崽。只需将鱼叉扎入其心脏,小鲸鱼很快就会死掉。雌性小弓头鲸最受猎人的喜爱,在因纽皮亚特语中它们有自己的名称,叫作“因尤塔克”。有时候,鲸鱼会跑掉。生于18世纪末的那头弓头鲸在其出生后的几十年里,身上被扎下的鱼叉不止一个,在它的整个余生都会带着这种古老的捕鱼工具游走于海洋。
鲸鱼死后,捕鲸者们把鲸鱼的鳍肢绑在其身体上,然后把它拖向冰面或是陆地来进行宰割。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来帮忙将鲸鱼从水里拖出。到了陆地以后,鲸鱼的身体成了深蓝的一堆,冰上满是浸入的鲜血,全村一起出动将鲸鱼的皮、鲸脂、肉和骨头相分离,空气中满是血腥之气。光是鲸鱼的舌头就有一吨重。孩子们也在宰杀现场,嚼着小块的鲸脂,脸上泛着油腻腻的光。除了骨头,弓头鲸的每个部位都进了人类的嘴巴,从心脏到肠,再到据说能够预防坏血病的鱼皮。女人们把肉埋入冻土层里以便能够储藏度过夏日。鲸脂也被保存起来,可以食用,也可用以灯盏的燃烧,为半地下的房子供暖;一些房子的梁架就是用弓头鲸的腭骨做的。
当鲸鱼巨大的身体被肢解开,就要按照社会等级进行分配了:上好的尾鳍上的肉属于最先下鱼叉扎住鲸鱼的船只,鳍肢属于第一只和第二只船,鲸鱼下巴低一点的位置归第四只和第五只船。还有一些人没有分到,比如老人、弱者和寡妇,丰裕的家庭就需要照顾他们了,就像鲸鱼将自己奉献出来一样,他们需要把得到的鲸鱼分给这些需要的人。这样的做法既现实,又能获得别人的尊敬,这样能使捕猎者和他的妻子在群体中获得领导地位,也值得未来更多的鲸鱼为之献身。捕到鲸鱼后的几天中人们大摆宴席,并举行其他仪式活动,每个部落都会唱歌跳舞,供奉祭品。斯乌卡克的尤皮克猎人,将鲸鱼扎破的眼睛流出的液体与木炭混合在一起作为涂料,在他们的捕鲸船上绘出神圣的图案。提基格阿克的提基格阿格缪特人在将弓头鲸的头骨倒入海里之前,会在上面浇上新鲜的水,这样它的灵魂会找到回家的路,并且能转世再次成为鲸鱼。就在前文所提到的那头小弓头鲸出生那年,大约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提基格阿格缪特部落差点灭绝。一个夏天,满载提基格阿格缪特人的一艘小船被科尼金的一队人伏击。随后又被从诺塔克河沿岸来的一群内陆人攻击。第二次的攻击更为惨重。一半的提基格阿格缪特人,差不多一百多人,死于弓箭之下,他们出事的地点后来被他们称为“因纽克塔特”,意思就是“很多人殉难之地”。幸存者不得不将他们之前的大量领地拱手让与他人。
像提基格阿格缪特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并不鲜见。不久之后,斯乌卡克岛被海对面不到四十英里楚科奇半岛上的翁加齐克人袭击。谢苗·莉娜说,一个叫奈格帕克依的男人带着一千人坐着皮船过来,“屠杀了所有人,连孩子们都不放过”。政治争夺一直在白令地区上演,无论是争夺领地、贸易、奴隶,还是为了复仇或是因为信仰的差异。当邻近部落一个法力高强的女萨满将戴着手套的手伸进火中把武士的心脏从胸膛中扯出,当楚科奇的牧民为了奴隶洗劫了尤皮克村庄,除了开战还能做什么呢?有些战争是在有着同样语言的部落间爆发的,因纽皮亚特的凯塔格缪特部落的老妇人曾被卡内格缪特的男人切成碎条,放在鱼架上晒干。有的战争是在说不同语言的部落间展开的,比如楚科奇、尤皮克和因纽皮亚特三个部落之间也是战火连连。沿着阿拉斯加海岸,大陆对岸五十英里之外说楚科奇语的部落也会过来偷妇女。从19世纪白令陆桥本地流传的历史和外来者的记述中,我们知道这片区域并不是和谐宁静的,而是不断发生着剧烈变化。
因纽克塔特大屠杀的八十年后,提基格阿克地区的居民告诉一个外来捕鲸者,在这场劫难之后他们的生活异常艰辛,因为“所有的领袖、厉害的捕鲸者和有技巧的猎手”都被杀死了。在弓头鲸出没的海岸沿线生活的族群中,各个村庄里的权力分配要基于对鲸鱼的捕猎和再分配。一个人如果可以让鲸鱼为之献身,就会获得道德上的权威和食物充足的实在好处,他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增加,也就能够占据领地、获得俘虏。因纽克塔特的幸存者需要重新证明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们做到了。年轻的猎手每到春天都会外出捕猎鲸鱼。捕猎就是“每次带着肉安全归来时也获得了知识。靠着祖先们流传下来的智慧保驾护航,他们一路向前”。捕鲸时,萨满把鲸鱼唤到岸边,拿着鱼叉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待,纵然时光流逝,这一切依然世代相传。他们的一举一动代表了整个民族的过去,他们为了未来的生活而努力。如果托马斯·诺顿在1852年发问什么是鲸鱼,那么这就是白令人可能给出的很长答案的一部分。它使人们在北极的夜晚也能看见光明,使人们能够忍受酷寒、填饱肚囊。它有着鲜活的灵魂,它是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因为它死后的躯体能够供养人类生存,它能够使一部分人获得权力,它使人类共同劳作;因为它,人类有了诸多期许和仪式,有了关于历史的看法。
二当弓头鲸不再独居时,它会和体型差不多大小的鲸鱼一起生活。当出生在18世纪末的那头鲸鱼离开妈妈时,它可能和其他年幼的鲸鱼一起,最早一批来到冰原上,随后年老的鲸鱼也来到这里。在那个年代,人对鲸鱼造成的威胁是很有限的。在楚科奇,人们每年杀死的弓头鲸有十到十五头,在阿拉斯加西北部,数量有四十到六十头。数量应该不会更多了。如果弓头鲸从同伴的叫声中或者从它们被鱼叉扎过的记忆中了解到人类是危险的,那么危险也只是发生在岸边。在外海是没有危险的。直到像托马斯·诺顿这样的人来到之后,情况变化了。
对于“市民”号上的船员来讲,鲸鱼是没有灵魂和国度的,它们只有价值。如果弓头鲸被简化为只是运往新英格兰的鲸油、鲸须,那么它们就只是商品,是能够马上换成货币的自然物。这些货币又能变成其他很多东西,比如个人财富、地区权力、铁路投资、奴隶种植园或国家荣耀的某些观念。
弓头鲸的商业价值主要在于它鲸脂中浓缩的能量,还有鲸须。这对于新英格兰和白令地区的鲸鱼购买者来说是一样的。但是,19世纪的美国捕鲸船若捕到鲸鱼,是不会把其当作食物的,鲸鱼的脂肪为这个正走向机械化的国家提供了润滑剂。首先,它可以润滑缝纫机、钟表、轧棉机和织布机。鲸须的“纤维性和富有弹性的结构”是很有用的,在塑料和弹簧钢还没被发明前,鲸须可用于生产“鞭子、阳伞、雨伞……帽子、吊袜带、颈托、手杖、花饰、坐垫、台球桌、钓竿、探矿杖、刮舌板、笔架、文件夹、切纸机、画家用的绘画支架、靴柄、鞋拔、刷子和床垫”。精制鲸脂可以成为上等的肥皂、香水的原料,以及高质量皮鞋的填充物。果园和葡萄园将鲸脂用作杀虫剂,作为涂层“防止绵羊啃咬树苗”,也作为化肥。鲸脂里贮存的能量并不能直接为工业提供动力,动力来自水车以及木头、煤炭和石油中的碳,但是鲸鱼制品对于纺织业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一家棉纺织工厂一年大约能用将近七千加仑的鲸油—这需要从三头抹香鲸身上提取。绵羊剪毛前需要在其身上涂抹一层鲸脂,机器织布前也需要在纤维上涂一层以使其强韧。
最重要的是,鲸鱼身上贮存的能量可以化身为光。在新英格兰,从17世纪30年代起鲸油就已经用于照明。19世纪早期,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室内照明的需求也在增加,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将化石燃料进行提炼用于燃烧煤油灯。灯油大多来自动物脂肪或是植物籽油。鲸油,特别是抹香鲸油,能够制造出最为明亮的灯。它还不会像猪油脂一样,燃烧起来有一股培根的味道。鲸油也不像莰烯那么易爆。在波士顿、纽约以及普罗维登斯等其他东部城市里,日落早且冬日漫长,燃烧鲸油的灯盏照亮了家和工厂,点亮了街灯和火车上的照明灯。燃烧鲸油的灯塔指引着船只归家。从远方海洋获取的能量成为人们日常居家、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与人们生活关系紧密,而使用它们的人可能从未看见、触摸或是品尝过鲸鱼。
将遥远地方的鲸鱼躯体与需要灯光的人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上千人的劳动。到了19世纪,大多数劳动力来自大西洋沿岸,比如楠塔基特岛、玛莎葡萄园岛、米斯蒂克,还有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这里有着鹅卵石街道、砖瓦砌成的保险公司大厦,石棉瓦搭成的寄宿所里每年驶出几百艘船只。托马斯·诺顿在楚科奇遭遇海难前,也是由新贝德福德出发的。如同所有离开这个深水港口的船只一样,“市民”号的建造离不开附近农村的资源支持。森林中的树木变成了船板和桅杆,田野中的大麻变成了船帆,铁变成了鱼叉和刀。羊毛变成了毛毡垫,铺在涂有沥青的船体上,船体上刷了一层铜以保护木质船板,防止船蛆啃咬或是腐烂。将原材料变成能够行驶的三栀船、横帆双桅船或是纵帆船(船只的类型根据帆的数量和位置划分)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包括木匠、捻缝工、制桶工、铁匠、缆索工和织帆工等;将他们这些人组织起来并付给他们酬劳则需要中介、装备店以及财务人员;航行需要船员和船长,加工处理鱼获则需要加工厂、购买者和营销商。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新贝德福德有两万人的工作是与鲸鱼的捕捞和加工相关的。
所有的鲸脂都是白花花的钞票。新贝德福德每年来自鲸脂初级产品的收入有一千万美元。不管鼓吹者如何向国会宣扬,鲸类资本从来都不是美国国家生产的重要部分,在19世纪50年代只占1%,到60年代就更少了。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却是第三大产业,紧随鞋袜业和服装业之后。一些家族从鲸脂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然后将这笔钱投资到其他工业,如造船业、铁路业和棉纺织业。浓缩的能量变成了巨额财富。赫尔曼·梅尔维尔对于新贝德福德这样写道:“在全美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有如此多贵族式的住宅、公园和花园”,这种奢华是“从海底捕捞鲸鱼所得到的”。
19世纪,对鲸鱼的需求使新英格兰的捕鲸者跨越世界各大洋进行捕猎。18世纪中叶,新英格兰的船员无法在陆地附近的海域找到鲸鱼,而当时鲸脂需要在岸上进行加工。造船工程师便改装了船只,使固态的鲸脂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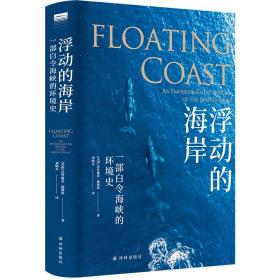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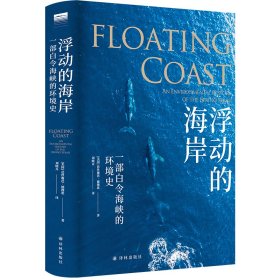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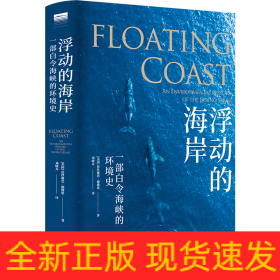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