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故乡下雪了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0.9 3.5折 ¥ 59.8 全新
库存4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王雁翔|责编:李向丽
出版社北岳文艺
ISBN9787537861458
出版时间2020-03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59.8元
货号1202102216
上书时间2024-06-09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001 从前的一些事情
014 故乡的味道
027 核桃、黄花及其他
036 几重春色逐灯来
053 旧时光里的秦腔
064 快乐的碎屑
079 李铁匠
090 刘瓦匠
101 流星划过夜空
110 柳石匠
125 麦场上的倒影
146 每当日落你会想起谁
156 母亲的流年
167 那些渐行渐远的生活
179 漂在城市的大哥
190 悄无声息的悲伤
216 苏骟匠
229 娑罗柳,以及它俯视的事物
260 童年纪
277 我的故乡下雪了
294 乡村手记
329 姚木匠
343 忧伤的田园
358 张皮匠
371 作物,大地的子民
内容摘要
《我的故乡下雪了》是青年军旅作家王雁翔最新散文力作。
全书汇集的24篇文章,以一个个横切面呈现时代发展中的乡村变迁,细腻而真实,不少篇章发表后得到读者的广泛肯定与喜爱。王雁翔是作家,也是资深记者,有深切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平静舒缓的叙述里,流淌着生命的忧伤与叩问,笔下的事物洋溢着厚实的人间滋味。书稿文字真诚、节制,既有生命体温和情感热度,又表呈着时代气质和理性叩问。
精彩内容
作物,大地的子民大自然万物都笼罩在乌黑的浓雾中,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可以穿透天与地。
――西塞罗母亲说,这个季节野菜好吃,想吃就去田里拾些回来。我说,等忙完园子里的活儿再去吧。我不敢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说自己很想吃一碗苜蓿芽拌汤,一盘凉拌苜蓿芽,苜蓿菜汤下面条,或者嫩苜蓿白面锅盔,我不能为满足自己儿时的口福增加母亲的烦恼。
我在菜园里帮母亲种下了旱黄瓜、豆角、辣椒、洋柿子(西红柿)、茄子、小葱、绿头萝卜,在地边种下几棵玉米、向日葵、大豆和篦麻。又将韭菜畦里的土松了松。昨夜落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泥土湿润,我将母亲从炕洞里掏来防虫的草木灰均匀地洒在韭菜畦里。又帮母亲种了一小块洋芋(土豆)。
母亲坐在小凳上,笑呵呵地看着我种菜,像看一棵树在风里欢唱,一株玉米不声不响地拔节。母亲的笑容,是对我娴熟劳作姿势的肯定,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母亲的菜园几十年不变,一色儿老品种,从不用化肥和农药。村里人都不养牲畜了,找不到农家肥,母亲让我拉着架子车跑了十多里路,专门去养羊的二舅家为菜园拉回满满一车羊粪。用城里人的时尚说法,母亲种得的是绿色无公害蔬菜。母亲种菜喜欢老品种老味道。城里人不种地,不知道老办法种出的老品种味道地道、朴厚,不晓得有机绿色蔬菜要施农家肥。
我拎着篮子和一把磨亮的小铲子,挽起裤脚在田野挖苦苦菜。村里几个从地头上走过的人远远地看着我,指指点点。离得远,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我心里清楚,他们肯定是说,瞧,这个人在城市里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没脱庄稼汉的皮。
我回来的次数少,村子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几乎都不认识我。或许他们听家里老人偶尔说起过我,一个游子的曾经与过往。
日子一晃而过,一晃就晃过去几十年。村子里的许多事情在时间里慢慢生疏、湮没,但我是在田野里闻着泥土和植物气息长大的,田野上的农事,像我小时候拿刀子刻在路旁树上的字,已长进我的骨头和心里。我相信,我肯定比那几个说笑我的人懂更多乡村事物。
少年时我跟父母一样,是娑罗原广袤原野上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耕地、撒种、施肥、锄草、收割、打碾、扬场,样样农活拿得起,放得下,是一个会干各种农活的庄稼把式。比如在烈日下一边挥镰割麦,一边荒腔走板地吼秦腔,在田头地角的树荫下四仰八叉,脸盖草帽睡困觉,端着碗蹲在门前树荫下一边吃饭一边跟左邻右舍大声说笑,听男人们七荤八素地谈论新媳妇的风骚以及年轻姑娘的丰臀细腰。
娑罗平原一望无际。少年时代在田里劳作,我常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庄稼,或者村道上的一棵小树,大地上的一粒草籽。我能听懂庄稼在风里私密对话,逗趣。所以,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片田野上的事情,一坨牛屎,一粒豌豆,一株高粱,一碗纯正的米酒,都清晰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十八岁那年,春天刚刚在大地上露出微茫的脸,我站在一棵青皮白杨树下,心里一片缤纷,一片苍茫。我想看看田野里的作物再走,但初春时节,还看不到那些亲切的作物在风中摇曳。狗盛爹扛着锄头走过来,说三娃你站在树下想啥呢,听说你要去当兵,好好的书咋不念了?人和树一样,经过风雨吹打才会长得好,才会有自己的天空与梦想。但我没这么说,我想了半晌,很认真地说,我不念书了,出去锻炼几年再回来种庄稼。这是真话,我当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喜欢在浮动着植物气息的庄稼地里撅着屁股忙碌。
现在,我站在暮色笼罩的田野上,大地仍然苍茫,但狗盛爹和我当年种过的许多作物都不见了,像深秋的一片片落叶,被风吹走了。当年我抚摸过的杨树已长成粗如人腰的大树。这是我家地头上的树,它的孤独跟我一样,在时间里疯长。
田野上的人纷纷逃离,都拼命往城里挤。母亲说,现在农村男娃找对象,女方不光要求男方城里要有商品房,还得有车。我在外头挥霍完了自己的青春,也住厌了商品房,被车水马龙的喧嚣噪聒出了失眠症,又折身回来,在田野里寻寻觅觅,像一条反向流淌的河,难免让人奇怪,不解。他们不知道,我心里装着城市的秘密,也和村里老人一样,装着这片土地上的秘密。或许那些一心往城里挤的人和我当年一样懵懂,看不清幸福的源头,不明白田野里那些消失的作物,像一个又一个亲人的亡故,失散了,就再难相见。
篮子里很快拾满了野菜,够我吃好几顿。我在田埂上坐下来,点一支烟吃着歇脚。天高地阔,田野里一派寂静,细密如针尖的阳光一层一层落下来,层层叠叠,地气蒙蒙,像翻晒我少年的田野时光。
人的味觉很难改变。我确实很想吃一顿阳春四月的苜蓿菜。记忆里,苜蓿不仅仅是牲畜的优质草料,也是救人性命的“粮食”。
生产队时代,农田耕作不能没牲口,队里饲养着上百头牛、马、驴、骡,耕种,打碾,拉运,样样离不开。开紫色小花的苜蓿是牲口最喜欢的草料,每个生产队种植面积都不小,平原上种着,山坡上的梯田里也种着。牲口吃一冬天干草,瘦得皮包骨。春天来了,苜蓿在春雨里迅速葱郁。饲养员先是在干草里拌少量嫩苜蓿,随着苜蓿日渐繁茂,干草逐步退场,苜蓿和各种青草登场,牲口开始了一年里的幸福生活,并一直延续到寒霜铺地。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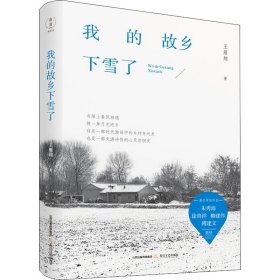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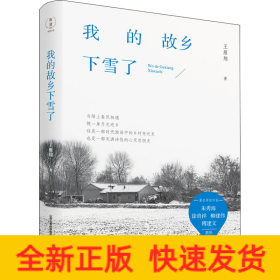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