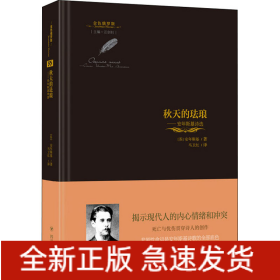
秋天的珐琅:安年斯基诗选/金色俄罗斯丛书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7.03 3.5折 ¥ 78 全新
库存3件
作者(苏)安年斯基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0126574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1446901
上书时间2024-05-28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秋天的珐琅:安年斯基诗选》
马卫红 译
俄罗斯诗坛的隐士(译序)
安年斯基是20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精致、敏感、深情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创作对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至关重要。他对新的诗歌节奏和诗歌语言的探索,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主要诗人。他丰富了俄国印象派诗歌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但象征主义者却视他为俄罗斯新诗的发起者,而饱满的诗歌情感和口语化音调又引起了阿克梅派诗人的关注。尽管安年斯基的创作遗产不多,但作为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其诗歌形象的鲜活生动、诗歌语言的绚丽飘逸以及诗歌情感的真挚细腻,为不同时代的诗人所称道。
伊诺肯基·费奥多罗维奇·安年斯基((Иннокентий Федорович Анненский,1855-1909)是俄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 翻译家、教育家,1855 年 8 月 20 日生于西伯利亚奥姆斯克。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位高级官员,母亲是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远亲,负责在家教养六个孩子。1860年其父被升为内务部官员,全家随之迁居圣彼得堡,后来其父因卷入商业投机而负债累累,终丢官,卧病在床。到了圣彼得堡后,五岁的安年斯基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这让他的未来生活变得复杂:身体日渐虚弱,健康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禁止的——热闹的户外活动被他姐姐教的阅读和哥哥教的拉丁文语法课所代替,他自幼就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但孤独促进了未来诗人早期的精神发展。上学期间,安年斯基多次因病情恶化而中断学业。由于生活中出现的诸多不顺利,成年后的安年斯基很不喜欢回忆自己的童年。1875年安年斯基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和语言学系学习。他从小就学会了法语和德语,至大学时期已经掌握了包括希腊语、英语、拉丁语、意大利语、波兰语、梵语、希伯来语等在内的14种语言。在大学学习期间,热爱创作的安年斯基突然中断写诗,“我爱上了语言学,除了论文什么都没写”,他后来回忆道。读大学三年级时,他深深爱上了36岁的娜杰日达·瓦连京诺夫娜·赫马拉巴尔谢夫斯卡娅。尽管心有灵犀,但这位矜持而谨慎的寡妇、两个儿子的母亲,并不急于成为她学生的妻子。只是在安年斯基大学毕业后,这对有情人才终成眷属,不久就有了他们的儿子瓦连京。安年斯基一生都从事教育工作,毕业初期在中学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1891年升任基辅“帕维尔·卡拉甘学院”校长,这是一家由卡拉甘夫妇为纪念他们早逝的儿子而建立的私立封闭式教育机构。在基辅期间,安年斯基决定将欧里庇得斯的所有悲剧翻译成俄文,并附上详细的评论。终他完成了这个计划,翻译了当时俄国读者所知道的17部悲剧。1893 年安年斯基又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第八中学校长。1896年被任命为皇村中学的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10 年,在任期间象征主义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曾在这里学习。此后安年斯基又担任地区督察,直至生命尽头。1909年11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于皇村火车站。
安年斯基的创作命运与众不同,颇有些“大器晚成”。他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比年龄较大的俄国象征主义诗人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巴尔蒙特都大得多,比“年青一代”的勃洛克大24岁。本应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开路先锋的安年斯基,在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界却仍然默默无闻。安年斯基一生都在写诗,却从未刻意宣扬过,许多作品只是在他去世后才为人所知。部诗集、也是生前出版的一部诗集《浅吟低唱》于1904年面世,不过这位谦逊的诗人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使用了“尼克托”这个笔名(读音同никто,意为“无足轻重的人”)。诗集出版后,除了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和勃洛克之外,似乎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直到安年斯基去世一年后,也就是1910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柏木雕花箱》问世,才为诗人赢得迟来的喝彩。
安年斯基可以称得上是文学生活中的隐士,既没有与象征主义诗人一起开疆拓土,也没有为捍卫“新艺术”的权利而战斗。尽管他“出场”的时间比同时代许多著名诗人要晚得多,但这种特殊的“出场”顺序反倒成全了安年斯基在当时文学运动中树立的特殊地位。安年斯基曾在一些评论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俄国象征主义和颓废派诗歌的好感,但他与这些文学流派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甚至缺乏与其诗人之间的亲密接触。而这样,恰恰就让安年斯基得以独悟、独明、独见,形成了远离团体责任和团体意图的立场,可以自由选择为实现自己的创作目标所需要的东西,而不受某种创作框架和原则的束缚。
安年斯基身上聚合了几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一个正直的官员和一个独特的评论家、一个严格的老师和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这种多元的个人身份和反常的创作命运在他身上凝集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气质,在他的诗歌体系中留下了非常完整和独特的、源于矛盾和复杂层次的印记。例如,在体量不大的诗集《柏木雕花箱》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层次: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法国和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熏陶、印象主义的画风、浪漫主义的情怀、现实主义的自省、唯美主义的追求,以及19世纪俄国心理小说的影响,甚至还有对诗歌实验一时兴起的尝试 。
在安年斯基的创作生涯中,对其影响深的当属法国象征主义。安年斯基与法国象征主义美学有着极深的联系。因此,就其诗歌世界观而言,安年斯基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其诗歌主题常被封闭在孤独和存在的苦闷中,字里行间散发着淡淡的忧伤和愁绪,诗中经常出现枯萎和昏暗、噩梦和梦境、阴云和落日等意象和画面。安年斯基的诗歌具有室内精致性、个人心理主题封闭性的特点,这是一种暗示诗、言未尽意的诗,追求艺术印象的感染力。然而,安年斯基的诗歌却与象征主义诗歌有着根本区别。作为反映文化衰落和弃绝上帝的法国象征主义的拥护者,安年斯基同样不想亲近上帝,这与俄罗斯象征主义(尤其是以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勃留索夫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在创作中寻求上帝很是不同。安年斯基试图找到世界的基础和中心,但不是像基督教教义所教导的那样在上帝身上寻找,而是在他自己身上寻找。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安年斯基诗中的“我”和“非我”之间存在一种不和谐,这一点在《天上的星辰能否黯淡……》这首诗中可见一斑:
天上的星辰能否黯淡,
人间的痛苦能否持续——
我从不祈祷,
我不会祈祷。
时光会熄灭星辰,
我们会战胜痛苦……
假如我去往教堂,
我会和法利赛人在一起。
安年斯基的诗中没有象征主义诗歌特有的对两个世界的暗示,诗人只不过是在描绘生命的瞬间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和对周围环境的瞬间感知,从而呈现出抒情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抒情主人公也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通人。安年斯基诗中的个人主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是与众不同的:这是对内在的“我”的极大关注和敏锐的孤独感。然而,这种个人主义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处于边缘状态中——处于与“非我”(即外部世界)和他人意识的关系之间的紧张体验中。需要指出的是,心理描写的深度与精致、专注于自己的“我”并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自我肯定,而是恰恰相反,让诗人转向了他人的“我”——这个“我”代表了整个世界以及同样悲惨的自我封闭。
安年斯基称自己为诗歌领域的“神秘主义者”,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另一个世界怀有特殊的兴趣,而是因为这个词揭示了诗人的创作愿望——力求理解和揭示存在的奥秘。为此,安年斯基总是尝试把人的个性与自然世界、与整个宇宙联系在一起。象征对他而言,不是了解“不可知”的手段,而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与其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对应关系,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新诗正在寻找感觉的准确象征,即对于情绪而言的生活的真正基底,即一种精神生活形式,它能让人们平等,它以同样的权利进入人们的心里,就像进入个人的心里一样。”在安年斯基的认识中,象征主义通常是“现代主义”与被其掌握的社会心理学经验的结合,这种结合在他的诗歌中孕育了一颗奇特的果实——一种被称为“心理象征主义”的创作方法(金兹堡语)。
虽然人们总是把安年斯基归入象征主义诗人阵营中,但总的来说,在安年斯基的诗歌中,即使是复杂的诗歌中,仍然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俄罗斯传统抒情诗的音调,有时甚至是浪漫主义的音调,《转瞬即逝的忧伤》就是这方面的优秀范例:
白昼消失。一轮朦胧的黄月
凝望着阳台,洒下了辉光,
而在敞开的窗户的绝望中,
失明的白墙暗自神伤。
此时夜晚将近。云层幽暗……
傍晚后的瞬间令我惆怅:
在那里度过的一切——是渴望和忧伤,
在那里亲近的一切——是沮丧和遗忘。
在这里傍晚犹如梦幻:怯懦而短暂,
但对于没有琴弦、泪水和芬芳的心房,
这乌云不断碎裂与融合的地方……
亲近傍晚胜过亲近玫瑰色的夕阳。
安年斯基细致地区分了“新诗”的个性和浪漫主义个性。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深渊将源自拜伦抒情性新诗的个人主义与和源自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区别开来”,新诗中的“我”——完全“不是将自己与似乎完全不了解的整个世界相对立的‘我’……”。肯定个体的价值和滋养它的超人性价值是浪漫主义激情与浪漫主义悲剧的永恒源泉。安年斯基揭示了现代人的内心情绪和冲突,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意志坚定、反省深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又类似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和契诃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不适应社会斗争,也无力创造个人幸福。因此,契诃夫的人物所特有的渴望、无法实现的和谐,在安年斯基的诗中完全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如《紫水晶》):
但愿炽烈的光线莫将
紫水晶的边缘灼伤,
但愿一束摇曳的烛火
在那里流泻和发光。
光芒在那里暗淡碎裂,
只为自己许下的承诺——
某处呈现的不是我们的联系,
而是辉煌灿烂的融合……
安年斯基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印象主义特点,他所描绘的并不是他所知道的,而是他此时此刻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印象主义诗人,安年斯基与俄罗斯抒情诗人费特和象征主义诗人巴尔蒙特远不相同。在他的诗中有深深的真诚、隐秘的感受,甚至是一些极为复杂的心理体验,如对于生活和生活诸多瞬间的困惑、无信仰的悲剧、对死亡的恐惧等,这诸多的情感与情绪在他的诗中都找到了完美的表现形式。而当他言及抒情主人公与既充满敌意又与之紧密联系、且在其物质表现上令人痛苦而美丽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他的诗就显得更为有力和更为独特。
俄罗斯诗人霍达谢维奇称安年斯基为“死亡诗人”,不论是否言过其实,这却揭示了安年斯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安年斯基的确写了不少关于死亡、垂死和墓地的诗,当然,这并非偶然。安年斯基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终生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因而,他对死亡的感知要比许多诗人更强烈、更尖锐,死亡也因之成为贯穿始终的诗歌主题。安年斯基对死亡的认识使他有别于俄罗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他不相信彼岸,不相信人有来世。在安年斯基看来,死亡即代表了灵魂的消失、存在的终结:
沉寂的四月暮色苍黄,
告别了璀璨的星空,
柳枝节便在后的
死亡的冰雪中隐没行踪;
它消失在暗香浮动的烟雾里,
消失在停息的悲哀的钟声里,
远离了目光深幽的圣像
和被忘在黑色墓穴里的拉撒路。
残缺的淡月高悬于天穹,
为了不能死而复活的众生,
一捧热泪顺着柳枝流淌
流淌到天使绯红色的脸上。
《柳枝节》这首诗充满了死亡的语义,正如诗歌标题所示意的:这是复活节前的后一周,正值春季的一个宗教节日。与传统上对春天的认识不同,这首诗赋予春天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柳枝节在沉寂四月的苍黄暮色中慢慢离去了,“苍黄”这一色彩含有消极语义,象征着疾病、枯萎以及终的死亡。“暮色苍黄”即是日薄西山的傍晚,是白昼的结束,这里可以理解为是对生命的终结、对人的灵魂即将消失的暗示。拉撒路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象征着人的死而复生,但诗中的拉撒路却被“忘在黑色墓穴里”,诗人以此表达死亡的必然性和人死后无法重生的思想,后一个诗节对此表达得尤为清楚。
童年的经历和缠身的病痛让安年斯基对死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也赋予他敏锐的嗅觉——总是能够从世间万物的华美表象中嗅到背后所隐藏的腐朽和死亡的气息,《九月》一诗证明了安年斯基对秋天的态度与许多俄国古典诗人截然不同。在安年斯基的眼中,秋天是死亡和走向衰败的象征,九月是一个人生命的后和弦,是衰老和疾病不可避免的开始。看着枯萎的大自然,抒情主人公感受到了生活的奢华与疲惫。美不再属于他,他谦卑地放下双手,面对着厄运和必然。
沐浴金光的花园已然凋零:
散发着慢性病般的紫色诱惑,
太阳后的光焰划出短促的弧线,
它已无力化作芬芳的硕果。
死亡主题在安年斯基的艺术世界中具有象征意义,它常与忧伤主题交叉融合。“忧伤”对于诗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或者更加确切地说,不仅仅是主题,还是一种认识、一种情绪。“忧伤”贯穿了诗人的全部创作,是他常用的词语之一,且多姿多彩、无处不在:忧伤不仅是时间上的,还具有颜色;不仅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不仅属于人,还属于世间万物。许多诗歌标题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回忆的忧伤》《归来的忧伤》《约会前的忧伤》《蓝色的忧伤》《转瞬即逝的忧伤》《缓缓滴落的忧伤》《我的忧伤》《幻影的忧伤》《火车站的忧伤》《钟摆的忧伤》《沉寂雷电的忧伤》,等等。忧伤是什么?对安年斯基而言,忧伤是缺乏多样性的生活,是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对逝去时光的追忆,是失意的爱情,是落红残叶,是斜阳晚照……忧伤总是不经意间悄悄溜进人的心头,让你感慨渐行渐远的童年和青春,而在地平线上,所能看到的只有即将到来的晚年和自己生命的落日。抒情主人公感觉到死亡的临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过去的岁月——这些岁月已经无法挽回,也无法弥补。例如《忧伤》:
椭圆形的淡红色蓓蕾,
被晨雾紧紧地包裹,
一簇簇银灰色的花朵
化作虚幻的花束坠落。
……
倘若你被寒热所折磨,
一连数周卧床不起,
你就会懂得隐藏在单调
时日中大麻的甜蜜,
你就会懂得,当你小心地
数着野蔷薇光泽上的色调……
当你在哀伤的各时期之间
无意识地筑造一枚枚徽标。
安年斯基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有人生经历的人,他告别了自己的青春,为充满离愁别绪的爱情而痛苦(如《在三月》《什么是幸福?》),并预感到生命末日的临近,简言之,生活中的一切都令他不安和忧伤。抒情主人公“我”所代表的个人生活成为生命的象征,诗人将其阐释为生活失败、无可挽回(如《生命的驿站》《从杯子的四周》《很远……很远……》)。不仅如此,生活还是一种欺骗,这种生活、这种现实,以其丑陋、粗俗、违反某些“理想的”审美规范而令诗人感到恐惧和排斥。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导致诗人将生活、大自然和世界视为虚幻的、不真实的幻影,于是,失眠、噩梦、女巫、幽灵等意象便频繁出现在抒情主人公的意识中。象征主义诗人沃洛申认为,极少有人像安年斯基那样用诗的语言“如此生动、如此丰满、如此令人信服地完整描述噩梦和失眠”,在此以《另一个声音》为例:
啊,绵延不绝的忧郁!
疯狂的诗句,
就像婚宴中
衣着随意的宾朋,
我读着,悲从心生……
在那里,有朦胧夜色中
清冷的繁星,
在那里,有先知的心灵
忍受的三昼夜的苦痛,
在那里,在沉重梦呓中
含情脉脉的幽灵
将自己黑色的面纱,
安娜夫人的面纱,
向他的床头
垂下,笑靥如花……
抒情主人公自觉无法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他很清楚这一点,并因此而痛苦。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内心的矛盾、幸福的短暂。他清醒地意识到,美好的梦想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庸俗尖锐对立,这庸俗总是让他想起如幽灵、如噩梦般的社会弊端和生活现象(如《不眠之夜》)。令人感到压抑和苦闷的现实生活阻碍抒情主人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无处倾诉的“我”总会在梦境中展露内心世界,因为睡梦中的心灵不会受到任何束缚(如《哪一个》):
丢掉了令人厌烦的面具,
也感受不到存在的桎梏,
自由的“我”进入了
多么神奇的童话乐土!
在那里,有我内心隐藏的一切,
多年来不敢对众人言明;
有烁亮的星星缀满夜空,
还可以爆发纵情的笑声……
在安年斯基的艺术世界中,梦境被描绘成一个神奇的国度。在那里,世界是抒情主人公意识的产物,“我”是真实的,可以大胆地敞开心扉,也可以纵情欢笑。有梦想的生活是美好的,而诗人需要思考的是,真实的生活在哪里——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他请求造物主为他揭开这个奥秘:
彼岸世界的君王啊,
我的存在之父,
你至少要向诗人的心坦言,
你创造的是哪一个“我”。
一般而言,在象征主义诗歌中,超现实比现实本身更美,但读者在安年斯基那里却看不到现成的答案。造物主真的能为抒情主人公破解这个谜底吗?不得而知。诗中留下了一个未完成的结尾,它要求读者自己做出结论。或许正是由于诗人强烈地感受到世事的艰难、生活的不如意,才让他更加珍惜时光、热爱生命、渴望生活。安年斯基在许多文章中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而《痛苦的十四行诗》形象地、具象化地诠释了这一思想:
蜜蜂的嗡鸣刚刚停息,
蚊子的呻吟却越来越近……
心儿啊,白昼结束了不安的空虚,
你不会原谅它的哪些骗局?
……
我需要黯淡天空上的云烟,
云烟漫卷,而随之消散的是往昔,
是微合的眼睛和梦想的音乐,
是不知歌词的梦想的音乐……
啊,只需给我一个瞬间,生命的瞬间,而非梦幻,
但求我能变成火或在火中涅槃!
安年斯基写社会主题的诗不多,著名的诗篇就是《爱沙尼亚老妪》。诗人用这首诗回应1905—1906年发生在爱沙尼亚的革命事件,表达了对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革命运动并处决革命者的抗议,同时也概括地反映出不公正的世界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生存气氛,以及处于其中的个人的生活不如意,甚至是悲剧性命运,而这,几乎是安年斯基诗歌的全部底色。
【免费在线读】
商品简介本书收录安年斯基诗歌200余首,大部分为国内*次译介。安年斯基被誉为俄罗斯诗坛的隐士、死亡诗人,是俄罗斯现代诗的发起者,诗歌以精致细腻、言未尽意、象征暗示而见长。抒情诗主题常常被封闭于孤独、忧伤的心绪中,擅长抒发对生活的瞬间感受、心理的细微变化、对周围环境的瞬时感知,地关注内在的“我”,即对孤独的尖锐感受,突出个人心理主题中的孤独感和幽闭感。可以说,在安年斯基的诗中,深沉的真情、私密的体验、以及对复杂事物的哲理性思考,如对生活的思考、失去信仰的悲剧、对死亡的恐惧等,都找到了一种完美的书写形式
作者简介
马卫红,女,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从事俄语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教授20余年,潜心俄语教育研究及教学改革,教学经验丰富,现任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目录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俄罗斯诗坛的隐士(译序)
诗
神秘的座右铭……
在灵柩旁
同貌人
哪一个?
在门槛上
叶子
临窗遥想
理想
五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风
无用的诗章
在途中
涌上心头的回忆
生命的驿站
在那里
?
首钢琴
还有一个
从杯子的四周
Villa Nazionale
又在途中
在水面上
秋天童话的终结
清晨
管家万卡在狱中
蜡烛即将熄灭
布景
失眠
百合
阳台即景
锤子与火星
归来的忧伤
诗人的诞生与死亡
“苍蝇如同思想”
在绿色的灯罩下
第三首痛苦的十四行诗
第二首钢琴
平行线
忧伤
心愿
淡紫色的雾霭
转瞬即逝的忧伤
蜡烛送进来了
罂粟
弓与弦
在三月
蒲公英
一台老手摇风琴
柳枝节
你又和我在一起
八月
那是在瓦伦科斯基瀑布
冬日的天空
冬末的月夜
Trumerei
闹钟
坚强的蝉
黑色的剪影
紫水晶
灰蓝色的晚霞
一月的童话
噩梦
基辅的教堂
彼与此
抑扬格
拳头
噢不,不是身躯
照魔镜
三人
清醒
祭悼之前
民谣
赠诗
明亮的光环
沉寂雷电的忧伤
回忆的忧伤
白石头的忧伤
雨
十月的神话
无乐的浪漫曲
Nox vitae
方形小窗
痛苦的十四行诗
冰冷的囚牢
雪
睚鲁的女儿
火车站的忧伤
在车厢里
冬天的列车
致女伴
死去的女人
版画
我在水底
青铜诗人
“Pace”和平雕像
钟摆的忧伤
一幅画
一座老庄园
前奏
音乐会之后
巴黎的佛教弥撒
银色的正午
儿童球
死亡
黑色的春天
幻影
云
中断的韵律
第二和第四一扬三抑格音步
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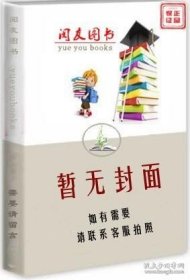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