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都市(空间与记忆)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20.47 5.4折 ¥ 38 全新
库存2件
广东广州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比)斯特凡·赫特曼斯|译者:张善鹏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295670
出版时间2018-07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38元
货号30226522
上书时间2024-05-20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斯特凡·赫特曼斯(StefanHertmans),享誉国际的弗莱芒语作家,小说《初见》(Alsopdeeerstedag)曾荣获2002年度荷兰费迪南德图书奖;小说《战争与松脂》(WarandTurpentine)荣获2014年度荷兰AKO文学奖,并获2017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
译者:张善鹏,历史学博士,国际政治学博士后,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目录
\"进城 3
1 悉尼的平行世界 11
2 图宾根的哥特涂鸦 31
3 的里雅斯特的夹缝生存 42
4 德累斯顿 61
5 城市之间 84
6 布拉迪斯拉发的年代错乱 100
7 维也纳 125
8 萨尔茨堡 139
9 马赛的都市传奇和沙丁鱼 165
10 永远不要逃避爱人的吻 195
11 浮云与家乡 214
12 天涯海角 239
出城 244\"
内容摘要
\" 在《大都市:空间与记忆》中,作者游走于欧洲那些深具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的里雅斯特、德累斯顿、布拉迪斯拉发、维也纳、马赛,以及他的家乡根特),他在城市空间漫游的步伐始终围绕着“记忆”这个主题:在维也纳他追随耶利内克和伯恩哈特的足迹,在的里雅斯特他“邂逅”了乔伊斯和温克尔曼,在德累斯顿他“巧遇”了穆里施小说中的主人公……作者借所游历之地的历史文化探讨了构成当代欧洲认同的要素,也探讨了当代都市生活的深层本质。
《大都市》描述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悟,即以局部的自我迷失,获得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作者以一种诗意的语言把游记和哲思结合起来,印证了16世纪的一句古话,“任何旅行都是在家边游走”。
精彩内容
\"进城有一部小说,它最富野心地描写了现代城市,开篇即是一幅浓缩的世界文学场景。为《没有个性的人》作旁白的人仿佛是从一颗地球卫星的高度俯瞰“大西洋上空的低压带”,继而把目光投向维也纳这座城市:再往东走,就是俄国的高压地带,北边则依旧没有降低的趋势……大气层中的蒸汽含量达到了最高点,空气中的水分含量却降到了最低点。简言之,用一句老话来描述这种情景极为合适:那是一九一三年八月的一个晴日。狭窄深邃的街道不时窜出摩托车来,冲入阳光明媚的广场的荫凉之中。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熙熙攘攘,汇成了黑压压的人群。
随着这个长镜头的推进,罗伯特·穆齐尔把自己《没有个性的人》的开篇,完美地设计成了当时流行的“维也纳咖啡”风格:一种科学思维练就的视角(这是毛特纳与恩斯特·马赫生活的城市),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孤傲(这也是勋伯格与韦伯恩生活的城市),一种突破常规感知未来的天赋(卡尔·克劳斯那样的批判精神),一种以开放心态重新审视事物的能力(就像维特根斯坦),同时也有一种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可以把琐碎的日常生活放入或毋宁说是嵌入和融入俗世的框架之中,给人感觉维也纳是一座大都市,它为现代世界而生,也是现代世界的宠儿。然而,就在这个独特的视角刚刚展开,仿佛一幅大幕刚被拉到舞台一侧的时候,他就把精心挑选的城市琐事特写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略带玩世不恭地描写了一起交通事故,介绍了一些人物,他们日后成了对手,此时则只是看客。这种开篇风格难免被人模仿,但已不可能被超越,即便是十七年后,美国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无法做到。帕索斯在创作关于美国城市的宏大的《美国三部曲》时,为《北纬四十二度》写下了这样的开篇文字:一个年轻人快步从人群中走过,他身后的人群在夜幕下的街道渐行渐远;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双脚早已疲惫不堪;他努力睁着眼睛,眼皮却昏昏欲睡,他的脑袋歪向一边,一侧肩膀已经下沉,一只手松弛地垂着,另一只手仍握紧行李;他饥肠辘辘,头昏眼花;脑子仿佛变成了蜂窝,嗡嗡作响;他腰酸背疼,搜寻着招工的信息:修路工要会使铁镐和铁铲,渔夫要会用鱼钩……这个年轻人在人群中独自行走,他孤身一人,贪婪地看着,贪婪地听着。
读者几乎早已看出:这个人物来自乡下。对于新鲜的事物,他都天真地表示惊讶;对于古老的行当,他却崇拜得不得了,从而暴露了一个乡下少年的无知。这种情况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事:乡下人不会习惯于对事情熟视无睹,他有着新移民的开放胸怀,使他更加敏锐地倾听和观察。这种开篇风格,虽然被日后小说的现代叙事手法发展得无以复加,但与穆齐尔最初的权威版本相比,都显得十分老套。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主人公是步行来到城里的,随着他的脚步,我们看到了他在途中遇到的重要人物。普鲁斯特当年也是步行来到巴黎的,只是在必须赶时间的情况下,才跳上舒适的敞篷车沿着布劳涅森林的道路前进。伴随着斯万先生的活动,这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不断闪现,仿佛悄然融入他的小说当中。当詹姆斯·乔伊斯像一个荷马时代的流放者徘徊在的里雅斯特的街道时,脑子里想象的却是都柏林未来的街道规划。相比之下,罗伯特·穆齐尔几乎是一个从波音747飞机上俯瞰城市的彻头彻尾的现代旅客。有所不同的是,此处出现了一位带着文学放大镜的解剖学家和科学家——此人可以在飞机降落之前系紧安全带时,以及乘务员微笑着提醒他收起小桌板时,仍能飞速地观察窗玻璃上那只濒死的苍蝇。
当年,托马斯·品钦也曾在《万有引力之虹》的开篇以这种特写风格展现大城市生活的混乱不堪和暗藏危机:空中传来一声警报。这种警报此前也曾响过,此次却显得异乎寻常。天色已晚。疏散仍在继续,但到处都是战场。车里没有亮光。周围漆黑一片。车站那老得不像样子的钢梁耸立在他头上,玻璃窗应该在更高的地方,白天能让阳光照射进来。但此时正是晚上。
最后这句话点亮了该书后面的主题。品钦在这一点上比穆齐尔略胜一筹。穆齐尔主要描写的是白天的城市,品钦则主要描写光怪陆离的城市夜生活:只能看到近处的人脸,就像照片底片里的半光画面,让人联想起在城市急速穿行的车上,深色防弹车窗投射在那些大人物脸上的绿色斑痕……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在《美国精神病人》中描写主人公初进纽约的情形时,让人感觉径直堕入了但丁笔下的地狱:第十一大道和第一大道交叉口的化学银行大厦一侧,涂着几个血红的大字,“入此门者,万念俱灰”。这些印刷体字母极大,从在拥挤的车流中颠簸着驶离华尔街的出租车后排座椅上都能看到它们……当然,城市全都包含这些东西——入口和出口;公共汽车冒着恶心的黑烟缓缓驶出车站;天刚蒙蒙亮,通往市中心的主干道上,汽车就已排成慢慢蠕动的长队;晨光熹微中,某个凌乱不堪的房间里,两个偷情的人仍在意犹未尽地享受良宵;凌晨四点,某个小酒吧的后院里,一个小伙子在呕吐;商店橱窗的反光照射着人脸,人们想不看它都不行;某座酒店的后门,服务员不小心崴了自己的脚;公园里满是尘土的便道上,有人在跑步;老醉汉不知道自己正在喝第几杯酒;吸毒者无所事事;一个头发油光闪亮的人行色匆匆,腋下一如既往地夹着新秀丽牌公文包;一脸困倦的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穿过人行横道;菜贩子准备在中午之前收摊;一扇窗户反射出一道闪光;或是电车来不及刹车,轧死了行人,尸体只能依稀可见。若是从空客飞机上俯瞰城市的话,这些都是看不到的,至多只是一些移动的黑点,像甲虫一样在地面到处乱窜。
威廉·科尔斯(WillemKoerse)在《无边的城市》(TheLimitlessCity)中写道:“人们来来去去,只有车轨留在原处。”即便如此,人性的力量依然附着在城市的概念上,这一点永远也不能被忽视。城市是人类交往领域的终极形式。
在波德莱尔看来,19世纪的城市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场所,规范人际关系的不再是财产的所有权,或是宗族、家长、联姻这样的古老风俗,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漂泊感。城市属于每一个人,但不单单属于某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社交和性交活动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顶多产生一些心理影响;它也是为什么城市可以接纳匿名者,而且孕育出一种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风气。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的解放。卢梭在《爱弥儿》中斥为城市堕落标志的东西,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后,就被波德莱尔积极大胆地称赞。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四个等级的特权,即必须基于普遍接受的公意的基础之上的特权,据波德莱尔看来,早已在浪漫主义者卢梭痛恨的巴黎市区得到迅速发展。波德莱尔关于城市的构想后来证明颇有先见,它率先解放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碰了她就得娶她”曾是乡下农村的格言,因为性别关系直接涉及继承家产的问题,意味着分割土地和财产。在城市
里,这种潜在的契约消失了。城里的社会契约只在某时某地生效。
在二十世纪,这些思想被安迪·沃霍尔发挥到了极致。沃霍尔通过他的“工厂”工作室及其夸张的画作,强调城市组织的剧场特质,以纽约最为显著。然而,这种剧场特质并无负面含义。城市就是一座临时的舞台,那里的人们心里清楚,许多事情注定要被周围的观众无情地加以分析。安居于乡下的人永远也意识不到这一点。
刚刚来到城里的乡下人一定要克服人格危机,而且一定要为自己设计一个新形象。这就意味着城市仍是文化自恋主义的中心,而这种自我意识的相应特征,是彻底消除根基、故土或起源之类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一个人在大城市里建立的名声,不是来自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源于争自由、求解放的奋斗。
下面这种情况或许并非巧合。近年来,一些知识分子,包括萨曼·拉什迪和雅克·德里达,都在致力于创建所谓的“避难之城”(citiesofrefuge),那是一种由自治性质的友好城市组成的国际网络,可以接纳形形色色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只要他们的合法诉求说得过去,就能找到避难所。通过这种办法,就能让城市
再次扮演波德莱尔在国际关系领域安排给它的先驱者角色:接手世界其他地方无法顺利开展的事情,成为国际关系正常化的先锋。
“避难之城”的概念来自德里达所谓的“热情好客的义务”。为了推广这种合法组织,有必要重温在二十世纪业已退居幕后的一种古老思想:城市主权论。换言之,这些避难所应该能够取得古代城邦和传统城市国家那种切实可行的自治权。根据这种关联性,德里达提倡一种普世政治:能够真正解决那些棘手的社会问题的,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城市。鉴于民族国家不再准备为庇护权提供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保障,或在政治上太难操作,也许应该赋予城市一种新的角色,就像科恩·布拉姆斯(KoenBrams)在为德里达的一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所称,它们不应再像在十九世纪那样成为“民族国家的奴性象征”:如果城市和都市身份这样的话题,讨论起来依然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城市能否超越民族国家,或能否在更为具体的层面,在以宜居和避难为关注点的新型“自由市”的意义上,把自己解放出来……国家主权不能,也不必成为避难所的终极原则。这种愿望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选自德里达1996年3月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首届“避难之城”大会上的发言)现在有一种推测,从众多启示录般的卡通连环画中可以看出,近来城市已经被都市丛林吞没。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一
种接近生态学意义的文化多元论,即城市在民主、开放的社会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人类活动的缩影,城市不断在末世幻象和郊区贫民窟这一端,与优雅的广场、纪念碑和小型社区工程构成的另一端之间寻求平衡。我们的文化实质,其实与众多城市一样,分散在许多地方。不论异域都市的经历如何不同,电影《橡皮头》和我在的里雅斯特看到的斯洛文尼亚女乞丐,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描写异国城市的作品早已够多,谁若打算去蓬塔阿雷纳斯、达喀尔、巴库或安克雷奇的话,将会惊讶地发现一种即将成为大都市的社会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利弊。墨西哥城、巴黎和新加坡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只需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角落走一走,就能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同样的例证。这也是实情,它们只不过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而已。\"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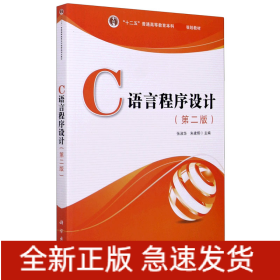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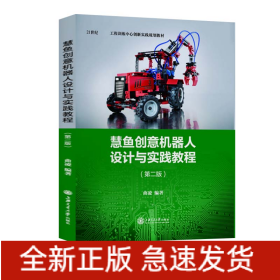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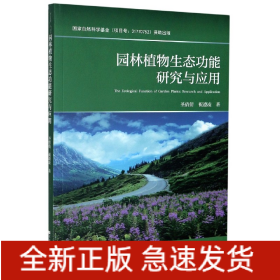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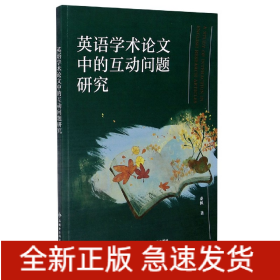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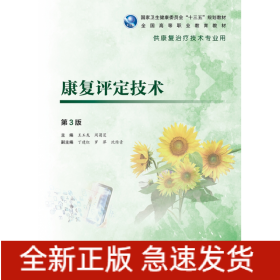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