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一罚四】迷影程波
集团直发,全新正版书籍,假一罚四,放心选购。可开发票
¥ 30.4 5.2折 ¥ 58 全新
库存7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程波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5252
出版时间2022-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628427
上书时间2024-09-15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程波,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毕业,现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教育部戏剧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著有《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电影的探索策略研究》《光影路:世界电影地图(三卷本)》《现象与影像:立雪斋电影笔记》《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西风破:西方美学讲读》《天才与疯子:达利传》《光影中国十讲》《影视艺术概论》《西方美的历程》等多部作品,发表学术论文、影视评论百余万字。理论研究和评论写作同时,从事剧本、小说、诗歌创作,创作、策划、拍摄、监制影视剧、纪录片、专题片多部,曾在《山花》《青年文学》《小说界》《小说家》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
目录
?迷影
?别人的房子
?达利的一天
?对岸的树林
?呼喊
?马拉美的婚礼
?面试
?痊愈
?青年主人公
?周年
?三声炮响
?醉酒带来歌唱
?左肾
?寻找李眉
?玻璃
?异禀
内容摘要
“我”是一名生存于斗室的实验科学家,带着一个神秘的小木盒走向对初始狂热爱情的寻找。
行程中,“我”遭遇偶劫、丢失车辆,辗转来到海边码头,以确认心中“她”与“她们”的历史信息……遁入暗夜大海,“我”游向城市的水道,解救了一条受难的美人鱼;她赠“我”发光鳞片,说:当需要时,对它们说要有光,于是便会有光。
借助美人鱼鳞片的微光,斗室中诞生出“地铁进站”的巨大影像,一种地老天荒的情感在幽暗的房间里荡漾。
#我迷恋的那些影子,其实一直就在那里等待着我,等待凭我而生#该小说集收录《迷影》《寻找李眉》《左肾》《对岸的树林》等16篇短篇小说,风格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先锋倾向,部分作品具有一定的类型感,有影视改编的质感基础。
主编推荐
《迷影》这部小说集强调叙事试验,具有一定的先锋意味,即着力营造如何讲述一个故事,小说技法征用了电影表现手法,有一定的艺术性。其二,小说散发着一定的青春感,作者将青年生活的记忆进行了裁剪,特别是将青年人生活的某种迷茫和孤傲,以及对身体的沉溺做了较为深入地表达,具有自白书写法的特点,有一定的文学感染力,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代入自身体验。其三,程波小说有一定的镜头感,在描写小说人物的时候,就像用摄影机跟着人物的脚步,有丰富的细节,又有斑驳的光影感,特别是写到情感的时候,这种追踪写法让文学本显得自如,也营造了较为饱满的氛围场景感。
精彩内容
《迷影》1那天天一亮就开始下大暴雨,雨大得出奇,似乎是在一瞬间从地下涌出来,想把我卷到街上去。城市另一端的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我,说每当雨水多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见我,她还煽情地说,房子建在水上,就只有一生漂流了。
不过,我是该去见见她了。
几个月以来,我都躲在这个绝少人知道的地方,摆弄一些玻璃做的罐子管子,同时收发食物和信件。那些在眼前晃动的人影,跟我隔了层玻璃似的有些隔阂,他们从不正眼看我,也许还觉得我是个无所事事的家伙,也罢,反正贴了太阳膜的窗子,更适合偷窥,我液晶屏上闪动的光,比太阳光更能长久地让我凝视。
几个月前,她在海洋世界有玻璃顶篷的走道里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告诫过我,不要以为自己是在洞彻中幽居,不要以为别人都像这里的鱼,你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你,其实,你看见的不过只是暴露狂们并不在场的表演,而别人对你的窥淫癖也许根本就不介意。
那夜四次,我们进进出出。开始是海洋世界人工岛上的灌木迷宫,然后才是我们的身体。她说,根据走出这个经常迷失孩子的迷宫的攻略,不论路直路弯,每走四百步,就要向左转一次。我对她的话不以为然,因为很明显我们都不是被魔鬼追杀的小孩子,我即便是倒退着走结果又能怎样呢,就真的走不出去吗?她抱怨我,道理这么简单,我为什么就是不听她的话呢?她甚至还假装自责地提起一个古怪的念头,说都怪刚才还不够四百下,她就心软让我从她身体里逃了出来,她原本想好了默数到四百下的时候,才放开我。据说,如果那样的话,女人就可以把她身上的这个男人变成听话的孩子。
我躲起来,不全是因为害怕变成孩子。
作为一个还没有什么成就的实验科学家,我需要时不时地消失一下,干点别人现在还不理解、将来一旦理解了就有可能欣喜若狂的事情。从本质上说,我憎恨斗室中的浮士德博士,但是每当我躲起来的时候,这种日子我过得比他还有滋味。
就在几天前,为了光线射入房间能有一个更好的反射角度,我把那些原本在我安心工作时就会吱吱嘎嘎脱落的老式墙纸全部换掉,换成了纯白色的,还装了好几面镜子。那些旧墙纸的背面胶水早已老化,油腻腻的,还粘满了虫子的尸体,我把它们扔在卫生间里,分了好多次,一把火接一把火地在马桶里烧掉,灰烬随着排泄物冲走。
我还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装置,当房间里最明亮的那一面墙的亮度也达不到八个流明的时候,感光开关就会被激活并连动一个输出功率高达三马力的液压机械设备,随后屋顶的滑轮和地板上的滚轴转动起来,一面由坚硬轻巧的复合材料制成的墙就会从屋顶上迷幻地渐垂渐低,把原本就不大的房间再分成两半。这种时候,我就会从我的工作台这边穿墙而过,坐在更幽暗的那一边的矮沙发上,随便地听上一张名为“门”或者“墙”的唱片,休息一下。当然,这只是正事之余的小把戏,我要做的事情远比这个复杂。不过谁能够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人们怎么说来着,凡门都是墙?还是凡墙都是门?不管哪一个吧,我想那意思都是说:自己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关系就是那么回事,虽然艰苦的事情可能永远都没法结束,但也不能总是工作,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
我是要去见见她了,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一下。
2雨刷和雾灯都还能用,全景天窗也没有渗水下来。好多天没有人管,又淋了这么大的雨,它还能有如此表现,真是难为它了。想当初我从一个戏剧学院女孩手里搭救这辆“迷你”的时候,满目疮痍的它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锤子一锤子的敲打、一砂纸一砂纸的抚摸才让它获得了新生。那时候,我正和上一个女友如胶似漆,它没少偷窥我们的罗曼史,还装得如同一个饱经风尘却依然羞涩的少女似的,时不时地因为醋意撒点脾气。后来女友离我而去,我就开始了这样的生活:我总是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穿梭,寻找和搬运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然后蛰居数日,如此反复;“迷你”总是先被当作苦力,然后又被冷落得如怨妇一般。这么长时间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我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知道这种事情急不得,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只是时机还不成熟。
女友离开那一年的河流,水漫过堤坝,我注视着整个城市的倒影,之后,我就迷上了现在的事情。
雨小了些,像是雾升起来,从挡风玻璃看出去,雾中的风景若隐若现。我猜想北三环现在一定是水泄不通了,我可以摇开车窗,用手轻轻一挥,就让眼前的雨雾散去,但那些满脸横肉的铁家伙“迷你”怎么能够赶得开呢?那是一条循规蹈矩的路,如果前方就是车祸现场甚至还有血迹呢?在无休止的等待中筋疲力尽的滋味可不好受。我还是应该早点换一部带GPS功能的手机,以免出门的时候永远记不住装导航仪,我约略地记得应该有另一条可以直达目的地的路,但是这样的天气,那里可能隐藏着我并不能预料的风险。
其实,一开出辅路我就在犹豫走哪条路好,幸亏我把那个小木箱随身带着了;我想,少一点后顾之忧,我也许更愿意冒险一试。
水中驱车,如同陆上行舟,不能停怠,也不能冒进,这需要适度的忍耐和巨大的耐心。有那么一小段,一位套着雨靴撑着伞的大姐和我等速并行,她敲我的车窗,问我要不要来份地图,我没要也没开窗,她竟然不依不饶地问我要不要把雨伞―即便这样我都没有发火,我需要保持适度的忍耐和巨大的耐心。
从前面的立交桥下穿过,就离开大路,我凭着记忆这样决定。我还记得,桥洞下时常有些流浪艺人出没,五毛钱一段的吉他弹唱,给不给钱都行的洞箫横吹,还有撂地撒把式画圈逗闷子的,不一而足。我注意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是瞎子,实际上不仅看得见还能凝视;他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是侏儒,实际上侏儒也能干大事,他们个个都是大力士;他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是男人,实际上那话儿可能只有一英寸,只是我不知道那是由易装癖还是同性恋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是人,实际上不是人……哈哈,有一次深夜路过那里,远远听见桥下有人在唱歌,我才忍不住这么想。
看见“不准掉头”的路标,觉得那像是一个讽刺―我即便想掉头已经来不及了,积水进了排气管,“迷你”在桥下换上了比基尼。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过来,路边高地上赤着脚、肩扛铁管手提绳索的那帮人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他们高挽裤腿一拥而上,乐呵呵地把水搅浑。我认得出,他们就是那帮艺人装扮的,看天吃饭的道理,叫我永远不要低估水面以下的事物,而孤立无援的境地让我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我坐在车里,开始犹如待在水底一般压抑,我挂着空挡,心里空荡荡的。“迷你”被扎得像个“死夜恶”女郎,四角套在铁管上,随着那帮人口中有节奏的“哼哧哼哧”劳动号子,艰难地向前蠕动。随着车外水位的下降,我的内心感到了一丝愉悦,后来竟然还被一会浮在水上一会又接触到地面的机械运动弄得荡漾了起来,在快要到达高潮的时候,我猛踩了一脚油门,“迷你”呻吟着吐了两大口水,然后嘶鸣着尖叫了起来,真像个娘儿们。
他们大汗淋漓地从我手中接过钞票,恨不能把钱挤出水来,因为一时间分配不均,领头的行吟歌手竟然还想向我多要一点。原本我不是不可以满足他们,只是想到这样的天气,一路上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得留点以备不时之需,我才像一个审慎的资产阶级那般言词委婉地拒绝了他们。
卸下绳索和铁管的当口,他们中的一个西洋景艺人发现了副驾驶座上的那个小木箱,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就伸手去拿,我一把推开了他,把车门关紧。那群人围上来,我们差一点扭打在一起。可能是注意到了我态度的突然变化,行吟歌手猜出了小木箱对我的重要性,趁着我和别人争执,他让侏儒兄弟爬进了“迷你”。当我转过身来,它已经在他的手中了。
在要么给他们展示一下小木箱是干什么用的,要么拿一笔钱赎回它的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他们有些诧异,可是他们哪里会知道,小木箱在关键时刻能够使用且仅能使用一次,为了那一次也许一分钟也许只有几十秒、不知是否能有收获的使用,我就要付出几个月的辛苦,我怎么可能为了钱而放弃它呢?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在你们面前使用它的,到时候,我要让你们为了它而放弃钱,即便那些钱并不源于敲诈,即便那些钱是你们沿街卖艺而来。
…………6从大海里游过来,我从来没有奢望能在下水道里碰上美人鱼,即便是鱼头人身的那一种。
我知道,每年的这个时节,只有那些丑陋的大嘴鲑鱼成群结队地从大海中逆水而来,它们交配产卵,然后在它们父母第一次做爱的水域腐烂死去,同时让孩子们接过他们手中的枪,开始新一轮生命的轮回。我想,这是一个人世的象征,千百个寂寞的集体。
我从水面以下三米的地方找到了下水道的出口,而这应该就是来前我被告知通往公共游泳池的入口。我随着鲑鱼群一起躲闪着迎面而来的湍急水流,游出不长的一段,我就可以起身行走了,而那些鲑鱼在我身旁跃起,时而溅起明亮的水花。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城市中和大海相连的河流已经干涸,只有污水在下水道里流淌,人们再也看不见它们的身影,只能按照自己的欲望幻想着它们的味道和样子―食色,性也;德州,巴黎;鱼子酱和美人鱼。
我仿佛看见她在前面透进更多光线的转角处扭动了一下尾巴,然后把飘散的长发和我的凝视抛在了脑后我背离了预定的路线,想证明幻想的事物是否就真的不存在。
下水道的拓扑结构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它们四通八达,如同一个巨大的章鱼在地下伸展着触手,只一会儿工夫,我就迷路了。四周浓黑,我想我的手机准是没电了,屏幕不亮,我没法像一个迟到的观众那样用它照亮脚下的路,甚至我想通过它知道现在的时间,也是不可能的。
黑暗中的跋涉艰苦而又劳累,有一瞬间,我几乎都要崩溃了,我甚至忍不住想,只要现在能让我见光,死又何妨。我靠在弧形的下水道壁上几乎睡去,身体弯成一把弓。然而我不敢睡去,我想如果睡梦中我终于找到了出口,爬到大雪覆盖的山巅呼喊,如石头一般尖叫,而醒过来的时候,我却依然还在这里,那样的绝望真的会让我但求速死的。我的小木箱还在,我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想象死亡。
前面有光斑在墙壁上跳动,我走上前一些,它就朝着更远一些的地方移动,我跟着它左拐过不知道多少个弯,推开了面前的一扇木门。一个灯火通明的世界,瞬间让我雪盲,眼前的景物一下子淡成白,然后才在我眼中渐渐恢复它本来的面目:我看见一大群人在一个巨大的有如地下城市的空间里各行其是,并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闯入者,而在中央的一块空地上矗立一个巨大的盛满了水的玻璃盒子,那里面游动的正是她。她尾巴上的鳞片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再经过水和玻璃的折射,更让人心醉。玻璃外面,有几个男人正注视着她的表演,就像海洋世界里的参观者。
我决定不论她是否愿意,我都要让她回到大海里去。我做到了,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正是她想要的。
我手握那把刀大叫着突然冲了过去,使劲地扎向玻璃,玻璃碎了,水从里面瀑布一般倾泻下来,在那些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卷着她和我奔腾而去。她把我托离水面,告诉我爬上面前的这段梯子,然后打开头上的窨井盖,我就可以离开下水道了。告别的时候,她拿我的那把刀,在水中刮下了一些她下半身上的鳞片,交到我的面前,她说,她也没有什么作为答谢,就把它们送给我吧。
需要的时候,对着它们说,要有光,她摆动尾巴离去前回过身对我点点头说,于是便会有光。
7在下水道和地面之间,隔着一层地铁。
我探出头来,正好是地铁狂欢节的落幕表演在我头顶上演,我穿着潜水服,斜挎背包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所以围观的人群一定把我当作了彩排中就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小丑了。我爬起来,跟在队伍最后,为了不让人们失望,我还做了几个夸张的动作和人们打招呼。
我看见行吟歌手和他的那帮兄弟也在队伍中,只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们竟然出落得如明星一般。我担心现在脱下衣服,他们一定会认出我,但我又热又渴,所以我溜进一段没有人的人行隧道中,躲在拐角处。
我该如何表述接下去的事情呢?
从表面上看,事情是这样的:我看见一个穿黑色风衣的中年男子,尾随她来到了隧道中,突然间,他掏出刀子的同时也掏出阳具,他的威胁让她呼救,很快又开始哭泣。他用力把她推倒,用手捂住她的嘴,趴在她的身上开始有所动作,还不断地说着脏话,低沉得如同腹语。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冲了过去,在与那个家伙的搏斗中,他用刀挑破了我一侧的鼻翼,而我用刀扎进了他的下体。
不过,事实的真相是:她说她在这里等了我好长时间,要把她手中那一卷东西交给我,我接过一个厚度大约是十六毫米的小铁盒子,发现上面写着我看不懂的文字。她还说,还有十五分钟,最后一班地铁就要进站,而我要在站台时钟的正下方把铁盒子里的东西装进我的小木箱,她特别强调这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使用这个小木箱最好的机会。她说,告诉我这些是她应该干的,而作为对我搭救行为的报答,她还可以额外多告诉我一点。她说,随车而来的,可能有我最想见到的人。如果她来了,那我一定可以见到她;而如果她并没有来,那么我的小木箱即便是用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地铁呼啸而来,然后呼啸而去,那短暂的一分钟,并不为我停留。我尽力去注意任何一个从小木箱前闪过的女人,但我又似乎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她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铁车站一下子从地面上消失,然后又在任何一个出其不意的时刻瞬间从地下冒出来:她来了,她看见了,她走了,一切似乎都在偶然中发生,一切又在每天按部就班地精确上演。她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柳媚花娇,实际上可能并非荡女;她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在夜归时手持蔷薇,实际上可能内心空如白昼,更适于蔷薇的葬礼;她们中的一些人表面上离我那么近,实际上却跨越真实和想象,直奔象征的世界远去。
她们要我等的那个人是谁?而谁又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等着我?……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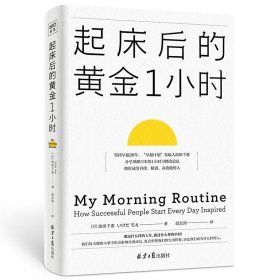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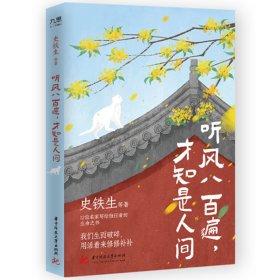

![【全新正版,假一罚四】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加] 马修·派瑞9787544798501译林](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19363336/ec517fa93239f8f3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