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一罚四】弄堂里的西西弗斯路明
集团直发,全新正版书籍,假一罚四,放心选购。可开发票
¥ 39.7 6.8折 ¥ 58 全新
库存5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路明
出版社中信
ISBN9787521760859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31922946
上书时间2024-06-30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路明,物理学博士,大学教师,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非虚构写作者。已出版《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出小镇记》。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分
赵乐盐失明的第三百九十五天
病床上的赵乐盐
平行宇宙的另一个我
一次疫情期间的电信诈骗
给孩子的礼物
少年下落不明
第二部分
沈厂长的最后一战
爷叔传奇
一个萨克斯手的流金岁月
多情应笑我
少年游
第三部分
弄堂的瓦解
武林往事
上海足球往事
撕裂一九九九
后记
内容摘要
这是一个关于上海百姓的真实故事。长久以来,关于这座城市的特质,一直众说纷纭。上海不只是咖啡馆、梧桐树、小马路,或者大家熟悉的工人新村、老公房之类,路明发现在自己的视野之外,在主流媒体的叙述之外,还有另一个上海,这个上海从来都是存在的,那是工厂文化,是早期的商业文明与契约意识,是上海阳刚、粗犷的一面。
作者路明深入采访上海的十位普通人,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他们是私营企业厂长、下岗工人、乐器修理师、萨克斯乐手、患癌女孩……个人背后是一个群像的变化,群像背后则是社会场景的变化。本书记录了“魔都”阳光之下的烟火气息、随意杂乱的生活状态,从微观的具象的个体、家族命运,透过普通人的故事,展现背后的宏大历史变迁图景。而快速变迁的时代面前,普通人的选择与坚持也是最动人珍贵的。
主编推荐
1.一部平凡人的史诗,记录普通人在命运跌宕中感人至深的坚守与抗争
“一般对上海人的误解,一是小气,二是优雅”。
路明眼见了蝴蝶牌缝纫机、较为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等优质时尚的“上海制造”,更目睹了从国营厂统销统购到工业衰落,工人瘫坐在地无声恸哭的悲凉。
本书展现了重大时代变迁下,普通人对抗命运跌宕的决心和颠沛流离下珍贵的坚守与骄傲。
2.作者路明以极大的真诚和坦率,深入田野、挖档案、做访谈、追踪家族史,换回一个个掏心窝子的生命故事
据说好的非虚构写作者,会与采访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冷静客观,也冷眼旁观。
路明知道这是对的,只是做不到。
他总会不自觉地靠近,倾听他们,理解他们,成为朋友。他愿意听那些絮叨和家长里短,渴望刨开事件的表面。他目睹过病痛与绝望,好几次,因为太难过引起胃痉挛。最重要的是,这些袒露心扉的时刻,相视而笑的时刻,默默流泪的时刻,都被一字一句深情记录下来。
3.严飞作序推荐,在细腻而厚重的生命体验中,找到广阔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记忆
为什么个体的情感和经验,从来都是宏大叙事的零部件,只能在边缘的位置不断盘桓?本书书写的不是恢弘的主题、正确的记忆,而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下的厚重生命记忆,让人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难以忘却,不忍告别。
精彩内容
少年下落不明阿福推开酒杯,问:“X怎么没来?”几个人面面相觑。是啊,怎么忘了还有这么个人。感觉上,他已经消失很久了。
尤面筋小声说:“X好像是生病了。”尤面筋在小镇医院当护士,她说曾见过X来检查,不知道是什么病,好像有点麻烦。后来X没再来小镇医院,尤面筋也就没见过他。
我想起一些往事。X是我们年级的风云人物,当然,属于那种反面的典型。X旷课、抽烟、打架,门门功课不及格。老师也不管他,让他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男生风传,X是混江湖的,X对此不置可否。那时候,“江湖”不是贬义词,江湖意味着义气、热血、轰轰烈烈的生活,也意味着台球厅、摩托车、后座上露大腿的女人。有一阵,每天放学后都有几个社会青年在校门口等X,男的女的都有,他们歪在摩托车上,见面嬉笑一番,骂几句脏话。X书包一甩,坐上摩托,绝尘而去。
初三没毕业,X就从校园消失了,听说他去了县城的“青龙帮”。起初几年,还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如何一战打出名声;如何出面摆平一场械斗;如何跻身“青龙帮”四大金刚;如何搞了老大的女人,结果被打得死去活来;如何拖着一条伤腿,远走他乡。再后来,“青龙帮”被一网打尽,几个头目都被判了刑。往后的日子里,渐渐没了X的音讯。
阿福说:“王芋艿,你不是前两年跟X混过吗,你怎么会不知道?”王芋艿说:“瞎讲八讲,我哪跟他混了,我也是碰巧在老街遇到X,他说自己刚从广东回来,他爹中风在床,没人照顾。”我想起那个中年人来,粮机厂的劳动模范,小镇工人阶级力量的代表,唯一滔滔不绝的时候是在酒后,优点是只砸东西,不打人。每个月总有那么几次,酒馆伙计找到家里,X再去把他爹架回来。X那时比他爹矮一个头,像纤夫一样斜着身子,他爹的两条腿拖在后面,像一头被打倒的熊。
那后来呢?我问王芋艿。
王芋艿挠头皮。“后来嘛,我只知道他有段时间在台资厂的电镀车间干活。后来,后来有一次,大概是两年前吧,”王芋艿说,“我约了张毛豆、阿福几个人一道吃老酒,我打电话给X,叫他一起来,你知道他说啥?”“说啥?”“他说,他现在工资也不高,花个三百五百见同学,不划算,不来了。你讲讲看,阿有这样说话的,”王芋艿气鼓鼓地说,“要么你就找个借口,出差啊,家里来亲戚啊,身体不舒服啊,怎么都行,要不要这样说的。”大实话嘛,我忍不住笑出来。
“我对他讲,你不要在意那三五百了,我帮你出,你来就是。他说‘操你妈’,他在电话里要操我妈,然后就挂掉了。你说这个人,阿是(是不是),啊?”王芋艿气不打一处来。
我拍拍王芋艿。
“后来嘛,我们就不带他混了,都这么讲了,还混什么混,”王芋艿说,“不过,我老婆认识他老婆,她们或许还有联系,你要是想见X,我现在帮你问。”有件事王芋艿不知道。那是初二的一个下午,我踢完一场球,看见X一个人坐在看台上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的头深深埋了下去,肩膀剧烈地抽搐。我犹豫了一下,走到X身边。他抬起头,满脸的泪水。
他说:“我娘不要我了。”我看见他用夹着烟的手捂着嘴,无声地颤抖。我伸出手,放在他的肩头。
小镇没多少秘密,我听我爹讲过,X的父母在闹离婚。我当时不知道的是,X想跟着他娘过,他娘拒绝了。
X抹了抹眼睛,对我笑笑说:“你走吧,别让班主任看见你跟我在一起。”聚会的第二天,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女人说:“喂,阿是路老师?”我说:“是,你哪位?”女人用普通话说:“我是X的老婆。”声音有点沙。我说:“你好。”女人说:“我知道你,X跟我说起过。”我说:“我们好多年没见了,X在吗?”女人犹豫了一下,说:“他现在不方便跟你说话。”我说:“哦。”女人沉默了一会儿,说:“要不我们出来讲吧,我不想在电话里说这件事。”我们约在小镇一家名叫托斯卡纳的咖啡馆。大门口的招牌显示,除了咖啡,这里还供应意大利面、三明治和牛蛙饭,以及各类商务套餐。店里没几个人,大概是刚装修不久,一股甲醛的味道。她已经坐在那里了。我走过去,说:“你好。”她欠了欠身。我坐下。她是个消瘦的女人,皮肤偏黑,扎一个马尾巴,坐着看不出身高,但显然不太高。她看着我说:“知道我为啥愿意出来见你吗?”我说不知道。她说,“昨天王芋艿老婆打电话来,说你在找X”,她顿了顿,“刚好,昨天是他的断七。”我说:“我猜到了,这是最坏的可能,你节哀。”她说:“你抽烟吗?”我说不抽,她从包里掏出烟盒,点上一支,自顾自抽起来。抽了几口,女人摁掉烟头,说:“你有空听吗?”我说:“我不赶时间,慢慢讲。”女人说:“我和他是在厂里认识的,我在喷漆车间,他在电镀车间,都是操作工。”我说:“台资厂,听说了。”她说:“厂里的工人,除了几个老头子,没什么本地人。本地人不愿干这个活。有一次,经理欺负我们几个外地小姑娘,他去找人家理论,三句两句把人家吓住了,乖乖给我们赔了礼道了歉。我这才知道,他是本地的,听说以前混过黑道,有点名气。”我点点头。她接着说:“你知道,来这里打工的小姑娘,有的很单纯,有的很实际,就想找个本地男人嫁。本地人嘛,多少有点积蓄,运气好点,碰上拆迁,四五套房子拿在手里,住一套,租出去几套,也不用上班了,日子不要太好过,阿是?”我说是的。她说,“我就找机会跟他说话,时间一长么好上了,谁知道他家里那么穷,”女人苦笑,“钱都给他爸看病了,看么看不好。我第一次去他家里吃饭,吓了一跳,那个楼快倒了,走道里堆满垃圾,廊灯是坏的。他家里倒蛮干净,就是没一件新东西。我数了数,家用电器有一只电饭煲,一台收音机,和他爸床前的一个老式电视机。”我说:“那你还嫁给他?”“啊呀,后悔来不及了呀,”女人的脸生动了一些,“我想嘛,两个人都赚钱,熬一熬,日子总会好过起来。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总共两桌人,都是亲戚,他的朋友、同学一个都没叫。来的人说,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寒酸的婚礼了。”“结婚第二年,我们有了宝宝,那天他喝了点酒,跟我说,不能让我和宝宝住在这种地方。我说那你搬呀,你有本事搬不?我没想到他是认真的。第二天,他去找他娘舅借钱,自己添一点,凑了个两室一厅的首付。接下来的一年多,他基本上天天加班,一边还债、还按揭,一边还得把新房子装修的钱赚出来。他说上个月加班加出个彩电,这个月再使把劲,能加出个空调来。我跟他讲,钱是赚不完的,我们现在简单装修下,能住就行,以后有钱了再弄。他说不行,不能留到以后。你大概也知道他的脾气的,就是倔,十头牛拉不回来。
“住进新房子不到半年,他开始掉头发,睡觉的时候,肺像个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后来开始咳血。拉到医院一查,肿瘤,已经转移了。
“我瞒住他,带他去上海的大医院治,医生很坦白地对我讲,治不好了,回去吧。我跪在医生面前,说,我只要我男人的命,你让他多活一天,我倾家荡产也愿意。后来他察觉到了,到那个地步,再迟钝的人也察觉到了,就坚决要求回家。我叫了个车,把他从长征医院直接拉回镇上,抬到家里。一路上他都昏睡着,后来他睁开眼睛,看了看,说不是这里,要回去。他娘舅说,囡啊,就是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啊。他摇摇头,不说话,眼睛朝我看。我说知道了,我们走,就让人把他搬到那个破得不像样的老屋。他在那里咽了气。别人不知道他的心思,我知道,他怕死在新家里,我和宝宝以后没办法过日子。他就是这么个人。
“今天出门前,我给他上了一炷香,我说,你看,还是有老同学记着你的。他就朝我笑。他以前不太笑的,现在天天朝我笑了。好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有什么要问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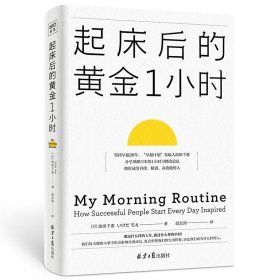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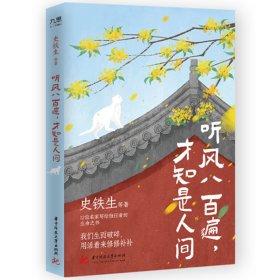


![【全新正版,假一罚四】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加] 马修·派瑞9787544798501译林](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19363336/ec517fa93239f8f3_s.jpg)






![【假一罚四】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汀](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cecdbdbf/ba05d4280a9bd438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