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一罚四】刘晓东系列:而黑夜已至弋舟
全新正版书籍,假一罚四,可开发票。24小时内发货。
¥ 23.5 5.2折 ¥ 45 全新
库存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弋舟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08474
出版时间2021-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5元
货号31124466
上书时间2024-06-07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弋舟,当代小说家,历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刘晓东》等多部,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我们的踟蹰》等多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无论那是盛宴还是残局》等。
目录
《而黑夜已至/刘晓东系列》无目录
内容摘要
“刘晓东系列”是著名作家弋舟的中篇代表作品,也是当代文学的名篇,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自我意识有着深入探索,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质、人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塑造,有着精湛的表现。其中的刘晓东,可以看作有着共同精神困惑(疾患)的同名者,也可以看着同一个人因应叙述环境需要的不同分身,他是教中文或者艺术史的教授,是画家,是游走者,是见证人,更是探索者、忏悔者,他以一己之身负载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景。《而黑夜已至》讲述朋友的学生,幼年父母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多年后,她发现真相,委托刘晓东帮她讨回公道。诸般巧合下,刘晓东轻易要来一百万,却发现这件只能依赖良心的事,一开始就被人拿良心做了局。
主编推荐
是游走者,是见证人,是忏悔者,是负罪人一个人的受难记,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鲁迅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当代文学名篇
精彩内容
壹她没进咖啡馆前我已经隔窗看到了她。
窗外的马路被隔离墩分割成两半。我总觉得这样的马路像是一根超长的、闭合了的拉链。咖啡馆左侧不到50米就是学校的大门,但要从路对面过来,你得往前、或者退后200米左右,才有敞开的人行道和天桥。这显然不太合理。我隔窗观望,时刻能看到两侧的行人躲避着车流,在一个看起来分寸拿捏得不错的时刻,跨栏而过。这就像是漫漫人生路中一个个光彩熠熠的小机遇。他们抓到了,没有被车流剐擦或者撞飞,走了个捷径。他们捞着了便宜,却也没有显得格外振奋。天知道什么样的“捷径”才能令这些见多识广的家伙们感到满意。——我这么想,有些夸大其实。是的。半年前我被自己诊断出了抑郁症。而与现实环境不相称的悲观,就是抑郁症的症候之一。
正对着校门,马路两边择机穿梭的大多是些学生。看起来她和他们并无两样,披肩发,戴一顶蓝色的棒球帽,白色的、长度过膝、紧紧包住下身曲线的裙子,灰色帆布鞋。只是她比他们显得更加十拿九稳。她根本无视路况,仿佛一切都将为她让道。她径直在两辆车驶过的空隙穿插而过,步伐恰到好处,几乎不需要调整,便抬腿跨过了隔离墩,然后用同样均匀的步态,流畅地再次从逆向而来的车子之间穿过。她的腿很长,只是紧身的裙子稍微有些碍事。她就像一个跨栏运动员。她训练有素,预设了步幅,把握了频率,计划了路线,跑了一个好成绩。
我用手机拍下了她举步跨栏的那一瞬。裙子弹性不错,即使紧到贴身的程度,她跨越之后也并不需要重新整理一番。这个时候我还并不确定是她。我用手机拍照并没有针对性。我已经拍了十几张横穿马路者,有男有女。
此刻是四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我们约在下午三点见面。我中午就到了,午餐就是在这里吃的,一份咖喱鸡饭。点餐时我有些犹豫,正在闹禽流感,有个新词,叫H7N9。据说鸡肉已经没人吃了。我对咖喱鸡饭的犹豫,并不是来自那种杯弓蛇影的恐慌,相反,我几乎是在犹豫着故意找事。我偏要吃。这会让我对午餐的选择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气概吗?我在找事儿,或者干脆是找死。又夸大其实了。这儿是学院周边我定点用餐的地方,老板就是学院的同事。半年来,大致上我所有的午餐都是在这里吃的。过了午餐时间,这里往往就是我一个人的地盘。我的桌子被固定下来,最后面,靠窗。服务生会为我留座。当然,大部分时间他们不需要这么劳神,这家咖啡馆的生意没有好到总是会有人来抢那个最后面靠窗的位子。我常常在午后坐在自己的专座里,隔窗看马路上的过客,并且用手机毫无目的地拍照。
进来后她马上认出了我。这里只有我一个客人。当然,我也因此确定了她就是我的访客。她没有停顿,绕过吧台走向我。我将她从马路对面行至眼前看成了一个连贯动作。她就这样像是被人瞄准好了、准头不错地一股脑儿投掷在了我的面前。
她说:“刘老师吗,我是杨老师的学生徐果。”我点头,请她坐下,告诉她杨帆给我打电话交代过。
她伸手给我,是要握手的架势。这不是个年轻女孩常有的动作。我该将之视为落落大方还是老练世故?她做得倒是很自然,没有其他意味,只是一个动作而已。我们的手轻微地互握了一下。她的手冰凉,够得上柔若无骨。坐下后她从包里摸出手机摆弄了一番,似乎是在翻看各种进来的信息。这个动作同样没有其他意味,不表示没礼貌和旁若无人。如今每个人都天经地义地随时摆弄着手机,地铁里,餐桌上,会议中,乃至床头和枕边。这让我有机会观察了她几秒钟。她很漂亮,但也不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城市里这样的漂亮女孩比比皆是。她们像是在流水线上成批加工出来的。人和人的差别在日益磨平,世界像一台巨大的磨具。
我幻想在几秒钟时间里找出她的某些特质,将她从漂亮的众生中挑拣出来。这很难。但我觉得我找到了,那是什么,我却不好把握和形容。我觉得她的脸上潜藏着一丝笑意,不,那不是发自愉快或者出于礼貌,她是在对着自己会心地笑,像心怀秘密的人那般窃喜。我认为这是自己心理暗示的结果。毕竟现在这个女孩坐在我的对面,和我有着既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在马路上擦肩而过,她在我眼里,顶多只是个跟橱窗模特差不多的塑料人。我推算她的年龄,二十二岁,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她将手机放在了桌面上。让我稍感意外的是,紧接着她又从包里摸出了另一只手机。服务生过来问她喝什么。她看了一眼我面前的柠檬水,说她也要杯水好了。而这期间,我也停止了对她的打量,低头争分夺秒地刷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短短的时间,有十多条新微博。最新的是:江西省卫生厅今天通报,新增两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她的水端来后,我喊住了服务生,要求给我来杯特浓咖啡。我感到有些焦躁,情绪开始低落。
之前通过百度,在某个“寻医问药”的网站,我看到过这样的信息,有人提问说:他的表姐被男友甩了,于是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睡觉,抱着照片自言自语,并且迷上了喝咖啡,家人非常担心表姐的状况,问表姐可否继续这样将咖啡喝下去。这条信息描述的内容,当时给了我小小不言的、没什么道理可说的欣慰——另一个病人提振了我低落的情绪。
可是其后各路医者给出的指导意见却大相径庭:你好,抑郁症患者要尽量少喝咖啡。因为咖啡因摄取太多会加重抑郁症。茶、可乐和咖啡都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失眠症状,因此患者不宜饮用。
你好,可以,咖啡有保健医疗功能。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得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不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员在10年期间跟踪5万余名女性后发现,与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较,每天饮用至少4杯咖啡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减少了20%,每天喝两三杯的则少了15%,咖啡因能促进人体某些精神传导物质的释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够帮助调节情绪和降低抑郁。
诸如此类。
茶,可乐,咖啡,10年,5万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
诸如此类。这些就是城市的符号。毋宁说,不是人,是这些诸如此类的符号,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城市。据说从前人们只面对土地和植物,那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说成是另外的一套世界观也无妨。我不知道如今这座城市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接收着诸如此类的信息,有多少人通过网络自我诊断着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过网络在给自己开药方、找对策,同时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无主。我就是通过百度确诊了我的抑郁症。我就是通过百度加深了我的虚无。那么,我可以说成——我是通过百度患上了抑郁症吗?
我显然走神了。而注意力减退,正是抑郁症的症状之一。
她在对面叫我:“刘老师。”同时还用手机轻敲着桌面,意在唤回我的注意力。“你没听我讲话,”她并不客气,“你在想什么?”我回过神,看到自己眼前那杯漂浮着一层厚厚的、棕红色油亮泡沫的特浓咖啡。
“没想什么,我在听,你继续说。”我并无歉意,如今城市里人和人之间似乎已经没有“失礼”之说。无所谓,不过是没有彼此认真倾听而已。这并不妨碍我紧接着又自相矛盾地问她:“噢,你说了什么?”“你认识杨老师很久了吗?”她也不以为忤。
是的,我认识杨帆很久了。儿子四岁时被我送到杨帆那里学小提琴,如今儿子十岁了。半年前我母亲去世,当天夜里我在杨帆的床上。她说她认识杨帆更久,杨帆是她初中时的音乐老师。这一点杨帆告诉过我。她说杨帆对她好极了,“就像妈妈一样”。
“那时候我常在杨老师家住,对音乐的兴趣也是她培养出来的。杨老师告诉你了吗?我现在是一个歌手。”我点头表示这些我都知道。
“杨老师真漂亮。”她的语气不是在陈述,是在提问,里面有让我附和的意思。
“嗯,是挺漂亮。”“只是‘挺’吗?”她直言不讳,“你不觉得是‘很’漂亮吗?”她直视着我,毫不含糊。她的眼睛真大,这个应该是天生的,流水线制造不出这样的大眼睛。而且,她的眼珠有种奇异的色泽,绝对不是黑色的,黑褐中泛着蓝色的薄翳。
“好吧,是‘很’漂亮。”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在潜意识里给杨帆的漂亮打了折扣。我在想,她如此求证,会不会是因为她知道了我和杨帆之间隐秘的关系。
“而且杨老师还特别善良,善良的漂亮女人可不多,是不是?”我同意不多。“初中第一学期,我们班主任生孩子请了假,杨老师就代理了我们的班主任。”她奇特的眼睛焕发出神采,“我真该庆幸,我因此有了一个妈妈。”她的情况杨帆对我交代过:有这么一个学生,自幼父母双亡,身为班主任,杨帆和她之间发展出了不同于一般师生关系的情感。这个学生如今有事需要我的帮助。此刻,我在想,这个女孩更像是来替她“妈妈”追讨什么的——她的妈妈善良而又美丽,这种女人不多,对我似乎理应成为某种压力。可这很荒唐。真的荒唐吗?我又难以如此去界定。总之我有种荒唐的负疚感,觉得自己是在被谴责或者是勒令。我觉得自己有罪。而“自罪”,也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说说你的事吧,”我需要打断她,“杨帆说你有些法律上的问题。”“是的。”“你需要打官司?”“噢不,我不打官司。”“那你有什么事需要和法律扯上边儿?”“和法律扯上边儿不是我们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如今什么事不跟法律沾边儿?法治社会咯,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她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反驳我,“懂法的人都好强大,我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人来帮助我。”“我不怎么懂法。”说着我正了正身子,为的是让她看看我,看看眼前这个胡子拉碴、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的确不是一个强大的家伙。我是个病人。
“可你是政法大学的教授。”我得费一番口舌了,得让她明白,并不是政法大学的教授都懂得法律。大学扩张,院系林立,如今连政法大学都设立有艺术分院,而我,不过是个教艺术史的。这是很荒唐,世界的确变了,一切都有那么一个规矩,这个规矩,似乎并不是法律——而是没有规矩。否则你没法解释政法大学干吗要有个教艺术史的。明白了吗?“杨帆没有告诉你吗?”我对她说,“也许我的法律知识都不如你。”“没有,这个杨老师倒没说,”她并不吃惊,“我说想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帮我,杨老师就向我推荐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个跟法律沾边儿的人呢?在我理解,你一定是遇到了法律上的难题。”“不能说我遇到了法律难题——怎么说呢,当然,什么事儿又都是归法律管的。”她说得有些吃力,但不是因为表达的笨拙,“我说过了,我觉得跟法律沾边儿的人会显得很强大。好吧,我并不一定非要找个律师或者懂法律的教授,当然如果能找到最好。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强大的人。”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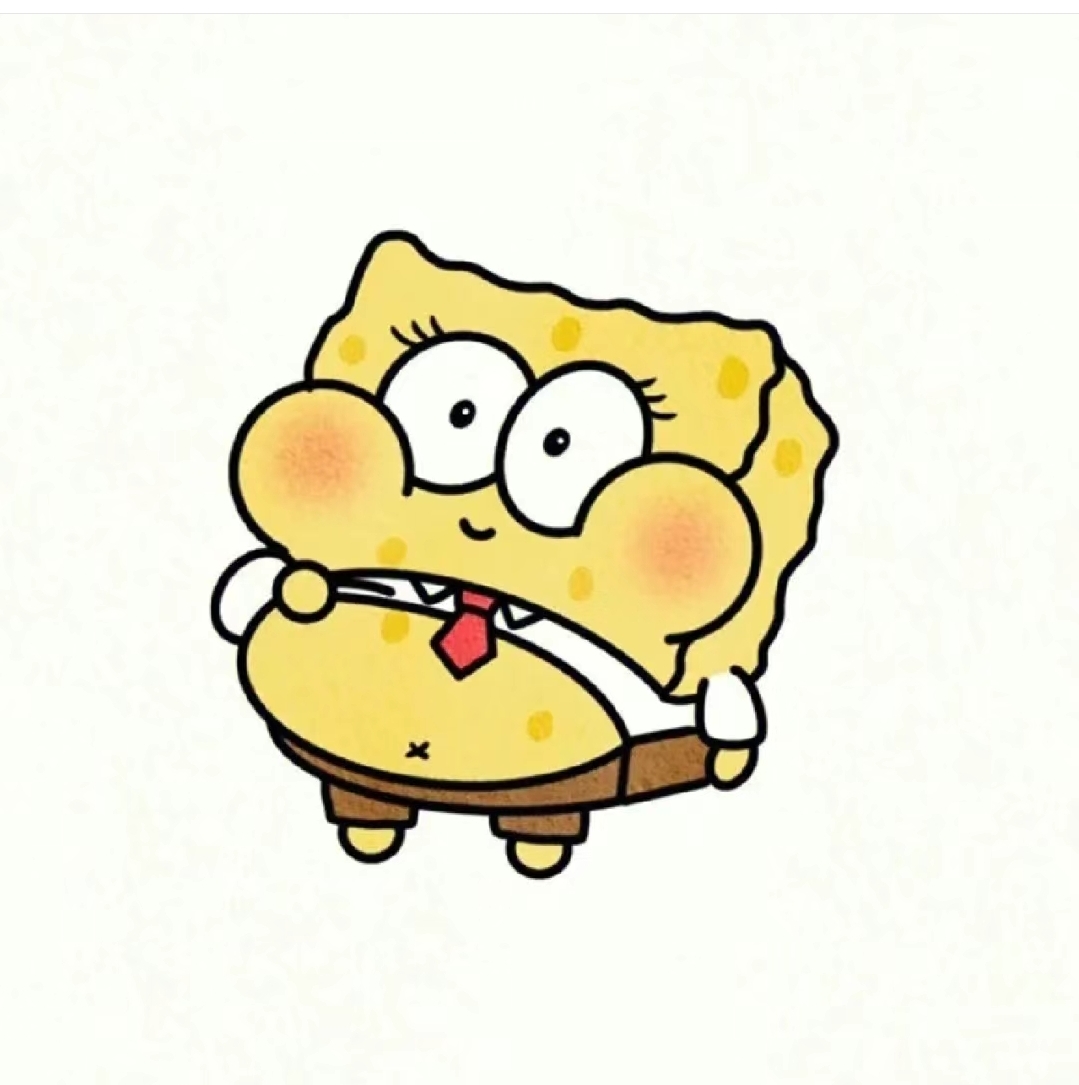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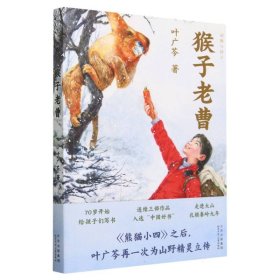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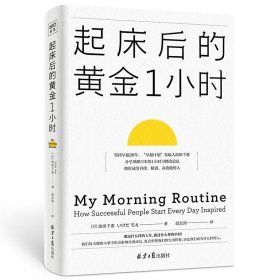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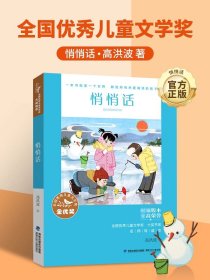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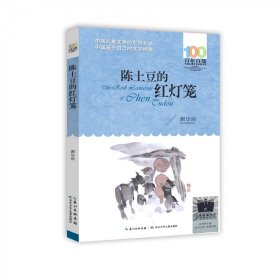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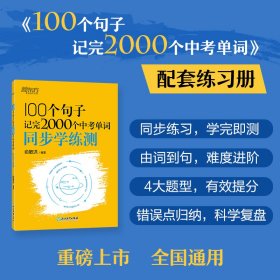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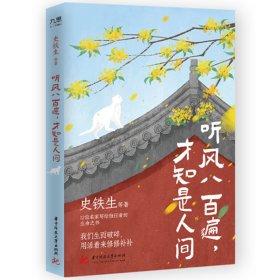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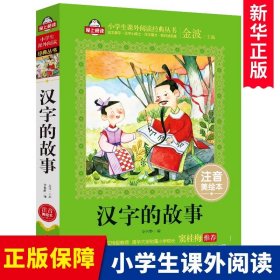
![【全新正版,假一罚四】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加] 马修·派瑞9787544798501译林](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19363336/ec517fa93239f8f3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