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三部曲
全新正版 极速发货
¥ 43.7 5.8折 ¥ 76 全新
库存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乔治·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52407
出版时间2000-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76元
货号31400657
上书时间2024-11-1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法国小说家,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一生写过百卷以上的文艺作品,以及大量书简和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代表作有《安吉堡的磨工》、《魔沼》等,《娜依》是她近七十岁高龄时的力作。
目录
目次
译本序 艾珉
魔沼 罗旭译
弃儿弗朗索瓦 徐和瑾译
小法岱特 陈丰译
内容摘要
《田园三部曲》集齐了乔治·桑的三部充满诗情画意的小说《魔沼》《弃儿弗朗索瓦》和《小法岱特》。这三部作品都歌颂劳动,歌颂自然,歌颂纯朴、善良、正直的品格,都体现了超越财富及社会地位的平等观念和一种以勤劳、智慧来衡量人的价值观。《魔沼》中的热尔曼舍弃富有的寡妇而选择一贫如洗的小玛丽,是因为他在小玛丽身上看到了聪明、勤劳、自尊自强且又善解人意等优秀品质;《弃儿弗朗索瓦》中的弗朗索瓦原是受世人鄙夷的弃儿,却凭自己劳动的双手和正直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与曾经关爱和抚养他的磨坊女主人结了婚;《小法岱特》中英俊、能干的朗德烈没有去追求村里的漂亮姑娘,却深深爱上了衣衫褴褛、貌不惊人的村姑小芳舒,因为他发现在这姑娘野性难驯的外表下,隐藏着超人的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组组牧歌式的爱情,完全摆脱了金钱、地位、年龄、容貌等世俗、物质的考虑,体现了一种高度净化的精神境界。
乔治·桑在我们时代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人是伟大的男性,她是伟大的女性。我们这个时代,大革命结束了,人道革命已经开始,两性平等是人道革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应证明既有男性的才干,又不失天使的禀赋;她是强有力的,又不失温柔。乔治·桑具有这些能力。她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雨果法国女作家描绘的田园牧歌,歌颂自然,歌颂纯朴、善良、正直的品格。
精彩内容
译本序若问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最著名的女性是谁?大约非乔治·桑莫属了。这位闻名全欧的女作家,非但以其多达一百一十卷的作品令人瞩目,还曾因其对传统婚姻和“夫权”的大胆挑战,以及接二连三的浪漫恋情而惊世骇俗。
乔治·桑(1804—1876)原名奥罗尔·迪潘,出身于一个颇有声望的贵族家庭,曾祖父是十八世纪著名的金融家,祖父是梅斯和阿尔萨斯地区的税务官,祖母是波兰王奥古斯特二世之子萨克森元帅的私生女,父亲是拿破仑帝国的那不勒斯王——著名的缪拉元帅的贴身副官。奥罗尔四岁那年,父亲不幸意外身亡,从此她常年住在诺昂乡间,由祖母教养成人。乡居生活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尊敬与同情,另一方面由于母亲出身微贱,备受祖母歧视,也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使她从小就体验到社会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因此,她一接触到卢梭的著作便深受吸引,卢梭对大自然的崇拜,对人类淳朴状态的赞赏,特别是他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都在她思想上引起强烈的共鸣,使之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卢梭的理想。正是缘于这一思想基础,乔治·桑无法忍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屈辱地位,并勇敢地挑战世俗偏见,起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为了早日摆脱祖母的束缚,奥罗尔十八岁就嫁给了一个名叫杜德望的乡绅,但三年后就不得不和丈夫分居。尽管她曾给丈夫带来五十万法郎的嫁妆,男性社会的法律却不允许她支配自己的财产,所以她要想挣脱不如意的婚姻,取得独立生活的地位并不那么容易。一八三○年,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移居巴黎,丈夫每月仅提供二百五十法郎作为她和孩子们的生活费。显然,靠这区区二百五十法郎,母子三人在巴黎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奥罗尔不得不用她的一支笔来养活孩子们和她自己。起初她和儒勒·桑多合作,化名儒勒·桑为报刊供稿。一八三二年,她以乔治·桑为笔名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印第安娜》和《瓦伦蒂娜》,从此作为职业作家登上法国文坛。
和同时代的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一样,乔治·桑也是一位多产作家,在她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共写作了上百篇小说,五十余部戏剧,还有大量的散文和书简。当然,使她闻名于世的,仍是小说。她的早期小说无一例外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爱情的失误和婚姻的不幸是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印第安娜》《瓦伦蒂娜》《莱丽亚》(1833)、《雅克》(1834)、《莫普拉》(1837)……所有这些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化身,表达着作者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现实爱情及婚姻的失望。乔治·桑通过她的作品倾诉自己的屈辱感和愤懑不平,她指摘那些合法却不道德的婚姻,赞美敢于追求爱情的自由而对抗社会习俗的女性。尽管乔治·桑常因爱情多变受到指摘,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倒都是对爱情极为认真、精神境界极为崇高的。事实上乔治·桑那些闹得沸沸扬扬的浪漫经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和作家缪塞及钢琴家肖邦的恋情),与其说是由于轻率,不如说是由于过分憧憬理想,以致她永远对现实的爱情感到不满足,对现实中的男性感到失望。
在三十年代,乔治·桑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突破个人在婚恋问题上的感受,题材范围比较狭窄,立足点也不很高。到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和拉梅内、布朗基、皮埃尔·勒鲁等人的交往,视野逐渐扩大,特别是勒鲁的思想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思想变化反映在她的中期创作上,便是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小说的产生。如《木工小史》(1841)、《康素爱萝》(1842—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接着她又着手写作一系列以普通农民为主人公的田园小说,总标题为《打麻人夜话》。第一部《魔沼》于一八四六年发表,被公认为乔治·桑最优秀的杰作,第二部《弃儿弗朗索瓦》于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间在《论坛报》上连载。第三部《小法岱特》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嗣后又发表了《敲钟师傅》(1853)等等。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曾激发起乔治·桑的政治热情,她积极参与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深信共和国的诞生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她怀着天真的信念撰写了多篇热情洋溢的政论,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民民主的思想,呼吁以“兄弟般的联合”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区分。然而共和国并没有进行她所期待的社会改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很快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被镇压以后,乔治·桑的幻想破灭,从此远离政治,隐居乡间,从田园生活中寻求精神寄托。尽管政治理想受挫,乔治·桑并未陷于悲观,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并坚持不懈地在作品中宣扬她的社会理想。
乔治·桑到晚年仍然笔耕不辍,但成就未能超过她的田园小说。田园小说是乔治·桑最富个人特色的作品,在她同时代的作家中,还没有第二个人像她这样,以农民为作品的主人公,从普通劳动者平凡的生活中发掘诗意。在这些作品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卢梭的精神达到了奇妙的融合。作者歌颂劳动,歌颂自然,歌颂劳动者纯朴、善良、正直的品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超越财富及社会地位的平等观念和一种以勤劳、智慧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新价值观。《魔沼》中的热尔曼舍弃富有的寡妇而选择一贫如洗的小玛丽,是因为他在小玛丽身上看到了聪明、勤劳、自尊自强且又善解人意等优秀品质;《弃儿弗朗索瓦》中的弗朗索瓦原是受世人鄙夷的弃儿,却凭自己劳动的双手和正直的品格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与曾经关爱和抚养他的磨坊女主人结了婚;《小法岱特》中英俊、能干的朗德烈没有去追求村里的漂亮姑娘,却深深爱上了衣衫褴褛、貌不惊人的村姑小芳舒,因为他发现在这姑娘野性难驯的外表下,隐藏着超人的智慧和一颗善良的心。这一组组牧歌式的爱情,完全摆脱了金钱、地位、年龄、容貌等世俗、物质的考虑,体现了一种高度净化的精神境界。不能否认乔治·桑描绘这一切的时候,理想化的成分多了一些,真实的农民未见得像她描写的这般儒雅且充满诗意,真实的乡野生活也不是她所说的“充满香味的伊甸园”。和巴尔扎克笔下的农民相比,显然还是巴尔扎克的农民更贴近生活。但乔治·桑的理想化方式,恰恰是其创作方法的基本特色。舍去这一点,乔治·桑就不成其为乔治·桑了。
乔治·桑是位理想主义者,她的创作观充分体现了她的理想主义原则。在《魔沼》的《致读者》中,她明确提出:“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乔治·桑和巴尔扎克是关系非常友好的两位作家,但他们对创作的看法完全不同。巴尔扎克从一开始就将社会研究作为创作的出发点,他的雄心是充当法国社会的秘书,使整个法国当代历史在他的作品中再现。乔治·桑却说:“从什么时候起,小说就不得不把存在着的一切,把当代芸芸众生和万事万物的冷酷现实记录下来呢?我知道,或许应该是这样;于是巴尔扎克(我对这位大师的才华一向是景仰的)就写了他的《人间喜剧》。不过,虽然友谊的纽带把我和这位卓越的人物连在一起,我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现象。我记得曾对他说过:‘你在写《人间喜剧》,这个题目不过分,你完全可以把它称作人间戏剧,人间悲剧。……而我想写的是人间牧歌,人间歌谣,人间传奇。你有愿望,也有能力把你亲眼看到的人物描绘出来,这是好的;而我呢,却感到不得不把人物描绘成我希望于他的那样,描绘成我相信他应该如何的那样。既然我们不是相互竞赛,就让我们相互承认对方吧!’”所以,读者很难指望在乔治·桑的作品中看到巴尔扎克式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层次揭露或分析,而只能感受到一颗善良灵魂的理想憧憬。
作为卢梭的信徒,在乔治·桑心目中,原始生活始终是最令人憧憬的理想境界。她认为都市的文明已经毒化了人们的心灵,当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提倡返璞归真,去追求原始生活的魅力。她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1842)之类作品不以为然,觉得这类作品过多地宣扬了暴力和伤风败俗的行为,迎合了社会上某些低级趣味。她创作这一系列以陶冶情操为目标的田园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这种文学倾向。乔治·桑反对文学作品一味地描绘和刻画歹徒、刺客,而主张着重塑造善良、高尚的形象。因为“只有善良的人们才有能力感化他人,歹徒只会令人生畏,而心生畏惧不仅不能克服自私心理,反会令其变本加厉”。她以为艺术的使命就是“感情和爱的使命”,“创作的目的应当在于令读者喜爱作者关怀的事物,必要时,作者还可以对这些事物略加美化”。基于这一思想,她为读者描绘金色的田野、葱茏的林木、美丽的牧场、健壮的牲畜,引导读者去审视和发现农夫身上真挚纯朴的美……这一切仿佛一股清新的凉风,拂过充斥着凶杀、诈骗的文学书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和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作家相比,乔治·桑的作品在观察的深度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她的作品内涵比较单薄,人物往往不够有血有肉,甚至流于概念化。但是,乔治·桑是一位说故事的能手,女作家丰富细腻的感情,通过诚恳质朴的叙述自然流露出来,自有其天真单纯的特殊魅力。而且乔治·桑写作田园小说的时候,艺术技巧已臻于成熟,文笔比较精练,不再有早期作品中那些拖沓累赘的议论或说教,因而这组田园小说被公认代表了她的最高艺术成就,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列为世界文学的精品。
艾珉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刚看到一幅霍尔拜因的版画。他笔下的农夫令我久久凝视,深感忧伤。于是我来到田间漫步,苦苦思索乡间生活和农夫的命运。农夫要消耗体力,折损元气和寿命,才能掘开悭吝无情的地面,从肥沃的地下发掘种种宝藏。而如此辛苦耕作一天以后,换来的却只是一块最粗最黑的面包,农夫的心情当然是阴郁沮丧的。地上的财富:收获的庄稼果实也好,靠丰足的饲草喂肥的牲畜也好,一概都属少数人所有。对于大多数农夫来说,这些不过是压榨和奴役他们的工具。而一般有闲人也并不喜爱田野、草场、健壮的牲口和大自然的景色本身,他们需要的只是能供花销的金币,是用这一切换来的钱财。他们来到乡间小憩,不过是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将息身体,然后回到大城市中去尽情挥霍农夫辛勤劳作所赢得的果实。
另一方面,庄稼人过于劳累,心情阴郁,他们为将来担惊受怕,当然也不会有兴致去欣赏野外的景物和乡间的美好生活。在他们眼里,金色的田野,美丽的牧场,健壮的牲畜,也都意味着装满金币的钱袋。他们只能分得极为菲薄的份额,远不足以维持温饱。但是为了满足主人,换取在其领地上省吃俭用地苟活的权利,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辛苦操劳,不断地把金币填进那该诅咒的钱袋。
可是,大自然却永远是生机勃勃、美丽富饶的。对凡能在自己怀抱中自由生长的生灵和植被,她都赋予诗情画意。她拥有幸福的奥秘,任何人无从剥夺。那些掌握了耕田的技艺,能用双手操劳,并能凭借智慧的力量赢得安逸和自由的人们,定会成为天下最为幸福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会有闲暇,能够同时用心灵和头脑去享受生活。他们会理解自己的劳动,也会热爱造物主的创造。艺术家通过观赏和再现美好的大自然是能够达到这种心旷神怡的境界的。但是只要看到大自然这个人间天堂中尚有无数生灵涂炭,仁慈正直的艺术家就会感到内疚,愧悔不该有此雅兴。上苍赐人以赏心悦目的景色,当人们能够在这种环境中手脑并用,让意志、心灵和双手协调配合时,上帝的慷慨赐予和凡人的欢乐就会和谐协调,达到神圣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也许就是幸福!到那个时候,寓意画家们就会舍弃可怜而又可怕的死神,那个手执马鞭在犁沟中奔跑的幽灵,改为刻画神采飞扬的天使降福人间,将成把的麦种撒向蒸腾着雾气的犁沟。
农夫应当享有甜蜜、自由、富有诗意、勤劳简朴的生活,这种憧憬应当不难实现,而不应被斥为幻想。维吉尔曾悄声悲叹:啊,农夫,若是你能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你该会多么幸福!维吉尔表达的是惋惜之情。而通常表示惋惜就意味着预作论断。总有一天农夫和艺术家将会一身而兼二任,如果不是为了描绘美(届时这将无足轻重),至少也能感知美。难道人们还不相信,农夫身上已具有对诗意的神秘直感,只是还处于本能反应和朦胧向往的状态而已。就是在极度劳累、生活艰难的农夫身上,心灵也并没有被扼杀。至于那些日子稍稍好过些的农夫,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已得到发展,眼下这些人对于完美的幸福都已有了初步的感受并能略加欣赏了。况且,诗人既已从痛苦和劳累的深渊中发出呐喊,何以还会有人断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互不相容的呢?这种互不相容的现象只是长期过度劳累和生活困苦所造成的。但也不能认为一旦人们都能适度从事有益劳动,世上就会只剩下平庸的劳动者和诗人了。凡能从诗意中感受到崇高的快感者便是诗人,哪怕他生平从未写下过一句诗!
我的思路顺势而下,并不曾意识到是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我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并且对此信心倍增。我沿着田边漫步,田里有农夫在耕作,准备来年播种。眼前的景色开阔,一如霍尔拜因的版画。远处,郁郁葱葱的层林已染上一抹暗红,预示着金秋即将来临。雨后初霁,深棕色的田野上,小沟里还蓄着雨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缕缕银光。天气暖融融的,新犁的地面蒸腾起薄薄的雾气。有一个老农在地头犁田。他的肩背宽阔,神色严峻,令人想起霍尔拜因的版画,但他的服装毫不寒碜。他使的旧式犁由两头毛色浅黄的牛拉着。这种牛是古老草原的真正主人,长得高大而不够健壮,长长的牛角向下弯曲。一对牛若长期结伴干活,像我们乡下说的,就会变成兄弟。若有一头死了,剩下的也会伤心地随之而去,而决不同新来的一起犁田。城里人不熟谙乡间风情,还以为说乡下的牛有情有义是无稽之谈呢。那么他们最好能亲自到牛棚里来看看那可怜而瘦弱的牛!牛儿无精打采地用尾巴甩打着干瘦的两肋,见到饲料,会厌恶地嗤之以鼻,眼睛直瞪棚外,一面用蹄子跺着身边的空地,一面嗅着失去的伙伴留下的牛轭和链条,口中还不断发出呼唤的哀鸣!牧牛人会说:“这一对儿算完了。死了一头,剩下的不肯干活,本该喂肥了好宰了吃肉,但它不进草料,很快就会饿死!”老农从容不迫地干活,一声不吭,丝毫也不白费力气。拉犁的牛很驯顺,动作很从容。老农已很熟练,干活时从不停顿,持续向前,结果他犁田的速度竟与自己的儿子不相上下。年轻人在离他不远处干活,那块地土质硬,石块多,使唤的四头牛也不够壮实。
随后,一幅真正的美景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景象庄严肃穆,很值得画家描绘:田野尽头一个英俊的年轻人驾驭着几对出色的牲口正在犁田。拉犁的共有八头小牛,毛色深重,闪闪发光还夹有黑斑。牛的头部不大,鬃毛拳曲,看去酷似野牛。牛群怒目圆睁,动作突兀。它们那烦躁不安、时断时续的走动说明牛群是新套上的,对牛轭和刺棒都不习惯,只是勉强干着。本地人称这类牲口为“新套的”。年轻的农夫是在一块草场上垦荒,地面满是多年生饲草的古老根茎。他虽年轻力壮,驾驭的八头牛却刚学会干活,所以也只是勉强能对付下来罢了。
犁铧边上的垄沟里,有个六七岁的孩子,他手拿一根很轻的长棍,边走边用棍端不太尖利的钉子去刺戳牛群。这孩子长得美如天使,穿着工装,肩上披一块羊羔皮,看去酷似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笔下那些童年时期的施洗者约翰。孩子每戳一下,牛群就哆嗦一下,把牛轭和额前的皮带振得咯咯作响,犁辕也剧烈地晃动着。每逢铧刀遇到草根,农夫就高声唤着每头牛的名字,不是要去刺激,而是为了安抚牛群。因为牛群每遇动作受阻就会怒气冲冲,烦躁不安,跳起来用宽大的叉蹄扒开泥土。若是年轻人边吆喝边用棍戳还不能稳住前面那两对牛(后面两对由孩子驾驭),牛群就会带着犁,离开垄沟,横穿田地而去。可怜的孩子也在使劲吆喝,但他的嗓音还是那么细柔,一如他那天使般的容貌。景色、男人、孩子和轭下的牛群,这一切都显示着力和美,或者说是优雅的美。尽管征服土地是一场剧烈的搏斗,但一切却都笼罩在一种恬美肃穆的氛围中。农夫看到障碍除去,牛群重又迈出平稳的步子,便收起怒容,恢复平静,一种质朴的人所特有的平静,并且怀着为父的满意心情注视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转身对他报以微笑。因为农夫刚才只是佯装发狠,不过是在表明自己精力充沛,稍一使劲就能应付裕如。然后年轻的父亲用浑厚的嗓音唱起一首庄严而哀婉的山歌。这山歌是本地自古以来世代流传的,并非所有的农夫都会哼唱,只有那些善于激发和保持耕牛活力的农夫才能掌握山歌的要领。这山歌的起源和流传都带有一种神圣和神秘的色彩。但迄今这里的人们仍然相信,耕牛干活久了,感到厌倦烦躁时,只要听到这歌声,便能生出活力。山歌的魅力就在于此。本领高强的农夫,光会扶正犁铧,驾驭牲口开出笔直的垄沟,是不够的。他还应当学会给牲口唱歌,这可完全是另外一门学问,需要具有全然不同的素质和技能。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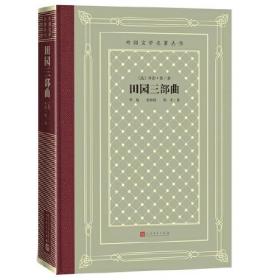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