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手正版】 风流家族 雷铎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7536080096
本店图书 都是正版图书 可开电子发票 需要发票的联系客服!
¥ 10.5 3.0折 ¥ 35 九品
仅1件
作者雷铎
出版社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ISBN9787536080096
出版时间2016-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1309015704112584243
上书时间2024-12-2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品
- 商品描述
-
前言
我是怎样被生下来的
我一被生下来就睁开了眼睛,看见了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个脖子上夹着一个气球样物体的陌生老女人,那是接生婆。我后来常常推测我当时眼看到的是爸爸还是妈妈,后来确信先看到的是爸爸,然后是被临时用来当我的接生间的那座牛棚,然后才看到妈妈,因为大家都说,爸爸一把我从接生婆手里接过去,我便睁开了眼睛,看着他,象早就认识了,不惊奇,也不陌生。这时候有一束阳光从牛棚墙上的小方窗射进来,照在我小小的脸上,我眯了一下眼睛。我想那便是我次看到太阳,一轮刚刚从云里生出来的太阳,一片白炽的、耀眼的,五颜六色的、会旋转和会放射箭状光晕的东西。妈妈说:“别照坏他的眼睛。”爸爸就把我递给她,这时候她已经从床上坐起来,那是一块用两条板凳支起来的铺板,然后铺上草席。她接过我,让我吃她的奶,那天是一九五○庚寅年农历三月初三。我小时候吸奶的技术相当好,至今还记得后来有些小媳妇们奶憋得难受,她们自己的婴儿吸不通的时候,就到我家里找我妈妈借我去吸奶,我看到的第三张脸是祖母的,那张脸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一直到她去世的时候我都不喜欢。第四张是接生婆的脸,脸的下巴吊一个肉瘤在脖子上,这当然不好看,可是我对脖子上长有肉瘤的人们并不象一般孩子那样怀着厌恶感和恐怖感。这大约是使我顺利生下来的这个恩人长有肉球的缘故。这个女人还会算命,跟爸爸妈妈说这孩子长大了一定大富大贵,因为生下我的那个日子和时辰是黄道吉日吉利时辰,并且长有一副贵相。虽然三十六年过去了,我没有大贵,更没有大富,但我还是感激她,至少她的话使对儿媳妇抱有敌意的奶奶对我不敢太苛刻,以免有一天我真的大富大贵了不给她一点什么好处。
今后命运会对我怎样,我不知道,但三月初三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是已经证实了的,它很奇怪地和我的家族的许多大事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些大悲大喜、大吉大凶的事件,有过人被砍头、剥皮,也诞生过幸运的转机和美丽的女子。三月初三至清明节,是寒食古俗,是仕女们、民女们到郊外踏青的日子,也是上坟祭扫先人的日子。在我的家乡,至今仍保存着这种风俗,每逢这一天,男人们便用一把锄头,挑着猪头、鸡、鸭三牲和酒、茶、纸钱、香烛、挈妇将雏,上坟山去,将祖宗坟前的草用锄头锄去,在花岗岩坟碑凹刻的字里,拿三角刀刮去旧年留下的漆皮,用红绿两色油漆将上面的字重新描一遍,古老的坟碑便全用绿漆填字,只在开头的“祖”字上和结尾的“之墓”字上用红漆填,而如果坟碑上那一对夫妇的名字当中,还有一个尚且活在世上,死去的便用绿漆,活着的便用红漆。我从小便觉得这个风俗很奇怪:一个人还好好的,只是死了另外一个,便得把他或她的名字也和死去的那个并排刻在一起,好象这一个先睡了给另一个留好一个枕头似的。待到他或她也死了,便埋在先去的那个人身边,然后子孙们便全部改用绿漆来描。描完了,便在坟堆的草丛里用小石块压上黄纸条和白纸条,纸条在风中翻飞着,喇喇作响。石供桌上摆好了三牲及一并祭品,点燃红烛黄香,依辈序长幼轮番跪下磕头,然后烧化纸钱,点起鞭炮,洒酒祭奠,于是五十里坟山,烟雾飘飘袅袅,炮仗声此起彼伏,一方的人们,便在一种充满宗教气氛的音响画面和烟味酒气之中,怀念和告慰了自己幸或不幸、大幸或大不幸的祖先。
三十六年前的那个清明节,我爸爸因为生我没有上山,我祖父和他的兄弟和堂兄弟去了,去祭奠他们的父辈、祖父、曾祖父。祖父的曾祖父的坟里是空的,只有几件衣服,他是被清朝官府凌迟处死的,不许收尸。那天是他被一把用铁钉做成的钉梳一梳一梳梳死的九十六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家族祭奠了慓悍的先人,接生下它的纤细的第六代男儿。
祖父那一天是才真正当上祖父的,他本来只是父亲,他曾经当过两次祖父都没有当成。他是带着家族香火继续被绵延下来的喜讯去告慰先祖的,所以他上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山上早已经鞭炮响成一片。五十里坟山茂密的草木之下,挤满了八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死去的人们,他们安眠在子孙们为他们建筑的地下居室之内。他们当中,有些人不久前还是祭奠别人的人,如今却被人祭奠着。这一方土地的子民,总是如同这片峰峦绵延的坟山上砍不尽,烧不绝的草木一样,在天灾和战乱之中依旧繁衍不息。
那一天没有纷纷细雨。丽日蓝天,花红柳绿,泉鸣鸟啼,是大自然怀春的日子,是一切动物怀春的日子,是人类与别的生灵、与整个大自然一同回顾生命的意义,同时也是挖掘和发挥生命意义的日子。
对于我母亲,这一天是一个大痛苦而又大喜悦的日子。在我被生下来证明是个怎样的活物以前,我母亲的灵魂是忐忑不安的,不知道在肚子里等待出世的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因为在我之前,她生下过两个儿子,个没有活过三天,第二个没有活过十天。当我被生下来的时候,个奇迹使她相信,当算士的三祖叔和接生婆的吉利话,将在这个儿子身上得到证实。我父亲回忆说,当时那红红的一团肉,有着小得令他惊讶的小手小指甲的这么一个小生命,居然一落地便睁开了眼睛,先是睁了两下,又闭上,然后睁了第三下,便认真地打量起周围的一切来。眼睛是出奇的大,出奇的亮,所以妈妈没等胎盘生下来,就坐起来,抱过我,看我怎样用眼睛看人。因为眼睛太大,后来人们都说我是牛眼,小时候爱我的长辈们和我后来的女同学们,首先爱的便是这一双眼睛,不过到今天,这双眼睛已经失去太多的光泽,这是常常使我遗憾,令我一看起小学和中学照片上的炯炯目光,便常常恨起岁月来。
说我是牛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生我的地方,是一间牛棚,这是我家屋前一间守更的小楼,在寨墙角上用石头和石灰砌起的简单的二层楼,楼上有隙望窗,和平岁月里是更夫夜间敲更的所在,动乱年代,便是瞭望哨和枪铳楼,楼下没有用处,便用来圈牛。那更楼是清朝砌的,至今还在,今年春天我回去探家还去过并打扫过。不过已经有些破败了,石灰和黄泥的墙剥落了许多,露出里面形状不一的石块来,至今也还用来圈牛,有一股黄牛特有的香膻味混杂着阳光气息的干稻草味和牛粪尿很有穿透力的气味。
不过我被生下来的那天,这牛圈是特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前面有两个哥哥没有养活,便请精于算道的三祖叔算过,三祖叔说,妈妈先前生产的那间房间地底下不干净,必须去牛棚生,牛可以辟邪。在我的家乡,牛是被当做一种神物来崇拜的,一种低贱劳累的神物,它们吃的是草,拉的是很重的犁耙,还常常被鞭子抽着,老死了,有钱一点的人家是舍不得杀的,抬出去到山上,埋在一个不被人知的地方,以免被那些饿疯了的人们挖出来吃了。穷人顾不了许多,牛老死了还是要杀,不过杀了也并不自己吃,只是卖给别人吃,就象大饥荒年人们没有别的东西可吃了,便吃小孩,而自己的小孩是不能自己吃的,所以便卖了自己的对小孩,去买了别家的小孩来吃,道理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妇女们,则是不吃牛肉的,她们相信,牛是一种犯了错误的天神投胎的,拉犁和挨鞭打是玉皇大帝对它们的惩罚,而吃它们的肉是一种罪过,会受报应的。不过我想那仅仅是在和平年代,在战乱和大饥荒年代,小孩都可以煮了来吃,牛要不被吃,大概做不到。
我在牛棚里被生下来,生下来马上用布包好抱回家里,后来居然没有大灾大厄便被养大了,所以祖母在世的时候,常常说是牛神爷的功劳。可是到我懂事以后,我知道并非如此,其实是仅仅因为没有我祖母的罪恶我才活下来的。
按一辈一辈相传不息的无数规矩当中的一条,媳妇临产了,是不需叫什么接生婆的——只有那些死了婆婆的不幸人家才请接生婆。婆婆既然能当婆婆,这身份便说明她至少已经亲自生过一次孩子。所以便具备了当接生婆的资格。媳妇在床上挣扎,婆婆问:破水了没有?破水了,便烧一大锅热水,从箱里柜里翻出一些用不着的破衣服、碎布头,等媳妇挣扎到孩子露出头发的时候,使用一只手接住,另一只手压在产妇肚子上,把它挤出来,出来了。便剪脐带。
说到剪脐带,我心里便起鸡皮疙瘩。剪脐带有一种固定的诀术:有一把固定的专门用来剪脐带的剪刀,一代一代传下来,放在婆婆床下放鞋子袜子那块脚踏板的右角上,拿出来用的时候,摘一枝石榴枝,在剪刀上刷三下。口里念道:“玉皇大帝、观音娘娘、财神爷、灶神爷、龙王爷、土地爷保佑:一二一:生儿象孵;鸡一二二,生儿象养鹅;一二五,生儿象生猪;一二九,生儿象生狗。”念完了便可以启用。有钱人家用金剪银剪,没钱人家便用铜剪铁剪。我的两个小哥哥,是我祖母用一把据说传了九代人的镀了铜的钢水颇好的剪刀剪的脐带。刀是不许磨的, 因为脐带是极软嫩的,所以用极老极钝的剪刀,只要方法得当,多剪几下总是可以剪得断的。我那两个没见过面的小哥哥死于“脐风”。我长大以后,懂得那叫破伤风。是我奶奶用那把后来我还见过的,一动便有铁锈象酥饼一样剥落的老剪刀,用带着露水的石榴枝刷过三次,念过一串十几个菩萨的名字,和从一到九如生鸡生鹅生猪生狗的口诀,去在脐带上留下淡黄色的锈迹,才终于死于破伤风的。
而我有幸,有了两个小哥哥的死,才有了被安排到牛棚里和请来接生婆的权利,对于妈妈,这是不幸的结束:她是不幸的后一代。为了请接生婆,从来孝顺的我父亲,还和祖母吵了嘴,祖母说你反了,父亲说谁反了,祖母说天下都反了,父亲说,天下都在反封建。那正是我们的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上,那组具有历史意义的麦克风前被宣布成立半年之后的事情。祖母曾见地主被贫雇农吊着打着踏着,是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势力”的缘故,既然“封建”是这么严重的事,她也便只好让儿子三分了。
所以,如今想来,我能活下来,除了两个哥哥的死,也许还因为社会在变迁。生逢其时。谢天谢地。
我至今一闭上眼睛,好象看见我被生下来的情景。那是共产党掌权之初的一个清晨,在中国南方一间牛棚里,一个中农的儿子被生下来,正好是日出的时辰,金黄的阳光从牛棚东墙上那面有移动木板窗门的方窗外面射进来,一个人类的新生儿便和古老的三月三的太阳一同升起。
这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三千年前发源在被雨水分割成许多裂块的渭水之滨的黄土高原上,禹的儿子启在封亲赐戚时被排挤,迁到长江汉水之间的黄县。其中的一支汉朝时东迁入闽,它的后裔当中有一个策应洪秀全残部起义,全家被处了极刑,有五颗人头和另外一百四十二颗起义领袖的人头一道,分别挂在四座城门外的竹杆上,每根竹杆挂了四十个人头,象一棵很奇怪很整齐挂满了果实没有叶子的椰树,或者象一串孪质发黑的串糖葫芦。家族当中有四个男儿逃脱了,带着妻子,背着祖宗牌位,流亡他乡,行前去向死难的亲人被挂到旗杆上的脑袋告别,弟弟血气方刚,扑向旗杆,想将父亲的脑袋解下来,守卫的官兵围上来,把他的双手砍了,押回府衙,和新捕到的一只华南虎关在一起,让虎爪一点一点去撕他。他的哥哥,想到父亲赴难前的叮嘱,不敢鲁莽,携了妻子和弟媳,投奔异乡的同宗远亲,后来白手创起一番家业,出了巨富、异人、侠客、术士、美女、哑巴、半面人、党支部书记、麻疯姑娘。携妻女流亡的那个人,是我祖父的祖父。祖父的祖父告别人类的那一天,正是三月三,也是那一百余颗人头被割下来的那一天。
九十六年后的同一天,我被生下来。长大后,当了兵,在军队里当文官,于是有了这部带自传色彩的小说。说是小说,不仅仅由于有意的虚构,也由于无意造成的虚假:一个家庭很有传奇性的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肯定渐渐被省略了许多、修改了许多、又增加了许多。我无意严格考察历史,写一本史书,只将我的某些经历,和家族的历史的传说,用我的记忆和想象组合出来,给读者提供一本消遣的闲书,作为饭后的话题。为了写作起来自由一些,从下章开始,将舍弃人称,信马由缰,信意随笔,真真假假,由它生灭,鬼鬼神神,任我道来,有时会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悲壮惨烈,有时会爱得地暗天昏,卿卿我我,悱恻缠绵。
谨此开篇之际,我祈求我的缪斯,一如当年我的祖母为我剪脐带前用带锈的剪刀拂过了石榴枝,求诸天神地神那般祈祷:一二一、作文如养鸡;一二二,作文如养鹅;一二五,作文如养猪;一二九,作文如养狗。
【免费在线读】
导语摘要
雷铎所著的《风流家族》为广东籍作家雷铎带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以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秋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写了潮汕平原秋氏家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展示了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趋向。
故事在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中展开,其间,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时代风云和民俗风情娓娓而清晰地呈现。语言老道圆熟,节奏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饱满。
商品简介本书为著名作家雷铎教授带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以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秋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写了潮汕平原秋氏家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展示了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趋向。
故事在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中展开,其间,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时代风云和民俗风情娓娓而清晰地呈现。语言老道圆熟,节奏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饱满。
全书将文学、历史、文化熔于一炉,有大视野和人物的细腻刻画,具厚度感和温情,是极具阅读价值的小说作品。
该书是作者的成名作《子民们》的修订版。1984年,作者考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新的层面反思战争与人生,对文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在此期间写下了长篇小说《子民们》。
作者简介
雷铎,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国家一级作家。从事哲学文化研究,文学方面屡获国家大奖,学术方面成果多为国家级社会科学权位刊物转载收录。
目录
引子我是怎样被生下来的
甲一章斩蛇起事
乙一章乌狗白鸟
甲二章石玻天惊
乙二章童年断忆
甲三章潮州之役
乙三章升平岁月
甲四章海盗父子
乙四章共产年代
甲五章荒年活祭
乙五章茫茫大地
甲六章风雨姐弟
乙六章中学时代
甲七章二男三女
乙七章戎马生涯
尾声三月三古老的太阳高高升起
内容摘要
《风流家族》为广东籍作家雷铎带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以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写了潮汕平原秋氏家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故事在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中展开,其间,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时代风云和民俗风情娓娓而清晰地呈现。作品将文学、历史、文化熔于一炉,有大视野和人物的细腻刻画,具厚度感和温情。
主编推荐书稿为广东籍作家雷铎带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以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基本框架,通过秋氏家族的百年兴衰史,写了潮汕平原秋氏家族一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展示了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和发展趋向。
故事在历史和现实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中展开,其间,近现代潮汕的历史风貌、时代风云和民俗风情娓娓而清晰地呈现。语言老道圆熟,节奏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饱满。
全书将文学、历史、文化熔于一炉,有大视野和人物的细腻刻画,具厚度感和温情,是极具阅读价值的小说作品。
【内容简介】
精彩内容
又十天之后,元宵节下半夜,地复大震,浩浩荡荡东流入海的韩江东堤,震裂十三处,堤崩水决,一
夜之间,几十个村落、百万亩良田,化为一片汪洋。
一片肥沃的潮汕平原上,几座突兀的小山,成为汪洋上孤岛,唯有远远近近一些露出水面的大树和屋顶,证明那是村庄。木床、木箱、木柜、木盆,在未平息的漩涡和余波上漂流、旋转。幸免于难的人们趴在床上、坐在箱里柜里盆里,等待救援;屋顶上、树干上挤满了人;有少数的船,来来去去运送着人。人们聚集到附近的山包上去,人头攒动如同蚁群。衣物、木片和倒塌的房屋梁楹随波漂流,很少有人去捞取,死牛、死猪和死人,也静静地漂浮。
救人的船,被从屋顶上、树干上下来的人们和抱着房梁、木片、坐着水盆游过来的人们包围了,人们争先恐后爬上去,于是翻了几条船,又死了一些人。
余下的船,装满了人,看着要翻了,使用木桨敲打抓住船帮不放的手,那些手便放开了。也有被打烂了,依旧抓住不放,如同吸在上面的水蛭一般,船家便命令船上的人用手将那些手掰开。
天下着没停过的淫雨,水是浑黄和腥臭的。天茫茫,水茫茫,死了亲人的,漂走了生计所依的,被木桨打烂了手的,都木木然,如同旁观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真戏。另外有几条船,也救人,也捞物,救起来,看看有些值钱的金银细软,便留下了,将人和用不着
的物,依旧推回水里去,被劫过又被推下水的,似乎也没有一句怨言,世界大概要毁灭了,发生了什么,都无须怨言。
这一片古老的平原,三千年来,已经被水淹过多少次、被火烧过多少次、被刀犁过多少次、被人血肥沃过多少次,已经没有人去计算。计算是多余的,该发生时便发生,该停止时便停止。活下来的,便默默活下去,默默重新经营起生计,在废墟上盖起茅房,在荒废的地里犁沟播种;有儿孙的,养育儿孙,没有儿孙的,拼凑一个家庭,生养一些儿女;没法子生育的,收养一二个三五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村落总是在被毁灭的地方重建起来,待到草房有些变成了瓦房,暮霭里飘散着稻米香,星空下村子里有笑声传出,清晨各村寨的雄鸡又你呼我应热闹起来。这时候,便总是有一次新的灾难袭来。
但是潮汕平原总是活着,收养和繁殖着依附在它身上的子民,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
甲寅这样的大水有过多少次,只有大地自己记得。
第二夜,正月十六,月亮出来了,很圆,很亮,若无其事地照着这一片汪洋。水波很平缓,月光照着
,如一片极大的平湖,留在水面的山包、屋顶和树冠,黑黝黝的,如同小岛和礁群。没有鸡鸣,没有狗吠,鸡狗都淹死了,没淹死的也被吃掉了;也很少有婴儿哭,深更半夜发的水,大人能活下来,便挺不错的,个把幸存的婴儿,似乎也极懂事,并不太哭。
有过多少次这样浩瀚的大水和默默的忍受,月亮也应该知道。
月亮出来了,天便开始放晴,水便开始消退。
府城地势高,四面又有城墙,把四大门和七小门的三层水闸关紧,水便进不去了。水退了,城门又打开了,关了门的店铺,又重新开张起来。
乡下做买卖的,又拥进城来。而更多是乞食的,扶老携幼,拖儿带女,见人便作揖、下跪、磕头,哭,说些好话,心灵圻裂,唱着一开口便有血一起流出的歌,换得一二枚铜钱,三两口米粥,然后又磕一阵头,祝施主长寿百岁,下辈子全家变牛变马、变鸡变狗来报答。孩子们也跟着父母磕头,发誓要变成牛马猪狗、小虫子、小蚂蚁来报恩。当中也有标了价要卖的,男童五升米,或二十五斤地瓜,女童三升米,或者十五斤地瓜。也有白送的,谁家心好,收留下,当个使唤,打骂在所不计,只要有口吃的便可。果真也
有买下的、收下的,孩子与父母分别的时候,并不太哭,能活下来,已经不错,只要活在世上,总还有相见的一天。
P10-P11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正版二手]风流家族9787536080096](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eababaea/52dbc2b88b4b4a89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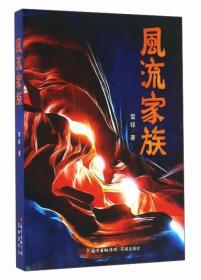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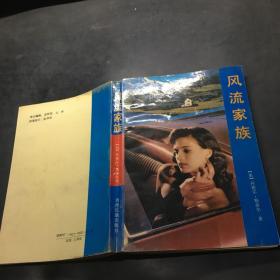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