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能性
批量上传,套装书可能不全,下单前咨询在线客服! 正版书 !!!
¥ 23.67 6.8折 ¥ 35 全新
库存18件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5189364
出版时间2017-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25201080
上书时间2024-10-19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本书为法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论及诗歌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由三个文本构成,分别是《老鼠的故事》《狄安努斯》《俄瑞斯忒斯纪》。这些由日记、小说、诗歌、文论等不同文体混合而成的文本,晦涩难懂,其意义难以把握。在色情而暴力叙述的外表下,巴塔耶似乎围绕“不可能性”这一核心观念论述了其对于诗歌的看法。他认为“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而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的经验”,诗的目的在于通过词语,召唤“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召唤不可能性,如此诗才具有反抗的暴力。
作者简介
乔治·巴塔耶(GeorgesBataille,1897—1962),法国著名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博学多识,思想庞杂,其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巴塔耶的思想上承尼采、克尔凯郭尔、萨德的批判倾向,下启20世纪后期法国诸家思潮,对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等人的影响尤深,颇具反叛精神,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曹丹红,198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进入南京大学法语专业学习,2008年取得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文论。已翻译出版《日常生活颂歌》、《柏拉图的理想国》、《身体日记》、《马拉美:塞壬的政治》、《批评与临床》(合译)、《艺术家的责任》(合译)、等多部法国重要文学与社科类著作,并著有《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一书。
目录1/老鼠的故事
93/狄安努斯
135/俄瑞斯忒斯纪
内容摘要本书为法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论及诗歌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由三个文本构成,分别是《老鼠的故事》《狄安努斯》《俄瑞斯忒斯纪》。这些由日记、小说、诗歌、文论等不同文体混合而成的文本,晦涩难懂,其意义难以把握。在色情而暴力叙述的外表下,巴塔耶似乎围绕“不可能性”这一核心观念论述了其对于诗歌的看法。他认为“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而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的经验”,诗的目的在于通过词语,召唤“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召唤不可能性,如此诗才具有反抗的暴力。
主编推荐
乔治·巴塔耶(GeorgesBataille,1897—1962),法国著名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博学多识,思想庞杂,其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巴塔耶的思想上承尼采、克尔凯郭尔、萨德的批判倾向,下启20世纪后期法国诸家思潮,对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等人的影响尤深,颇具反叛精神,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
曹丹红,1980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进入南京大学法语专业学习,2008年取得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国巴黎索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法国文论。已翻译出版《日常生活颂歌》、《柏拉图的理想国》、《身体日记》、《马拉美:塞壬的政治》、《批评与临床》(合译)、《艺术家的责任》(合译)、等多部法国重要文学与社科类著作,并著有《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一书。
精彩内容
选自第183—186页这些蛇是给谁的……?
未知和死亡……没有牛的沉默,在这样的路上,只有牛的沉默才足够坚强。在这未知中,失明的我弃械投降(我放弃了理性地穷尽所有可能性的打算)。
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对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的经验,它仅仅是通过词语,对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的召唤。
相对于经验,召唤有一种优势,它是丰富的,具有无限的便利,但它令人远离(本质上被麻痹的)经验。
如果没有过度的召唤,经验将是理智的。如果召唤的无力感令我恶心,那么它将从我的疯狂开始。
诗令夜晚向过度的欲望敞开。被诗劫掠过后的夜晚在我身上是对某种拒绝——对我超越世界的疯狂意愿——的量规。——诗也超越了这个世界,但它无法改变我。
与其说我那虚构的自由摧毁了给定的自然的限制,不如说它确保了这种限制。如果我满足于此,我将渐渐屈服于这给定的东西的限度。
我继续质疑这世界的限度,同时抹除那些满足于此的人的悲惨处境,我无法长久地承受虚构的便利:我要求现实,我发疯了。
如果我撒谎,那么我就处于诗的层面,处于以言语超越世界的层面。如果我坚持盲目地贬低世界,那么我的贬斥就是假的(就像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世界的和解得到深化。可是,由于不能蓄意撒谎,我发疯了(能够忽视现实)。或者,由于再也不懂该如何为我自己上演一出胡言乱语的闹剧,我又发疯了,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体验了黑夜。
诗是一种简单的迂回:我通过诗逃离话语的世界,这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世界。我与诗一起进入某种坟墓,其中可能性的无限性诞生自逻辑世界的死亡。
走向死亡的逻辑孕育出疯狂的丰富性。可是被提及的可能性却是不真实的,逻辑世界的死亡是不真实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并逃离到这种相对的晦暗中。我可以在此嘲笑我自己,嘲笑别人: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一切价值都是不真实的!从中很容易产生致命的滑移,在滑移中,我不知道我是在撒谎还是发疯了。夜的必要性即来自这种不幸的处境。
夜晚只能通过迂回产生效力。
对一切事物的质疑产生自某种欲望的扩张,而这种欲望不可能是对空的欲望!
我的欲望的对象首先是幻觉,之后才是幻觉消失的空。
不带欲望的质疑是形式上的,是无动于衷的。对于这种质疑,我们无法说出“这和人是一回事”这样的话。
诗揭示了未知的某种力量。但是,未知如果不是某种欲望的对象,那么它便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诗是一个居间的词汇,它在未知中窃走了已知:它是装饰有太阳那刺目色彩和外表的未知。
数以千计的形象令我眼花缭乱,无聊、急躁和爱在这些形象中组合而成。现在,我的欲望只剩一个对象:这数以千计的形象之外的东西,和夜晚。
然而,在夜里,欲望撒谎,而夜晚因此停止成为欲望的对象。我“在夜里”的这种生存仿佛爱人死去时情人的生存,仿佛得知赫尔弥俄涅自杀时的俄瑞斯忒斯。在夜里,它无法认出“它等待的东西”。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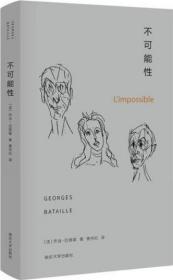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