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问 “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
正版全新 快速发货
¥ 52 5.9折 ¥ 88 全新
库存99件
作者承红磊 大学问出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63102
出版时间2023-1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8元
货号29640192
上书时间2024-11-1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序
承红磊博士的新书《“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行将出版,邀我写序,我感到非常荣幸,欣然应允。
承红磊博士现在是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多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在章开沅教授、马敏教授和朱英教授等的带领下,成为内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亦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年轻学者精英。红磊受到这种良好氛围的滋养,近年来有很大成长。
承红磊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取得学士和硕士之后,于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深造,以近代史为专业,而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的发现——晚清“社会”话语考论》,2014年完成。其论文在资料、文字、方法、思想和创新各方面皆见功力,是一篇优秀的论文。其后红磊应华中师范大学之聘,担任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深得学院的器重,而他本人也在教学和研究上力争上游,不断努力,先后发表多篇论文,相信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承红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对张灏教授所说的“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时期”尤为措心。所谓转型时期,亦即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到民国初期二十年代的那段时候。那是一个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由旧到新的转换时期。当中派系可见各种思想和各种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有保守的势力,有激进的势力,也有温和的言论。这些不同的思潮也都有各自表达的途径和出版的地盘。承红磊所要做的研究,主要是以“社会”这个词语与概念为重心,把这段时期发表的文章做深入详细的分析,尤有进者,对一群作者做追踪式探讨,察看其网络,分析其思想,研究其行径,然后对此段时期的新旧思想交缠、人物晋接及其相互的影响,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论文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甚为创新,相信本书出版之后,必会引起同人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前院长暨历史学讲座教授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
导语摘要本书是研究“社会”概念兴起和广泛运用的shou部系统专著。作者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全书研究视角独特,方法创新,以“社会”这一微细的单一概念为基础,将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次进行量化分析,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揭示了“社会”逐渐取代“群”“人群”等词的原因。同时,作者并不只聚焦于词语的考证和论述,而是以“社会”一词为切入,再现了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社会”概念的讨论,呈现晚清民初各种思想和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
作者简介承红磊,男,河南商水人,复旦大学本科、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初政治史、思想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史林》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绪论
第一部分 晚清“社会”概念的产生
第一章 Society的诞生及其在华早期翻译
第二章 甲午战后的“群”“群学”与“社会”一词的再使用
第三章 从“群”到“社会”:以梁启超为例看庚子前后“社会”概念的形成
第二部分 清末“社会”概念的集中使用及其影响
第四章 严复对中国“社会”所做分期及性质判定
第五章 “社会”与早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第六章 “社会”概念与清末伦理变革
第三部分 民初“社会”话语的流行与“社会”内涵的转变
第七章 民国初年“社会”话语的流行与内涵转变
结论
附录一:《申报》“社会”使用情况整理(1873—1894)
附录二:梁启超论著目录及“群”“人群”“社会”使用情况(1899—1904)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本书是研究“社会”概念兴起和广泛运用的shou部系统专著。作者从词汇史和概念史切入,爬梳了“社会”这一词语由西方引介到中国,并且逐步普及的过程。全书研究视角独特,方法创新,以“社会”这一微细的单一概念为基础,将清末报刊和著作中使用“社会”一词的频次进行量化分析,材料丰富,论证周详,揭示了“社会”逐渐取代“群”“人群”等词的原因。同时,作者并不只聚焦于词语的考证和论述,而是以“社会”一词为切入,再现了严复、梁启超等近代学人对“社会”概念的讨论,呈现晚清民初各种思想和潮流的角力、争持和交替。
主编推荐承红磊,男,河南商水人,复旦大学本科、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初政治史、思想史、近代中外关系史,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史林》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精彩内容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些思想的传播,不仅塑造了“社会”话语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还逐渐改变了“社会”的内涵。受唯物史观影响,思想界越来越倾向于从生产和经济方面来理解“社会”。
——编者按
从精神到物质——“社会”内涵的转变
“社会”与“社会主义”包罗万象。随着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了解的增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增大,其所主张的唯物史观也随之越来越受到认可。到了1920年11月,杨端六在其《马克思学说评》一文中承认“近来我国人多鼓吹社会主义,就中尤以马克思学说为最流行”。
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较早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陈文说:“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社会上经济上的构造,这就是社会真正的基础了。在这基础之上,再构造法制上政治上的建筑物,适应社会的意识形态。”该文还提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法,可以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的过程。人类的意识不能决定其存在,人类的社会的存在倒可以决定其意识”。这就把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表述了出来。
李大钊在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介绍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总结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并提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
1919年12月,《建设》杂志刊登了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该文梳理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等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并介绍了士探拉(Rudolf Stammler,1856—1938)、巴拉奴威士奇(TuganBaranovsky,1865—1917)、卞斯天(Eduard Bernstein,1850—1932,今译伯恩斯坦)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批评。但是最后,胡得出结论说,“唯物史观经济一元论的论据,并不因此动摇”。
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应该是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发行。毛泽东回忆称,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是让他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本重要作品的其中之一。
在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影响下,经济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重心。戴季陶谈道:“人类的一切进行,都从经济的进步来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受那一个时代经济组织的影响很大。”胡汉民也开始谈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什〕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以至于林云陔在1919年10月宣称,社会主义,“近已成为‘经济的命运之机械的理论’”。
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知识界开始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按:书名中“惟物”现为“唯物”,下同),以及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戴季陶在文章中指出,欧美所发生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其本国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中国所发生的社会问题,原因并非本国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而是“外国输入的资本家组织的机器生产”。与此相应,欧美出现“农民的工人化”“直接生产的工人奴隶化”等社会现象,而中国则出现的是从前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受外来机器制造品的压迫,多数变了失业者”。戴文同时指出,此前革命事业的失败、革命党的破裂,根本原因都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政治上的破落户”或者“思想上的破产者”。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惟物的研究》一文,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两千年的中国哲学,所做的综合性、概观性研究。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物质生产的方法变化,一切社会的关系跟着变化。人类所有种种感情、想象、思考,以及人生观,其根据都在社会的生活状态之上,即从物质的组织及跟此发生的社会的关系而起。”综合作者之意,社会的生活状态,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是特定哲学产生的原因。比如先秦哲学,该文即认为乃“共产制度(主要指井田制——引者)崩坏之后,最大多数人生活不安的问题,是有强权的人掠夺多数人的衣食,无强权的人衣食被夺不能生活的问题”,社会思潮因而激起“非常的反动”,“由是产生老子以次的哲学”;其二,哲学演变的倾向,及其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心情的要求”,而这种“心情的要求”,是社会生活状态所决定的。比如该文在谈到由老子、墨子往慎到、尹文法治主义的过渡,以及由孔子儒学到孟、荀儒学过渡的时候即作此解释。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在开篇就提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在具体分析中国的状况时,李认为,中国受到欧洲各国资本制度和日本的二重压迫,“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农业经济受到了巨大压迫而发生动摇,与此相应,大家族制度便难以持续,反孔思想便应运而生。
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集中的表现。自杀问题不是这一时期才有的,不过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由于唯物史观的传播,更多人把自杀的原因归结于社会方面。如同李大钊所表示的,“自杀流行的社会,一定是一种苦恼烦闷的社会。自杀现象背后藏着的背景,一定有社会的缺陷存在”。陈独秀也表示,“个人的行为或者不能说全没有意志自由的时候,但是造成他的意志以前,他的意志自由去选择信仰行为以后,都完全受环境暗示的支配,决没有自由的余地”。为此,陈提出自杀的救济方法,除了改造人生观,更重要的是“解除社会的压迫”,也就是“改造道德的制度的组织”。青年毛泽东也表示,“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并且认为,为了“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唯物史观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对当下问题的政策。陈溥贤在介绍唯物史观时早就表示,以道德说教的方式补救社会组织的缺点必定是无效的,“要想改革社会,必定是要组织一个没有做坏事必要的社会出来,为最快的路径,最好的方法”。施存统宣称,“要解决社会各种问题,惟有找他〔它〕的根本所在”,“根本问题一解决了,枝叶问题当然是迎刃而解”。而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济问题。“社会的经济组织一有了变动,其余的一切组织都跟着变动。”由此,施存统开始批判单纯对教育普及甚至自由恋爱的宣传,认为“不把私有财产制度根本推翻,教育那〔哪〕里会普及”,“私有财产制度打破,儿童可以公育”,“自然可以实现自由恋爱了”。结论是:“经济问题不根本解决,一切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
1920年6月,《申报》开始出版“社会经济丛书”。为丛书所作的出版预告表示,“经济组织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基础”。该预告还表示:“自去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应着全世界改造的潮流,激动起来。由空泛的文化运动,向着经济组织改造运动进行。”这大致可以表示此一时期的基本趋向。
甚至“革命”本身的定义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变化。戴季陶表示,革命的最大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的缺陷,不单是压迫着许多人,使他丧失生活地位,并且使多数人,不能获得生活必须的技能”。因此现阶段革命的目的就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对比梁启超在1904年对“革命”所下之定义,可知“革命”含义之变化。
1915年,商务印书馆所出《辞源》解释“社会”称:“多人结合为一体而互有关系者,即个人之精神结合体也。”这种“社会”观无疑是对此前“社会”认识的总结。到了邢墨卿1934年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则这么解释“社会”:“人们在历史的条件所赋予之一定的经济的、政治的、观念的关系之下所结合成功的组织。这随着生产关系的变迁而变迁,有原始共产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的区别。”辞典的编撰有一定滞后性,但是也大致可以看出“社会”概念的内涵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转变。
王汎森在研究“五四”前后的思想界时发现,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后的两三年间,主张“整体的”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者渐多,出现了一种“唯社会”观。这种“唯社会”观是一个连环:“‘社会’是极重要的,但‘社会’是令人痛恨的,‘社会’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之后的‘社会’可以是极光明的。”正如本节所言,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结合,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些思想的传播,不仅塑造了“社会”话语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还逐渐改变了“社会”的内涵。受唯物史观影响,思想界越来越倾向于从生产和经济方面来理解“社会”。“社会”在“五四”前后的核心地位及其内涵的转变,是王汎森所称“唯社会”观的基础。
节选自承红磊《“社会”的发现:晚清民初“社会”概念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媒体评论现代“社会”概念的兴起和广泛运用,是透视清末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革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一面聚焦镜。承红磊的《“社会”的发现》一书,可谓这方面研究的shou部系统专著。全书视域广阔,内容细致充实,特别是对“社会”概念内涵中西日互动的复杂性以及它向各领域多维渗透路径和特点的把握,不乏深入分析和独到见解,值得一读。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当前中国文化史脉络里,研究概念史,务须纵横古今中外思想,努力“收拾”相关学理,寻觅统整相关史料;论析所得,始可一脱“空中楼阁”之弊。现下新进,假借检索资料库为能事,号称“数位人文”,其实既无“人文”,亦非“数位”,不过是“摩登玄学”,识者不取。本书具体落实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概念史研究路向,胜义频出,确可别显新局。读者一览,必然开卷有益。
——潘光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承著聚焦于“社会”这个在近代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新名词,不但从翻译史角度对其追根溯源,还再现了关键文本和若干重要思想家对“社会”的建构与使用,以及“社会”作为一种话语同时代思潮的关系,在当时的流行和内涵演变,包括其所产生的影响。全书视角多元、结构清楚、材料丰富、论证周详,体现出作者具有不凡的治史功力和比较全面的史学修养,是一本值得关注与阅读的概念史著作。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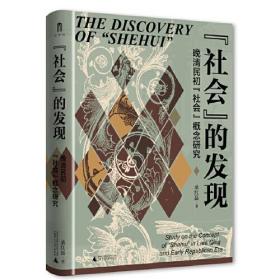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