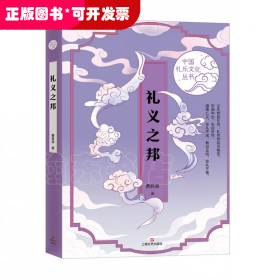
礼义之邦
正版保障 假一赔十 电子发票
¥ 31.03 5.4折 ¥ 58 全新
库存42件
作者曹胜高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4378
出版时间2023-04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4336561
上书时间2024-01-25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前言
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礼仪之邦”?
这要先从“礼”的含义说起。礼是古代中国建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其按照道德认同和人文精神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对人的心性进行引导,以推动社会向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礼借助于外部形式所确定的行为规范是礼仪,为维护行为规范而使用的器物是礼制,蕴含在行为规范之中的道德认同与人文精神是礼义。
《仪礼》记载了早期中国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士丧礼、丧服、既夕礼等礼仪活动的程序,约定了人在特定社会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周礼》描述了早期礼仪背后的制度形态,尤其是职官体系,设计了各级官吏在礼仪活动中的具体职责,记述了众多礼仪用品的使用制度。《礼记》解释了诸多礼仪的含义,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阐释了礼仪和礼制的用意,强调在看似繁琐复杂的礼仪活动中,蕴含着特定的道德赋义。《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为“三礼”,系统说明了礼义、礼仪和礼制的基本形态。
礼仪与礼义的区分是明显而清晰的。礼仪是礼的仪程,礼义是礼的内涵。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仪式化的活动,如开学典礼、结婚典礼、成年礼以及运动会的开幕式等,都有程序化的仪式安排,这是礼仪。所有礼仪活动或者礼仪程序的背后,都蕴含有特定的道德认同、价值导向、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这是礼义。礼义是所有礼仪形式的内在规定,礼仪尊重并体现着礼义的原则和精神。如果说,礼仪是礼的形式,礼义则是礼的本质。
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社会运行、道德认同和价值判断等综合起来的公共原则,凝聚为礼义。这些公共原则转化为社会秩序、行为规范,便是礼仪和礼制。借助礼仪和礼制,可以从外到内约束人的心性,《尚书》言之为“以礼制心”;将心性修为的成果转化为由内到外的自觉行为,即是儒家推崇的“礼乐教化”。由此,礼义是礼的内在规定性,也成为了礼仪和礼制建构的基石。
最早关于“礼义之乡”的记载,出自《史记·三王世家》: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汉武帝晚年,戾太子刘据因遭巫蛊之祸,起兵造反,后失败自杀。汉武帝又未立太子,燕王刘旦上书要求来宫殿护卫。此言一出,汉武帝就明白了,刘旦这是想来出任太子以继承皇位。刘旦本一介武夫,有勇无谋。汉武帝一直对其不屑一顾,他现在也居然想来当太子,这立刻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将刘旦的上书扔在地上,大骂一通,把他派来的使者斩首,以示警告。在这里,汉武帝提到的“礼义之乡”,是对齐鲁地区的一种代称。
西周初期,鲁国是最早用礼来进行社会治理的诸侯国之一。周公制礼作乐,其子伯禽封鲁之后,移风易俗,推行礼治。春秋时,晋国大夫韩宣子访鲁,参观了鲁国所传的典章制度,感叹说:“周礼尽在鲁矣!”
《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二《昭公二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2页。鲁国按照礼义原则与礼仪制度来治理国家,尊重仁、义、忠、信、孝、悌等道德观念,用礼乐教化百姓,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楚汉之争时,项羽封在鲁地。项羽被杀后,鲁人坚持不降,忠于项羽。直到刘邦命人将项羽首级送到鲁地,鲁人按照礼仪安葬了项羽,才接受了汉王朝的管理。
齐与鲁并称为“礼义之乡”,在于齐国也重视礼。春秋中期,管仲辅佐齐桓公,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强调一个国家应该以礼、义、廉、耻为原则。其中提到的礼义,便是让百姓形成道德认同,尊重社会秩序,外守礼节,内知廉耻。礼节是礼的精神原则和行为方式的结合,廉耻是按照礼义原则形成的价值判断,由此凝聚社会共识,维持公共秩序。
鲁重视礼乐教化,齐重视礼义廉耻,齐鲁便形成了由道德原则确定的社会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既能约束个人行为,又能作为社会事务的评判原则,使得齐鲁地区形成了不依靠国家力量约束的社会自运行体系,保持着良好的民风民俗。汉武帝称之为“礼义之乡”,正是肯定齐鲁地区的百姓能够遵守礼的原则,言谈举止合乎规范,社会生活井然有序。
其实,战国时期已经以“礼义”来形容鲁人的特点。《庄子·田子方》中记载温伯雪子入齐,路过鲁国时拒绝见鲁人,理由是:“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温伯雪子回来路过鲁国时,又有人请见。温伯雪子连续两天见了鲁人,回来叹息,弟子问其缘故,他说:
吾固告子矣:“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见我者,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其谏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叹也。
王先谦:《庄子集解》卷五《田子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7页。
这段谈论以温伯雪子的见闻,说明鲁人在待人接物时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是为礼节;劝告和教诲的语气也不相同,是为礼容。温伯雪子觉得鲁人进退有一定规矩、说话有特定方式,感叹鲁人只守外在规矩方式而不懂人心。这表明此时的鲁国已经遵照礼义形成了特定的行为规范和通行的社会风尚。因此,温伯雪子便以“中国之民,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概括自觉坚守礼义的区域。
两周时期,“中国”是一个区域概念。最初是指周王直接管辖的王畿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到周王朝管辖的主要区域。现在看到最早提到“中国”的考古资料,是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所言的“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洛阳地区。随着周王朝的发展,“中国”所指的区域逐渐扩大。《尚书·梓材》言:“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中国”指周王室统治的核心区域。《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其中的“中国”,指代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包括齐、鲁、卫、唐等诸侯国;“四方”则指周王朝的周边区域,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
温伯雪子所说的“中国”,是包括鲁国在内的周王室统治的核心区域,那里人人明乎礼义,待人遵守礼仪。在庄子学派看来,中国与周边区域最大的区别,是中国按照礼义来建构社会秩序,以礼义作为道德准则进行价值判断,与周边区域形成了差别明显的文化传统。
温伯雪子“陋于知人心”的评价,体现了儒家与道家的学术分野。道家倡导保持人的天性,天性不受后天的约束和改造。与天性相符的人心,应该是不受尘俗污染的赤子之心。道家更注重随心所欲,认为礼义约束了人的天性和赤子之心,让人不能道法自然,自由自在。其实,儒家也关注人心,但多从先天道德来理解人的心性。孟子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形成了仁、义、礼、智,作为道德认知。在儒家学说里,人心合乎仁、义、礼、智,体现着人不同于动物的属性,表现为人性之善。道家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人应该尊重自我,少些外部约束,过多的约束会忽略人的自我要求,成为自在的负累,认为礼义约束了人的天性。儒家则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认为社会之所以形成公共秩序,正在于礼义的约束,认为体现群体共识的礼义,比体现个人要求的人心更为重要。
礼的设计原则是“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84页。“节”是节制,“文”是文饰。人有各种各样的感情体验,若要形成稳定的心性,要形成合理的秩序,必须要让情感体验能够合理生成,得以适度表达,这就需要适当的节制与文饰。人有食、色的需求,这些需求既然合理,就要有节度。对这些需求进行必要约束,便是“节”。如吃饭时要按照座次入座,上菜后要先奉至长辈、宾客面前。通过节制来约束人的争夺、占有、贪婪、随意,强化并倡导合理的、规范的行为,将之提炼、升华出来,用仪式化的方式促成有序的社会交往,就是“文”。用节制约束,用文饰引导,就可以为社会秩序、个人行为提供一个外在尺度,为社会运行提供一套行为规则,为心性修为提供一个参照标准,这便是礼。这些尺度、规则、标准所体现的道德认同、价值判断和人文精神,则是礼义。
经过了周礼的规范,中国的广大区域形成了以礼义作为原则的社会秩序。礼义也就成为道德行为的内在要求和外在规范。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自己:
身出礼义之乡,而入无知之俗,违弃君亲之恩,长为蛮夷之域,伤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军北征匈奴,战败后投降。汉武帝诛其家族,李陵知道无法归汉,遂在匈奴娶妻生子。后来,李陵见到了出使匈奴被扣留的苏武,劝苏武投降。苏武却不为所动,仍然持汉节牧羊。汉昭帝时期,匈奴与汉朝交好,同意苏武回国。李陵写信送别苏武,言及自己老母被戮,妻子被杀,不能归汉。而苏武回去后,必然会受到尊荣,李陵由此感慨自己却只能留在匈奴。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李陵说自己“身出礼义之乡”,不是说自己在齐鲁长大,而是说自己在中国长大,没想到最终却接受匈奴习俗,变成了戎狄之人。可见,西汉时用“礼义之乡”来指代中国,其含义是遵照礼义来确定行为规范的区域。
东晋范宁注《谷梁传》时说:“中国者,盖礼义之乡,圣贤之宅,轨仪表于遐荒,道风扇于不朽。”
《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十《哀公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认为中国之所以与戎、狄、蛮、夷有别,在于其按照礼的原则和精神来治理。其所言的圣人,包括周公和孔子。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礼仪制度,孔子克己复礼推崇礼乐教化。“克己”是克制内心的私欲,“复礼”是恢复礼乐的精神,主张恢复周朝以礼治国的传统。范宁所言的轨仪,指的是规则和仪式,是礼仪的外在形式。规则和仪式中体现出的礼的精神,涵养了道德认同,凝聚了价值共识。
礼义维持的是道德认同和价值共识。人借助仪式能够形成共同情感,通过共同情感形成道德认知,当道德认知被作为判断事物的依据时,就可以作为价值共识。礼之所以能塑造人,正在于其将道德原则转化为行为准则,通过行为方式来维持道德自觉。孩子从小参加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会培养出对家人的亲情。参加社会活动,会形成特定的情绪体验。如在升旗仪式中产生的庄严感觉,在参加婚礼时形成的祝福心态,在参加葬礼时感受的肃穆气氛,正是基于情感体验而形成的情感认同。父亲出远门时,孩子随母亲送别,说“爸爸早日回来”,这一做法不仅强化了父子感情,也会养成待人接物的良好方式,体现着道德原则和行为方式的合一。
南北朝时用“礼义之邦”来指代中国。《晋书·苻坚传》载:
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吕光发兵征讨西域。苻坚送行时,言及西域地区没有按照礼义进行治理的传统,与内地不同。周朝以周王室所在的王畿地区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五服。其中的荒服是指王朝统治之外的边远地区,只要给周王朝进贡,表示认同周王,可以不改变饮食、服饰的习惯与制度。苻坚叮嘱吕光对西域的治理,要恩威并用,推行礼乐教化,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因此,“礼义之邦”的含义,特指按照礼的精神来治理的区域,其既可以指代一个地区,也可以指代一个国家。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东汉破先羌,对“礼义之邦”做了清晰的界定:
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六《灵帝建宁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17页。
司马光认为,如果御之有道,周边地区就会归顺;如果御之失道,周边地区就会背叛。既背叛要讨伐,要用威服去治理,也要用礼义来教化。关键是不要让周边区域的习俗来扰乱“礼义之邦”,毁弃中国以礼义治理天下的传统。北宋宣和年间,宋与金联合灭辽。金朝君臣决策时担心北宋会爽约,就有大臣说:“中国,礼义之乡,必不爽约。”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徽宗宣和四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48页。这是从域外正式称呼中国为礼义之乡,用以指代北宋统治的全部区域。
中国之所以成为礼义之邦,正在于较早按照道德原则来确定社会秩序,评判是非对错。不断推行礼乐教化,形成了以礼义治理国家的传统。在中华文化中,礼义被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用“礼义之邦”来形容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正是强调其按照礼义来治理国家、评判是非、确定秩序,有稳定的道德认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礼义之邦的形成,得益于历朝历代的官员主动推行教化,改造旧俗,使得原本比较荒蛮的地区,能够按照礼的规范来做事,按照礼的精神来判断是非,引导诸多未开化的地区成为礼义之乡。南宋朱熹在《龙岩劝谕榜》中倡议龙岩县的百姓:
自今以后,各修本业,莫作奸宄,莫恣饮博,莫相斗打,莫相论诉,莫相侵夺,莫相瞒昧,爱身忍事,畏惧官司。不可似前咆哮告讦,抵拒追呼,倚靠凶狠,冒犯刑宪。庶几一变犷悍之俗,复为礼义之乡,子子孙孙,永陶圣化。
他提倡百姓各修本业,不要奸盗,不要饮酒赌博,不要打架,不要无事生非打官司,不要想着去占有别人的好处,更不要相互隐瞒欺骗。朱熹引导百姓改变彪悍民俗,尊重规则,让龙岩县成为礼义之乡。可见,朱熹所推崇的“礼义之乡”,正是按照礼的尊让恭敬等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尊重道德,遵守规则,形成更为文明有序的社会风气。
从西周开始,中国的行政体系不断对社会进行道德引导、秩序改良,推动了礼义从文明核心区域向四周不断延伸。随着中国的发展,礼义之邦所涵盖的区域不断扩大,礼义所体现的道德认同也在不断深化。元朝杨维贞在《竹月轩记》中说:“益中青年,而才气甚老,尊师乐友,化势利之俗为礼义之乡,无忝奕叶义门之后。”他鼓励读书人尊师乐友,把原来依仗权势利益来处理人际关系的风俗,转化为相互尊重、相互谦让的礼义原则,推动社会秩序持续向好。
因此,礼义之邦的形成,是用礼的精神不断改造传统旧俗,让百姓知道该如何按照道德原则去做人做事,具备道德自觉,行为自律。明代王阳明在《送李柳州序》中言:
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张廷坚、孙觌、高颖、刘洪道、胡梦昱辈,皆忠贤刚直之士,后先相继不绝。故柳虽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贤士。是以习与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为礼义之邦。
宋元时期的广西柳州属于边远地区,最初未受礼义熏染,范祖禹、张廷坚等人知柳州,持续推行社会教化,改善民风民俗,使得柳州百姓知礼用礼,逐渐形成良俗,成为礼义之邦。
中华文化较早确立了人际交往、社会协作的原则,以尊让为方式,以恭敬为要求,建构起稳定的亲亲、尊尊秩序,确立了自觉理性的公共秩序,确定了自然秩序、祭祀秩序、社会秩序的运行原则。这些原则以制礼作乐的方式确定下来,成为礼乐制度,作为社会规范。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人文精神,合称为礼义。中华民族能够按照礼义的要求去认同情感、涵养道德、约束行为、判断是非,既形成了合理恰当的社会秩序,也养成了合情得体的行为方式。这些社会秩
【书摘与插画】礼的形成
从字形来看,礼的繁体字是“禮”。“礻”表明其与祭祀有关,“豊”为礼器,“礼”字的本义是击鼓献玉,敬奉神灵。《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认为礼形成于侍奉鬼神、以求福报的活动。
《尚书·皋陶谟》追述了尧舜时期建构礼制的过程: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伪孔传的解释是:“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义,当敕正我五常之叙,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尚书正义》卷四《皋陶谟》,《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其中的“五常”,伪孔传认为指仁、义、礼、智、信。其实,尧舜时尚未形成明确的五伦观念,五常应该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确认了这些基本社会关系,才会形成尊卑亲疏的观念。依据社会关系来确定地位,才可能将贵族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再形成吉、凶、宾、军、嘉五礼,用礼仪制度来正诸侯,治万民,就形成了早期中国的基本秩序。
以五礼作为社会的基本秩序,所有的社会成员就明确了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特定条件下,应该如何行事。特别是“五服五章”制度,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服饰器物,随时提醒其铭记自己的身份,采用合宜的行为去做事,由此形成了秩序分明、等差清晰的礼制。礼仪活动维系着社会事务的运行,礼仪制度落实于个人行为,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最初的礼仪制度。
夏、商、周三代之礼继续发展演变,并日渐完善。《礼记·表记》中言: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夏人普遍认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天命。有统治继承权的是部落领袖,没有继承权的是普通百姓,似乎任何人生来便已经命定。因此,夏人尤其敬重居于支配地位的鬼神。大禹作为最高的神职人员,统率其他部落领袖,降丘宅土,建立土地祭祀体系。
曹胜高:《降丘宅土、敷下土方与九丘观念的形成》,《山西师大学报》,2019年第5期。以祭祀权的分配来象征统治权的获得,建构了神权与王权合一的运行秩序。
商朝更加尊神,笃信天命由神赋予的观念,以求获得更多的护佑: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5页。商人相信天地之间有神秘的力量,能够支配自然、社会与个人。人臣服于鬼神之下,社会秩序要服从于祭祀秩序,商朝由此建构了复杂的祭祀之礼。殷商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礼器,多用于礼神。甲骨文记载着商王几乎无事不占,时时刻刻向鬼神卜问吉凶祸福。从考古材料来看,商人的祭祀之礼不仅有详细的程序安排,所用器物也有严格的规定,形成了细密复杂的礼制。
周朝在夏商重祭祀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人与人的交往秩序: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486页。周人的“尊礼”,更尊重礼的原则和制度。夏商之礼重视天人秩序、人神秩序,周人将礼用于人人秩序,制定了更多的人际交往之礼,注重以礼来约束人的行为。周人也尊重鬼神,但采用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平时不谈论鬼神,祭祀时则虔诚以对。相对于夏商淫祀自然之神,周人更注重祭祀先祖。周人认为,周族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正在于文王的仁德和善治,由此强化先王之德。周礼中体现的“近人而忠”“赏罚用爵列”,正表明周人试图用礼来确立道德原则,强化社会秩序。
由此,我们就可以来思考祭祀制度如何转化为道德认同,又如何借助道德认同形成群体共识,将之转化为公共秩序和行为准则,最终确立了社会通行的行为规范。
首先,通过仪式化的祭祀活动,可以引导百姓形成情感认同。孔子言:“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礼记正义》卷五十四《表记》,《十三经注疏》本,第1470页。祭祀鬼神之前,要进行斋戒。借助严谨的斋戒仪式,让参与者意识到祭祀活动的庄严。仪式感会促成大范围的情感认同,如祭祀先祖的怀念、感恩、庄重的情感体验,会强化恭敬、诚实、认真等情感认同。在现代社会中,重大典礼前的彩排,也是强化参与者的情感体验,以形成特定的情感共鸣。
其次,情感认同被反复强化,就会形成道德认同。孔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八佾》,《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4页。认为在参与祭祀之礼时,仿佛神灵就在面前,这就将祭祀时的“敬”转化为敬重、尊敬等道德认知,体现于祭祀的各个环节中。早期中国祭祀活动的普及,引导大量的参与者持续形成群体认同。在祭祀场合中,每个人都应该体现出与他人相通的情感,体现出相应的道德要求。孔子就是这一实践的典范:“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朱熹:《论语集注》卷五《乡党》,第121页。大傩是每年腊月举行的驱鬼仪式,孔子即便在旁观傩祭,也会穿上礼服,以示尊重鬼神,表明他与乡人同样庄重肃穆,有着敬重虔诚的道德认同。
再次,道德认同会促成群体共识。群体共识不仅可以作为社会规则,而且可以作为个人的行为方式。孔子言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为政》,第55页。父母在世时依礼侍奉,父母去世后依礼来安葬并遵礼祭祀。孝是普遍的情感认同,也是当时的道德共识,其作为社会的通用规则,转化为日常行为,就成为礼的形式。侍奉、安葬和祭祀中所体现的礼义是孝,具体的礼仪、礼器、礼容、礼节则是礼的形式。
周朝借助了道德认同来确定礼义,形成礼制,建构起运行顺畅的社会秩序。《周礼》载大宗伯掌管五礼,以祭天、享祖、祀地确立祭祀秩序,协调天人关系。周礼制定了各种仪式,形成等级差别序列,约束社会行为。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所用的礼器均有明确规定,祭祀时所用祭品的数量、规模、形态、质地等各有不同,建构了详细的礼制体系。由此来看,礼的形成,是通过特定的仪式来强化情感认同,转化为道德共识,确定共同的行为法则,确立为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公共秩序。
礼是早期中国祭祀活动、社会秩序和行为方式的累积、整合与发展,是社会秩序不断完善的结果。《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与子张的对话,其中谈到了夏、商、周之礼的因革关系。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认为殷礼来自于夏礼,周礼来自于殷礼,夏、商、周之礼在传承中皆有损益。损是减损,益是增加,有些减损有些增益,三代之礼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三代调整的只是礼的形式,如礼仪、礼制、礼器等,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精神则是礼义。如夏、商、周、汉、唐、宋、元、明、清都举行祭天之礼,其祭祀的地点、形式不同,但祭天之礼所体现的礼义却是一致的,期望风调雨顺,保佑天命永久,实现物阜年丰。因此,孔子意识到礼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和精神则百代不移。
周朝时,夏、商之礼之所以存在于杞、宋两国,是因为周有“存二代之后”的制度。二代为夏朝和商朝。周朝为了强调自己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就必须承认上天曾经授命于夏、商。大禹有治水之功,商汤伐夏桀而立商,上天曾授命给二人分别建立夏、商。周朝若否认天命存在,就无法证明文王受命的合法性;若周朝承认天命,就必须承认夏、商曾受命的合理性。周立国后,将夏遗民封在杞,商遗民封在宋,允许他们用天子之礼来祭祀受命之王,杞、宋分别保留了夏、商的祭祖之礼。周王室举行大朝会、大祭祀等盛大典礼,常邀请杞公、宋公作为宾客前来助祭。
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谈到了礼曾发生过多次变化,礼义却始终贯穿其中: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认为,夏、商二代的礼义可以说明。作为夏人后裔的杞人、作为商人后裔的宋人,所保留的礼仪、礼制等诸多细节,却不能详细考察。这就印证了夏、商、周三代一直延续着礼的原则和精神,其所损益的不过是礼的外在形式。形式一旦丢失,难以追寻;但有了礼义,还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形式。
总的说来,礼是经历了漫长历史进程所确定的秩序原则和行为规则。作为原则和规则,礼是抽象的道德认同和价值判断。作为明确的秩序和行为,礼体现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这就决定了礼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将原则和规则转化为可行的行为规范,施用于公共秩序。《中庸》言: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朱熹:《中庸章句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