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勒克莱齐奥作品)
¥ 15 ¥ 10.5 九五品
仅1件
上海金山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著 李焰明 袁筱一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805674063
出版时间1994
版次1
印刷时间1998
印数2千册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页数255页
定价10.5元
上书时间2016-08-01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5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 商品描述
-
【编辑推荐】:
《战争》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之力作。
文学新领域的开拓者,作品充满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欢,是对当代文明掩盖下的人性的积极探索。
——诺贝尔委员会
【内容简介】:
普通的中国读者,或许对勒·克莱齐奥并不熟悉,尽管他早已跻身法国文坛并成功地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但这份陌生,与读这本《战争》是丝毫无妨的。
1994年,勒克莱齐奥的惊世骇俗的小说《战争》第一次被翻译到中国,它理所当然地被读惯了之乎者也和马恩列斯巴尔扎克的中国人视为异端而拒之门外。《战争》的形式颠覆了中国文学。《战争》的内容让中国人从所未见。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故意对此自欺欺人似的视而不见。真理之被人接受,往往要背负沉重的代价,当然,有可能,经历久了物质的贫乏时代的中国人,无法一下子就理解反抗物质控制人并使人异化为物质的奴隶的观念。
本书以边缘世界为背景,以流浪者、儿童、逃犯等漂泊不定的边缘人物为主角。这些人物的存在,以一连串的迁徙建构起来,漂泊则是他们自由的标记。他的作品也由此反映出他对原始部落、消逝的古老文化的关注。
【作者简介】:
勒克莱齐奥(1940- )生于法国尼斯,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并获得勒诺多文学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1980年,勒克莱齐奥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1994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作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
【文摘】:
战争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又是怎样打起来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它就在人的脑袋后面,如今,它在人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正喘着气。战争,就是种种罪恶、声声诅咒,是狂怒的目光,是脑海迸发的思想。战争就在这里,展现在世界面前,使其笼罩在它设置的那张电网下。战争时刻在扩展,只要抓住什么,就将之碾为灰烬。在它看来,什么都值得一击。它有无数獠牙、利爪和尖嘴,没有人能坚持到底。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这,这就是事实的眼睛。
白昼,它的武器是光明;夜晚,它使用的是茫茫无边的寒冷和沉寂。
战争启程了,要持续一万年,比人类历史更长。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也没有任何人来谴责。我们低着头面对战争,我们的身体将成为弹靶。尖利的军刀在搜觅人的喉咙和心脏,偶尔还有肚子。沙地要饮血;残酷的山峦想在行人的脚下挖出一个个深窟;道路期望人们摔倒,不断有人身亡;大海要压碎人的气管;宇宙间,有着可怕的意念,要用虎钳将星空严严实实地钳死,让群星不再闪烁。
战争的狂风掀起,将席卷一切。滚烫的瓦斯从排气管出来,一氧化碳侵入人的五脏六腑。人们的嘴圆圆地张着,于是,一圈圈灰蓝色的烟雾从嘴里飘出,悠悠荡荡向天花板升腾。嘴唇向两边裂开,吐出一连串置人于死地的词句,让人恐惧。这就是战争风暴。
霓虹灯的光照射在年轻姑娘的脸庞上,似乎要穿透她的肌肤,烧焦她那线条柔和的面容,将她那长长的乌黑头发烫卷。
电灯泡不停地射出强光;炽热的灯丝在玻璃泡中闪亮。这就是战争的目光。它毫不留情地投射在房问的各个层面上,光影滞留在不透光的物体表膜上。
这目光,如枪管急射的火焰,飞逝而过;如炸弹爆炸,又如那城里沿街滚动的汽油弹。白色大厦,教堂,楼塔,倒坍吧!你们没有权利再立在这里。带着熟悉面纱的女人,趴下吧!你没有权利再面对陌生人。战争要人们低下头,在布满污泥和铁丝的地面上匍伏行进。女人,你裸露身体不再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而是要去挨枪弹,去接受羞辱的目光,在你的身上留下道道伤口,揭示出生命的内心隐秘。
两只眼皮之间射出的目光在闪亮,仿佛夜空里星星在闪烁,告诉人们天地间迢迢,这数十亿公里是不可逾越的。这年轻姑娘,她的名字无任何涵意,她的知觉犹如一滴水,一滴血。她不再感到孤独,不再骄傲地拒绝什么。如火如荼的战争陡然火光冲天,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一切。这样的情形下,谁还会感到寂寞呢?当你的心里,你的周围,一切时刻都在说“是”的时候,你怎能说“不”,甚至这样写呢!
因此,这发生的一切全都要退到第三人称来。再也没有“我”的位置。目击者已被驱走,只剩下了当事者。这些人的眼睛不再是两只,腿不再是两条,乳头也不再是对称的两个。他们的脑壳里涌现不出清晰的图像,丧失了叙述、分析的功能。数字,不计其数,像雨点从空中筛落下来,敲打着地面。词语不愿复说同一事物。记不起该用什么单词。也许人们仍在写信,也许……诗人正伏案走笔,然而不过是些风流轶事。咖啡馆里,空气沉闷,回响着颤悠悠的歌声、吉它声和一个女人数落着爱的词眼的声音。是的,也许……但这无关紧要。这并不说明什么。它们不过是众多喧嚣声中那巨大的振动器发出的音响。而我们现在要说的,是那天众人的真实情况。不再有灵魂,不再有孤立无援的感觉。再也没有与其细微的线性图案相一致的思维。世上不复有任何东西。
于是,一切都蜂涌而至。像一群耗子,成群结队向前进发,结成一个战线,撞击城墙,又仿佛像那海浪,形成成千上万条波浪,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压倒一切。所有的词语,所有的肌肉,所有拥有生命的触角都会加快步伐,在探索,在开辟一条道路。谁会去谈及这一切呢?最终理解万众之路的又是谁呢?它就是路。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恐怕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要确切弄清此事,已为时太晚。战争在灰蒙蒙的平原上展开,弥漫整个空间。战争是一种疾病,切断了人的隔膜组织,于是淋巴液流淌。它选择了人类生存的环境而进行。它冲破堤坝。它在这世界上插置了一把制造痛苦的尖钻——人的神经系统的一根神经。它从千百万姑娘中选定了一位年轻姑娘的躯体。但显然,战争总是战争,它存在于人的思想之外。它无处不在:夜晚的梦魇中有它,阳光下的急行中有它,爱情,仇恨和报复中也有它。它只是刚刚开始。
战争既不是一个小插曲,也不是一个大事件。战争就是战争。
它写在墙纸上,画在花草和建筑物的圆花窗上;它刻印在玻璃上;它漂浮在水面上;它燃映在萤萤的火柴光中;它记载进每一粒沙尘里。
战争无意取胜也无需取胜。它不再是人们之间的争吵和赛跑,非争个输赢,它也不是但泽长廊或第十七战壕这些兵家常争之地。这一切似烟过云散。然而如果那些死去的人们不是战死于疆场的话,是纯属偶然,因为一颗子弹“嗖”的划空而过,正从他们的咽喉或肺部穿越。人的眼睛预见了死亡,铁弹头在死亡上钻了个洞,然而这两者之间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它经历了这些。它是彻头彻尾的死亡。
重机枪、毛瑟枪、弩、弹丸吹管及斧头毫无目标地乱击一气,其实已无杀伤力。它们只是一些武器而已。但我跟你说的这战争,是有的放矢进行摧毁的。它的武器装备齐全。它的罪恶接连不断。
战争善于乔装打扮。忽而火红一片,忽又如海上落日的色彩。它步履轻柔,头发若海藻般碧绿。战争具有生命,它是现实,是未来!为什么有一天世界定要宣露战争的隐秘呢?
它不在一个姑娘的灵魂里。如果是的话,一切都简单了。像医生拔牙,把她的灵魂根除,那么一切又将重复正常。如果这是在一个姑娘的眼中发生的,我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挖去她的双眼,代之以两颗葡萄。不,它不在任何人的眼中。它在人的目光之外,人的灵魂之外。这不是一根神经在受痛苦的煎熬。它在神经以外。做你愿做的人,说你想说的话: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改变。闭上你的双眼,去作几首小诗,去拍女人的胸照,去亲吻那笑意漾然的嘴唇。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和平安宁。
那么怎么说呢?说透了,必须轰炸,使世界残垣断壁。必须使用这些词语,它们闪电般从天边急驰而来,一路扫荡;它们如岩浆喷涌而出,在空中呼啸,在地面挖出一个个沸腾的巨大火山口。
必须摆脱自我,必须这样。必须深入自己的内心,直到面目全非,直到一切重新得到创造。
事情就这样姗姗而来,出现在世界上。比如,就像飞来一只只圆圈,环链相继落到地上。宇宙中某处一条巨蛇正盘绕着猎物,静静的躯体不停地向外抛着圆圈。一旦窥见一块还没有让人宰割的肉体,便抛出套圈把它缠住,死不放松。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一条蛇不会有如此大的力量。为了生存而战要简单得多。而这更为隐秘,既无头也无身。圆套产生于事物内部。任何事物都能制造出圆套。它们在灰尘周围泛游,向四处分散,使物质微微振动。这连续不断的振动使得原有一切固定的,静止不变的事物遭到破坏。意愿不是外部产生的,危险也不是外来的。是恐惧振动了世界,搅乱了真实情景。这里安全再也不存在。快垒起石块,矗立起花岗石纪念碑,快!快!否则就为时太晚了。恐惧需要岩石和高山。正因为如此,人类建造了众多的金字塔和教堂。数世纪以来,人类顽强抵抗,以免世界变成一片汪洋。
死亡本是无所谓的。可是变成水……尔后,水向四周扩散,冲破人体层层隔膜,再变成汽体。这正是人们惊恐的原因所在。当河流纵横交错,沙漠和沥青之漠便是人的精神归宿。
城市上空,乌云就要撕裂,可谁都不想逃离。某一天,我们来到了这世上,我们看见了太阳,我们预见了干旱,我们便也从未准备足够的荒漠和地道来藏身。
口腔中,舌头与唾液相抵触。说话是牙齿与硬腭、紧绷的嘴唇在相互作用。涎腺分泌出唾液,话语便像泡沫一般穿透唾沫。偶尔,有一个士兵被枪弹击穿肺部,跪倒在地,于是,一股鲜红的唾液顺着咽喉冒上来,溢满整个嘴。那本该是说:“救命!救救我!来,快来!”可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发出的类似这样的咕噜声:“啊啊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啊啊!”
太阳的文明行将终止。它们无法持续下去。所有石堆、庙宇、楼梯都阻挡不住奔涌而来的洪水。石头变脆,趋于风化成灰。山高再也高不过云彩。眼睛不是闪烁的星星,它们是熄灭的灯。思想也不像那光线直射向前,它是啐出的唾沫,四处喷散。
这由来已久的孤独,把你抛向宇宙的尽头,使你保持缄默——沉浸在这无声的寂寥中全身感到快乐无穷——怎么再相信这些呢?当一切都成为语言,便是说不再有悟解的希望。孤独一人,就是试图清明事理。而和众人一同置身于巨大的旋流中,那里急流迅猛而下,冲毁河岸,像这样,就不是明理。这是在痛苦地承受极大的惊惧。
“我是。”
“我要。”
“我……我爱。”
“我,我,我我,给我,我的,我的东西,我的,我,我,我,我!”
所有这些话语,所有这一切往事悠悠的回忆:这些涂抹着阴暗神秘色彩的照片,这些画在笺尾的图画,这些诗——当“我”眺望大海,当“我”举目凝视凌空的群鸟,当“我”依偎在女人旁倾听她的心跳或当“我”面对死亡所作的诗。这一切全是欺骗,全是谎言,是墨镜!全是为了不去目睹战争来临。这是为了忘却兵匪的长统皮靴那越来越响的橐橐声,而当他们来时,佯装不在那里!
世界什么也没忘记。它要报复。它从远古赶来屠杀。它将猛地打断人们的一切旧梦和所有赞美歌。它要割断喉咙来结束单调的咏唱。它的思想将与血同迸。
它刮起落下的一圈圈烟雾。于是黑影渐渐扩展。
喊叫有何用呢?你尽可以声嘶力竭地嚎叫,痛哭流涕,世界接收你的呼叫声并将其变为各种声音!巨响声、哀叹声、爆裂声、撞击声、轰隆声以及鸽子的咕咕声,狼的怒吼声,母鸡的咯咯叫声,鸟儿喳喳的啼声。人们的歌声和咚咚的鼓声。听吧,这巨大的嘈杂声!你永远也难以摆脱。
孤零零的,只身一人。永远像这样存在。这就是和平。而如今,头颅打开了,灵魂从里面出来。它在宇宙中漫游,隐失在海面。出于习惯,或者出于怯懦,或者别的原因,灵魂留下残余,这些嘟嚷低语声,这些签名。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她的。有时,人们自以为无所不有,其实早已掉进了公共墓穴。人有嘴是为了占有,有眼睛是想征服。人们用脚度量世界。怎能忘记这一切呢?难道就没有一小块土地留着你的名字?难道就没有一个梦幻,一阵和风,一缕阳光是属于你的?
一切都属于众人。任何都不属于个人。一切就是人。哦,目光,恢复力量吧!重新征服世界!世界永远依然如故。每当水龙头滴出一滴水,就意味着人们可以从那众多的无名事物中攫取某样东西。每当一个生命诞生,就是说一幢房子造好了,老鼠将驱逐房屋的主人。
一支大军在前进,践踏田野,摧毁桥梁,一路抢劫,一路侵犯,将一切全都碾碎。这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没有思想,没有行动!
它是从哪里来的?也许从人的头脑,仅仅是从头脑中出来,竭尽摧毁之能事?也许人对人有着本能的仇恨,树对树也有本能的仇恨?万物存在都是为了毁灭、憎恨。从来没有爱、没有安全。有的只是这支凶残的部队,他们呆滞的眼神在空处游移。没有娱乐。只有取胜的需要,天天如此。
灾难最终降临。从谈论它的那时起,人们就开始预料到了。直到发生的这一天,它还是无足轻重的,它有自己的英雄和审判官,它有自己的边界。它出现在地球上,几乎是偶然的。它像雷雨爆发,伴随着聚光、闪电和雷鸣。紧接着是一片宁静。今天,人们终于知道灾难为何物:它不再是各种因素互促成的结果,也不再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无穷大的外在物。
灾难,战争,就是设想外部世界。然后,想出了一个外部世界,再打开内心世界的大门,轻物质便逃遁出,汇入密集的海洋。那天,当年轻姑娘说:“我毫无意义”时,恐惧就开始了,她说这话也许是为了笑笑而已,或者只是因为此刻这已既成事实。
于是,宣告自由的声音接踵而至: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孩子。”
“我不再相信什么。”
“你不存在。”
世界并没有如姑娘想象的那样彻底毁灭。一切依然如故:汽车继续在柏油道上行驶,人们仍然存活着,飞机一如既往在天空飞行。然而,可怕的是,有什么东西消亡了,离开了人体的中枢。这是肉眼看不见的。人们弄不清它到底是什么,但确实是一样东西。每一物体的中心都有一个洞,现在,它的出口虽然很窄,但里面比岩洞还宽阔,类似女人的肚腹。
战争就是在这些窟窿里产生的。每一物体都是一个茫茫无边的子宫,这子宫又存在于那更为广大的世界子宫里。
每个肚子都在生产。战争,甚至就是出生证。
世界正在产生,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在人类周围,在姑娘身旁,世界正使出浑身解数在分娩。姑娘看到阵阵痉挛穿过天窄和大地。其中一部分打着寒战,瑟瑟地从她体内透过。世界要彻底冲出。它痛苦地向着出口,向着亮光蠕动。对于人类这样的环节动物来说,这难道不可怕吗?
某天,谈了话。说了很多话,写下了它的自由。后来,又一天,最伟大的自由来到了。它不在乎说的什么,只为了获得解脱而全力抗争:孩子出世时将一口吞下胎盘里的羊水。
年轻姑娘不要这孩子。她想在他出世前毒死他。人们怎能接受一个将杀死自己母亲的儿子呢?
不再有知觉。眼睛不再来回转动。它只是疯狂地向井底,向天边扫射。世界循环往复,人们永远碰不到墙壁。要想有反弹力,得撞击那最后一道城墙。那曾使我们的灵魂完成它的环程旅行的那道城墙。现在,人们明白了,这种漫游是没有终点的。认识到了这种狂热的限度并且找到了它,那么所谓的知道又意味着什么呢?微小的事物在脚下飞过,躲藏起来。虚无甚至不愿被人发现。深坑陡然变得平坦,这就是它成为深不可测的最佳方式。
要想认识事物,必须触摸到物体。谁曾触摸过它们?那么要了解自己,当然得碰触自己这个物体。而宇宙万物,你们是碰触不到它们的,这就是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
人人都失去了面孔。
然而,我跟你说的这年轻姑娘有一张面孔。大约是这般模样:仿佛面具似的脸,皮肤白皙,细嫩,两颊、下巴及鼻翼点缀着红斑点。鬓脚有几根青筋,眼角及额头零星布着些鱼尾纹,两三粒痣和百十来个雀斑。
这是一张黯然无光的脸,轮廓稍突;一张石头脸,因长期被流水冲浸而变得滑润。它朝前挺着,于是风从她的头旁擦过,分向鼻冀两旁,掠过面颊。
她的脸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是她把它塑造成这样,也许是用她的双手,也许是用她的思想。这样塑造,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光亮,为了穿透雨水,为了越过空气层。她在脸正中装了个金字塔形的器官并钻了两个孔,这样,冷气便可长驱直人体内,并且在通过毛茸茸的鼻孔时,清除杂质,增热并保持温度。
鼻子下面有一条小槽,鼻涕大概就是从这条细流中流出来的。
接下来是嘴唇,这是两片略带紫色并布满细细皱纹和小裂痕的软垫。外部世界正是通过那里顺着咽喉下滑,浸湿细胞,侵入体内,并伸展出数千个触角来冲刷身体。当嘴唇向两旁咧开,对神秘的气味张开口腔,世界便毫不迟疑地溜进来。正因为如此,年轻姑娘在脸的下端开了这扇门。这里曾是反抗沉默的第一场所。头不再是石头,不再穿行于茫茫黑夜。气流潜入,裹挟着无休止的喧嚣声和各种各样的声音。
我也想说说眼睛。年轻姑娘设想了一个光灿灿的世界,她向往那阳光下耀眼迷人的景色,那深沉的夜,那一切美好的事物。于是她在脸上构画了两种花案,这两个蓝色的洞孔立即熠熠发光,光线从那里摇曳着进入。她在这两个光芒四射的洞孔旁嵌上浓黑黑的仿佛沾满沥青的睫毛瓣,它们微微跳动,瞳孔一翕一张。眼睛是脸部涌动生命力的物体。知觉正是从那里出来。也正是它们使得这世界顿时变得广阔无边。
眼睛注视着。世界就在眼前。
当年轻姑娘在她的脸上画出这两幅新奇的画时,她就明白从此之后任何东西都不再一样了。正因为如此,她每天早晨都端坐在镜前,用细小的毛刷和一管管黑颜料,完成重新塑造眼睛的仪式。
这些做完,脸也就装饰完毕。只须在头上钻两个洞用来听声音,在头皮上种植数千根头发以免脑袋裂开,脑物质飞散到空中。
接着,脸消失了。面部线条相继隐退,极其自然。鼻子不再迎风挺立,金属脸上光泽殆尽。眼睛流着泪,泪水和着眼睫膏抹脏了面颊,弯弯的眉毛不见了。嘴先闭了起来,双唇紧抿着;伤口愈合了,最后仅留下一个痕迹,几乎看不见,就像一道紫色刀痕,罩着一层白皙的肌肤。
生命的一切细微标记都一一消失了:皮疣、汗毛、头发、酒窝、皱纹、耳肉坠、肌腱、血管。
这是一幢楼,人们就这样用铁锤和炸药摧毁了它。这高大别致的楼房正面倒塌了,任凭尘埃满天飞扬,成群蟑螂四处乱窜。窗顷刻间像是假的,高悬在空中,开得很大,人们根本看不见它们。终于,在最后的一次震动中,它们也掉下来,像枯叶铺盖地面,于是人们明白,从此不再有房屋了。
荒凉的城里,男男女女都躲藏起来了,突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一座火山在城市中心张开大口,在空中耸立起无色的火柱。街石板高高飞起又落下,砸碎了房顶。窗户炸开,地板在脚下晃动,门楣被突来的重力压断。爆炸声传来,横扫地上的一切,这旋风般的声音像巨影在城市上空飞越,直朝姑娘扑来,要把她湮没,使之化为灰烬。
往哪里藏身?哪里?世上是否还有一个爆炸声传不到的地方?是否有一个清澈、寒冷的湖,一个位于山顶、平静如镜的湖,一个人们可以跳进去洗个澡的静谧的湖?
是否有这样一个海滩:一个长长的、空旷的、被阳光烤得灼热的海滩,那里,大海日夜不息翻腾着,一群苍蝇正围着一堆海藻嗡嗡叫着?
是否有这样一条路:一条柏油路,它无视左右发生什么事,直通到姑娘面前,它猛地在天边钻个洞,在空中开出一条裂缝,远景的轮廓渐渐逝去,最后将从这里逃离?
是否有……这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否有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争,名叫Bea(贝娅),或者Eva(夏娃),或者Djemia(吉米娅)的年轻姑娘?一个没有用她的身体、用她柔嫩的面容和泪汪汪的眼睛,用她的嘴和牙齿,用她的头发去制造战争的姑娘?一个没被猎人捕获、从未打过猎的姑娘?到处是窥视的目光,插出城墙枪眼的密密匝匝的标枪。到处是坦克铁甲、大炮防护板、炮弹起爆管、炮架尾、机关枪枪管。
当杀声响成一片时,她逃了。她赤脚跑过断壁残垣的荒漠。布满灰尘的地面上,陷阱正疯狂地张着口,发出吸吮的怪声。年轻姑娘跳着、滑着,时而走着之字形,时而独脚走,避开陷阱。她朝一个圆形的山走去,这是一个石头、烂泥堆成的小山丘,俯视着平原。她朝它奔跑着,因为她明白这是她唯一的机会。就在快到达时,她摔倒了。她疼痛万分,叫不出声来。她像一只痛苦不堪、惊恐万状的疯狗在满是灰尘的地上乱啃。她趴倒在地上,前臂撞在一块燧石上。血流出来了,和这血一道流的是生命。她很快分崩离析了。她的肉体、骨骼、思想在这荒野消逝了。既美妙又可怕的死亡来临了,渐渐减轻她的痛苦。她变得轻盈。她飘了起来。她醉了。
或者,某个夜晚,比如一月十日,她梦见自己身体向左,侧躺在床垫上。一个无头的身影在房间里站立起来,缓慢走着。她看不见它,但她知道它:白晃晃的尖刀在黑暗中向前移动着,昏暗的屋子中间射着一道横光。过了很长时间,刀刃刺进了年轻姑娘的背里,正好在两肩胛骨中间,并直戳到心脏。刀尖触到了心脏,在上面戳了一个洞,把它撕裂,像切一只西红柿一样把它切开。于是,她感到有一股热流在体内散开,沸腾着。她高兴得昏了过去。
或者还有,五月十二日,年轻姑娘梦见自己上吊自尽了。
八月十九日,她摔倒了。
八月二十日,她溺死在一个水池里。
十二月四日,两条带斑点的大狗把她吞吃了。
可究竟怎样呢?您不明白吗?这些怪物、这些减叫、这些声音,您从未听说过!您的战争只不过是想象罢了!梦,这很好解释。这可恶的东西,就在这里,在您身旁:幽灵!幽灵!从大海露出的面容,轻雾!现在,就靠在这里吧。一切将过去……盯着这些怪物吧。用您那没有眼皮的目光杀死它们。什么也阻挡不住阳光。恐惧、嘈杂声:这一切狂怒只是内心的。您看这世界多安宁。什么也没发生!大地从未像现在这般宁静。落日从未像现在这样死气沉沉。您的那些深坑、海渊是水洼、鼹鼠洞!
您在哪里听见了叫喊声?像往常一样,除了寂静,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单调、冷漠、令人麻木的沉寂。您的眼睛在看哪里?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确实是真的。只有几个蓝色的球深嵌在眼皮的角膜翳里。一切都在您身上,您的身上!
没有什么可制造麻烦的,肯定是这样。一束束花、一团团焰火!可是年复一年的节日,只持续几分钟!汽车在规定的车道里行驶吗?它们停下了,它们将停下!说话的声音:对您的耳朵来说是一些嗡嗡的嘈杂声!不必害怕。世界的画面从未这般清晰,黑白从未这般分明。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箕雅校注[精装全二册]](https://www0.kfzimg.com/G06/M00/50/24/p4YBAFqkyvGAZVExAABG4d_IyGU168_s.jpg)
![观堂集林(附别集)[全二册]](https://www0.kfzimg.com/G06/M00/C4/64/p4YBAFqYGZCABfhiAABoH6kv4Ew094_s.jpg)
](https://www0.kfzimg.com/G06/M00/EC/F1/p4YBAFqZHtGAAnTjAADIZx0_1m0949_s.jpg)
](https://www0.kfzimg.com/G06/M00/8B/63/p4YBAFqmqmuAc6B5AAC1O7o_lXc186_s.jpg)
](https://www0.kfzimg.com/G06/M00/19/9D/p4YBAFqaN72AIpFkAADYoTOx1qc484_s.jpg)
](https://www0.kfzimg.com/G06/M00/19/A9/p4YBAFqaN-mAWbwSAADw8g96ZE0019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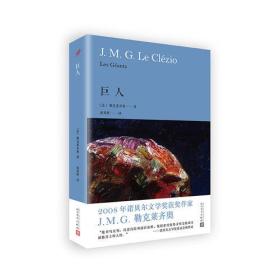
![战争 [法] 勒克莱齐奥 著](https://www0.kfzimg.com/sw/kfzimg/3394/02e859c6baa5a62ddc_s.jpg)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