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战太平洋之瓜岛浴血记
正版图书保证 可开电子发票
¥ 20.1 4.4折 ¥ 46 全新
库存4件
湖北武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美) 罗伯特·莱基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79487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46元
货号3466304
上书时间2024-06-24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21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本书从亲历者的视角,真实还原了太平洋战争的诸多场景与细节。与全局视角不同,全书以个人回忆为基础,特色在于对人物内心的描写和挖掘,以及对战争的反思。作者身为太平洋战场上幸存下来的前线战士,同时也有着良好的智识水平:入伍前曾在纽约大学就读,退伍后发展成战争史学者,这就保证了作品不只是简单的记录,更与反思和升华相结合。
根据史料记述战争是惯例,军官们从个人角度描述战争也属常见,但普通的海军陆战队员将个人对战争的印象付诸文字是罕见的,因而珍贵。作为Di一手材料,本书是重访历史的起点,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文献。
作者简介
罗伯特•莱基(19202001) 太平洋战争亲历者,美国有名作家、战争历史学家,美国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生于费城一个天主教家庭,曾入读纽约大学。1942年1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应征入伍,加入海军陆战队,担任重型机枪手。获海军陆战队嘉奖奖章、紫心勋章、总统集体嘉奖、亚太战功奖章、二战胜利奖章。另著有《武装的强人:抗击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太平洋的挑战:作为转折点的瓜岛》《冲绳:二战的zui后一役》等与二战和海军陆战队相关的作品。
目录
自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上的新兵训练始, 作者罗伯特·莱基经历了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几场战役, 历经艰险, 九死一生。战争之惨烈与残酷深刻地影响了莱基。受伤退役后, 莱基决定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真实还原太平洋战争, 于是写下了这本书, 后成为2010年美国HBO迷你战争剧《血战太平洋》的拍摄蓝本之一。莱基讲述了自己在海军陆战队Di一师服役的经历, 以及瓜岛之战、新不列颠之战、贝里琉之战等几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身为枪林弹雨的亲历者。
内容摘要
自南卡罗来纳州帕里斯岛上的新兵训练始,作者罗伯特·莱基经历了太平洋战争中很为惨烈的几场战役,历经艰险,九死一生。战争之惨烈与残酷深刻地影响了莱基。受伤退役后,莱基决定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真实还原太平洋战争,于是写下了这本书,后成为2010年美国HBO迷你战争剧《血战太平洋》的拍摄蓝本之一。莱基讲述了自己在海军陆战队一师服役的经历,以及瓜岛之战、新不列颠之战、贝里琉之战等几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身为枪林弹雨的亲历者,作者的描述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无比真实。其中关于战争的内容少见视死如归的冲锋陷阵,多的是对敌我双方阵亡士兵的同等悲悯,以及作为纯粹的人的士兵在战争中真切的迷惘与恐惧。
精彩内容
第七章第三节
贝里琉岛已经成为屠宰场。
该岛地势平平,几乎毫无特色可言,但它却注定要成为一万七千人的祭坛。
陆军和海军的飞机已经对它进行了轮番轰炸,而在我们到达之前一大批海军巡洋舰和军舰也连续几天对它狂轰滥炸。这座环状珊瑚岛只有五英里长,zui宽处也不过两英里宽,完全笼罩在弥漫的硝烟之中。岛上火光冲天,远远望去就如同一团粉红色的云团,间或随着雷鸣般的爆炸声它还会像霓虹灯一样闪烁摇曳。
在距离海岸还有半英里的地方我们的登陆舰就吐出了水陆两用军车。我们就像火星人丑陋的孩子一样随着军车从登陆舰的肚子里滚出来,立刻感受到了轰炸声中的咆哮声、爆炸声、咝咝声以及噼啪声所带来的冲击,在我们看来,这些声音简直就是这个小岛的丧钟。身后是我们的巨大战舰,前面则是我们的敌人。头顶上所有的战机都是我们的,此刻我们的信心空前高涨。极度的兴奋占据着我的内心,竟然忘记了死亡的恐惧,我匆匆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征服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海军军舰发射的炮弹从我们头顶嗖嗖掠过,朝着小岛的方向飞去。我们之中那些曾经历瓜岛之战的人对海军轰炸之残酷记忆犹新—不过谢天谢地,现在遭到轰炸的是我们的敌人。小巧的火箭船以及驱逐舰正在向岸边靠近,动作优雅如同纯种马。当火箭船突然接二连三地发射火箭时,耳边传来了可怕的轰鸣声,就像把红彤彤的滚烫烙铁放进水里一样,而火箭船上方则黑烟滚滚。
此时巨大的声响正在减弱,岛上的火势也正在消散。欣喜之余我转身看了我们的登陆舰zui后一眼,只见登陆舰舰首黑压压一片挤满了挥手示意让我们前进的水兵,他们朝着贝里琉岛方向挥动着紧握的双拳,似乎是前来观看角斗士搏斗的看客。
猛然间一阵寂静。
接着我方水陆两用军车的马达轰鸣起来,我们乘军车向浓烟滚滚的岛上逼近。
我的头必须露在外面,因为我选择了自己操纵机枪。山地人坐在旁边的一辆水陆两用军车上,和我一样脑袋露在外面。看到了我,他一边笑着一边朝着小岛的方向点着头。我从他的笑容里读懂了他的意思,于是举起手向他打了个OK手势。
“小菜一碟。”我在风声和嘈杂声中向他喊道。
山地人再次冲我笑了笑,也向我回了个手势。就在此时,我们的军车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接着传来熄火的声音。海水开始像间歇性喷泉一般涌了上去,空气中开始充斥着被炸碎的钢片。
敌人正在回敬我们,他们用迫击炮和大炮迎接我们。贝里琉岛上一万名日军正在严阵以待,他们和自有人类战争以来任何一支守备部队一样勇敢、果断和熟练。是的,他们的防卫技术很熟练:炮弹雨点一般落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上岸之前非常有效地压制了我们。
在他们的Di一轮轰炸过程中,山地人和我都像鸭子一样躲在车厢里。我不敢把头抬起来,直到我们离岸边只有一百英尺的时候。
尽管我们的水陆两用军车处在Di一波攻击队伍之中,但是海岸上已经散落着被烧成黑色的军车、阵亡士兵的尸体以及受伤的士兵,此外还有迫击炮的炸弹。海滩上到处都是浅坑,这些浅坑或者是在白沙土上挖出来的,或者是炸弹炸出来的,全部挤满了戴着绿色头盔的海军陆战队员。
我们的军车动弹不得。
我和六连的“宽胸膛”中尉一起翻身跳出了军车,恶心人佛瑞德和温顺的“双胞胎”以及我本人都归宽胸膛中尉指挥。我躲在军车旁边,匆匆忙忙为自己挖一个浅坑作为掩体。一枚炸弹落在我身后,炸飞了一名陆战队员的高帮热带靴子。这名陆战队员和我在新不列颠之役中并肩战斗过,在那次战役中,当日本兵从我身后冲上来时,他从我头顶上向他们开火。所幸他没有被这枚炸弹炸死,不过他不得不退出了战场。
宽胸膛中尉试图向我说着什么,但是我听不清楚,于是示意他写下来。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事。正在此时,一名陆战队员跌跌撞撞地翻过我面前的一个沙丘来到我旁边,他的脸由于恐惧而变了形,一只手紧握着另外一只手,只见那只手食指的手指头已被打掉—剩下的部分汩汩地冒着鲜红的血液,像一支罗马蜡烛。他是一名下士,在瓜岛的特纳鲁河之役中得罪了笑面虎,原因是他把我们的机枪弄到了泥巴里。此刻,在那张充满恐惧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惊奇和轻松。
不单单是敌人的迫击炮压制着我们向前移动。从一座易守难攻的碉堡里射出来的机枪火力同样也阻止了我们,碉堡位于珊瑚礁上,居高临下俯视着海滩,日本兵从那里不停地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缺口,于是用各种轻武器一齐朝它开火:手榴弹、由爬过去靠近它的陆战队员扔过去的炸药包,以及由架在附近坑里的火焰喷射器喷射出的滚滚火焰,但是碉堡里的敌人依然用机枪向我们扫射着。
此时我审视了一下我们的处境,发现海滩后面是一排灌木丛,再往后就是我们要和日本人争夺的小飞机场以及日本人的主要军事要塞(我们后来把这个要塞称为血鼻岭)。我看到一只黄色蝴蝶在灌木丛里横冲直撞,看到一个东西在灌木丛里向前移动,上面的三角旗随之舞动着—原来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一辆坦克。突然出现了片刻的安静,接着当坦克轰隆隆地开到压制我们的碉堡对面时,我听到了一阵欢呼声。我们的坦克开始向碉堡口连续开炮,坦克上面的机枪也对着碉堡口不停地扫射—可是碉堡里的日本人依然顽强抵抗。
接着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碉堡口突然出现了一个日本兵的身影,他很快就跳了下去不见了,紧接着日本兵一个接一个地陆续从碉堡口跳了下去。每在碉堡口出现一个日本兵身影,我们就用轻武器噼里啪啦疯狂向他射击。其实射击效果和打兔子一样,因为他们像兔子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快速出现在洞口,然后又像兔子一样快速地消失,就好像他们的堡垒是个养兔场—事实上确实如此,因为日本人已经在那里驻扎了二十年,已经把这个珊瑚岛筑成了一个相互贯通的洞穴网络。当一个日本兵跳下去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向另外一个阵地转移—也许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
在所有逃走的抵抗者中只有一名日本兵被击毙。他肥硕笨重,再加上裤兜里塞满了大米(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在瓜岛上被鳄鱼吃掉的那个贪吃的日本人),动作缓慢之下就被我们的子弹击中了,血肉模糊,大米撒了一地。
天气炎热。热浪透过白沙子传到了我们的衣服里。这种酷热就和蒸汽房里的闷热一样让人倦怠。汗水渗进了嘴里,加重了我们的焦渴。水罐里的饮用水也是热的,一饮而尽之后,我把弹坑里的脏雨水装进水罐里。贝里琉岛上没有饮用水。日本人用露天蓄水池存储饮用水,我们的饮用水则是装在汽油桶里,而一些愚蠢的军需官竟然忘记了把油桶中的油渍清洗干净,这使得水闻起来有股汽油味,尝起来也有股汽油味,根本没法喝。黄铜色的太阳照射在我们身上,一俟敌人的要塞安静下来,我们即刻站起身来穿越灌木丛向机场方向进发。
我们来到了灌木丛的边缘地带,再往前就是飞机跑道,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弹坑。我们在弹坑里占好适当位置。也是在这里我遇到了艺术家。
“自由人死了,”他告诉我,“一发迫击炮弹击中了他和‘士兵’。”“士兵怎么样了?他现在如何?”“腿被弹片撕开了一个口子,伤势相当严重。不过现在没事了,”艺术家笑了,“总之,比我们强—他现在退出战斗了。” “是的,不过,自由者就太可惜了。他是个好人。”“弹片击中了他的腹部。我离开海滩时看到他靠在一棵树上坐着,还在笑。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自己没问题。可是他坐在那里还是死了。”艺术家无奈地摇了摇头走了。自由者死了实在是可惜:他受的良好教育消失了,他那张淡黄色的率真的脸上透露出的幽默消失了,他理想中关于社会主义蓝图的所有美好愿望消失了—一切的一切都消失了,生命如同脆弱容器里的水随着不可知的裂缝消失了,而那个靠树而坐的男人微笑着抽着烟,确信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确信自己的伤口也只是暂时的小碍,因此他在思考着未来的人生。然而他就这样和我们永别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我们暂停了进攻,继续待在弹坑里,我们的伤亡太严重了。防御者意志坚定也足智多谋。海军陆战队员们开始在机场跑道上挖掘散兵坑。中午时分,我想吃点东西。背包里有部队发的豌豆罐头,但是我一口都咽不下去。我没在贝里琉岛上吃一口饭。
敌人的坦克突然朝我们猛扑过来,有十二三辆。它们快速穿过机场,径直朝我们开来。这太让人震惊了,要知道我们这里只有步兵和机枪。一阵猛烈的枪声响了起来。我把头探出弹坑外,透过灌木的枝叶,我看到一辆敌军坦克正在快速前行,后面有几个身穿伪装服的狙击手紧紧地抓着坦克。仅仅这一瞥我还看见六连的一位老兵向坦克后面跑去,他的脸都变了形,边跑边喊:“坦克!坦克!”一位军官冲上去抓住他,把他按倒在地,用脚踢他的屁股,zui后把他赶回了他原本的位置上。在弹坑里,我们准备拼死抵抗,如同沙漠中的大篷车抵抗印第安人的攻击一样。敌军坦克疾驶而过,轮子在履带里飞速旋转。机枪声响成一片,反坦克火箭筒重重地射向坦克—我们的战机从天而降,投下的炸弹吼叫起来,于是坦克的爆炸声随即轰鸣。
有一次鱼雷轰炸机从身边一闪而过,它飞得太低,肚子几乎都要刮到岛上的珊瑚了。在右方,我看到我军的一队坦克开了过来,边行驶边开火,每次开火时似乎都要停顿一下。战斗很快结束了。
日本坦克被摧毁了。
我站起身来,向机场方向走去。大约二十码开外的地方有一辆坦克还在燃烧。一些敌人的尸体还在坦克里面。狙击手耷拉着脑袋挂在坦克上,就如同塞在圣诞袜里的洋娃娃。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差点踩上一只人手。我赶紧说了一声“对不起”,但是定睛一看,原来那是一只断手,或者说是一只脱离了人身体的手。它静静地躺在那儿—五指张开,手心朝上,干净,能干,孤苦伶仃。我无法把目光从那只手上移开。手是心灵的工匠,它在三位一体—脑、手和心—的人身上位列第二。一个人身上,zui具人性的是手,zui美丽的是手,zui具表达力的是手,zui具生产力的还是手。而那只手孤独地躺着,仿佛被遗弃了一般,不再是某人身体的一部分,不再是他的助手,看到那只手就看到了战争的野蛮和荒唐,看到那只手就看到了我们自己创造的车裂术的残暴,看到那只手就看到了人类被永恒的恶所驱使而势不两立相互厮杀,zui后在傲慢的狂怒中撕扯着自己的内脏。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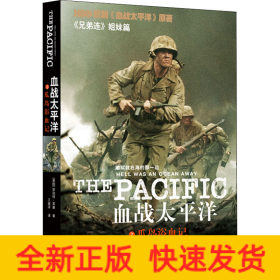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