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千万人的密室
正版图书保证 可开电子发票
¥ 35.4 6.1折 ¥ 58 全新
库存16件
作者蔡骏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21671
出版时间202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4329806
上书时间2024-04-2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商品简介
《一千万人的密室》 著名作家蔡骏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
《一千万人的密室》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一起迷雾重重的密室谋杀案。要从一千万人的密室里找到凶手,只有一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小说既有凶手设置的精妙诡计,亦有主角超乎常人的推理能力,以及刑警强大的破案意志。父子情、母子情、父女情……彼此深刻的救赎,长达十五年矛盾心结的化解。
《一千万人的密室》经典悬疑推理结构,连续三桩杀人案,环环相扣,层层剥茧。每个人都可能是罪恶的帮凶,每个人也都有机会偿还正义……
《一千万人的密室》“调查员”雷雨,有公安大学刑侦专业高材生的背景,与警方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关系。作为“杀人犯的儿子”,内心充满矛盾。雷雨是条硬汉,玩世不恭,毒舌,实则内心柔软,嫉恶如仇,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既有菩萨心肠,也有雷霆手段。可以帮助好人,也足以震慑恶人。实为当今中国本土悬疑作品中罕见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蔡骏,作家、编剧。已出版《春夜》《无尽之夏》《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最漫长的那一夜》《天机》等三十余部作品,累计发行1400万册。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山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曾获茅盾新人奖、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作品被翻译为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十余个语种。数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目录
本书是畅销书作家蔡骏最新长篇力作, 小说二十多万字, “本格”、“硬汉”、“社会派”三大流派融会贯通之作。雨夜, 调查员雷雨被神秘贵妇人洪姐雇佣寻找失踪了一天的儿子钱奎, 却意外发生车祸, 之后在杀人疑案的漩涡中越卷越深。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超大密室, 凶手插翅难飞。但要从一千万人的密室里, 找到这一个凶手, 只有一千万分之一的机会。直到凶手落网, 埋藏在令雷雨心动的李雪贝身上长达十五年的秘密终于水落石出。破解谜团, 令人震惊和悲伤的真相, 然而雷雨发现。
内容摘要
《一千万人的密室》 著名作家蔡骏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一千万人的密室》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一起迷雾重重的密室谋杀案。要从一千万人的密室里找到凶手,只有一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小说既有凶手设置的精妙诡计,亦有主角超乎常人的推理能力,以及刑警强大的破案意志。父子情、母子情、父女情……彼此深刻的救赎,长达十五年矛盾心结的化解。《一千万人的密室》经典悬疑推理结构,连续三桩杀人案,环环相扣,层层剥茧。每个人都可能是罪恶的帮凶,每个人也都有机会偿还正义……《一千万人的密室》“调查员”雷雨,有公安大学刑侦专业高材生的背景,与警方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关系。作为“杀人犯的儿子”,内心充满矛盾。雷雨是条硬汉,玩世不恭,毒舌,实则内心柔软,嫉恶如仇,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既有菩萨心肠,也有雷霆手段。可以帮助好人,也足以震慑恶人。实为当今中国本土悬疑作品中罕见的人物形象。
主编推荐
第一章我的一生得过两回流感。第一回尚在吃奶,第二回差点死了。那一年,美国总统尚是老布什,萨达姆吃掉科威特,柏林墙倒了十个月,苏联只剩一年阳寿。我爸爸刚到九省街摆地摊卖牛仔裤,隔壁批发走私太阳眼镜,对面兜售盗版耐克运动鞋,斜对面卖香港金利来领 带。街上的泼皮无赖要收摊位费,卖太阳眼镜的女人被打了。我爸爸一拳砸断了那个混蛋的鼻梁。人人劝他逃命,他却点一支烟,坐在摊位上开始读一本古龙的《欢乐英雄》。稍后,他赤手空拳跟十个男人对打,八个上了救护车,两个进了派出所,地上掉了三颗门牙,一颗犬牙,热血一路奔流到长江。我爸爸嘴上烟头尚未熄灭,走到医院缝了十八针,双眼肿得像大熊猫,生龙活虎地收摊回家。当晚,我写完汉语拼音作业,发了四十度高烧,清水鼻涕拖到肚脐眼,眼看就要咽气。我爸爸仿佛架着一个布玩偶,把我架上他的粗壮脖子,扔进急诊科说 :“大夫,告诉这小子,打了针就会好,要是不听话,再打一针。”我的屁股上挨了两针,哭得如丧考妣。三天后流感痊愈。今晚,我已经三十八岁,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七十公斤。我吃着香草味冰激凌看完英超直播,切尔西2:2打平阿森纳。木头窗框外落着雨。空气冰冷得像一间肉库。门铃响了。我转开门把手。铜锁舌“咔 哒”一声,拔出所罗门王的瓶塞。她蒙着白色N95口罩。眼影浓烈,睫毛刷得如同苍蝇腿。眉毛似乎文过好几遍,一头大波浪卷发,巧克力色,令人分泌唾液。她穿一件苹果绿双面呢大衣,左手挎着爱马仕鳄鱼皮包,右手拿一把长柄伞,水滴晕染在地板上,漫延到西班牙小牛皮靴下。香水分子如飞蛾扑火 而来。我戴上蓝色医用口罩,压紧鼻梁上的金属条。我们既像两个秘密交易的毒枭,又像整容手术失败后的医生和病患。“探照灯调查公司,欢迎光临。” 我递上一张名片。我叫雷雨。既是董事长,也是总经理,兼任首席调查员。次席调查员尚未生出娘胎。回到故乡三个月来,我尚未接过一单生意。或许全城居民皆无秘密,男人们忠诚于信仰,女人们贞洁于道德,流氓无赖都熟读《论语》或列夫·托尔斯泰。“我能叫你小雷吗?” 成熟妇人是一把中提琴,声音温暖、醇美、丰满,肖斯塔科维奇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姑娘是小提琴,声音细得能绞断脖子。而如我这般的男人,自然是一把低音提琴,沉得像秦始皇的青铜棺椁。“上一个叫我小雷的是个房地产商,每次出门给我三百块一小时保安费,两周前死于马尼拉赌场。”我放她进来,“如果我没回来,恐怕他尚在人世。”房间里有电冰箱、玻璃茶几、两张人造革沙发。书架上收藏着五百本推理小说,弥散着一股被害人的气味。这不像一家调查公司,更像密室谋杀现场,或是停电三天的殡仪馆。地板上有个凶狠的捕鼠夹,我把它挪到墙角,以免女客户的皮靴踩进去。“小雷,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她坐上沙发,双腿叠加,看了一眼左腕上的镶钻女表,腔调犹如中国男子足球队征战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探照灯调查公司全年无休,二十四小时营业,承接商业调查、个人征信调查,寻找失踪人口,恕不接受婚姻调查,也不负责捉奸在床。”“我的老公已经死了九年,你要去阴间才能捉奸。” “抱歉,本公司只接阳间的业务。”我指着公司招牌,一盏刺破黑夜的探照灯。 “小伙子,你挺有意思。”“谢谢,可惜‘小伙子’或‘挺有意思’均不属于我的服务范围。” “小雷,我想请你找我儿子。” 寡妇的口音不是本地人,远在江浙一带。但并不在上海、苏州或宁波,而是沿着崎岖的海岸线南下,越过象山和台州,直达温岭、乐清甚至温州。“小孩失踪的话,建议立即报警。”“我儿子三十一岁了,他叫钱奎。”女人抓起茶几上的铅笔,扯过一张便笺纸写下,“他在读博士。” “什么专业?”我像在询问牛肉的等级与产地,澳洲还是美国或者巴西。“文学。” “我会跟你儿子成为好朋友的。”我不想让寡妇在我的房间停留过久,“请告诉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间地点。” “昨天半夜,我儿子突然出门,到现在还没回来。白天我打过他的电话,但他不接。傍晚六点半,我又打电话,他还是不接。他的手机定位在鹦鹉桥。然后就关机了,我很担心他。”“你们装了位置共享软件?”我从不批评客户,但我会提出善意的建议,“您真爱贵公子,但他是三十一岁的博士,不是逃课的初中生。我不觉得他会乐意让妈妈二十四小时掌握行踪。我猜他正在女朋友的床上,明天中午,你会看到儿子坐在厨房,饥肠辘辘地等着妈妈做午饭。”“不会,我儿子的未婚妻叫李雪贝。半小时前,我去她家找过。没人开门。我打她电话,听到手机在房间里响。”寡妇的手指尖像发莫尔斯码敲着茶几,“我打电话给公安局的秦处,他说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 不能立案,他向我推荐了你。他说世界上没有你找不到的人。小雷。”“你找对人了,我有一半的朋友是警察,剩下一半是无耻混蛋。” 我听到天花板上的老鼠家族咚咚疾行而过,“请把贵公子的资料发给我, 从他最爱吃的巧克力到最爱穿的内裤牌子。天亮前,我保证把他送回家,一根毛都不少。”“小雷,请你开个价。” “涨价了,三万块。”“成交。”她的爽快让我别无选择,“你可以给沙发换个真皮的。” “我还欠着三个月房租。”我素来对客户坦诚相待“,要吃冰激凌吗?香草味?还是抹茶味?” “能抽一支烟吗?”寡妇未等主人同意,已经摘掉N95口罩。灯光变成了一张磨砂纸,你能看出三十年前的美丽风光,仿佛保存良好的考古遗址。她的右腿叠在左腿上,露出一小截黑色丝袜。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包软壳中华,拆开包装,把一支烟塞入嘴唇之间。ZIPPO 打火机的金属声像手枪装上弹匣。火苗舔上,丝绸般的烟雾。“小雷,你有哮喘?”她看到茶几上的哮喘喷雾剂,像个同情心泛滥的老娘,“我儿子也有哮喘,不要让他发病。再见。”她只抽了半截烟,急着在烟灰缸里扼杀。 “请先付一万订金。”我举起二维码牌子,“找到你儿子后,再付剩下的两万。”她用手机付了一万,加上我的微信。她叫“洪姐”。她戴回 N95口罩,白底上生着一片绿色橄榄叶。洪姐提起长柄伞,我帮她开灯照亮幽暗的楼道,这年纪的女人骨质疏松。她是我的幸运女神,探照灯调查公司的第一位客户。我想把她的照片裱到墙上。深夜十一点。阒寂无声的兰陵街,仅有一盏路灯亮着。一辆银灰色特斯拉轿车,车窗上贴着违章停车罚单。雨幕冷入骨髓。撑开的长柄伞移动到车旁,车门拉开,收伞,关门。车灯在黑色污浊的路面上 照出一条银光闪闪的大道。我要在天亮前找到她的儿子,也许送他上天堂,也许下地狱。第二章我收到一组照片。他叫钱奎,三十一岁的文学博士,眼神跟蜂蜜一样甜美,也像蜜蜂一样蜇人。他是一个乖小囡,所有妈妈都喜欢的那一种。他的妈妈是个寡妇,也是个有故事的女人。我的沙发尚且残 留她的余温。钱奎的手机关了。我给他的未婚妻打电话,彩铃是 Love Me Tender。猫王温柔地爱我,温柔地唱了一分钟。无人接听。她住在海上邨,距离我只有九百米。我回到镜子前审视自己。我不丑。鼻梁略有攻击性。乌青色嘴唇,仿佛轻度中毒。黑发密如野草。胡须如仙人掌刺在双颊,酷似一个抽雪茄的拉美男人。他在三十九岁时被枪毙,希望我也能活到这个岁数。 我抽出牛角梳,篦好头发。穿上黑色皮夹克,戴上一枚日本机械表。口罩上单眼皮光滑。哮喘喷雾剂塞进裤袋。大门上锁的刹那,屋顶的老鼠们发出胜利的尖叫。我能在雨点之间躲闪穿行,米高扬这么说过。我走到太湖街,坐 进一台挂着上海牌照的黑色大众甲壳虫。发动机点火颤抖,雨刮器扫去风挡玻璃的眼泪,黑人歌手在车载音响里开始唱 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走洪泽街,路过天主教堂,抵达海上邨的红色砖墙下。迎面而来一台藏青色本田 CR-V。我的右车轮压上台阶,紧贴着小龙虾店的卷帘门。本田车擦着我的左后视镜开过,旋即被大肠般的黑夜消化成粪便。十一点半,我钻入海上邨的院子。几台停泊过夜的轿车长眠不醒。底楼挂着铁皮信箱。楼道里散发出一股橘子皮腐烂的味道。拉动一根 油腻的绳子,电灯泡亮起,照出木头楼梯。我戴上皮手套,循着扶手 裂缝爬上三楼。防盗门上一只猫眼窥孔瞪着我,态度极不友善。门缝底下一摊光线蔓延到我的足尖。我按下门铃。年轻女子的脚步声。门缝下多了脚 踝的阴影。她在猫眼背后看我。这不失为一个好习惯。“你好,李雪贝。”我隔着门说,“钱奎在吗?” “他不在。”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隔壁班的女同学,你永远没机会跟她坐在一起。“李雪贝,每拖延一分钟,你未婚夫的危险就会增大 10%。”我摘下口罩,掏出身份证举在脸前,“你可以从猫眼里拍张照片,我要是个劫财劫色的大盗,注定插翅难逃。”六十秒后,防盗门打开一道缝。但有一条链子挡着我。口罩遮住 她的半张脸,有无粉刺或雀斑?嘴唇单薄还是丰润?鼻子纯天然或动 过刀?我一无所知。“我暴露了整张脸,你只露一双眼,这不公平。我能进去吗?”“没门。”她控制住防盗链,保持一尺之遥,“你是警察吗?” “我像吗?”“再见。”李雪贝要关门,我伸手挡住门板。 门缝此刻像一只撬开的扇贝。我可以伸手进去,拔出防盗链,撕下她的口罩。但我不会这么做。我只是个调查员。“雪贝,我是钱奎妈妈的朋友,她出了点麻烦,她拜托我找到钱奎。” “她恰好是全城最讨厌我的那个人。” “妹妹,跟你分享一点微不足道的经验——你一生的命运,往往是被自己或者别人瞬间的决定改变的。” “我同意。”她瞪了我一眼,“但我不是妹。” “我也没兴趣做你哥哥。”我的目光既凶狠又温柔,“告诉我,钱奎在哪里?”李雪贝仍然躲在防盗链和口罩背后,双眼如 X 光把我的五脏六腑 甚至前列腺,透视个干干净净,确认我没有窝藏病毒、炸弹、核武器, 或者催情水之类的脏玩意儿。“我猜他在巫师。”她的嘴被我撬开了。 “文学博士信仰萨满教?还是说一款波兰游戏?” “巫师酒吧,在江街,我猜你不是本地人。” “你错了。我只是离开了二十多年。如果一小时内没找到人,我会回来的。”“我跟你一起去。”她关上门,“等我五分钟。” 我戴上口罩等她。李雪贝准时而完整地出来。蓝色口罩蒙面。乌黑长发盖着雪白的羽绒服。她捏着一把短刀似的折叠伞,侧身擦过我的肩膀下楼,我从背后观测她的靛蓝色牛仔裤。她的脚下升起一团淡 薄烟雾。走出海上邨,我拉开大众甲壳虫的右车门。她坐上副驾驶位,给自己绑上安全带。零点还缺一分。发动机余温未消。长江下的隧道像一条大蛇的消化道生吞了我。车窗映出李雪贝蒙着口罩的侧脸。她眯起双眼看手机说 :“你打过我的电话?”“我喜欢猫王唱《温柔地爱我》。”我斜睨着她,“你有近视?现在的妞都不爱戴眼镜,就像抢银行的不爱戴头套。”到了长江对岸。雨一直下。江街的夜店几乎都打烊了。下了车,李雪贝撑开折叠伞,斜睨我一眼。“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伞。”我踩过水塘,推开巫师酒吧的玻璃门。 加泰罗尼亚风格的装修。高迪借尸还魂。背景音乐是《忧郁的星期天》。我转到英式吧台前,年轻的酒保裹着黑马夹,郁郁寡欢地擦着 玻璃杯。李雪贝问他 :“钱奎来过吗?” “他来过,又走了。”酒保及时戴上口罩,声音同眼神一样甜美。 “走了多久?”“大概十五分钟,他叫了代驾。” “肯定用过手机。”李雪贝拨出一通电话。钱奎又关机了。 酒保拿出两个玻璃杯,各放一个冰球。我摇头不喝。他只倒一杯威士忌。琥珀色液体浸泡冰球,暧昧不清地反光,假装岁月静好。 李雪贝摘掉口罩,坐上高脚凳,脱了羽绒服,露出咖啡色薄毛衣。吧台顶上灯光,穿过酒杯折射,让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她有一只小翘鼻子,冒充大学生绰绰有余。她咽下一口威士忌。没化妆的嘴唇湿了。 剩下的威士忌像雨天水洼,死皮赖脸地贴着玻璃杯底。“小弟,怎么称呼?”我坐上凳子问酒保。 “杰克。”酒保常用花名,像个古老的杀人狂。 “钱奎是几点钟来的?他有同伴吗?” “九点多,钱奎一个人来喝酒。如果他不来,酒吧早关门了。”酒保向我背后张望,恍若钱奎的魂还没走,“他很累,脸色难看,就坐在你这张凳子上。”“钱奎说过什么?” “他安静得像一条金鱼。”酒保杰克举起酒杯,“先生,您喝什么?” “一杯冰水。”我摘了口罩,含一小口冰水,给口腔降温,冰水刺入喉咙,“钱奎喝了多少酒?” “六杯威士忌加冰。” “你知道钱奎要去哪里?”“钱奎醉了。他好像忘了什么东西。”酒保说,“我陪他去了停车场。他对代驾说要去鹦鹉桥。”“鹦鹉桥?”我抽出一张钞票扔上吧台,“谢谢你,杰克,不用找零。” 我戴上口罩,拖着李雪贝冲出酒吧。坐上黑色大众甲壳虫,我收到钱奎老娘发来的微信 :“找到了吗?”我回她一条语音 :“你儿子刚去鹦鹉桥,你儿媳妇就在我身边,保证一小时内找到人。”李雪贝瞥了我一眼。潮湿的路面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车子如一尾 黑色的大鱼,滑入雨水丰盛的冬夜。车灯下的雨点像金粉洒落。风挡玻璃上的雨刷舌吻交缠。这座城市漂亮得像个装了电梯的假古董。电视塔是千杯不醉的夜店姑娘。上了大桥,全中国的潮水贯穿我的胯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众甲壳虫穿过鹦鹉桥的十字路口。钱奎的老娘发来一条手机定位。傍晚六点,她儿子在此关机。我的脚底板点一下刹车。江边戳着 一栋孤零零的居民楼。整栋楼黯淡无光,如同黑漆漆的通天塔,楼顶 几乎连接暗夜上的乌云。唯独顶楼的窗户亮着灯,灯塔似的提醒夜航 船不要靠近危险。楼下停着两台车。第一台是藏青色本田 CR-V。记得一个半钟头 前,我在海上邨的门口与这台车擦肩而过。当时我就应该顶住车头, 把开车的混蛋拽下来。如果他妄图反抗,我会用耳光教会他一点人生的哲理。还有一台宝蓝色阿尔法·罗密欧轿车。意大利原装进口,倒三角进气格栅,车牌只能挂一边。发动机熄火不久,像一杯热咖啡在雨夜 蒸腾。李雪贝放下车窗说 :“这是钱奎的车。”“隔壁的本田 CR-V 是谁的?” “他叫麻军,麻子的麻。如果见到他本人,你就知道这名字有多准确。”她抬头说,“他住在顶楼。” “我的问题来了,深夜十一点,麻军来找你做什么?” “麻军是我妈妈的表弟。” “妈妈的表弟,不就是表舅吗?但你不这么叫,说明你讨厌这个人。钱奎为什么在六小时内,先后两次来找他?”我熄了火,解开安全带,“我们上去找你的未婚夫。许多人在这一夜崩溃了。别怪我没提醒你。”上楼以前,我摘下口罩,掏出哮喘喷雾剂,塞入嘴巴,缓缓吞入 0.1 毫克布地奈德。我像个病入膏肓的人,每天必须使用两次。我重新戴上口罩,喷雾剂收回口袋,推开车门,左脚踩上泥泞的地面。他出现了。他像刚从娘胎里爬出来似的冲出底楼门洞,摘下白色 N95 口罩,双手撑着膝盖喘气。我回到驾驶座上点火,大众甲壳虫的远光灯轰然击中他的脸,惨白得如同乞力马扎罗的雪。他的外套和眼镜片上沾着 暗红色污迹,好像逃出斯蒂芬·金的闪灵酒店,住客们多半有三只眼睛、六条胳膊,以及两对乳房。钱奎抛下口罩,钻进楼下的阿尔法·罗密欧。他的发动机如同死 亡金属音乐会的燥热开场,车子倒向近在咫尺的长江。我狂按喇叭提 醒他不要妄想横渡亚洲第一江河。钱奎凶猛地打方向盘,扬长而去。车轮激起一片泥泞的暴风雨,像排队枪毙的子弹,溅满我的风挡玻璃。 我好像戴的不是蓝口罩而是黑眼罩。我在长江大堤上掉头。雨刷焦躁地打碎泥水。轮胎凌迟处死般惨叫。李雪贝被晃得七荤八素。安全带嵌入她的锁骨。远光灯照出阿尔法·罗密欧的宝蓝色臀部,性感得像一个西西里美丽传说,万一错过就要孤独终老。黑猫来了。 从耳朵尖到尾巴尖全是黑的,仿佛在波斯湾的油桶里浸泡了三生三世。唯独一对金色眼珠子,宝石似的反光。这只猫凭空出现在地球上,横冲直撞到我面前,像个半夜查酒驾的交通警察。阿尔法·罗密欧开出史前巨蟒般的轨迹绕过了黑猫。大众甲壳虫的油门踩到最深,不知死活地狂奔。雨点万箭穿心。李雪贝抱头尖叫。 某个非洲裔美国人吟唱 Smoke Gets In Your Eyes。我打了方向盘。鬼使神差。轮胎在泥泞中打滑,像丢失重力的宇宙飞船,滑向吞噬万事万物的黑洞。大众甲壳虫疯了。阿尔法·罗密欧疯了。文学博士疯了。钱奎的妈妈疯了。钱奎的未婚妻也疯了。全城的一千万人都疯了。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维持不了几秒,我也疯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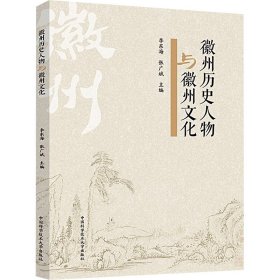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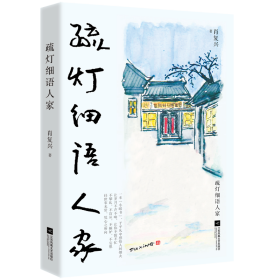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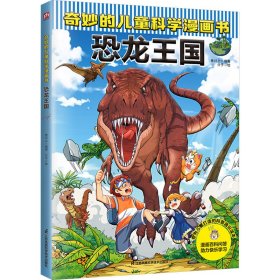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