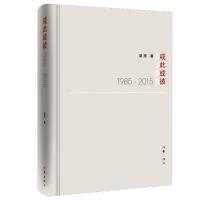
或此或彼
正版图书保证 可开电子发票
¥ 43.5 7.3折 ¥ 60 全新
库存38件
湖北武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吴亮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04360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60元
货号3321945
上书时间2024-01-23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目录
本书收录吴亮三十余年来最为重要的评论性文字, 看似谈论的是作家、作品, 但在写作与批评间、在作家与论者间, 绝非非此即彼的选择, 而是或此或彼的潜望。
内容摘要
程德培第四个十年集,所收皆为万字以上长文,融细密阅读、精致阐释、优雅行文于一体,在词语的连绵间,见当代文学的波涛翻滚,见当代作家的心性格局,进而超乎单纯的文学批评,抵达写作之本义。
精彩内容
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对变幻莫测的当代小说再要作一完整的巡视和综述,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一两个人来承担了。一年来的小说创作现状像团不断扩张的迷雾,把原先公认的那些清晰框架弄得一片模糊。这些纷至沓来的小说如同一大群匆忙向前赶路的旅行者留下的杂乱足迹,简直难以辨认。批评家刚刚理出一点头绪和轮廓,打算予以及时的归纳,但是新涌现的小说马上使原先确立的某几个观点发生了倾斜。今年初,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在五家文学杂志同时和国内读者见面,随后就引起了批评的骚动。当有人振振有辞地以虚构是小说的最基本构成这一规范向《北京人》提出疑问时,另一些人则以“口述实录”这一纪实的形式本身拥有的审美认识意义——如可靠的逼真性、实况效果和还原性等等范畴——来为《北京人》的非虚构性进行理论上的辩护。不过,与此同时,这样的批评家却极难对差不多时间出现的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做出敏感的反应。由于对西藏民族历史、宗教、神话和种种野蛮的风俗所知甚少,也由于对那种怪诞的叙述形式和隐语感到极为生疏,人们只好对之表示沉默。这种沉默开始在蔓延——曾写了轰动一时的《棋王》的阿城,写了若干篇实验性的印象笔记体小说《遍地风流》,至今还未能看到批评家的反应。由于这串小说不但舍弃了情节,而且也难以看出那些印象背后究竟有什么象征意味,结果批评家就感到缺乏一种让他们阐发见解的客观依据。然而,恰恰是印象本身,构成了我们日常感觉的重要方面。日常感觉、心境、情绪和对某种氛围的期待,组成了《遍地风流》的几个要素,这一点被批评家们不以为然地忽视了。
批评家开始感到迷惑和惶然,往日那种全知全能的地位在迅速瓦解。当校园小说《你别无选择》和人们见面后,除了一些华而不实的赞词,更普遍的反应仍然来自对一般社会变迁乃至心理波动的描述与概括,或者从一代人的观念落差中窥见了大洋彼岸塞林格的影子,甚至还看到了海勒笔下的尤索林的幽魂。当然,指出这篇小说的反叛精神,一种青春期的躁动与不安分,是不无理由的。可是对这篇小说所涉及的某些音乐领域的课题,却还没有人作出内行的应答,而这恰恰是理解这篇小说的枢纽所在。小说在今年的大分化趋势中,愈来愈走向小型化、圈子化和专门化。这显然是对全知型批评家的重大挑战。权威的意义被缩小了,权威的影响也跟着缩小。已经很难听到一锤定音的批评之声,这声音已经被抹去了。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它们彼此合奏,彼此干扰,不能传得更远。权威消失了,是人们各自的个性崛起让它消失的——你们、我们还有他们。
当代小说犹如一棵参天人树,数不清的枝桠在自由伸展,向空间展拓,谋求生存。仅仅关注这棵大树下的土壤,或者仅仅看到这棵大树的树身,已经远远不够了。仅仅说所有的树都仰赖土壤而生存,或者仅仅说一切枝桠都从树干上生长出来,也已经远远不够了。说一切树呀、花呀、草呀都是植物,于我们知识的增进又有何益?批评愈来愈要求细密化、精确化和特殊化,那种大而无当的批评应当寿终正寝了。
由于批评家知识结构和审美习惯的定向化和普泛化,使他们容易产生自以为可以对一切小说发表议论的幻觉——当然,也只是普泛的层次上发表议论。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并不是任何小说都能一目了然地提供普泛意义,进而顺顺当当地装进那个事先准备好的理论匣子里的。当小说的实际阅读发生了障碍,和既成的判断尺度无法对应时,那个普泛的尺度就开始失效了。对无法把握和观察的事物是谈不上进一步测定的,而简单的异议又缺乏可靠的依据和充分的自信,于是缄默就成了批评家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小说家们受不了这种难堪的缄默,因为他们多少懂得,倘若没有有力的小说批评作为见证,他们的实验小说和其他种种和既定规范有悖的小说是很难长久确立的。当代小说的变幻莫测,在时间的飞轮下很快就会变成一道彩虹,随后就因为水汽的蒸发而消散得无影无踪。小说批评和理论概括,就如一架摄影机的快门,只要略一按动,就能把瞬息即逝的艺术幻影化为永恒。小说家们愈来愈希望有一种真正理解他们用意的批评,如果他们的希望落空,他们就忍不住自己出面撰文了。
小说家圈子事实上在若干年以前就悄悄地形成了,因此,小说家们自己的批评,显然就是圈子批评家出现的预告。他们的批评,避免了隔靴搔痒的毛病,又有切身的经验和体察,往往具有局外人难以做到的细微和会心之处。他们阐发和交换各自的经验和印象,并不期望人们在理论上的高度归纳。他们彼此通信,侃侃而谈,把正儿八经的批评家撇在一旁,津津乐道地议论着只有他们感兴趣的各种艺术问题,或者相互呼应,或者争得面红耳赤。总之,他们已经不仅仅通过小说,而且也通过议论,来向社会说话了。
由于隔膜,也由于那些小说的费解——本来小说的概念是明确的,批评家可以轻松地参照这些概念来看小说的创作意图和内部的隐语——使得原来无所不评的批评家陷于窘境。但是,凭着多年艺术感受能力的熏陶,他们又直觉地感到这些小说是有意味、有分量的,不过就是难以一语道出。他们痛感小说家们自己撰写的文章主观随意性大、立论不充分、武断、偏颇和自鸣得意,但由于那些小说家们谈到了一系列他们感到生疏的课题,而他们一下子又不可能熟悉和通晓那些领域的知识,于是就很没有发言的把握,并由此感到心理的不平衡。今年初以来,韩少功、阿城、郑万隆、郑义纷纷谈起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根应当扎在何处的问题,它的余波至今尚未平息。指出这一问题在提法上的偏颇和对它的补救措施,其实只是批评家为了恢复自信和心理平衡的表现,而很少有批评家真正多年如一日地深入研究文化的课题。这一疏缺,无疑影响了理论的深度和说服力;但这个缺陷,在小说家那里则被一种想象力,智慧风貌和俏皮幽默所掩盖了——批评家却无力做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当代小说的多向性发展已经召唤着圈子批评家的成批出现,这一趋势明摆着了。批评家不可能是一支机动的、配备齐全的空降部队,哪里有了需要,他们就在哪里迅速降落,等到平息战火后便安全撤离。不,这已经不可能了。批评家必须是有专题研究的,他不必要也不可能对任何小说现象都议论一通。即便是文化小说,里面也包括着若干地域性的专题,要跨越这些文化地理上的屏障绝不是件容易事。李抗育的《炸坟》刊出后,还未有人将它剔离出来,放到吴越文化的背景下予以考察,更不用说一一指陈这篇小说所包蕴的诸种含义了。例如这篇小说的俚俗、幽默、荒诞和象征,构成了连成不等边四角形的四个点,这种构成关系和磁场引力,若要从美学意义上加以探讨,显然只能是属于专题批评家的分内之事,外人插手总觉得别扭。往上推移一下,像韩少功的《爸爸爸》,通体散发着既浓烈又峻冷的楚味,若单单从象征的角度来阐释丙崽病态精神包含着的国民心理状态的含义,仍然是远远不能穷尽这篇小说所隐含的复杂内容的。关于生存状态,关于民族和种族的原始记忆,关于风俗和迷信,关于语言的组合带来的暗示能力,都可以引发许多饶有深意的理论思考。遗憾的是,批评家们的专门知识过于贫乏了。再往上推移,郑义的《老井》既令人窒息又令人激动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对这篇小说批评家们说了些什么呢?对郑义黄河之行归来后一系列严峻的思索,批评家们又知道些什么呢?批评家坐在书斋中,遥观着一篇又一篇新刊出的小说,对它们所赖以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小说家的特殊经历却所知甚少。批评家对小说家的徒步远游表示了赞赏,但也不过是致以一个远距离的敬礼而已,他们自己仍然不能贴近小说家,和他们共同体验某种心境,诸如喜悦、忧虑和困惑。圈外的批评家,也许可以不被偏爱所拘囿,可以独立自主地发表个人的意见;然而,基于不理解之上的批评往往是难以妥帖中肯的。小说发展的多样化和小型化,暗示了一种批评分工的前景,这一前景已经向我们隐约地呈现出一个新的组合模型:不是小说家和批评家各自成为两个营垒,而是由几个小说家和几个批评家组成一个文学圈,这个圈子有着自身的运转机能和协调机能,以及对外说话的多种媒介工具。
圈子批评家的任务当然不止于被动地作阐释和作注解,他们还将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批评尺度与模式,提出主张,推动文学和文化的继续繁荣。他们将言之有据,自成一格,他们把自己的批评看作圈内小说的组成部分,而绝不是无所作为的伴郎。
圈子批评家和圈子小说家的携手,并不是单指一般意义上的友人关系。他们往往因为气质、审美意向、兴趣、主张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此外,还因为他们都触及同一个专题或同几个专题,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前者是知识和概念的,后者是经验和感觉的。另一方面,这些圈子批评家又特别重视圈子小说家的经验和感觉,而小说家也十分赞同批评家的知识和概念——他们本身也在探求着和他们的艺术倾向有关的各种知识。事实上,他们是水乳交融的统一者。
对小说家经验和感觉的熟识和领略,是圈子批评家必备的素质。批评家自身的确立和自信,反而使他们不耻下问,深入到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幻象世界中去汲取感觉的营养。相反,只有不那么自信的全知型批评家,才害怕和小说家的平等交流与对话,生怕被他们的才华所吞没。这种害怕心理,促成了隔膜的形成,对双方都极为不利,既有损于小说在规范意义上的确立和研究,也有损于抽象思辨的饱满内容。批评家的这种自夸意识其实是自卑感的无意识流露,他们竭尽全力地将一些貌似艰深的语汇和范畴来笼罩小说的艺术整体,可是这种笼罩物本身却极为无力与稀薄。
感觉,这沟通小说和批评的第一个媒触和中介,好像总不那么受到特别的关注。过多的概念思维,把批评家的感觉机能磨钝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实际上很大程度地唤醒和打动了人的感觉,批评家不是没有意识到。可是,他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凭着惯性思维,用一层知性的概念之壳来封裹那一连串新鲜的感觉印象,并有意无意地将它推进一个预制好的先验模式。从《透明的红萝卜》中发觉了“魔幻”和“童话”,这当然是有眼光的,可是若不能指出它是如何的“魔幻”和怎样一种“童话”,这种标签仍然显得苍白。至于用某些浮泛的措词来探讨这篇小说的艺术特征,如含蓄,虚实和模糊,同样令人感到无关痛痒,进而反显得模糊不清。批评家的尴尬,实在是因为不肯放下一副整天思索深奥理论的架势,在任何一个问题前都要高谈阔论一番。这也是因没有圈子意识和圈子交流而产生的隔离现象——批评家抓住某几个艺术症候,作随意联想,既远离了艺术本体,又没有批评主体的诗情洋溢其间。这样的批评漫游实际上便沦为一种无价值的空谈和知识的炫耀。关于莫言小说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美学和心理学问题。它涉及到感觉记忆、感觉的内视性、幻听和错觉,涉及到行为动作中的信息交换和自娱功能,涉及到语言转换过程如何保留最初的直观性质,还涉及到童年的观察、想象力和梦境的再现。由此,它还将涉及到作家的个人资禀和气质类型。很难想象,那些圈外批评家能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出令人满意和使人信服的回答。
陕西的贾平凹也有相类似之处:由于他气质上的羸弱和极度敏感,这一内向性格使他迷醉在各种传统文化的典籍、野史和笔记之中。若对他的个性不屑于研究,又不能对那些典籍、野史和笔记有所了解,就使批评家们满足于在一般社会历史范围内对他的小说进行单方面的功利主义评价,而把他小说里的某些精髓遗漏了。在这个框架里,批评家完全依据单一的尺度,忽而说贾平凹陷于迷途,忽而说贾平凹有了巨大的突破。这种外在的评判,实在和他精神的探索相距甚远。圈外的、全知型的批评家,总是企图找一把万能的尺子,来衡量所有的小说现象,这样就容易变得狭隘和武断。能弥补这一缺陷的,只有靠那些圈子批评家,因为唯有他们才深知小说家独特的精神探索轨迹,并谙熟小说家所热衷的某些专题乃至各种古怪的个人癖好。
当代小说的圈子化趋势有增无减。无论是前述的莫言、贾平凹,还是尚未论及的张承志、张炜、陈村和王安忆,都开始走向了自己风格的基本定型。莫言继《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又有了《秋千架》和《球状闪电》;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仍然不衰地持续出现,他的中篇《商州世事》让人感到那真是一个偌大的世界。张承志写了《晚潮》《残月》以后,他的《胡涂乱抹》和《黄泥小屋》又将相继问世;张炜的《本林同志》和陈村的《从前》至今还未见到评论,而这两篇小说都比他们的前作有了新的含义。陈村的《美女岛》马上就要出笼了,批评家将如何评价这部既非常荒诞又非常现实的小说呢?还有王安忆,她从《大刘庄》开始就有了对小说叙事结构的有意探索,《小鲍庄》也许是她近年来的一个高峰,她今后又有怎样一个发展前景呢?
要谨慎而细密地回答上述问题,是非圈子批评家莫属的。圈子批评家是圈子小说的对外发言者,他们沟通圈子和圈子的联系,协调着相互的关系和彼此的理解程度,为当代文学史的宏观记录提供翔实有据的材料和论证。圈子批评家完成着第一轮的筛选工作,把易被遗漏和易遭误解的小说重新推到研究者的面前,并附上一份辩护词和委托证书。圈子批评家在大分化的历史趋势中并不惊惶失措,他们将卓有成效地分工,并通力合作,澄清理论的空幻迷雾,把新涌现的小说现象理顺,并把里面的新经验逐一予以归纳和合理化;他们修正着既定的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为时代精神的更新和固有文化的整理提供活生生的依据。圈子批评家既是圈子小说的热情鼓吹者,又是严格的诤友,他们将毫不讳言友人的过失与迷误,并理智地汲取来自圈外的合理意见,纠正自己的偏颇——当然,他们的谦虚绝不意味着丧失定见,他们将坚持某些主张和观点;虽然可能有错,但至少可以留待时间的公正裁决。
为应付发展如此变幻莫测的庞杂局面,促成圈子批评家的出现将是一个有效的对策。不然,在若干年后,人们将意识到:由于我们轻视了这一历史的请求,当代文学的整理失去了许多可靠和详尽的依据。事后总结既感到累人,又因为没有充分的目击者和知情人提供的原始证词,判断就很成问题了。
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初的某一天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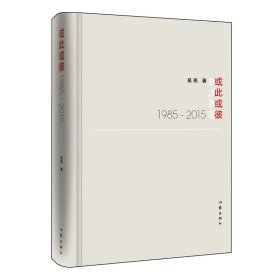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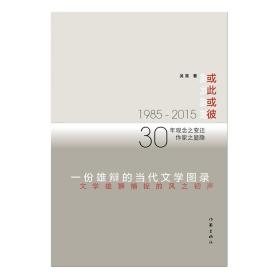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