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花六照 散文 梁羽生 新华正版
¥ 60.2 6.1折 ¥ 99 全新
库存5件
江苏无锡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梁羽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70691
出版时间2017-06
版次1
装帧其他
开本16
页数524页
字数440千字
定价99元
货号xhwx_1201541297
上书时间2024-04-27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笔花六照: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开创者,武侠小说闻名华人世界,拥有众多读者。他在武侠小说之外,也擅长散文随笔,文史诗词功底深厚。 梁羽生将生得意的一部分文章结集,并曾在去世前加以增订,彰显了梁羽生之情、志趣与文史修养。由梁羽生儿子亲自作序。
目录:
目 录新版序/陈心宇一九九九年初版自序/梁羽生甲辑 武侠因缘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在浸会大学的演讲中国的“武”与“侠”——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武侠小说与通识教育——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国武侠小说略谈公案侠义小说只因藏拙创新招达摩·禅宗·秘笈太极拳一页秘史谈“新派武侠小说”凌未风·易兰珠·牛虻魔女三现 怀沧海楼回归·感想·声明有才气 敢创新——序卢延光的《武侠小说插图集》的武侠小说冒险到底乙辑 师友忆往胡政之·赞善里·金庸——《大公报》在港复刊轶事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华罗庚传奇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亦狂亦侠 能哭能歌——怀念“百剑堂主”陈凡悼沙枫荣辱关怀见情——悼蔡锦荣论黄巢 怀高朗——传奇的历史人物文学院长的风流怀士堂前喜见层楼拓挽聂绀弩联京华犹剩未残棋记刘芃如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记谢克缘圆两度见圆融——怀念刘渭教授丙辑 诗话书话杨振宁论诗及其他原子物理学家的诗廖凤舒的《嬉笑集》重印《新粤讴解心》前言闲话打油诗黄苗子的打油词挑曹雪芹的错水仙花的故事本汉学家的水仙词锦心绣笔生花——“沟通艺术”的对话看澳洲风流 盼大同世界——序张奥列新著《澳洲风流》雪泥鸿爪 旧地深情——序黄文湘《美游心影》武侠·传记·小说——序林真《霍元甲传》柳北岸的旅游诗尤今是尤今音符碎在地上杜运燮和他的诗无拘界处觅诗魂——悼舒巷城舒巷城的文字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罗孚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从两首诗看徐訏梦境是一片胡言?梦谶的解释从《雷雨》到《阿当》 《啼笑姻缘》题诗章士钊的南游诗两偈·顿渐·陈寅恪饶宗颐初会钱锺书饶宗颐与敦煌学敦煌学是伤心史澳大利亚的中国移民文学走近黄惟群——读《黄惟群自选集》 《雷雨》《阿当》《耍花》展艺华堂信有缘——听雨楼诗札书画拜嘉藏品展览不拘规格的名联丁辑 读史小识 “万岁”从来多短命圣明天子半庸才末代皇帝的命运霸王难别虞姬 “六国大封相”纵横谈汉代女尸背后的王侯中国历史 上次筹码不足的风潮五胡十六国——略谈当时的民族问题武则天是否妇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秦桧是“论”的祖宗元宵杂谈论南北朝之庄园经济戊辑 旅游记趣悉尼桂林山水观敢夸眼福胜前人谈天气 怀大理何必江南赶上春雁山红豆之忆小国寡民之乐在朴茨茅斯食海鲜签证·食宿·交通 “买嘢”和“睇嘢”长屋风情还乡小记己辑 棋人棋事中国围棋的传统风格围棋争说聂旋风聂旋风摇撼本因坊赵治勋双冠在望三字真言:寻常心迷上围棋的名人挑战中棋圣让子遇险冷汗流新老沉浮各不同——围棋世界三事围棋世界两新星象棋国手杨官璘——其人·其艺·其事及其《棋国争雄录》九连霸胡荣华七大名手的棋风序《广州棋坛六十年史》 “棋坛三杰”的浮沉棋事杂写(六则)虎斗龙争一局棋——一九七五年象棋赛杨胡决战述评古晋观棋港澳棋队的表现——古晋观棋之二归心马战术的新发展皇帝与兵马——谈象棋与西洋棋的差异棋赛纪事词(两首)二四年再版后记 烟云吹散尚留痕
内容简介:
笔花六照:梁羽生对杂文随笔的热心热情,要远远超对武侠小说。他晚年隐居澳洲,特地将生很得意的一部分文章加以增订,分作六辑,既记武侠因缘、师友忆往、读史小识,又有谈诗书话、云游记趣、棋人棋事,故取“笔花六照”为书名。这些跨越半世纪的文字,不仅彰显了梁羽生之情、志趣与文史修养,亦白描出他与诸名士大家的往来轶事:陈寅恪、金应熙、聂绀弩、黄苗子等文人的风骨,张季鸾、胡政之、金庸、杜运燮等报人的风雅,尽现笔端。
作者简介:
梁羽生(1924—2009),本姓陈,名文统,原籍广西蒙山,“新派”武侠小说开创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公报编辑副主任,岭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名誉教授。梁羽生学识渊博,谙熟历史、诗词、对联、掌故、旧文学、新文艺、围棋、象棋等,是有名作家、楹联学家和棋评家;著有白发魔女传萍踪侠影录等三十五部武侠小说,另有笔花六照名联观止文艺杂谈古今漫话笔剑书等文集。晚年定居澳大利亚,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华人团体联合会”颁发的“终身成奖”。
精彩内容: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九七九年,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相识,当时他刚刚看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成年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自是更加不用说了。因为限于经济条件和知识水,的读物自是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多样化,而且“童话”也毕竟是属于他们的。童年时代:看的武侠小说不多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却没有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从小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虽然没有明令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之类是看过的,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两部,七剑十三侠和荒江女侠,内容如何,现在都记不得了。还有是兼有武侠小说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对七侠五义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虽然缺点很多(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的形象特别生动),却不失为悲剧英雄(他的收场,是陷入铜网阵,被乱箭成刺猬一般)。还有,水浒传是当然看过的,水浒传虽然是“”的农民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彩。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这部小说,我觉得开头两本写得较好,写的大体是正常武功,戏剧也较浓;后来越写越糟,神怪气味也越来越重了(我并不排斥神怪,但写神怪也是需要的,不能胡闹),写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已迹近胡闹,我几乎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对书中写的“张汶祥刺马”那段故事,倒是甚为欣赏。这段故事,武功的描写极少,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时代:唐人传奇影响很深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我的时代,对我影响很深的武侠小说却是唐人传奇。我认为那是中国很早的武侠小说,它作为“传记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时期。至于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虽然都是“武侠”品质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唐人传奇的,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虬髯客传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红拂)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李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很长。”遂喜曰:“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短短一段,写红拂慧眼识英雄,不拘小节;虬髯客豪迈绝伦;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方知来者乃是英雄,三人格,都是恰如其分。对白精练,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惧,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田承嗣驻地)之后: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寥寥数十字,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写了红线的“轻功”妙技,传神之极。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写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是取材于唐人传奇,把空空儿、精精儿、聂隐娘、虬髯客、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让他们“重出江湖”的。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时代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是基于这种。另外一个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金应熙,当年岭南大学很年轻的讲师,“”倒台后任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现在则是广东历史学会的会长。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着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 ,对它的传奇和艺术都推崇备至。金应熙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却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在岭大教书的时候,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而且借给有同好的他的看。我不但向他借书,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不过,或许是受金师的影响吧,我读的近代武侠小说,也是有点偏好的,白羽、还珠的作品我是阅读,其他作家的只是选读了。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写得尤其透彻;还珠楼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丰富,时至,恐怕还是无人能与之比肩。他们走的路子不同,我对他们的作品则是同样喜爱。欧洲骑士文学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流行过武侠小说,称为“骑士文学”。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是其中一部。西方小说中的“骑士”和中国小说的侠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抑强扶弱;不相同处是:一、西方的骑士必定要认定一个“主人”,效忠主人;二、“骑士”的称号必定要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的封予,而中国的“侠士”则是民间尊敬的称号;三、西方的骑士是效忠君王,维护为而战的“圣战”,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我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西方的武侠小说对我影响甚微,倒是那些属于“正统文学”范畴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对我影响较大。不过的来说,接受西方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接受中国传统的影响的。有人认为我的武侠小说“不脱其泥土气息”,或许是这个缘故。志愿在于学术研究尽管我在大学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的志愿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生竟然会跟武侠小说结下不解之缘!武侠故事每多“奇缘”,偶然的因素,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虽然说不上“奇”,但确实是因偶然的因缘才写上武侠小说的。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曾这样感慨地说:“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拉他‘助阵’的话,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登萍渡水’、闯入‘武林’?但‘下山’(七剑下天山)之后,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连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吧?”“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新晚报当时的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比武的地点则在。这是两派舵主之争,太极派的舵主吴公仪和白鹤派的舵主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比武。擂台设在,这是出于止打擂台而不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坊”和“快活楼”是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令得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更多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菜根谭 中国古典小说、诗词 [明]洪应明 新华正版](https://www0.kfzimg.com/sw/kfz-cos/kfzimg/eecbedba/fcaf92c7a1aa928e_s.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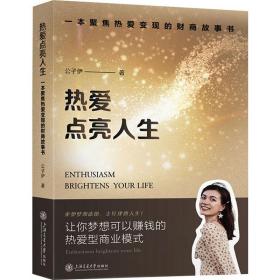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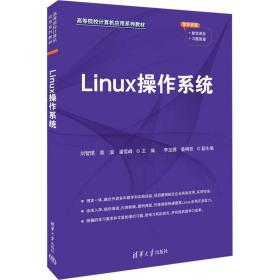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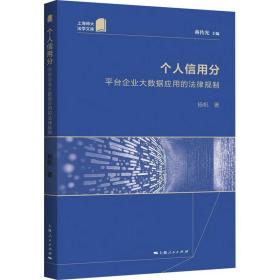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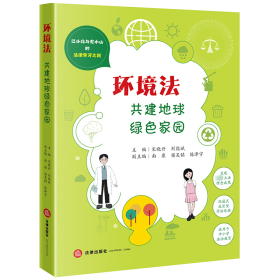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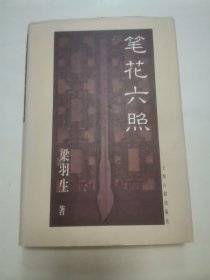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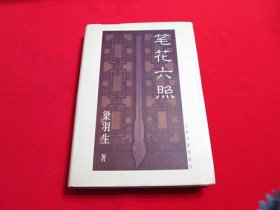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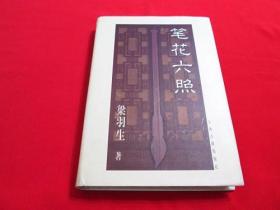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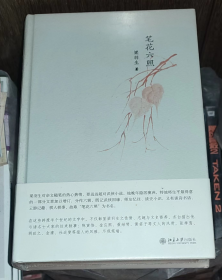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