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固的浮云 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四十年人生回忆 中国历史 吴长生 新华正版
¥ 42.75 6.1折 ¥ 70 全新
库存2件
江苏无锡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吴长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94242
出版时间2022-01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
页数408页
字数362千字
定价70元
货号xhwx_1202567477
上书时间2024-04-2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历史应该有细节,有个体出没其间。本书记录了作者与共和国一起度过的童年、和青壮年时光,清晰如昨,不带后视之明带来的偏见。结实的经验是人生的馈赠,它将你我联结起来。
目录:
童年往事
我从长沙来
参政胡同的来历
启蒙老师是祖父
祖母,三位民国女
中西混搭的家风
外婆家的“大宅门”
宅院内外的旧时风雨
旧时的“亲上做亲”
大宅门的末世当家人
“长沙章寓”
与“1号”沾亲的五位文史馆馆员
为待客家底儿的二姑婆
为“糖豆”伤心的九外公
大宅门里的“丑小鸭”
命运迥异的舅舅们
姨妈和姨父们
“侯府”托儿所
家里的三位保姆
我与父亲是“校友”
难忘的“重要政治任务”
二班由“治”而“乱”
霍老师的保票
“长大”的馒头
饥荒年代的冷暖人情
父亲的业余剧团
听“蹭戏”的诀窍
纯净的人心
胡同,我们的露天游乐场
风雨
四中,卧虎藏龙
老师和同窗
“半玩半读”上初中
困难时期的伙食
主动放弃中的同学
他们不能高中
令人敬佩的江一真父子
“斋”里奏响《骑兵进行曲》
山雨欲来
政治教育、劳动教育
京城的“后”棺葬
不知道为何而欢庆
群众自己闹
走在串联的大路小路上
骑车去天津取经
成为“不三不四”派
河南的“近期新形势”
在新疆见证氢弹爆炸
长沙观战
“怎么能忘记呢”
六姨父曾列席五大
再见四中,再见北京
西藏岁月
“传言”促我决心赴藏
曲折进藏路
10个月军营生活
还“上山下乡”吗?
26岁的候补委员
安家落户,挥镰割青稞
藏族农家的“开门七件事”
跨越千里的盐粮交换
独特的婚葬礼俗
三人分上新岗同伴各奔东西
碰壁的“烧炭改革”
编筐缝纫做豆腐养猪
出差探故知
“电”带来的惊喜
多种经营的尝试
终生愧疚的拦路“打劫”
亲历“一打三反”
告别东来
父亲的“功”与“罪”
偶遇“北京老乡”
成为新闻学徒
亲如手足的室友
次采访
苦涩笑话:火腿“”
学徒挑重担
两军对峙下的亚东
到阿沛家做客
赴藏北“蹲点采访”
三闯“生命禁区”
草食动物也“吃荤”
可可西里18天
这里曾经是海底
高原春风迟迟来
巧遇老,笑“怼”托马斯
大学梦碎,赌气赴昌都
川藏线上经“四季”
茶马古道镇芒康
类乌齐驯养马鹿
丁青:“玛尼世界”
亚塔打破“大锅饭”
记者行路难
探访险恶之地三岩
康巴流行的婚姻形式
被雪灼伤
一方土地养不了一方人
牧区的宰杀季
1980,转折之年
协助“钦差”调查
曾经的第二敦煌萨迦
远眺珠穆朗玛,近观希夏邦马
樟木偶遇“小叛匪”
离藏前的忧思
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辍学”12年的们
“春意盎然”的报社大院
政治部的“政治”
保山“新伤”引旧痛
无声巨浪迎面来
谦和、睿智的老李
新兵也“通天”
前辈的“熏蒸”
在新乡重逢刘源
“逼”省委书记接受采访
随行杜润生
乡镇企业:“十全大补丸”
两岸“三通”始于民
“农”“工”合组经济部
漫行、漫记西双版纳
农村遍地是“八仙”
倔强的草根
体验下乡“收猪难”
市场经济和“饭票新闻”
创刊纪念会上的尴尬
“规模经营”乱象与杜润生的智慧
内容简介:
本书是报记者吴长生的个人回忆录,时间跨度为19481988年,从个人视角展现了共和国从童年到青壮年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书分为四章:“童年往事”是祖父、外祖父两个家庭在1950年代由旧入新的过程以及作者本人小学时的经历;“风雨”是作者的中涯;“西藏岁月”是作者1968年到1980年在西藏插队、任记者的经历,以丰富的见闻展现了此一时期西藏的生产与生活;“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作者在报的工作经历与见闻,以个人视角展示了1980年代农村改革生机勃勃、上下同心的时代氛围。
精彩内容:
童年往事
如果从曾祖母吴柳氏“北漂”进京算起,我属于“京四代”。七十多年前,我还没出生,“参政”与“门楼”与我结缘了。前者曾经有我父亲的家,后者则是母亲的出生地。旧北京城的两条老胡同,留下了我童年、和青年的斑斑足迹与难忘记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仍,亿万人裹挟其中,我像一株小草静悄悄地在时代的风雨中成长。这段记忆中既有没落“大宅门”的逸闻,老胡同里的故事,同龄伙伴的经历,形形新旧人物的碎影,也有一个孩子眼中看到的一场场运动的潮起潮落。那是我的童年,也是共和国的童年。
我从长沙来
吴长生,是祖父起的名字。很简单,我是1948年5月4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比我整整大了一个“甲子”的爷爷得讯,给长孙起了这个通俗、上的小名,原来打算待长大后再改“更正规”的,但不知为什么,直到,也没再提改名的事,这么一直叫下来了。后来得知,祖父给我拟的“大号”是吴能,字希贤;弟弟是吴勇,字希英。吴家我们那一辈人的名字中间都是“希”字,但我和弟弟这两个“大号”都没用过,弟弟因生在湖南永兴县而一直叫永生。
父亲一辈名字中间是“崇”字。祖父三兄弟共育八男二女,分别是伯祖父的二男一女、我祖父的二男一女和叔祖父的四男。我亲姑姑叫吴崇一(1921~1929),我的父亲叫吴崇厚(1923~1996)、叔叔叫吴崇慈(1942~)。
为什么生在湖南?因为父亲大学后不久即赶上争结束,动荡中辗转多地,先是东北、天津,1947年被当时的国民资源委员会安排到湖南工作。已经怀孕的母亲贾栾1948年春也从北京到了长沙,并于当年5月生下了我,次年9月生下弟弟。
在湖南,我只生活了三年多,1951年秋天回到北京祖父母身边了,但孩童时的一些“碎片”仍牢牢地储存在脑海中,时时浮现在眼前。
其一,我的湖南家。那是湘南矿务局下属的湘永矿区,宿舍是一长溜房,我家是其中的一套。门朝南开,有五台阶,宽大的正室后面是灶房,后面还有个小院,烧的是柴和煤。门前台阶下是一条土路,路南侧是一大片荒地。应该是1950年冬天吧,我领着一岁多的弟弟到草地里去玩,发现几丛直立的草秆顶着一个小小的鸟窝,里面有两个青白的小鸟蛋!我让弟弟一手一个拿着鸟蛋,往家走。没想到他只顾手里的鸟蛋,没注意脚下,一不小心摔了个大马趴,手里的鸟蛋都碎了。六七十年过去,那浅黄的草秆、青白的蛋壳,还历历在目。
其二,戏水。一个夏天的傍晚,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宿舍附近的河里去玩水。母亲带着我、弟弟和小保姆梅文,坐在河边的浅滩水里嬉戏。河底的小卵石清晰可见,还不时有小鱼游来游去。父亲则在七八米外的深水处游泳,还露着头向我们招手。
其三,看杀虎。上午,门外突然有人往西跑,有人喊:猎户打到老虎了!听说打到了老虎,矿的工作人员都跑去看,父母亲一人抱一个,带我们也来到了杀虎现场。几十人的圆圈中间,几个头上包着布巾的大汉正围着一只已经开了膛的老虎剥皮。我是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这一场景的。
其四,弟弟被扔在路边。一次矿上放电影,邻居的大孩子抱着一岁多的弟弟,拉着两岁多的我一起往俱乐部走。走到半路,那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抱不动弟弟了,把他放在路边,拉着我继续走。我不肯走,他们撒腿跑了。我不知怎么办,守在弟弟身边哭起来。母亲闻讯赶来,问明情况,把我们领回了家。
其五,火车上扔拖鞋。1951年8月,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是普通的硬座车,在硬板木条座椅上,我和弟弟上蹿下跳,惊奇地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在湖南、湖北境内,天气不冷,母亲带了临时穿的木板拖鞋。为了“检测”火车的速度,我和弟弟趁母亲不注意,把一只拖鞋从半开的车窗扔了出去,眼看它瞬间没了踪影。母亲歇息片刻后伸脚找鞋时,发现画着油漆花纹的拖鞋只剩一只了。我们只好承认是我们扔出去了,是想看看它能“跑”多快。
至于湖南的人,只记得小保姆叫梅文,样子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对据说曾非常喜欢我们兄弟的“黄妈妈”“洪伯伯”“洪妈妈”,我一直记得他们的模样,直到十几年后重逢,但人家怎么喜欢我们,却没有半点印象了。初到北京,我一湖南乡音,“吃饭”说成“恰反”,“取”说成“酋”。一京腔的曾祖母,不止一次地给我纠正发音。很快,湖南长沙留在我身上的印记淡下去了,但“长生”这个名字已经伴随了我七十多年。
p13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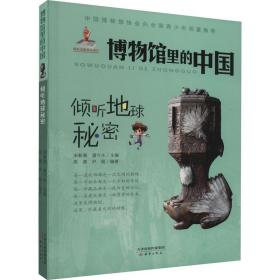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