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林书信集 卷2 启蒙岁月:1946-1960(2册) 外国哲学 (英)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新华正版
《伯林书信集》第二卷,记录伯林1946至1960年的青壮年生涯,重返牛津,学术转变,父亲去世,成为丈夫……个人身心的成熟,战后世界的变化,皆体现在书信中
¥ 90.84 4.8折 ¥ 188 全新
库存8件
作者(英)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75045
出版时间2019-04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页数1537页
定价188元
货号xhwx_1201875965
上书时间2023-12-26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 商品描述
-
主编:
伯林书信集(卷二)的信件比卷的涉及面更广,题材也更加多样。随着年岁的增长,伯林书信在知识方面的内容有明显增加,许多信件对其公开出版的著作提供了详尽的解释和背景交代;还有许多信件涉及各类书籍、音乐、城市、乡村,更多是围绕人有感而发,视角敏锐,并往往尖酸刻薄。之,这一时期伯林的书信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丰富又个鲜明的视角,来审视这些书信背后的时代。他的书信还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他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
目录:
序言
书信
幕间插曲
1946-1948:新学院
1949:哈佛大学
1949-1951:新学院与全灵学院
1951-1952:哈佛与布林莫尔学院
1952-1953:全灵学院
1953:哈佛大学
1953-1955:全灵学院
1955-1956:芝加哥与纽约
1956-1957:婚姻与盛名
1957-1960:齐切利讲席教授
附录
英美关系的困境
美国大学的知识分子生活
《瓦戈医生》
如何定义“犹太人”
年表:1946-1960
重要人物生
通信人与信件来源索引
索引
译后记
内容简介:
伯林书信集(卷二)的时间跨度自1946年至1960年,记录了伯林在战后重返牛津大学作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在此期间,伯林克服了很初的学术挫折和自我怀疑,从哲学转向思想史研究,并由此绽放了辉煌的学术生命。同时,他的私人生活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经历了父亲去世引发的情感波澜,开始了对有夫之妇艾琳?哈尔本的追求,并与其在1956年走入婚姻殿堂,完成了从单身汉到丈夫与继父的转变。伯林生命中这一段启迪他人也成熟自己的闪光年华,生动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书信当中。
作者简介:
作者介绍:以赛亚伯林爵士(sirisaiah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有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借撰写卡尔马克思的契机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
如何定义“犹太人”
以下是以赛亚·伯林对戴维·本—古里安一封信件的正式回复(于1959年1月23寄出;具体内容见原文第671页注3)。戴维·本—古里安的信是写给五十多位杰出犹太人的,请教他们关于以列人应该如何对待某些异族通婚所产下后代的问题。
致以列的备忘录
1.我认为当前摆在以列国面前很大的问题是,该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待父亲是犹太人而母亲是非犹太人的孩子。这种情形下,母亲并未改信犹太教,但是父母双方都希望孩子可以在以列登记成为犹太人。还有一个相关问题,机构是否能够接受犹太人因个人原因而不愿归属任何宗派或使用团体所提供的场所设施?当然,这两种类型的人群是有交的。
2.异族通婚生下的后代应该在以列被视为犹太人,并准予登记入籍吗?如果无神论者或非犹太教信仰者宣称自己的国籍为犹太人,那么应该允许他们以无神论者或基督徒等身份登记为犹太人吗?属于后一类人意味着什么呢?它所享有或者被剥夺的与权利又有哪些?
3.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常用词汇至少受到两类定义的影响:(1)按照律、神学或者科学的要求做出的定义,准确清晰却多少带有人工斧凿的痕迹;(2)根据常交流需要而产生的宽泛定义。照我看来,这似乎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事实。据我所知,依照犹太律对“犹太人”所做出的定义,狭义刻板的定义—犹太女子或者皈依犹太教之人所生的儿子—在常语中,它同样有一个更加宽泛的含义。根据这种宽泛的定义,只要任何一个熟知“犹太人”一词惯用的正常人,无须太多虑称另一人为犹太人,那么后者是犹太人(像“table”之所以为桌子,是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桌子。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比如出于某些商业或者律目的,“table”的意思得由人为限定)。从这个词的常规意义来看,我们谈及“不信神的犹太人”的时候,不需要感到自相矛盾了。因为当一个人在绝大多数方面与犹太群体一致无二的时候,我们应将他视作一名犹太人,即使他的母亲没有皈依犹太教,或犹太学者因此而义正词严地拒绝其想要成为意义上—狭义上—犹太人的要求。
4.以列国的存在产生了在律上准确定义“犹太人”的必要,因为非犹太人不能够享有或履行一些属于犹太人的权利与义务。那么,该如何定义“犹太人”呢?
5.在我看来,很显然,以列不能仅仅根据信仰判定其公民甚至居民的身份地位,因为以列宣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而非神权统治的(这点我认为确实如此,并且有理由这么认为)。如果以列不想成为一个神权统治的,或不想强制使用来判定民权,不能仅仅因为一些人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或所信仰的不被以列认可,剥夺其结婚权、离婚权、安葬权等。正如您在信中特别提到的,如果以列不会实施压迫,那么必须允许其居民自由地结婚、离婚,接近不需要借助任何形式的仪式。如果现今由于以列或犹太观念反对的影响,在政治上行不通,会导致程度上的歧视,即便情况不是特别严重;而在公民自由得到现代普遍了解的,只要以列上述情况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如何保障以列所有民众的公民自由这个问题无得到解决。目前这也许还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受到公民婚姻与离婚等制度缺失影响的公民毕竟只是少数;但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却是一个污点。尽管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与精神问题,但否认它的存在将毫无益处。
6.如果以列准备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现代自由的国度,那么归属不应该左右其公民则,也不会影响其居民应该享有的公民权益与政治权利。但另一方面,很显然,如果犹太教仅仅只是个,而非某种意义上的国籍标志,那以列也不成一国。我认为,单单安全因素虑,可以要求以列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去登记注册,选择是继续当犹太人,还是放弃犹太身份。一些人被视作犹太人(在其犹太或非犹太的社交圈子中),这是从“犹太”这个词很常见的含义来判断的;但依据拉比们按照传统接受的方式对犹太教律哈拉卡的解读来看,他们却非犹太族,对于这类人,在政治和律意义上,他们究竟该不该被当作犹太人呢?对此问题,并没有一个保证的或是现成的。如果我们打算消除高压政策,哪怕是很很温和的—受俗和公众舆论的压力而不得不为,因为它与个人自由的大力度优惠要求相违背(而且我看不出道义上以列有何理由做不到这一点,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坚持自由,犹太复国主义才得以诞生)—那么,必然存在这么一类人,他们有权只在国籍上登记成为犹太人,而不用加入犹太教。那么,该用什么标准来判定哪些人属于这一类别呢?我认为,常识的标准似乎已经接近了—人们认为某人是犹太人,那么他是犹太人,尤其是在那些以列以外的犹太人聚居国,在那些非犹太邻居的眼中。但是,这一标准似乎又有些不够明确,有些模糊不清。我们可以新建一条标准,例如某些以列人,我相信也包括您自己在内,所提出的宣告:某人未信仰其他任何,因此渴望成为一名犹太人。对此,有人发出反对之声,称这一标准的定义太过笼统,它甚至可以涵盖一个通常在别人眼中根本不是犹太人的人,例如前纳粹异教徒;同时,又太狭窄,这是因为,原则上该标准具有可行,但实际上却几乎没有人会遵循这一标准,何况这条标准看起来是多么不合时宜,设想,一个人,只要愿意,接近可以国籍是犹太籍,却信仰、教,或是其他什么。设一个犹太人,或一个阿拉伯人,又或亚美尼亚人,国籍都可以为其保留,但如果因为他信仰了,他的许多政治权利会被自动剥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歧视。或许你会说这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因为,目前而言,这还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因为想要在以列用犹太人身份生活,却又信仰非犹太教的怪人并不是很多。然而,问题在于,或许有(比如,的传教士们成功说服人们转信基督),这一现象变得普遍,原则践行变得举足轻重了。因此,只要《回归》 仍具效力,或许解决问题的很好方案是借助一些临时机构来决定这些非典型个案的国籍问题(特事特办):如成立专委会,可以归属现有的部门,也可自成一体,单独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由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组成,由其决定在以列的潜在移民和现有居民中,无论男女老少,谁该有资格,谁又不够资格登记入籍为(政治意义上的)犹太人。由于其特殊,这个机构不可能得到任何清晰的指令。他们只能听从民意,跟随理智之光,遵守公共常识。我本该想到以下两类人:(1)生活在以列之外,却仍保留犹太人生活方式的人,例如,某个人的母亲并非犹太人,但在犹太人社区中,他被一致认可为犹太人。如果他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拒绝加入犹太国籍,而不仅是犹太教团体,对他无异于严苛的惩罚。这些人当然会选择接受正规的改变信仰仪式(例如,我听说已故的英国勋爵迈尔切特是这么做的)。然而,一旦他们没有这么做,将从政治上拒绝他们加入犹太团体,直到他们履行仪式为止。在我看来这一点毫无理由,极其严酷。(2)同样,异族通婚者的小孩,父亲希望能够按犹太人的方式抚养他,我认为,应该允许其登记为犹太人。正如预期的,小孩在以列与其他的犹太人一起成长,也必然会产生足够的同化效应。如果我是登记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会倾向前面的决定。但如果其他专家不这么认为,那也只能随其便了。
7.希伯来当局势必所然,也颇为合理地不把这一群人视为犹太人。因此,他们将面临某种不可避的社会压力。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来止这种强制行为,或越过横亘在他们与世界各地犹太人团体正式成员之间很后的藩篱,改变信仰,真正皈依犹太教,也一样无济于事。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很可能对接受和实践犹太教义,至少是犹太教律中规定的起码要求并无异议。但也有些人选择不这么做。其结果是离开以列后,可能会发现在其他地方,他们不被认作是犹太人团体中的一员。这是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必然的结果,对其成员提出情理之中的大力度优惠要求,不让他们因为政治、律、道德或是任何非原因放松自己。但这样的人通常少之又少,而且在我看来,将以列和离散的犹太人联系起来的纽带也不会因为此类人的存在或他们的反常身份而折断,甚至紧绷。这里我要再次重申我之前的观点,除了通过对每个具体个案做出定夺的专门委员会,我找不到任何能够很终确定这群人身份的方。我们需要通过他们来判断,某人是否符合作为以列犹太人团体一员的条件,这些条件可以清晰感受,却往往无明确定义。
8.如果有人感到,对于这样一个解决方,以列的公众舆论尚未成熟,甚至可能会被它激怒,在以列靠前导致激烈的争端,很终造成以列与其边界之外的犹太人团体分裂,之,如果想要避势必带来痛苦后果的正面提前到来,我认为应该未雨绸缪,为这些成问题的个案人等提供一个临时身份。例如:未皈依的非犹太裔家庭的,以列犹太人未皈依的妻子(她们希望能够在犹太人团体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及类似的各人等,可以不在政治上定为“犹太人”,却可以登记为“犹太人出生;父亲为犹太人”;或是“犹太人妻子”,“爷爷或外公是犹太人”,诸如此类。先是简单记录事实,然后为他们预想出一个特殊身份,逐渐使之固定化。在这个尚未确定的真空地带中,这些人要么很终被犹太人团体有效同化,要么从中有效退出,很差的情况是,继续无限期地成为临界个案,直到更自由的立在政治上可行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自由地被吸纳进犹太人组织,成为其一部分,而不会遭到太多人的非议。这不是一个万全之策,但上述情况下,这是我能想到的很少痛苦的方。这种情形只能是暂时现象,否则绝不能容忍,没有比允许某一类公民较为处于低人一等的处境更邪恶并具有破坏的事了—混血的犹太人,无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像在其他出现的反闪米特人迫害行动中被丑化的令人厌恶的讽刺画一样。如果当局目前无尽快克服对这类人自由融合的抵制,那么,与其说让他们身处低人一等的少数族群恐怖境地,倒不如不让他们移民为好。
9.我必须承认,我发现很难去相信,常被人认为是犹太人的人(至少被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人,那些在乎成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人),尽管他们按照严格的犹太教律要求并不接近够格,但这些人在犹太人团体内的接受度,竟然会在以列或是在以列和外界的犹太人中导致深深的裂痕。但关于这点,我也很可能弄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应该有先入之见。从历史的观点上来说,犹太教、犹太种族和所有组成犹太的因素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持久的实体。这个实体无严丝合缝地融入现代西方的政治模式。以列国的兴起只可能通过允许—不是鼓励—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人来追寻其独立的事业,从而实现犹太人的“正常化”。这似乎既不是可以避的,也不会令人不快:人们当然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尽可能少地对犹太信仰和忠诚产生不良影响,但我怀疑这种不会冒犯到任何人的愿望能否实现。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对自己的“解决方案”也不甚满意。
以赛亚·伯林
精彩书评:
讽刺、八卦、机智、诙谐,时有深邃思想,但始终充满对人的热切关注。——星期电讯报以赛亚?伯林是一位谈话高手。读者会在字里行间看到他一如既往的风格:洋溢着谐趣、智慧和对人的洞察。——经济学人不出所料,阅读这卷伯林书信的辉煌合集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丰富多彩,不可抗拒。——新共和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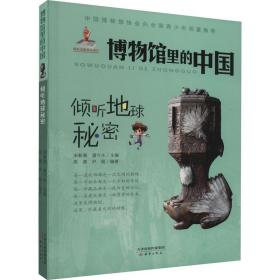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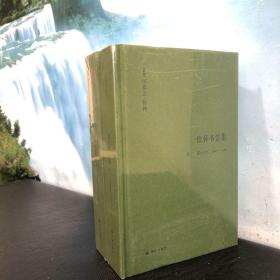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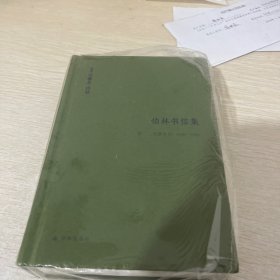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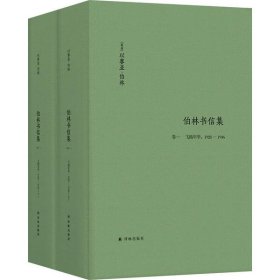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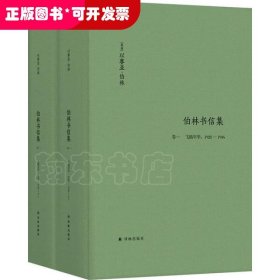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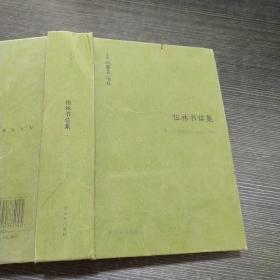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