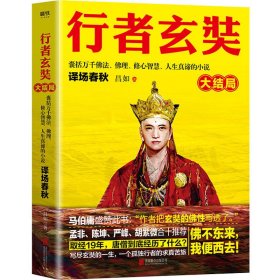
行者玄奘 大结局
¥ 50.6 ¥ 45 八五品
库存2件
河北保定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昌如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ISBN9787559631701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5元
货号9787559631701
上书时间2024-03-09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 商品描述
-
导语摘要
\"◆亲王马伯庸看完此书,拍掌称赞:“作者把玄奘的佛性写透了。”孟非、陈坤、严峰教授、沈浩波……数十位名人合十推荐,中国著名CG插画师翁子扬读后赞叹不已,主动为此书绘制精美插图!
◆取经19年,唐僧到底经历了什么?翻开此书,走进高僧玄奘的传奇人生,倾听一个充满奇遇的真实故事,重走那段关于苦闷、烦恼与解脱的人性之旅。一部讲述信念与勇气的旷世奇书,佛不东来,我便西去!
◆佛陀告诉人的法是什么?是无穷无尽的慈悲,是无拘无束的自在,是刚正不阿的骨气,是众生平等的胸怀,是无与伦比的智慧,是真实不虚的存在。一部关于信念与勇气的旷世奇书,囊括万千佛法、佛理、修心智慧与人生真谛,写尽玄奘法师的一生,一个孤独行者的的求真苦旅。
◆新兴的大唐王朝、马背上的突厥人、神秘的中亚、多种思想大碰撞的印度……历时19年,途经56国和110个城市,取回1335卷经文,行走5万里路,成就了人类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徒步修行之旅。\"
内容摘要
\\\\\\\\\\\\\\\\\\\\\\\\\\\\\\\"贞观二十二年,玄奘重回大唐已三载有余,在李世民的扶持下,建弘福寺译场得传万卷佛法。
当此时,贤臣相继离世,年迈的皇帝数次提出要玄奘还俗佐政的要求,却都被他婉言谢绝。二人数度长谈,论生死、佛法甚至权谋……无所禁忌,太宗将玄奘视为挚友。直至离世,太宗一生的心里话只说给了玄奘。
李治即位后建立了多所道观,对佛门却是明里褒奖暗里限制。玄奘为保存佛国的梵本,力促修建大雁塔。塔落成后,长安佛学更加隆盛,络绎不绝的外国学僧来到长安游学。玄奘毕生醉心于此,得见佛学盛世可谓满足至极。但李治对佛教的限制愈多,在释道辩论、寺庙的修建中偏向道教,暂停翻译经文,破制迎武后……玄奘在皇帝的步步贬抑中,又将如何求索、弘扬佛学智慧?
19年+56个国家+110个城市+1335卷经文+5万里路=玄奘西行。新兴的大唐王朝、马背上的突厥人、神秘的中亚、多种思想大碰撞的印度……一一展现在玄奘这样一个孤独行者的求真苦旅中,成就了人类徒步史上难以逾越的伟大的探险。\\\\\\\\\\\\\\\\\\\\\\\\\\\\\\\"
精彩内容
\\\\\\\\\\\\\\\\\\\\\\\\\\\\\\\"第01章终我一生,不夺我志转眼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尚未过去,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逝。
这个帝国重臣的离去对李世民打击很大,而在此之前的数年间,还有魏徵、高士廉等重臣相继逝去。皇帝身边一下子感觉凋零了许多。
这年四月,得知宋国公萧瑀和梁国公房玄龄病重的消息后,李世民的身体和情绪变得越来越坏,以致风疾复发,头痛不已。
偏偏这个夏天又异常炎热,太阳像一团火,无情地燎烧着大地。人们即使待在屋里不动也会出一身大汗。偶尔天降暴雨,如帘如瀑,却浇不去那弥漫于天地间的热浪和暑气。
李世民一向怕热,这样的天气自然在京城里待不住,于是驾幸长安北郊的玉华宫避暑。
然而这个关中地区最大最美的皇家行宫能避酷暑,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环顾左右,亲朋故旧一个个相继故去,没死的也都垂垂老矣,一些新纳的人才又因介入皇储之争的旋涡太深,而失去了他的信任。残酷的现实使得李世民心中生起一股无可奈何的凄凉与悲怆,以致焦躁上火,对未知的死亡的恐惧更令这个逐步迈入老年的皇帝心力交瘁。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还在长安的酷暑下辛苦译经的玄奘。这是个在朝野上下都有着莫大影响力的高僧,不仅德高望重、博学多才,更难得的是洞察世情。记得在长安时,每次同他交流之后,李世民都觉得自己的情绪缓和了许多。
如今的他迫切地想要见到这个僧人,想同他说说话、聊聊天,听听那些行云流水般引经据典的表达,以及各种有趣的异域传说。
同皇帝相反,此时的玄奘正处于心情上佳之际。炎热的夏天对他的身体并无坏处,干燥、高温和日晒让他的寒症缓解了许多。
而最令他感到愉快的是,五月十五日,他刚刚率领译场众德完成了《瑜伽师地论》的翻译,总计一百卷。这是他当年西行求法的初衷,自然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如今亲眼看着这部梵文大论变成一排排优美的汉文,法师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这笑容感染了他的助手们,整个译场都充满了盈盈喜气。
译完《瑜伽师地论》的当天,玄奘又翻译了印度胜论派学者慧月所撰的《胜宗十句义论》一卷。
所谓“句义”类似于范畴,十句义指的是:实体、性质、运动、普遍、特殊、内属、可能、非可能、亦同亦异、非存在这十个概念。
《胜宗十句义论》把宇宙万象,包括具体的和抽象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纳入这十个句义之内。此外,在认识论上,它承认现量和比量,并强调只有全面理解十句义,才能获得真知和解脱。
玄奘之所以翻译这部外道论书,显然是认为,其与佛法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就在玄奘做好准备,即将启译下一部佛教经典时,皇帝的传诏到了,请玄奘法师来玉华山避暑陪驾。
对于这道诏令,玄奘的心中并不抗拒,甚至有些欣然。
自从回到长安,在弘福寺内组建译场,迄今已有三年了。三年来,他从未踏出过长安城半步。这一方面是由于译经的忙碌,另一方面也来自朝廷的监管。如今刚刚结束《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能有机会出城透透气,轻松一下,总是一件好事。
几个弟子想与师父同行,玄奘劝慰了几句,还是将他们留在了长安。道归年纪还小,怀素是俗家弟子,都不方便带出去。至于玄觉,这沙弥是麹文泰的幼子,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容貌上的相似怎么也遮挡不住,玄奘可不敢让他跟皇帝见面。
玉华山距长安三百余里,玄奘与皇宫派来的十几名侍卫一同骑马前行。
一路上天气晴朗,阳光毫无遮挡地洒向地面,透入每一颗石子的缝隙间。整个大地都在冒烟,就连天空也仿佛被灼热的太阳烤掉了色,呈现出一种索然无味的淡蓝。
侍卫们早已热得满头大汗,使劲拿袖子擦拭。转头瞧见玄奘一脸的风轻云淡,似乎那满天的暑气未曾侵袭到他分毫,不禁好奇地问道:“这么热的天,法师竟然不出汗,莫非真有神通不成?”玄奘微微一笑,手执佛珠轻吟道:“人人避暑走如狂,唯有禅师不出房。非是禅房无热恼,为人心静身即凉。”听到这个偈语,众人只觉得一阵微雨拂过心头,顿觉清凉舒畅。
玄奘毕竟是经历过印度酷暑的人,对这样的天气自然不甚介意。况且眼下这点儿路,比起那漫漫五万里的西行路来,也实在算不了什么。反倒是这几年被禁锢在长安弘福寺里,有些憋闷和不习惯了。
一路上,他见缝插针,不时地讲些经文和佛理故事给侍卫们听,以缓解他们心头的暑热。虽然辛苦,却有无数法味在心头。
就这样一路兼程,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天路,终于看到了玉华山。
一进山来,立刻感到凉风习习。眼前绿树葱茏,风景秀丽,加上最近下了几场透雨,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小溪从茂密的森林中穿流而过,山风中带着松木的幽香,满身的暑气悄然消去。
玄奘心中十分欢喜。他一向认为,大自然的清净与神奇,是通往佛境的最佳助力。而眼前这座山似乎更合他的心意,恍惚间竟觉得这满山的松林都与自己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宿缘。
走了这一路,原本想先安顿下来沐浴更衣,谁知前来迎接的皇家侍卫却不同意,执意要他先去面见皇帝。玄奘无奈,也只得随他们了。
在几名军士的引领下,玄奘进入行宫区域,穿梭在层层叠叠的殿宇之中。身旁是大片的松木以及间杂其中的潺潺水流,这些水沿着山势蜿蜒流淌,每到一处平坦之地,便汇聚成一个水池,池边建有凉亭或殿宇,整个行宫笼罩在一片迷蒙的烟雾之中。
一路上曲折回绕,终于来到行宫最大的一座宫殿前。
从外面看,此殿以松木为墙,茅草覆顶,显得朴素而又风雅。然而进到殿内,却恍如回到了长安太极宫,别有一番奢华景致。
李世民身着一袭轻薄的便衣,坐在精致的软席上,品咂着琉璃盏中加了冰粒的葡萄浆。看似安逸,却是眉峰紧锁,神色深沉。
见到风尘仆仆的玄奘,皇帝脸上的阴云方才消散,现出几分欢喜之色:“朕在京城酷暑难耐,故来此山宫静养。只有到了这泉石清凉的地方,朕才觉得气力稍有恢复。只是许久未见法师,甚是思念,便想借此机会与法师一聚。累法师跑了这么远的路,实在是辛苦了。”玄奘微笑道:“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听闻陛下圣体欠安,玄奘心中也不安稳,只盼陛下能早日恢复清健。玄奘只是一介寻常比丘,蒙诏伴驾乃是幸事,没有什么辛苦的。”他轻轻道来,语气中自有一番恳切的情意,令皇帝感到十分舒服。
李世民亲手斟了一盏葡萄浆,递给玄奘:“法师在西域时,想必常喝这个。如今也来尝尝咱们大唐自酿的葡萄浆味道如何。”玄奘合掌致谢,接过杯盏赞赏地看了一眼——晶莹剔透的琉璃盏中,那晃动的液体犹如柔软的红玉,色泽艳丽,形象华贵,干净透亮。
轻轻饮上一小口,又觉得味道与西域的葡萄浆并不完全相同,在那熟悉的酸甜与冰凉中,竟含有一股特殊的辛辣之气!
“陛下,这是……”细细感受着那股辣意,玄奘不禁呆住了。
李世民却像个孩子一般拊掌大笑起来:“怎么样,法师?咱们大唐的葡萄浆味道还不错吧?这可是朕亲手酿造的呢!”这皇帝还真是越来越像个小孩子了。玄奘无奈摇头,将琉璃盏轻轻放在案上。
“陛下酿的葡萄酒确实漂亮,只是不该拿我这出家人寻开心。”“谁说是葡萄酒了?这分明就是葡萄浆!”皇帝摆出一副不讲道理的架势,“法师快快饮了,朕亲手给你斟的,你还拿架子不成!”玄奘微笑道:“沙门素喜清淡,吃不得辣。”“你这和尚,这般挑食,当初也不知是怎么去的西天!”李世民有些悻悻的,却也并不勉强。
闲谈几句后,便转入了正题:“朕请法师来,一为叙谈,二来嘛,还有一事相求,不知法师能允否?”“请陛下垂询。”“几个月前马周去世,法师听说了吧?”玄奘默然点头。
李世民眼中流露出几分伤感:“中书省事务繁多,按例应由两人共同出任中书令。可是自从岑文本去世后,中书令就只剩下了马周一人,也确实辛苦他了。几个月前朕刚刚任命了褚遂良,马卿却又逝去了……”皇帝说到这里就忍不住落泪,玄奘劝说道:“生老病死,乃世间无常之事,陛下也不必太过伤怀了。”李世民摇头道:“短短数年时间,魏徵、高士廉、马周相继病逝。如今萧瑀和房玄龄也都卧病在床,朕已接他们来玉华休养。可是据御医说,他们也都不太好……现在朝中只有长孙无忌、褚遂良这少数几个人撑着,而太子又年少学浅,并无建树。朕心中实在不安哪。”玄奘沉默不语,他见过太子,自然知道皇帝的不安来自何处。
印象中那个年轻人苍白清秀,若有病容。目光柔弱恭顺,毫无他父亲那种威风凛凛的帝王气象。
这样的太子,也难怪皇帝担忧。
可是再怎么说,这个太子也是他亲口册立的。身为帝王,李世民自然有自己的考虑。何况玄奘是个出世的僧侣,对于朝中之事,能不说话就尽量不说了。
然而这时,皇帝却已将热切的目光望向了他:“法师高才,世所罕见。若不嫌朝务烦琐,请到朝中任中书令如何?”玄奘闻言不觉一怔。自回国以来,皇帝已数次提出要他还俗佐政的要求,都被他婉言谢绝。谁料今天竟然直截了当地请他出任中书令一职。要知道,这可相当于宰相之位呀!
他心下感动,起身谢绝道:“沙门玄奘,多谢陛下圣恩。只是朝廷命官关乎天下安危和百姓祸福。玄奘一介比丘,释门之人,素来只知虔心向佛,从未入朝为官。陛下如今要我入仕高位,担任如此重要的职位,只怕玄奘力不从心,难以胜任。还望陛下三思。”李世民叹道:“法师还是曲言推托。朕让法师入仕中书省对佛法产生了兴趣,固然是因为《瑜伽师地论》本身的玄奥以及玄奘出色的解说吸引了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宋国公萧瑀在到达玉华宫没几天就病逝了,享年七十四岁。此时距他的姐姐萧皇后去世仅三个月。
这位亡国皇家的后裔,三朝贵戚,在隋唐两朝皆处于朝廷的权力中心。其一生大起大落,五次拜相、五次罢相,甚至一度被逐出京城。
这样一个人物的离世,给李世民带来悲伤的同时,更有无数感慨在心头。虽然萧瑀性格执拗,屡次与他争吵,弄得君臣两不痛快,但怎么说也是沾亲带故,当年在他谋取皇位的过程中出力不小,又辅政多年,成就盛世之业。感情自然非同一般。
萧瑀去世后,李世民赠其为司空、荆州都督,让其陪葬昭陵,可谓极尽哀荣。但在谥号一事上,皇帝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时太常寺拟谥号为“肃”,被李世民驳回,改为“贞褊”。这是个褒贬各半的谥号,既赞扬其“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坚贞性格,又表其性格褊狭之意。萧瑀此时长眠于地下,自然无法再与皇帝理论,只能任由其评判自己了。
而此时,另一位重病的宰相房玄龄,身体状况也极为不佳。李世民请宫中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并亲临探望。
房玄龄大为感动,拉着皇帝的手流泪道:“臣以布衣之身得遇陛下,遂成就一生富贵。陛下对臣恩深厚德,尽心如此。臣唯有感激涕零,不知所言。”悲泣了一会儿后,他又劝谏道:“当今天下清平,唯陛下东讨高丽未止,此为国患也!陛下含怒意决,一众臣下莫敢犯颜。老臣若是再知而不言,真是愧为人臣,会含恨而终的啊!《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的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土开疆亦可止矣。还请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停止征讨高丽。臣旦夕入地,倘蒙陛下纳此哀鸣,死而无憾!”这一番话说得声泪俱下,李世民听得也是黯然神伤,出来后便对房玄龄的儿媳高阳公主道:“你公公病得如此厉害,还在忧我国家,真是难得的良臣啊!”说罢潸然泪下,悲痛得不能自禁。
话虽如此,李世民依然没有放弃征讨高丽的打算。他敕令越州都督府以及婺、洪等州修造海船及双舫战船一千一百艘,以征伐高丽。致使雅、邛、眉三州的造船民工因不堪重负而造反。加上连年干旱,蜀地粮价猛涨,又引起剑阁一带发生骚乱。
就连玄奘也开始劝谏了,虽然明知这并非一个僧人的本分。
李世民却说:“非是朕过于狂执,只是辽东一带原本就是我中原王朝的地域。当年隋炀帝四次派兵出征而不能取胜,反而折损数十万兵马,此为国殇也。朕执意东征,也是想为中原子弟报其父兄之仇,为高丽百姓雪其国王被杀之辱。况且如今四方都已平定,只这一小块地方未平,朕心中实在不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执念,而李世民的执念似乎更加强烈,玄奘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况且他心里也明白,这种事情原本就是对错难辨的,多说无益,也只好缄口不言了。
虽然李世民雄心勃勃,其身体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很多事情已渐渐地有心而无力。特别是患了风疾之后,他开始对死亡产生了恐惧,竟然迷上了术士们提炼的金石丹药,指望借助这种神秘的外力来益寿延年、长生不老。
皇帝有了长生之念,自然便会有人投其所好,进献了许多据说是灵妙无比的丹药。李世民服用后,也确实有过短暂的兴奋,然而兴奋后的身体往往更加虚弱。
“长生之术终究还是无法验证啊。”他与玄奘在殿外松林中对坐品茗,悲哀地说道,“朕最初服食丹药时,还有些效果。现在却是越来越淡了。”玄奘迟疑了一下,低声劝道:“陛下,您能不吃那些丹药吗?”李世民猛地抬头,目光瞬间变得凌厉起来:“怎么,法师觉得那些丹药有问题?”“不是。”玄奘垂目道,“沙门只是觉得,生老病死,本意就是想让乃人间常事,世人对生命的执着愈深,面对死亡时的痛苦也就愈甚。陛下深具智慧,此事原不用沙门多言的。”李世民轻哼一声,冷冷地问道:“话虽如此,但是法师不也通晓医术,时常给人治病吗?若是不执着于生死,又何必治病?”玄奘道:“人之所以生病,原因有二:一是四大不调,二是业障现前。前者为身病,后者为心病。治心病要用佛法,治身病可用世法,也就是陛下所说的医术。若能二者兼施,则疾病易除。”“那么法师觉得,朕现在所患的,是身病还是心病?”“二者皆有。”李世民看着眼前的僧人,笑了:“法师倒是敢说话。”玄奘俯身抓起一把沙子,握在手上攥紧,那沙子便飞速地从指缝间漏了下去。
“陛下请看,光阴就像这指间的沙,你越是想拼命挽留,它流失得就越快。”李世民望着那飞速落地的沙子发了一会儿呆,终于长叹了一声。
“法师啊,其实你什么都不必说,朕心里都明白。这长生之术终究渺茫,当年秦皇汉武都做不到的事情,朕却想做到,实在是逆天而行。可是尽管如此,朕还是想服食丹药,不为别的,只是心有不甘罢了。”玄奘道:“陛下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又何必非要执着于永生?”皇帝的脸上漾起一丝苦笑:“印记?印记有什么用?终究是无常的。”“但是生命更加无常,有些印记存在的时间会比生命更长久。”“法师说得没错,但是朕还是想永生。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即使留下了印记,也没有人能代替‘我’去感受。当我死亡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也许还可以在别的世界存在,也许哪里都没有‘我’,‘我’永远都不存在了。我想长生,就是想要永远地存在下去。这大概是一种生命的本能吧。”玄奘道:“是本能,也是执着。而且,这样的执着只能给自己增添烦恼。”李世民黯然点头:“是啊,朕现在就烦恼重重。如果有对手站在我的面前,我自然不会惧怕。但是死亡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始皇帝对此不甘心,我也不甘心。你们佛门讲来生,但是朕对来生不感兴趣,朕就喜欢今生,不管今生有多少烦恼,我都希望能够一直延续下去。我可以做出这个选择吗?听说,行十善之人,来世可以有生入天道的善报,那里的寿命很长、快乐很多。那么,他可不可以选择吃点儿亏,放弃天道以求得今生的不死?这样两世并为一世,可以吗?”玄奘苦笑道:“陛下,今生的死亡也是一种果。我们之所以生在这个寿命短暂的世间,必定是有这个因的存在。因果是不可能相互抵消的。就好比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陛下总不能说:‘我宁愿吃点儿亏,放弃瓜,多换一点儿豆。’因果可不是这样算的,豆子再小,没有种子也结不出来。”“那么行善有什么用呢?果报再好也还是要跟着因果走,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玄奘道:“单独的行善确实是不究竟的,所以陛下若是不想跟着因果走,那就只有修行。等修到阿罗汉或菩萨的果位,就可以自由地选择来去了。”“可是朕现在没有修行证果,却又不想死。除了丹药,朕该往何处用力呢?”“陛下……”李世民摆了摆手:“我知道法师想说什么,其实朕对这些丹药也不是特别相信。不过话说回来,就算这些丹药不能长生,总可以拿来养生吧?朕见过很多修道之人,他们年逾高龄仍步履矫健,有如少年。即使是那些道行低的,看起来也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可见服食丹药还是有用的。”玄奘道:“陛下,沙门以为,他们年逾高龄而身轻体健,当是修行所致,而非丹药所致。”“法师又焉知他们不服丹药?朕当年曾见过一个老神仙,名叫孙思邈的,法师可听说过吗?”————————————[1]此句出自玄奘所译的《解深密经》。\\\\\\\\\\\\\\\\\\\\\\\\\\\\\\\"法师辅政论道,统和天人,间以佛理教化天下。至于那些烦琐的庶务,自有他人办理,并不劳法师亲自动手。莫非法师还要推托不成?”说最后一句话时,皇帝的脸色明显变得严肃起来,双目犀利如箭,原本的和颜悦色荡然无存,又回到了那个傲视天下的天可汗的状态之中。
然而玄奘还是郑重回绝:“陛下乃上智之君,当知纳士用人所长。玄奘所长只在于研修佛理、翻译经论,其余诸事皆力有不逮。”皇帝的眉头皱了起来,脸上阴云密布,看向玄奘的目光也变得锐利如电。
然而眼前的僧人却似毫无知觉一般,只是静静凝望着自己的君王,低声说道:“陛下,受戒缁门,阐扬遗法,乃是玄奘平生最大的心愿。还望陛下大慈大悲,终我一生,不夺我志。”这番话显然是要皇帝在他有生之年都不要再提此事了,虽是求恳的语气,却无丝毫畏缩之意,实可谓绵里藏针。
李世民心中不悦,却也得地没有生气,而对这个看似柔弱谦卑却始终不肯退让的僧人生出几分激赏之情。
终于,他无奈地叹息一声道:“昔日尧舜禹汤之君,隆周强汉之主,莫不仰仗群贤相辅。朕自问比不上明王圣主,当然更需要众贤者的辅助。本欲说服法师脱须菩提之染服,挂维摩诘之素衣。偏偏法师心高气傲,不肯还俗佐朕。”玄奘道:“非是沙门心高气傲,实在是有些自知之明罢了。”李世民点头道:“法师风骨,朕甚是欣赏。倘若佛门之中皆是法师这样的僧人,世间便无灭佛之事了。”“陛下说笑了。常言道,一样米养百样人,岂能要求人人相同?若说有人因此而灭佛,更是无有是处。”李世民笑道:“法师倒是敢说话啊,你这是在责怪朕吗?”“沙门不敢。”李世民认真地看着玄奘,欣赏之余却又带了几分失落。
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开始,他一直在大唐境内抑制佛教,甚至变相灭佛,似乎也收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自从玄奘回来后,他就感到有些棘手了。
这个僧人身上有一种十分独特的人格魅力,佛骨禅心,亦柔亦刚。可以说,从见到他的第一眼起,李世民就一直努力地想让这个僧人脱离佛门——将他所撰的《大唐西域记》用于战争,劝他还俗出仕,逼他翻译《道德经》等诸事,固然有时势方面的因素,然而让其脱佛入俗的念头却始终未曾改变。
可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无论他这个皇帝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眼前的僧人都始终以一种柔软的姿态来应对。既不强力抗拒,也不轻触底线,甚至偶尔还会以攻为守,比如请求皇帝为他的新译经文赐个序什么的。
李世民对此也是万分小心,生怕一不留神就会被这个和尚给绕进去。
这样几番交锋之后,他已然明白了玄奘的底线。这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守自己的目标和信念的僧人,既不为人间艰难所屈,也不为世俗名利所动。哪怕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无法说服他改变初衷。
这些年来,李世民见多了形形色色有志向的人,也见多了稍不如意就说自己怀才不遇的人。如今,面对玄奘的坚守,大唐皇帝竟情不自禁地肃然起敬。
他慨然道:“法师既有志于敷扬妙道,朕也勉强不得。从今往后,自当助师弘道。”“多谢陛下。”既然说了要助师弘道,自然就要过问一下译经的情况了。于是李世民随口问道:“法师最近译的什么经?”玄奘答道:“《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已于五月中旬翻译完毕,现正在翻译《唯识三十论颂》。”话未说完,李世民已然大惊:“一百卷!此论居然如此宏大,里面都说了些什么?”玄奘对皇帝的少见多怪感到无语。佛门中一百卷以上的经文并不罕见,至于这么吃惊吗?看来这个皇帝确实对佛教了解甚少,难怪会生出许多偏见来。
“此论乃是弥勒菩萨所说,又名《十七地论》。玄奘当年之所以西行,初衷便是要取得这部大论。”此言一出,顿时将皇帝的好奇心勾了起来:“能让法师不辞万死冒禁去求的经典,想必很不一般。法师能给朕讲讲吗?”玄奘道:“此论甚大,只怕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清楚。好在沙门已将此论带来,不如陛下亲眼看看?”李世民赶紧摇头:“我不看。你这和尚不安好心,想赚我入佛门吗?朕才不上你的当呢。再说你们佛门的经论也太难解,篇幅又大,一百卷哪!我来此地是休闲避暑的,可不想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搞得太劳神了。”玄奘道:“此论并不难理解,以陛下宏智,一看便知。”李世民道:“就算能读懂,读佛经也是很没意思的一件事。”玄奘笑道:“陛下未曾读过,怎知没有意思?经书都是越读越有意思的。只要陛下认真阅读,沙门敢说,陛下决不会感到扫兴。”李世民不觉有些心动:“那法师倒是说说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求这部大论?它究竟能为你带来什么?”玄奘道:“简单地说,此论是为佛教行者修行成佛之道所依循的根本论典。它将一个人从凡夫到成佛分成了十七个阶段,全面又详尽地介绍了各个阶段的修行次第和境界。”李世民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朕还以为,这是一部关于佛法推理的书,原来竟是修行次第。”玄奘笑道:“陛下,佛法从来都不是推理得来的,而是实证得到的。”接着,他便将这“十七地”的大义,举其纲目,逐一为皇帝做了说明。此论他曾在那烂陀寺认真学习五载,回国后又用了两年时间全力译出,早已熟悉到了骨子里,因而讲授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阻滞。
最后,玄奘总结道:“对修行者而言,此论甚有助益。学佛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了却生死之道。陛下,莫辜负了此生的闻法因缘。”这番话最终打动了李世民,他立即说道:“将此论拿来,朕倒要好好看看,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天书!”玄奘回过头,两名内侍已将他随身携来的一只藤箱搬上来打开,里面是堆放得整整齐齐的卷轴。
“总共一百轴,全在这里了。”玄奘起身合掌,恭恭敬敬地施了个礼,“陛下若是看得好,还请不吝赐序。”这是玄奘第二次为他的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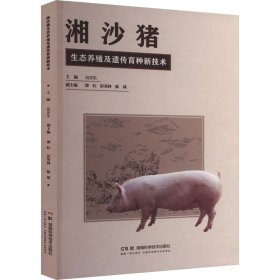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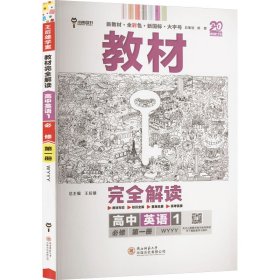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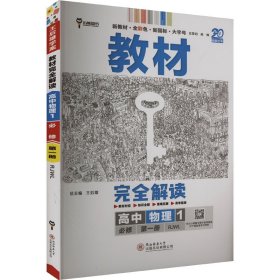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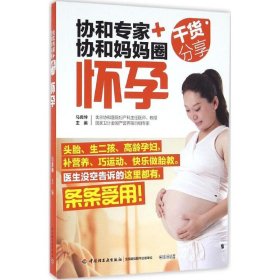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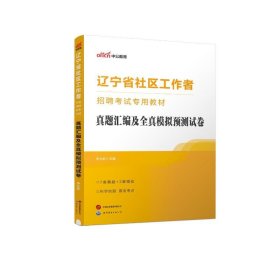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