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乐主义宣言
新华书店全新正版,极速发货,假一罚十,可开电子发票,请放心购买。
¥ 17.1 3.5折 ¥ 49 全新
库存7件
天津西青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法)米歇尔·翁福雷(Michel Onfray) 著;刘成富,王奕涵,段星冬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3725
出版时间2016-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1201392875
上书时间2024-10-1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6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米歇尔·翁福雷(Michel Onfray)(1959-),法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代哲学家。他提出了享乐主义理论。已出版八十多本著作,被三十多个国家翻译和出版。主要著作有《享乐的艺术》《享乐主义宣言》《尼采传》等。
刘成富,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导。代表性译著《消费社会》(波德里亚)、《改变命运:奥朗德自述》(奥朗德)。
王奕涵,南京大学法语系博士生。
段星冬,南京大学法语系2013级硕士。
目录
序言
第一部另一种方法
1另一种平行的哲学
2身体的理性
3哲学的生活
第二部选择性伦理
4无神论的道德
5内在游戏的规则
6享乐主义的主体间性
第三部阳光的情欲
7禁欲典范
8保证自由的力比多
9肉体的殷勤
第四部犬儒主义美学
10群岛式逻辑
11艺术的心理变态学
12犬儒主义艺术
第五部普罗米修斯式的生物伦理学
13摈弃基督教信仰的肉身
14人为的艺术
15浮士德式的身体
第六部自由主义政治
16悲剧的图谱
17享乐主义政治
18实践反抗
享乐主义宣言
内容摘要
《享乐主义宣言》是米歇尔·翁福雷很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哲学理论集大成者,在法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翁福雷推崇尼采和伊壁鸠鲁,推崇左派尼采主义、感官物质主义、享乐功利主义、犬儒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在深入思考了西方哲学之后,他在本书中深入思考了身体哲学、伦理、情欲、犬儒主义美学、生物伦理学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系统地阐述了作者思考了数十年的享乐主义哲学,让读者从另一个视角思考享乐主义,极具启发性。
精彩内容
序言 孩提时代的自画像 我1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在一个秋日的风和日丽的下午,在让人想要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阳光里。那一天,闪耀着9月份特有的美:梦幻的云彩、创世纪的光亮、温柔的空气、芳香的树叶和橙黄的阳光。从1969年9月至2005年11月。我一共出了30多部作品,但始终以各种借口来逃避我现在想要写的内容,今天,我终于诉诸文字来回忆人生中这段经历。这里,先简要地说一说,我从11岁至14岁在慈幼会孤儿院里生活了四年,如果加上寄宿学校的三年,前后有七年,痛苦的回忆难以言说。17岁那年,行尸走肉的我启程了,开始了一直召唤着我的冒险经历。从那时起,我决定将生命最核心的东西付诸书稿…… 10岁之前,我是在家乡香波尔的大自然中度过的,整天嬉戏玩耍:钓鳜鱼的小河、拾黑莓的小树林、用来制作古希腊牧羊人牧笛的接骨木、灌木丛中的小径、飒飒作响的树林、耕地的芬芳、如诗如画的天空、掠过麦尖的阵阵轻风、收获庄稼时的清香、嗡嗡飞舞的蜜蜂以及恣意奔跑的野猫。那些日子犹如田园牧歌,快乐无比。虽然尚未读过《农事诗》,但已亲身体验,身心与天地万物有了最直接的接触。 那时,我的痛苦就是我的母亲。其实,我并不是个淘气鬼,而她却无法忍受。也许她做得对,我后来才真正明白,因为长大了就不会埋怨曾经把我们误导到悬崖的盲人,理性地分析之后就会心怀怜悯地看待所有的一切。也许,母亲很好想要逃避真实的生活,和众多的女人一样,内心深处有着包法利夫人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怀着狂热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连自己的母亲都还不太认识的时候,她就遭遇过打骂、憎恶、遗弃,尔后被寄养在公共救助机构资助的人家,再次遭遇剥削、毒打和羞辱,这样的她自然就寄希望于婚姻,希望以此来结束那场噩梦。 然而,婚姻并不能改变她既定的命运。她出生的那天,恰逢诸圣瞻礼节,从那个礼拜日开始,从她躺在柳条筐子里被遗弃在教堂门口起,她的命运早已注定。谁也不能从被母亲遗弃的阴影中走出来。当她成为母亲并轮到自己遗弃儿子的时候,她就更不可能走出阴影了。因为在遗弃亲生儿子的时候,在潜意识的牢笼里,她以为自己的角色已转嫁给别人,不再需要扮演被遗弃者的角色。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不管是丈夫、孩子,还是家人,都不能给这个受伤的主体提供任何可以自我定位的东西。从被遗弃在教堂门口的那一天起,母亲就一直带着流血的伤口,这样的她如何才能平静地生活呢?想要治病,先得同意去看病啊。 毫无疑问,我长期被困在母亲的死胡同里,她在里面迷了路,盲目地使尽浑身的力气,就好像一头狂怒的困兽,不停地用头撞击着围栏,身上流着血,被自己的忧虑撕扯着,当发现自残并不能改变被困的境遇时,她变得愈发疯狂了。境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糟糕:笼子缩小了,自我戕杀的行为仍然在继续,血越流越多。八九岁的年纪,我已经知道很多。也许,母亲并没有发现,但并非毫无察觉。 我是个沉默寡言、自闭的孩子,平时逆来顺受,更不会表现出同龄人的孩子气。我观察着,我感觉着,我琢磨着,我无意中撞见了些事,我时不时到处打听这样或那样的事——在一个小村子里,大人之间的恩怨难免波及孩子……我发现了一些秘密,这是当然,但母亲是否晓得我已经发现了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曾经是挨过打的孩子,她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也打自己的孩子,不管手边碰到什么,拿起来就打。面包、餐具,各种东西,任何东西…… 我并不记得自己当时做错了什么,或干了什么蠢事,她总是拿少管所、童子军或者孤儿院来吓唬我……不厌其烦,没完没了!把活在世上当罪受,骂自己的母亲因家庭原因不能走到社会之镜的另一面,这恐怕不能为一个试图摆脱自己孩子的母亲开脱吧……我还记得她说我会上断头台!我没有杀父杀母(特别是母亲),也没有拦路抢劫,连做个屠夫都不曾想过,就被预言上断头台,感觉真的很糟糕。但母亲的感觉则恰恰相反啊! 母亲没有把自己所承受的仇恨留给她自己,而是将之不加分辨地还给了这个世界,一个令她备受折磨的、她的儿子也无法幸免的世界!对于这种毫无理智的行为,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能懂什么?这种行为将失去理智的戏中人硬生生地拽向毁灭性的疯狂。母亲打自己的儿子,就像瓦片从房顶上掉下来,再自然不过了;不能去责怪什么风。我的外婆(对于她,我一无所知)将自己的女儿遗弃在教堂门口,这一行为给我们母子两人的童年都打上了可怕的烙印。推动星球转动的盲目力量,在不知不觉中也会把正常的个体推向其阴暗的一面。 但是,我没有步我母亲的后尘,我被我的父母送进孤儿院,真是奇谈怪论……无法避免的重演,仿佛就在昨天。这是一出大脑清醒的戏,在这出戏里,我扮演了一个连自己也无法弄清楚的角色。我的母亲也如此。父亲无法抗拒母亲的暴力,也就听之任之,进而更加激发了母亲的负能量。父亲温和的天性与不惜一切息事宁人的个性,让他成了母亲的同谋,繁重粗野的农活和不幸的生活使他极为消沉,但他从不怨天尤人。 就这样,1969年9月我被送进一所名叫“苦寒”的孤儿院——“天寒地冻”和“辛酸苦涩”的缩写。事实上,那里确实会接受父母尚在的孩子,但在19世纪,那个孤儿院是为真正的孤儿而建的。在信封的封印、公函上的笺头、路边的指示牌、成绩单、学校椭圆钢印、报纸的公告以及当地新闻报告中,醒目地写着这个词:孤儿院。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要么被送进孤儿院,要么被遗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故事得继续往下说。母亲不再提教养所、童子军和一些其他的怀柔措施,从那时起,母亲常对我说我会进入高等学府,说寄宿生活会让我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什么我不能去离家最近的学校呢?弟弟就在那里上学,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其实,对我母亲来说,“苦寒”只是一个将自己从被遗弃者转为遗弃者的机会罢了。 寄宿学校离我出生的村庄大约有30分钟的行程——准确地说有28公里。那时,1968年“五月风暴”已经爆发,但尚未波及下诺曼底大区。在奥恩省,到处都是巫师、魇魔法、肮脏的农场和魔法师。两年后,当“五月风暴”开始发挥其影响力的时候,时兴的首字母缩略词取代了孤儿院:“苦寒”变成了“农校”——中级农业技术学校——但农校只是披上了另一件外衣,慈幼会的理念并没有改变。 大楼采用阿摩里卡丘陵地带盛产的石料修建而成,那是一种颜色晦暗的大理石,雨淋过后会散发出一种令人绝望的气息。不奇怪的是,这个地方接近参照了牢狱的建筑结构:收容所、监狱、医院、营房。整体的构造呈一个“E”字型。对于一个10岁、身高只有一米左右的孩子来说,置身于这样的建筑里面,身体肯定有种压迫感,灵魂也如此。孤儿院犹如一个内核,四周分布着农场、学习各类手艺的作坊、温室和一些体育设施。整个儿俨然是个村庄。600名学生加上全体教职工,人口比我的家乡小镇还要多。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工厂、一台吃人的机器、一个吃人肉的垃圾场。 监狱没有围墙,没有明确的界限,也没有明显的内外标识。什么时候才算进了孤儿院呢?也许,周围的村庄也应纳入孤儿院的范围。在离中心内核不远的地方,有奥恩河畔的穆兰以及神父们制作的独木舟、橡皮艇基底,有一排沿着奥恩省界建造的楼房,有一个仿制的小型卢尔德岩洞和通向岩洞的小径,旁边有个森林,在一个叫勒·贝尔维德尔的地方有片小树林,还有一些农田和一个露天垃圾场。这些都可以划在“苦寒”的范围内…… 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地方逃走。这一惩戒机构最黑暗的核心被层层包裹着,只有一条路通往其中。一旦有人想逃,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片敌意的乡野,如果他注意到乡野布局的话。附近两三条大路上,本堂神父、农夫和附近居民的车子来来往往,他们能够在时间得到通知:若某个小孩独自行走在路边,那么他肯定是从孤儿院跑出来的不良少年。在外面就像在里面,反之亦然。没有人能逃脱这座没有围墙的监狱。肉体和灵魂都被拘押了,哪怕隔着一定的距离,而且就是要隔着一定的距离。 中间的大楼正对着一个小教堂。“小教堂”是其正式的称呼。实际也算是一座真正的教堂,跟乡村堂区的差不多大小。作为组合式建筑的近期新式样,教堂接近不同于整体式建筑。中断的屋脊线线条形成一个凹角,极具60年代建筑的特色。有人将之想象成卡佐特(Jaques Cazotte)的多情魔鬼一屁股坐在小教堂上了,留下一个坑以证明自己曾经光顾过。黑灰色的瓦片、灰蒙蒙的花岗岩、由彩绘大玻璃窗构成的腰线延展开去——从外面看很晦暗,但从里面看则很光亮,还有混凝土钟楼(但没有钟),当雨淋湿教堂的时候,一切是那么令人绝望。 在小教堂旁边,在主楼前面靠近农场的地方(院子里有成堆的圈肥,牛群哞哞地叫着,费尔南在那儿走来走去,在那些爱说闲话的人眼里他就是个傻子,因为他总是在傻笑),有个小花园,门口有座塑像,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我觉得颇有些癖的意味:这尊塑像呈现的是圣若望·鲍思高(Don Bosco)和多米尼克·萨维奥(Dominique Savio),慈幼会神话的圣徒传里最早的两个圣徒。至于弗朗索瓦·德·撒勒(Franois de Sales)——其所撰的《精神对话录》中关于“人于己之温柔”写得妙极了……——他并没有留下什么有用的东西。 圣若望·鲍思高使弗朗索瓦·德·撒勒黯然失色。神父间传阅的是题为“圣若望·鲍思高英勇辉煌的一生”的漫画,而《成圣捷径》再也无人问津。根据雅克·德·渥拉吉纳(Jacques de Voragine)的准则,配以戈西尼(René Goscinng)和优德佐(Albert Uderzo)的手法,漫画成功塑造了一位积极向上的英雄人物,他穷其一生避免犯错,终受教皇皮乌斯十一世的恩典而被封为圣人。从出生时的一贫如洗到站在圣·皮埃尔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圣若望·鲍思高的一生正是卫道理论的完美写照。 根据漫画的内容,圣若望·鲍思高不仅批判了同代人的怀疑论,而且还批判了共产主义者的制裁手段、富人的玩世不恭与傲慢自大的态度以及教会某些公职人员的抵抗情绪。他遵循神意——通常以一条肥硕的护主忠犬的形象示人,名叫大灰……,从所做的每一件事中他都能够获得满足感。包括建孤儿院……有时为填补机构的亏空,我们乞求一大笔现金奇迹般从天而降;我们的祈祷直至深夜——结果第二天就来了位捐赠者,满足了我们所有的愿望! 慈幼会关注的是培养青少年,更准确地说,是引导他们做体力活。从那时起,组织内部的目的很明确:为每一个人找到与慈幼会这一名字相称的工作。农业耕作者、面包师、厨师、猪肉商,那时孤儿们能靠这些活儿自给自足,还有车工、铣工,而最精雕细琢的活是细木工和园丁。我当了四年园丁——从1969年到1973年。对于那些可塑之才来说,能选的职业就是教士。但慈幼会的思想体系并不爱才,而且轻视书本,害怕知识。读书人——一个虔诚的神父说——就是敌人…… 四年地狱般生活的天、个小时、分钟、第一次奠基性的体验:在9月仍有些炎热的天气里,我排队等候着办手续。各种文件、分发的内部规章、行政注册、开学仪式。一位神父把钥匙串上的管子当作哨子,指挥学生们按班集合,初一年级的学生像牲口一样一个个等待着,准备登记后进入孤儿院。 父母回去了。我把硬纸箱塞进楼梯旁堆积如山的箱子里。后来,回到村子的时间是隔了三周之后——只待了几小时而已。年仅10岁,是接近体会不到永恒和时间概念的,但从那一刻起,在我内心深处打开的黑洞则让我深深地体会了。我不寒而栗,几乎崩溃。就在那儿,在操场上,在孩子们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中,在孩子们的命运前,黑洞突然出现。就在那里,我的故事开始书写了,用的是生命之墨和战战兢兢的血肉之躯。这个身体麻木地记录着孤独、抛弃、隔绝和世界末日。往日的习惯、计划、熟悉的面孔和私密的空间一股脑儿被剥夺了,我孤身一人站在天地之间,体验着帕斯卡尔所描述的无穷无尽和随之而来的晕眩。灵魂、情绪如同旋涡…… 就在我拼命摆脱这幅缓慢融化的画面直至快要晕倒在人群之中的时候,一个翻着的衬衣领一下子吸引了我。旁边那人的衣服上有道褶皱,我先是看到一条白带,后来看到了用红线绣上去的姓氏。有名有姓。我一下子哆嗦起来:我的衣服上也有孤儿院强制绣上去的几根线,可是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而已:490。 我感到大地开始在脚下崩塌。米歇尔·翁福雷,这个名字消失了。我只是490号,这个号码把我的全部简化成了数字。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生活在孤儿院,人们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孩子们理应告别自己的名字,成为名单上的一个数字。在我面前的那个孩子可能有父母,有家族,有能够指望的亲戚,所以才在衣服上绣上红色的字母。但是我没有,一切都已结束。我死了,就死在那里,死在那一天,死在那一刻。至少,作为孩子的我死了,转瞬间,我成了大人。从那以后,没有什么能让我担心害怕,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了。 后来,我发现我就是490号,但只是在洗衣房的时候……因为我是学校寄宿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除了那些真正的孤儿……,所以我在那里要帮忙做些清洁活儿。在这个充满污垢、臭汗、小男孩体臭、不讲卫生的神父的体臭和随处可见痰渍的世界里,洗衣房成了我的避风港。那里很干净,散发着柔和的芳香——一如我童年记忆的味道。 在此期间,我发现那儿的运作机制犹如一台机器。跟所有的权力机构一样,这台机器根据不同的分组和等级运行。600名学生中的每一个人,除了是整个大集体的一员之外,还是各自小团体里的一分子,每个小团体有各自的原则、规矩和特点。主要分类:首先是教员级别的,包括学徒、男孩、硬汉、体魄健壮的人、他们认为的未来的工匠(所有职业中优选的一种);其次是低等级的人,包括知识分子、传统行业的新手、女孩,以及能背诵拉丁语性、数、格变化的弱小男生和缺乏男子气的“读书人”——在这群癖神父的圈子里,最多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类人是有一线转机的:如果能获得中学第一阶段毕业证书,就有机会参加类人的职业技能培训。顺利毕业的人不仅能够分辨夺格和宾格,而且还擅长陶轮和长刨,也许他曾向往绫罗绸缎和白嫩的双手,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木屑、锉屑为伍。在初四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我获得初中文凭的能力遭到质疑,他们接近排除了我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的可能性,并为我提供了车工、铣工的培训机会——我拒绝了,代价是母亲的一个耳光。在我父母的眼里,读书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根本就一钱不值。 同样,这台权力机器将传统的初中一分为二:高年级学生(初三和初四),低年级学生(初一和初二)。初一年级的学生不得不忍受十五六岁准成.人的戏弄、欺负和辱骂,而他们中最小的才刚过完十周岁的生日。当然,这种新生入学教育得到了神父们的默许。 班级按字母顺序排序:从A班到C班,水平逐次降低。传统老师眼中最很好的学生组成了前几个班。但神父们不一定奉行这一准则,他们有自己的分级方法。此外,还有一种双重分级标准:一是体育,二是音乐。慈幼会的人只崇拜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歌颂的鲍思高,另一个是足球。我两个都不崇拜…… 在孤儿院教区的唱经班中,有位神父是个狂热的球迷。他来自圣·布里厄,是个虔诚的马耶那人——我想他只是对马耶那的拉瓦勒足球俱乐部虔诚而已……,他会吹奏单簧管,尽管他的小指肌腱断了[有人说,这就是他没能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让·克里斯蒂安-米歇尔(JeanChristian Michel)的原因]。有时,他吹口风琴的时候流着口水。口风琴真是个奇怪的乐器,这玩意也许来源于人类的突发奇想,将口琴和迷你钢琴键结合到了一起。 这位大腹便便、身材矮小的神父把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有体育爱好者、“体育发烧友”的爱好者——阅读有关集体运动新闻的……,还有马耶那人、在弥撒合唱班中出类拔萃的女高音,以及能与他谈论足球赛事结果、奥运会或是别的杂七杂八运动会的学生;剩下的所有人便是另类,人渣。我就属于人渣,也就是“读书人”,总是躲在角落里埋头读书,从不参与讨论电视转播的赛事。这位神父在神坛之上教世人博爱,可一转身,他又将老一套的不公正的运作机制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我对他的记忆犹新:他的外表并不让人那样想,可用不了多久他就让人明白什么是专横,一种我不会屈从的专横。 对体育的崇拜让不感兴趣的人很为难……“体育”或者“户外运动”这门课有三个教员——那时的教育家尚未强制使用“体育运动教育”这一说法——他们炫耀着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和鞋子。那时流行荧光色:橙色、荧光红和带三条杠的电光蓝。其中一个教员是圭·德鲁特的有力竞争者,参加过墨西哥奥运会;还有一个是体毛极浓的图卢兹橄榄球员;最后是个驼背的人,因为饮酒、吸烟,也可能是因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弱不禁风,奶咖色莱卡制服总是在他的身上晃来晃去。他死得很早,制服并没有在他身上晃很长时间。 最重要的课是丛林越野跑。这门课被安排在孤儿院周围的森林里或田地里,遵循的是典型的丛林法则:教员们穿得厚实暖和,手握秒表,在一旁等着队伍通过。一进森林,在浓密的荆棘丛里,在灌木丛里,在小溪里,那些高大的、健壮的、岁数大一些的好斗分子,就会用肘推开年龄小的、弱不禁风的。跑在前面的,用力吐着痰,落在后面的,遭遇着一脸唾沫和鼻涕。 最有经验的会穿上钉鞋,有钱人家的孩子也这样。而其他人有双旧鞋就心满意足了。穿着旧鞋踩上烂泥后常常会滑到沟里,要不断加快步伐,还得看准方向。那些赢得神父偏爱的哈巴狗有时在路上会停下脚步,伺机绊倒身旁的竞争对手。这真是人生的大课堂,教人爱众生。 开学初,慈幼会的人会组织“勒芒24小时”活动,正式的欺负新生活动,一项充满神秘色彩的考验。老生都知道,新生也将亲身体验。三到四人被绳子捆在一起,进行丛林越野跑。在终点补给的时候,学生们满身污泥,汗流浃背,像狗一样地喘着气,被队伍里跑得最快的人拖着、骂着。在慈幼会神父嘲讽的眼神中,高年级的学生等着看笑话,看那些队伍被一桶桶冷水满头浇。 另一项活动——下诺曼底的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应该很喜欢——就是在耶稣升天节那个周四举行的奥运会。前一夜在黑灯瞎火的村子里举行点火开幕式,整个孤儿院从那时起就一直沉浸在浓烈的运动氛围中。每个班代表一个国家;母亲们负责购买相应国家代表色的运动衫,然后再绣上相应的国旗。 学生们列队游行,迈着军人的步伐,所有团队整齐划一,大人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旗手带领着队伍绕场行进,而奥林匹克火炬则由最很好的学生(!)举着。神父们歇斯底里,在栏杆后面狂喊乱叫,为他们的心肝宝贝加油。在颁奖、奏国歌或升旗的时候,慈幼会的神父们也在运动场上比赛,他们得意扬扬地展示着自己纤细、白嫩、汗毛浓密的双腿…… 我有运动天赋,比赛成绩很出色,尤其是速度项目,但这种受虐狂式的颁奖仪式,这种对蛮劲的推崇让我感到很恶心,我讨厌竞争。这帮慈幼会的人在世俗教员身份的掩护下,一边教学生“重在参与”——源自法西斯分子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那句人尽皆知的口号——一边又在赞美获胜者。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那些日子里,我亲眼看见了粗暴的自然法则是如何毫不掩饰地在现实中上演的。 在孤儿院里,人们喜欢邋遢、挂彩、疲累和衰弱的身体。神父们并不擅于清洁。衣服上布满了污渍、破洞和补丁,鞋跟是坏的,到处是油渍,袖子肘部脏得发亮,散发着莫名的气味,还有脏兮兮的指甲。血、汗、泪以及好斗的体育精神让这一场景变得出神入化。对于这种蔑视肉体的爱好和憎恶自我的思维方式,任何不认同的人都会被视为娘炮。真是奇耻大辱。 在每天的作息时间表中,至少包括一小时的运动。若额外加上“户外锻炼”——我始终不明白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一天之内必须忍受足足三小时的活动。然而,一周只能洗一次澡。没有例外。周四在那时就算是轻松的日子。如果周五再来一次泥浆满身的丛林越野跑,该怎么办呢?没关系:等下周再洗吧。 一间没有粉刷过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浴室。单人小隔间由木围栏、放在地上的条凳、莲蓬头和一个打开的绿漆木门组成,门是按照美国西部片里小酒馆的木门样式做的:那只是个象征性的推拉门罢了,既没有上端的部分也没有下端的部分,便于看守的神父透过水蒸气偷看某个纤美的身体。 我们手里拿着毛巾和洗漱包,穿着三角裤在门口排着队。布里永神父负责控制人流量,也就是洗澡时间。不可能有玩水的乐趣,不可能有清洁身体的满足,更不用说灵魂了。没有任何机会能让你享受独处,头顶上热乎乎的水花,远离世界、独自一人沐浴在洁净的雨露之中。洁身之乐?那是罪恶,那是女孩子的癖好。 一切都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大家排着队,不能讲话;飞速进去,赶紧冲洗,抓紧出来;把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地方再腾给后来者。然后,我们走进水泥地下室尽头的通风地窖,身上带着如落水狗一样的气味,在那里看上一个小时电视——当年的《佐罗》……与此同时,可能还碰到被罚的学生在黑板上演算。 神父的诀窍就是,当每个人进入自己的隔间后,他发出一系列具体的指令:到莲蓬头下淋湿,站到一边,打肥皂,回去,冲干净,马上出来,擦干,出去(哪怕身上还是湿淋淋的)。也许就是要身上湿淋淋的。当他大声命令大家从热水淋浴里出来的时候,大家必须保证服从,若有人在那一刻没有服从,那就遭殃了,神父会打开热水阀门。在巴普洛夫条件反射的作用下,集体淋浴从未超过规定的时间…… 有一天,布里永神父在某个隔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坨精致的大便,那真是可怕的一天。他狂怒不已,像魔鬼附体一般。为了避免这位慈幼会神父迁怒于己,大家都自觉地走开。在我看来,这个偶尔的嗜粪者如此执着地在孤儿院里奉行消灭个体和集体至上的理念,以至于认为排便也应跟其他活动一样遵守集体原则。 究竟在何时何地我才能安静地享受一下独处呢?在宿舍熄灯之后。但那时也一样,生存空间依然狭窄。一张床,一个床罩,在120人的宿舍里,红绿床罩相间,还有一个配有抽屉和门的衣橱。这便是我全部的家当,生活必需品和钱财都在这里。 很久之后,我才得知母亲曾扣下我心上人的来信,那是个在夏天来我们村子度假的巴黎姑娘。我没收到过什么信,除了父亲寄来的那一封,说我母亲因车祸住院,司机死了,一位乘客疯了。(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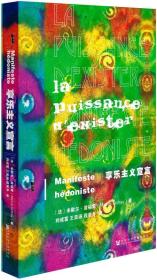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