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史记》到《人物志》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69.19 7.2折 ¥ 96 全新
库存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伏俊琏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23041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96元
货号31959149
上书时间2024-12-16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伏俊琏,现为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敦煌赋校注》《俗赋研究》《敦煌文学总论》《敦煌文学写本研究》等学术著作;主编学术集刊《写本学研究》《古代文学特色文献研究》等。
目录
论《史记》的悲剧性
秦朝的统一与司马迁对秦的态度
谈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封禅考
司马相如“买官”“窃色”“窃财”辨
《汉书·艺文志》“赋”分四家说
《汉书·艺文志》“杂赋”臆说
《汉书·艺文志》“杂赋”考述
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早期史学家创作人物传记的一种取材方法
《柏梁台诗》再考证
《人物志》及其作者
《人物志》的主要内容和人才理论
《人物志》人才学说的来源
《人物志》产生的文化背景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主要是从“人”入手讨论汉代文学与文化。《史记》是西汉描写人物的名著,《人物志》是汉末以来人物品评的总结。司马迁处在中国文化大变革的时期,他用文学的眼光叙述历史,描写了英雄的悲剧、平凡人生的悲愤。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从“人心”入手探讨文学和历史的生成,昭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自觉,而《汉志》“诗赋”的独立和赋分四家说,是从学理上对文学自觉的宣示。由对文章的理性判断,到对人物的理论品评,正是刘邵《人物志》的本质所在,因此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的才能和个性及政治作为的著作。
主编推荐
视野开阔的文史著作,人文的新意观点;文学自觉的宣示到文章的理性判断;《史记》到《人物志》有中华民族史学发展的对接,涵泳相通的恢弘气象;《史记》到《人物志》,是文化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在文字上的突出彰显。
精彩内容
有位著名学者曾说,我国漫长的古代文学史,出现过两次表现人的创作高峰:一是《史记》,二是《红楼梦》。司马迁自己曾说,他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前人阐释太史公的“成一家之言”,一般都归结到“不虚美,不隐恶”的所谓“实录”精神。其实,“实录”是史家的基本素质,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更多的是思考人的问题。
首先从我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谈起。《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史”就是记事的人,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字形讲,“史”是一个会意字,“从又持中”,这里的“中”是古代的简册,手持简册书写,就是“史”。但是仅仅纪事并非有“历史意识”,比如甲骨文有大量的“记事之辞”,但它只记载占卜祭祀之事,记录人与自然神、祖先之间联络,既没有对事件的详细记述,更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坐实。商周金文是宗庙之礼的关键部分,记录器主接受王的赏赐,进而制作礼器纪念祖先;殷商和西周初期的铭文几乎不提当时发生的历史大事,核心是强调神与人、祖先与子孙之间的联系,以祈求家族的昌盛绵延,无法系于具体的时空环境,所以它们都没有体现出历史意识。甲骨文、金文中有“作册”“作册内史”“作册尹”等,“史官”(官府)已经设立。但甲骨文中的“册”均为“祭册”,即贡献于祖宗或神灵的祭品清单;金文中的“册”为“锡册”或“封册”,即赐爵礼及清单,都没有体现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意识。
我国历史意识是从西周后期自觉的,《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瞽史”等史官。其中最古老的当为“瞽史”。在文字产生以前,人类的历史主要是口耳相传,这些传播部落史或氏族史的人是“巫”“祝”,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后来“史”的出现,逐渐代替了“巫”“祝”的某些权利。“史”官中当以“瞽史”为最早,而“瞽史”或者“瞽矇”由于视力差,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强。他们讲述的内容,一般是以历史故事或影响大的故事为主。远古时期的历史故事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应当归功于瞽史的作用。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史故事集《左氏春秋》就是传自瞽者左丘明,当然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瞽史代代相传下来的。比如《左氏春秋》中关于夏朝的几件事情讲得比较详细具体,如后羿和寒浞相继篡政,少康复国中兴及孔甲畜龙等,分别见于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和昭公二十九年。后来,当瞽史的口述历史书于竹帛,就成了史籍上所说的“瞽史之记”、“瞽史记”(《国语·晋语四》)。瞽史讲述历史,由于记忆的偏差,或者神化其祖先的需要,讲述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虚构或夸大史实,所以孔子有“文胜质则史”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史学与文学交集了。孔子说“文胜质则史”,照历史原样书写不是“史”,而是“野”,带有夸张虚构的“文”才是“史”。
孔子的这一观点,也与西方后现代学派怀特(HaydenWhite)的观点很相似;怀特认为,历史的本质其实就是文学。西周的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所以总结历史兴亡之道,秉要执本,这是早期“史”的核心。这一史学观念中,史家个人的“情志”起很大的作用。司马迁继承的正是这一史学传统,他对“成一家之言”有表述主要是: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这是《伯夷列传》中的一段。《史记》七十列传之首的《伯夷列传》,一共四段。
第一段讲古之高士,引到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然后是一段小传,小传后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质疑,最后又引用孔子、贾谊的话,反复陈说伯夷叔齐因孔子而名扬后世。“列传”占的比例不大,主体部分是高士之所以得名的缘由的讨论和读列传后的感慨。作为人物传记,这种写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司马迁借伯夷叔齐的逸事,主要是表达他的天道观,是他“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历史上伟大的作品,都是作者受到打击,志向不得伸展,所以通过作品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为了论证他的这一观点,司马迁罗列了历史上诸多伟大作品的作者,因为受到苦难的折磨,心意郁结,才发愤著书。刘知幾《史通·杂说上》说:“《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卷四:“按《列传》,《吕览》之作在不韦相秦时,《说难》《孤愤》亦韩非未入秦时所作。此乃自相背违。”司马迁这样不顾史实的论证,就是“文”的笔法,原始意义上的“文胜质则史”。司马迁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家之言”,其实就是“文学的自觉”,《史记》不仅有“发愤著书”的文学理论,而且在人物传记中自觉运用文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表现在对笔下人物倾注的同情心和故事情节描写的虚构上。《史记》写得最成功的是悲剧人物。所谓悲剧人物,指的是他们的遭遇悲惨,或者被杀,或者自杀,或者一生坎坷不平,内心时常处于痛苦之中。而他们的遭遇能激起人们对正义、美好事物的同情和对邪恶势力的憎恨。《史记》130篇,写人物的作品共112篇,其中57篇是以悲剧人物的姓名标题的,此外还有近20篇写到悲剧人物。在这近80篇中还有许多篇是几个悲剧人物的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等。还有一些篇章虽然只以一个悲剧人物命名,但实际上还写了其他次要的悲剧人物,如《伍子胥列传》中的白公胜和石乞,《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李将军列传》中的李敢、李蔡等。粗略统计,《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120多人。可以说,《史记》是一部悲剧人物传记。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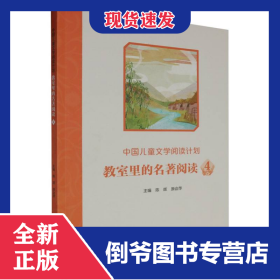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