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纷纭万端: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66.49 6.8折 ¥ 98 全新
库存27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中国台湾]沈松侨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
ISBN9787208188525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98元
货号32171879
上书时间2024-11-18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沈松侨汉族,1950年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现已退休。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思想史及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河南省),曾出版专书《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及论文十余篇。
目录
代 序
召唤沉默的亡者:我们需要怎样的国族历史?
上篇 思想与人物
一代宗师的塑造
——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
五四时期章士钊的保守思想
中篇 政治与经济
从自治到保甲
——近代河南地方基层政治的演变(1908—1935)
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
——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1930—1943)
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
——以棉花与烟草为中心(1906—1937)
下篇 国族与国民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国权与民权
——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
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
——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
后 记
内容摘要
本书为著名近代史学者沈松侨力作。胡适倡导文学改良,章士钊代表“五四的另一面”,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精英们有着怎样的复调构想?从“中国的一日”到“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生活叙事透露出大众怎样的国家认同?在一个盘踞土匪、列强、豪绅、军阀的宛西世界里,为了“活着”,各色生民又展开了哪些博弈与突围?本书从多学科视角解读近代中国的风雨如晦,细看巨变之下的思想争锋、区域社会与身份认同。
精彩内容
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前 言
近代中国史上,以一纯粹学者,全无政治凭借,而能享誉全国、蜚声中外者,舍胡适一人,殆不作第二人想。尤有甚者,胡适于民国初年成名之骤,崛起之速,也诚如论者所言,除梁启超之外,再无他人堪与比拟。1917年7月,26岁的胡适游美返国,9月,任北京大学教授,不数年间,声誉鹊起,一跃而成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在1920年代初期,俨然已有“一代宗师”之目。即胡适本人在晚年也自承早岁“暴得大名”,终生受累。
然则,胡适何人,竟能在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脱颖而出,“暴得大名”呢? 如果以严格的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青年胡适的治学业绩,实在难免予人“名实不称”的观感。以胡适的专业—哲学而言,历来批驳指摘之声,未尝稍歇。早在1930年,金岳霖评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便坦率指陈胡适研治中国哲学史,既不免于主观成就,“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以致其综论中西学说时,每多流于牵强附会。近人吴森也认为胡适对于乃师杜威之实验主义哲学“了解肤浅”,“有师而无承”,完全未能掌握杜威思想的精义。至于其他从文学、史学各方面,对胡适的学术成就提出质疑的,更是所在多有,不胜枚举。
平心而论,这些“反胡”“批胡”的言论,固不免夹杂着“文人相轻”的意气成见,却也尽多“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严肃批评,绝不是“无的放矢”四字可以轻轻揭过。即使是近人中对胡适最有“同情之了解”的唐德刚,在称颂胡适为“当代第一人”之余,仍不讳言胡适对于现代史学及各项社会科学所知甚浅,终其一生,“中学止于乾嘉,西学亦未超过赫胥黎、杜威二人”。因此,胡适的早岁得名,似乎并不能只由单纯的学术观点来解释。青年胡适之所以迅速占有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霸权地位,显然还牵涉到复杂的历史脉络与社会背景等因素。
1983年,余英时在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撰长序中,首度针对此一问题提出深入而有系统的分析。余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胡适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树立了一套崭新的“典范”,此项开创之功,正是胡适得享盛名的关键所在。
余先生治中国思想史,善觇大端,阐幽发微,迭出胜义。经过他的诠释,此一久悬人心的公案殆可谓涣然冰释,略无剩义。虽然,余先生该文格于研究角度与材料限制,殊少触及具体的历史背景,更未能点明作为一个现实人物的青年胡适是在怎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从事其学术文化活动的。所幸近数年间,胡适早期的日记、书信陆续面世,使我们得以在思想史的诠释之外,再就更宽广的面向窥探青年胡适成名过程的蛛丝马迹,从而更确切地把握此一独特历史事实所反映的意义。缘是,本篇之作,盖不过规抚时贤,勉为续貂而已。
一、中国学术的“哥白尼”1917年9月,满怀“为国人导师”之雄心壮志的胡适迈入北大校门时,他在中国的学术界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人物。
在当时,传统儒学仍是中国学术的主流,以章太炎为首的古文经学派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今文经学派,双峰并峙,二分天下,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界。而在众所瞩目的学术重镇—北大之内,四世家传《左传》的古文大师刘师培与章太炎门下高弟黄侃、马裕藻、钱玄同诸人,坐拥皋比,相率以训诂考据之“汉学”为号召,蔚为斯时北大的学统正宗。以论旧学之邃密,去国多年的胡适,当然是无法与这些人物分庭抗礼的。据耿云志统计,胡适4岁入塾,13岁赴沪入新式学堂,前后在塾9年,读过的经典古籍不过“四书”和《诗》《书》《易》《礼》等寥寥数种。1910年,胡适赴北京应留美赔款官费考试,才在友人指点下,接触到汉儒的经传注疏。及留美期间,胡适虽于课余之暇,力自修,点读旧籍,毕竟限于日力,涉猎无多。他在1922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便感叹说:“吾辈去国日久,国学疏废都尽。”1914年致胡近仁函中也说:“适近年以来,为蟹行文字所苦,国学荒落不可问。”自返国之后,每当研究工作中遇到音韵学的问题,他往往都要向钱玄同请教,或干脆请钱代作。从此一事观之,胡适的这些话,也并不全是自谦之词。因此,胡适在担任北大教授之初,“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深恐为学生耻笑。1919年2月,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封面上特别题署“胡适博士著”等字样;而蔡元培为该书所撰序文误以胡适为“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之后,胡适竟亦默不作声,不加更正。凡此诸端,在在反映出青年胡适甫行展开学术事业时的中情恇怯,不敢自信。甚至到了晚年,他在回忆其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深获钱玄同赏识一事时,也还透露了此中消息: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
然而时隔数载,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函》中,已肯定胡适“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更将胡适与章太炎相提并称,许之为清代考证学正统之殿军。
那么,胡适到底有何建树,竟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博取如此崇高的学术声望?这就不能不牵涉到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学术所面临的困境了。
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清代考证之学的基本典范在于“通经明道”,也就是通过训诂考订的绵密功夫,探求六经孔孟的义理。自顾炎武以降,“音韵明而后训诂明,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可以说是有清一代二百年间学者治学的不二圭臬,而其根本价值假设则是“信古”而非“疑古”,是“独尊儒术”而非“诸子平等”。
但是,清代学术经过长期发展,其所蕴涵的基本假定却逐步面临崩溃的危机。首先,随着考证工作的内在需求,自清代中叶以来,治诸子学的风气渐次兴起,知名学者如王念孙、张履等人,率多移治经之法以治诸子。逮诸子之书考订既明,其在义理上的地位,遂亦昂然振起,寖假威胁到孔孟的独尊霸权。乾隆年间,汪中治墨,已将墨子提升到与儒学相埒的地步。他说:《墨子》之说,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 又说: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
既然孔墨齿位相敌,操术纵有不同,又曾何轩轾之有?所以翁方纲痛诋汪中为“名教之罪人”,正是有鉴于这种治学路向终将根本颠覆清代学术的价值系统。
果然,降及晚清,古文大家章太炎上承汪中、孙星衍之余绪,更进一步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他在1906年发表《诸子学略说》一文,肆意摭拾《庄子》等书菲薄孔子之事迹,全面扭转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面目,“尊子贬孔”的观点在他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清末民初的知识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许之衡论章氏学术,便指出章一力排孔,“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大失其价值,一时群言,多攻孔子矣”。由此可知,清代中晚期以来诸子学的发展,不但以附庸蔚为大国,改变了中国学术的传统面貌,抑且直接撼动了考证之学赖以存立的典范基础。
另一方面,乾嘉以降学者对考证工作的常态研究,也和“明义理”的典范要求日趋脱节,逐渐流于琐碎饾饤、擘绩补苴的狭隘境界。一旦西力入侵,形势豹变,这种原已遭逢“技术崩溃”之内在危机的传统学术自然无法有效回应时势的挑战,而不能不被迫走上彻底改造的途径。梁启超在论清学之衰时,便说: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浮华之士亦竞趋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尽,后起者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运命自不能不复久延。
当然,在上述内外两重危机的交相侵迫下,清末儒学内部并不是没有产生过自救的努力,其最足为代表的,便是以廖平、康有为为后劲的今文学运动。
稍早于康有为,廖平已经试图弥缝诸子异端之学与西方文化对传统儒学所造成的强大冲击。为了应付诸子学的挑战,廖平主张先秦诸子也和孔子一样创教改制,诸子百家与“孔道”非但不相排斥,且有密切的源承关系,他说:“子家出孔圣之后,子部窃孔经之余。”对于西方文化的威胁,廖平则以一个全盘改装的孔子加以化解。他宣称西方现代文明皆为孔子所曾预言,西方“一切之说皆我旧教之所有”,孔子乃是“全球之神圣”,六艺则为“宇宙之公言”。
廖平这种以“奇伟尊严孔子”为手段来为危疑震撼的儒学注入新活力的努力,在康有为手中,阐发推衍,抵于极致。为了达成变法改制的政治目的,康有为不但斥古文六经为刘歆所伪托,一举推倒传统经学中的古史系统,更将六艺经典重新解释成孔子“托古改制”,“垂法万世,范围六合”的一套神秘符号系统。在他笔下,孔子俨然一教主大圣,其推尊高扬,可谓无以复加矣。
然而,廖平、康有为等人因应世变,亟亟乎维系传统学术基本典范于不坠的工作,反而对整个儒学传统造成了致命的一击。梁启超论《孔子改制考》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吊诡的现象:《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
(康氏)虽极力推挹孔子,然既谓孔子之创学派与诸子之创学派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则已类孔子于诸子之列,所谓“别黑白定一尊”之观念,全然解放,导人以比较的研究。
由是而观,中国传统学术在清末民初时,殆已濒临全面瓦解的严重危机。如何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下,重新建构一套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便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紧要的课题。章太炎所以在清末首揭“整理国故”的大纛,自然不是无因。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青年胡适展开了他的学术生涯,也担负起了树立新典范的革命性事业。
当然,胡适所以能扮演如此一个历史性的角色,除去有利的客观形势外,也和他个人的主观凭借密切相关。余英时已经指出,胡适的治学途径自始即遵循着训诂考证的正统路向。同时,他远在异域“自修汉学”,既然无家法师承,也就不受宗派成见所囿限,一以己意为断,反而多有会心发明。他在1911年4月的日记上,便对“汉儒解经之谬”痛加抨击,立志造作今笺新注,别开生面:读《召南》《邶风》。汉儒解经之谬,未有如《诗》笺之甚者矣。……诗者,天趣也。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
另一方面,胡适在留美期间,又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中提取了一套治学的“科学方法”。在胡适的理解中,这套哲学的精义不外乎“历史的态度”与“实验的方法”两大端,而其基本归趋则是将一切学说都当作由特定历史背景所造成而有待证实的假设,其价值须以其所造成的结果来做评判,绝无不证自明的“天经地义”可言。如余英时所论,这套方法在根本精神上与清代考证学原可相通,而其精密、严格与系统化的程度,则远非后者所能企及。因此,当青年胡适挟其“科学方法”,着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所造成的震撼也就有如“大地震”“火山大喷火”了。顾颉刚记述他在北大初听胡适授课,便有如下的形容:(北大)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汉章)。……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究竟为什么顾颉刚会对胡适的说法震惊至斯?我们从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撰序文中,可以发现一些线索。蔡序指出了胡适该书的几项特点,其中二、三两项明白点出胡适的主要贡献:一则在以“扼要的手段”截断众流,径从老子、孔子讲起;一则在于摆脱“独尊儒术”的传统成见,以平等的眼光对待诸子百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这两点,如前所述,正好扣住了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的关键性问题。因而胡适以严密的“证明方法”所完成的“系统研究”,遂能一举摧陷以往学术研究的基本典范,重行指出截然异趣的治学新径。他在晚年夫子自道,认定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民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项小小的革命”,就是针对这层意义而发。
也正因为胡适的学术工作与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深相契合,他的成就与声望也就迅速受到同时代的知识界所肯定。顾颉刚便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判,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及两月,即告再版,到1922年8月更已出至第八版。甚至僻处四川的熊克武也致函胡适,指出该书在川“购者争先,瞬息即罄”,并称扬该书“为中国哲学辟一新纪元”。可见当时胡适的声名已为全国知识界所公认,且其声光之盛,凌厉无前,我们只要对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交涉,略加爬梳,便可窥见一斑。
胡适早年为学,深受梁启超之启迪,但两人正式会面,则迟至1918年11月。当时梁启超早已誉满天下,隐然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而青年胡适仍无藉藉之名,因而胡适晋谒梁启超时尚须请人介绍,执礼甚恭。但是1920年以后,两人在学术上的主从关系便有了明显的变化。梁启超不但受胡适影响,回过头重理学术旧业,甚至在后者盛名的威胁下,几乎无时无刻不以胡适为其主要敌手。1922年4月,梁启超出版《墨经校释》,将胡适所撰序文置于书末,却将本人的答辩放在书前。同年3月,梁启超又穷二日之力,公开讲演,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凡此诸端,历历可见梁启超已视胡适为其在学术界霸权地位的最大竞争者。事实上,就在同时,胡适已受推主编北大国学研究所的《国学季刊》;等到1923年初胡适刊布《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他在中国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可说已是完全巩固了。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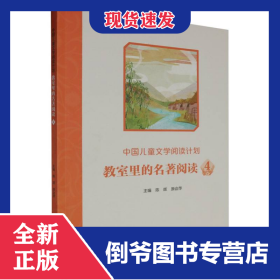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