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迪契作品:半轮黄日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36.72 4.3折 ¥ 86 全新
库存16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75302081
出版时间2024-08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86元
货号32171914
上书时间2024-11-05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NgoziAdichie)? \\\"天纵之才\\\"(\\\"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 \\\"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纽约客》)? \\\"世界樶有影响力的一百人\\\"(《时代》)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留学美国,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学和政治学,之后分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长篇小说《紫木槿》获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绕颈之物》获得2009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提名。《美国佬》摘得2013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小说奖。
2014年,她因TED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蜚声世界。
目录
第一部 六十年代初
第二部 六十年代末
第三部 六十年代初
第四部 六十年代末
作者的话
译后记:但愿我们永远铭记
内容摘要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NgoziAdichie)? “天纵之才”(“非洲文学之父”阿契贝)? “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小说家”(《纽约客》)? “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人”(《时代》)1977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南部城市埃努古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后留学美国,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学习传媒学和政治学,之后分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长篇小说《紫木槿》获2004年橘子小说奖的提名,第二部长篇小说《半轮黄日》获2007年橘子小说奖。《绕颈之物》获得2009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提名。《美国佬》摘得2013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小说奖。
2014年,她因TED演讲《我们都应该做女性主义者》蜚声世界。
主编推荐
⭐ “我们之所以这样活着,是因为我们不记得我们将死去。”我们可以如此有力地相爱,我们可以如此随意地杀人;在一场势必要剥除所有人的尊严的战争中,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人性?⭐ 史诗巨著,以女性视角呈现尼日利亚内战伤痛。关于种族与阶级,关于暴力与杀戮,关于人性与尊严,更关乎爱与忠诚。⭐ 阿迪契长篇代表作,2007年橘子小说奖、美国笔会奖、安尼斯菲尔德-沃尔夫图书奖获奖作品,2015年英国女性小说奖最佳小说⭐ 享誉全球,被译成37种语言⭐ 精装加护封×称手小开本×舒适阅读体验
精彩内容
1主人有点古怪。他在国外读书的年头太长;他会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你跟他打招呼,他不见得每次都理你;他头发也太密。乌古随姑姑走在小径上,姑姑对他嘀咕了这些话。“不过他是个好人,”她又说,“你只要活干得好,吃得就不会差。你甚至每天都能吃上肉。”她停下来吐痰,只听她吸了口气,啐出一口痰,挂在了草叶上。
乌古不相信有谁每天44都能吃上肉,当然也包括他要去伺候的这位主人。不过他没有表示异议。他满心期待,满脑子都在想象着远离村庄的新生活,顾不上说话。他们从汽车站的卡车里下来,已经走了好大一会儿,下午的太阳烤着他的后颈。他并不介意。他做好了在更加灼热的太阳下走更长时间的心理准备。走进大学校门后,眼前出现的是他从未见过的街道,如此光滑的柏油路面,让他忍不住想把脸颊贴上去。他永远都无法向妹妹阿努利卡形容这里的一切:一座座漆成天蓝色的平房排列有序,像极了衣着体面、彬彬有礼的绅士;平房之间的树篱修剪得非常平整,看上去像是被树叶覆盖的桌面。
姑姑加快了脚步,拖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在寂静的街道上回响。乌古很想知道,透过薄薄的鞋底,姑姑是不是也能感受到柏油路面越来越烫。他们路过一块街牌,上面写着“奥迪姆街”。乌古默念着“街”这个词,每次看到不太长的英语单词,他都会这样念一念。他们走进一个院落,乌古闻到了一股浓烈的芳香,一定是大门口的灌木丛里那一簇簇的白色花朵散发出来的。灌木丛的形状很像纤巧的小山。草坪闪闪发亮,蝴蝶在上面飞舞。
“我对主人说了,你学东西很快,osiso-osiso(很快很快)。”姑姑说。乌古郑重地点点头,其实姑姑已经给他讲过很多遍了,讲得同样多的还有他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一个星期前,她正在打扫数学系的过道,听到主人说需要一个男仆收拾屋子,她赶紧抢在主人的打字员和办公室通信员之前接话说,她可以帮忙。
“我会学得很快的,姑姑。”乌古说。他瞪大眼睛注视着车库里的小车,小车蓝色的车身上环绕着一条金属杠,仿佛戴着一条项链。
“记住,不管什么时候他叫你,你都要回答‘是,先森!’。”“是,先森!”乌古学着姑姑。
他们站在了玻璃门前。乌古强忍着没有伸手去摸水泥墙,尽管他很想知道水泥墙的手感与母亲的茅屋的泥巴墙有何不同,泥巴墙上隐约看得见手指的压痕。一个念头一闪而过:真希望此刻自己就在村子里,在母亲的茅屋里,在阴凉的茅草屋顶下;或在姑姑的茅屋里,那是村里唯一有瓦楞铁皮屋顶的屋子。
姑姑敲了敲玻璃门。乌古看得见门后的白色门帘。一个声音传来:“谁?进来。”说的是英语。
他们脱下拖鞋,走了进去。乌古从未见过这么宽敞的屋子。棕色的沙发摆放成半圆形,沙发之间隔着小茶几,书架上塞满了书,屋子中间的大桌子上摆着一个花瓶,插满了红色和白色的塑料花。东西虽多,屋子却仍旧显得宽绰有余。主人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穿着汗衫和短裤。他并没有端坐着,而是斜靠在椅子上,脸完全被书遮住了,似乎忘了他刚刚招呼他们进来。
“下午好,先森!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孩子。”乌古的姑姑说。
主人抬起头来。他的肤色非常黑,犹如老树皮,胸毛和腿毛更黑,闪着光泽。他摘下眼镜。“哪个孩子?”“就是您要的男仆,先森。”“噢,对,你带来了男仆。Ikpotagoya(你把他带来了)。”主人的伊博语听上去像羽毛一样轻柔。这是一种带英语滑音的伊博语,说这种伊博语的人经常说英语。
“他会卖力干活的,”姑姑说,“他绝对是个好孩子。您要他做什么,尽管告诉他。谢谢先森!”主人咕噜着回应了一句,眼睛盯着乌古和姑姑,脸上却带着几分茫然,似乎他们的到来使他很难记起某件重要的事情。姑姑拍着乌古的肩膀,轻声叮嘱他好好干,而后转身走出去。姑姑走后,主人重新戴上眼镜,看起书来,他依旧斜靠在椅子上,姿势更为放松,双脚也伸了出去。在翻页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书本。
乌古站在门边等着。阳光似水,透过窗户在室内流淌,时不时地,一阵微风把窗帘吹起。屋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主人翻书的声音。乌古站了一会儿,开始慢慢地挪步,朝书架靠过去,似乎是想躲在里面,过了片刻,他蹲在了地板上,膝盖紧紧夹着他的酒椰袋子。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如此之高,白得似乎到了透亮的地步。他闭上双眼,试着在脑海里描画出这间宽敞的屋子,还有屋子里陌生的家具,但他做不到。他又睁开眼睛,心里再次溢满了惊奇的感觉,他环顾四周,告诉自己这不是在做梦。想想吧,他将坐在这些沙发上,他将擦亮这光滑平坦的地板,他将清洗这些薄如蝉翼的布帘。
“Keduafagi(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主人问他,吓了他一跳。
乌古站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主人坐起身来,又问了一遍。他的身子塞满了整把椅子,浓密的头发在头上高高竖立,双臂肌肉饱满,双肩宽阔有形。乌古本以为主人是一个年龄偏大、身体虚弱的人,此刻不由得担忧起来:他也许无法取悦眼前的主人,他看上去如此青春,充满活力,似乎无所需求。
“乌古,先森。”“乌古。你从奥布帕来?”“从奥皮来,先森。”“你的年龄从十二岁到三十岁都有可能。”主人眯缝着双眼,“可能是十三岁。”“十三”这个词是用英语说的。
“是的,先森。”主人又读起书来。乌古站着没动。主人轻轻翻过几页书,抬起了头。“Ngwa(好了),去厨房吧。冰箱里应该有一些你能吃的东西。”“是,先森。”乌古一步一挪,小心翼翼地进了厨房。他看到一个白色的家伙,几乎与他一样高,知道这就是冰箱。姑姑以前给他讲过。一个很冷的粮仓,她说,吃的东西放在里面不会馊掉。乌古打开冰箱,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橙子、面包、啤酒、饮料—一包又一包,一罐又一罐,每一层都堆满了吃的喝的。最上面一层放着一只发亮的烤鸡,几乎是一整只,只差一条鸡腿。乌古伸出手,摸了摸烤鸡。他听到冰箱在喘着粗气。他又摸了摸烤鸡,舔了舔手指,然后撕下剩余的一条鸡腿,吃得一干二净,手里只剩下咬碎且吮过的骨头。接着,他掰下一大块面包,如果家里来了亲戚,带来这么一大块面包做礼物,他会兴高采烈地与弟弟妹妹们分享。他吃得飞快,生怕主人进来,不让他吃了。吃完后,他站在水槽边,拼命回想着姑姑给他讲过的话:打开水龙头,水会像泉水一样喷出来。就在这时,主人走了进来。他穿了一件印花衬衫和一条长裤。他的脚指头从皮拖鞋里露出来些许,也许是因为太干净了,看上去女人味十足,总穿着鞋的脚才有这么干净的指头。
“怎么啦?”主人问。
“先森?”乌古指了指水槽。
主人走过来打开了金属水龙头。“你应该在房子里四处看一看,把袋子放在走廊的第一间屋子里。我要出去散步,让头脑清醒清醒,inugo(听到了吗)?”“是,先森。”乌古看着主人从后门走了出去。主人个子不高。他的步子轻快、有活力,很像埃泽阿古,村里的摔跤纪录保持者。
乌古关上水龙头,又拧开,再关上。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魔法一般的流水,还有胃里芳香的面包,令他哈哈大笑起来。他穿过起居室,来到走廊。三个卧室的书架和写字台上、浴室的水槽和柜橱里都堆满了书;书房里,书从地板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储藏室里,一箱箱的可乐和总理牌啤酒旁边,也堆满了旧杂志。有一些摊开倒扣着的书,似乎主人没把它们读完便急急忙忙读起了下一本。乌古辨认着这些书名,大多数都太长、太难。《非参数方法》《非洲概览》《大生物链》《诺曼人对英国的冲击》。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他始终踮着脚,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脚很脏。看得越多,他的决心也越大:一定要让主人满意,一定要留在这个有肉吃、地板也很清凉的地方。他盯着抽水马桶,用手抚摸着黑色的塑料座圈,这时传来了主人的声音。
“你在哪里,我的好伙计?”他是用英语说“我的好伙计”的。
乌古冲到了起居室。“在这里,先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古,先森。”“对,乌古。看这儿,neeanya(看这儿),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乌古顺着主人指的方向,看到了一个金属盒子,散布在上面的旋钮看上去有点危险。
“不知道,先森。”乌古回答。
“那是一台收音电唱两用机。新的,效果非常好。不像那些老式留声机,老得用手摇。靠近它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小心才行。一定不要让它碰水。”“是,先森。”“我要去打网球了,完了之后去员工俱乐部。”主人从书桌上拿起几本书,接着说,“我也许很晚才回来。你先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是,先森。”乌古望着主人的车开出了庭院,方才走过去站在收音电唱两用机旁边,仔细观察了一番,不过他没有伸手去摸。他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转悠,抚摸着书、窗帘、家具和盘子,天黑了,他打开灯,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芒,不像家里的棕榈油灯那样在墙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深感惊奇。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正在准备晚饭,双手紧握捣锤,在研钵里捣木薯粉。小妈奇奥凯正在煮一锅清水一样的汤,汤锅就搁在火上架的三块石头上。孩子们从小河边回来了,在面包果树下互相奚落,互相追逐。阿努利卡可能在看着他们。她现在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大伙围坐在灶火边吃饭的时候,弟妹们会拼命争抢汤里的干鱼片,她会把他们分开。她会等到所有的木薯粉都吃光了,再把鱼分给每个孩子,她也会像乌古那样,把最大的一块留给自己。
乌古打开冰箱,又吃了一些面包和鸡肉,他飞快地往嘴里塞着东西,心怦怦直跳,仿佛是因为跑步导致心跳加速。他又撕下几大块鸡肉,拽下两只鸡翅膀。他把这些东西塞进短裤口袋里,来到自己的卧室。他要把这些鸡肉留着,等姑姑来看他时,让她带给阿努利卡。或许他可以让姑姑带一些给内西纳齐。说不定内西纳齐会因此注意他。他从未搞清楚自己与内西纳齐之间究竟有什么血缘关系,不过他知道他们属于同一个umunna(宗族),不可能结婚。但他仍然希望母亲不要总把内西纳齐叫成他的妹妹,总对他说:“把这些棕榈油送给内西纳齐的妈妈,她不在的话,就交给你妹妹。”内西纳齐跟他说话的时候口气总是很含糊,眼神也不集中,似乎他在不在她面前都无所谓。有时候内西纳齐叫他奇埃基纳,那是他堂弟的名字,可堂弟长得跟他一点都不像。他说:“是我。”内西纳齐则会回答:“抱歉,乌古哥哥。”听上去很疏远,很客气,让他明白她不愿意再往下聊了。不过乌古喜欢给她家跑腿。他有机会看到内西纳齐弯腰给燃烧的木柴扇风,或剁碎乌谷叶子,加到母亲的汤锅里,要不就是坐在屋外头,照看弟弟妹妹。她的裹裙系得比较低,乌古看得见她乳房的上端。自打她那对尖尖的乳房突兀耸起,乌古便不住地想:它们是像糊糊一样软,还是跟乌贝树上未成熟的果实一样硬?他常常希望阿努利卡的胸部不要那么平坦,让他可以摸一摸—令他不解的是,是什么使得她的乳房发育那么慢,毕竟她与内西纳齐年龄差不多。当然,阿努利卡会啪的一声拍掉他的手,或许甚至打他一耳光,不过他会速战速决—捏一下就跑—如此一来,至少他能做到心里有数,一旦终于有机会抚摸内西纳齐的乳房,最起码知道那会是什么感觉。
可是乌古担心,自己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抚摸内西纳齐的乳房,因为她叔叔已经提出让她去卡诺学做一门生意。等到年底,她母亲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她整天抱着的那一个—开始走路时,她就会去北部。乌古想表现得跟家中其他人一样地欣喜和感激。毕竟北部是个有钱赚的地方。乌古知道有人北上做生意,回来后拆掉了茅屋,盖起了带波纹铁皮屋顶的房子。可他害怕个大腹便便的生意人会看中内西纳齐,他知道接下来便会有人带着棕榈酒上她父亲家来,从此他就失去了抚摸那一对乳房的机会。很多个夜晚,他在手淫的时候,先是慢悠悠地抚弄阴茎,而后加大力度,直到一声微弱的呻吟脱口而出,内西纳齐的乳房是他留到最后时刻才让它在脑海里闪现的图像。他总是先想她的脸,她圆润的双颊,象牙白的牙齿,然后想象着她的双臂环绕着他,她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身体。此时他才让她的乳房现形。有时候她的乳房感觉很硬,他忍不住想咬一口;其他时候,她的乳房非常柔软,他担心光是在想象中用手捏一捏它们,便会让她疼痛难忍。
乌古考虑今晚想一想内西纳齐,不过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他在主人家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也是他第一次睡在这样的床上—完全不像家里那种手工编织的酒椰席子。他先是用手压一压柔软又有弹性的床垫,又仔细瞧了瞧上面覆盖的几层布,不知道是该睡在布上面,还是该在睡前把布取下收起来。他爬上床,躺在布上面,身体蜷缩成一团。
他梦见主人在叫他—“乌古,我的好伙计!”—他睁开眼睛,发现主人就站在门口,望着他。或许他根本没做梦。他赶紧爬下床,疑惑地瞅了瞅已经拉上窗帘的窗户。天很晚了?难道这张柔软的床欺骗了他,害得他睡过了头?他一般天一亮就醒了。
“早上好,先森!”“这里有股很浓的烤鸡味道。”“对不起,先森。”“烤鸡在哪儿?”乌古在短裤口袋里乱摸了一通,掏出来一些鸡块。
“你们那里的人睡觉的时候还吃东西吗?”主人问。他穿着一件像是女士外套的衣服,心不在焉地捻搓着系在腰间的绳子。
“您说什么,先森?”“你是不是想在床上吃烤鸡?”“不是,先森。”“食物不要带出餐厅和厨房。”“是,先森。”“今天必须把厨房和浴室清扫干净。”“是,先森。”主人转过身,走了。乌古站在屋子中央,浑身发颤,抓着鸡块的手依旧伸着。他多希望用不着走过餐厅,走到厨房。终于,他把鸡块塞进短裤口袋,深吸了一口气,走出了屋子。主人坐在餐桌旁,面前的一堆书里放着一个茶杯。
“你知道谁是杀害卢蒙巴的真凶吗?”正在看杂志的主人抬起头,问道,“美国人和比利时人。与加丹加省没有关系。”“您说得对,先森。”乌古希望主人不停地说下去,他想听主人洪亮的音,还有悦耳的夹杂着英语单词的伊博语句子。
“你是我的男仆,”主人说,“如果我命令你到大街上,用棍子打一个路过的妇人,你打得她的腿流血受伤,谁该为她的腿伤负责?你还是我?”乌古瞪大了眼睛,摇了摇头,不能确定主人是不是在拐弯抹角地说烤鸡的事。
“卢蒙巴是刚果的总理。你知道刚果在哪里吗?”主人问。
“不知道,先森。”主人立即站起身,走进了书房。乌古既疑惑又害怕,连眼皮都发颤。是不是因为他的英语说得不好,把鸡肉装在口袋里过夜,不知道主人提到的那些陌生地方,所以主人要把他打发回家?主人拿着一大张纸回来了,他展开这张纸,铺在餐桌上,书和杂志被他推到了一边。他用笔指着说:“这是我们的世界,尽管画这张地图的人决定把他们的土地置于我们的头顶。你看,根本不存在头顶和脚底。”主人把图纸拿起来对折,两端相对,中间留下一个窟窿。“我们的世界是圆的,没有尽头。Neeanya(看这儿),这都是水,都是海洋,这是欧洲,这是我们的大陆—非洲,刚果在非洲的中部。上方这里是尼日利亚,恩苏卡在这儿,东南部—这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他用笔轻轻敲了敲。
“是的,先森。”“你上过学吗?”“上过小学二年级,先森。不过我学什么都很快。”“小学二年级?多久了?”“到现在很多年了,先森。但是我学什么都很快!”“为什么退学了?”“我父亲的庄稼没有收成,先森。”主人缓缓地点点头,说:“你父亲为什么不借钱供你读书?”“什么,先森?”“你父亲应该借钱!”主人厉声说,接着又用英语说,“教育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没有知识,不了解剥削,我们如何能够对抗剥削?”“您说得对,先森!”乌古使劲点着头。他一定要尽可能地表现出思维的敏捷,因为主人的眼睛里闪烁着狂热。
“我要送你去上这所大学的子弟小学。”主人说,手上的笔还在敲打着餐桌上的图纸。
乌古的姑姑对他说过,他尽心伺候主人几年之后,主人会送他去商业学校,在那里他可以学习打字和速记。姑姑也提到过员工子弟小学,只是告诉他,上这所学校的都是这所大学的教师的孩子,他们穿着蓝色的校服和白色的短袜,短袜上面装饰着几缕蕾丝,十分精致,你会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为了区区一双短袜浪费那么多时间。
“好的,先森,”他说,“谢谢您,先森。”“我想你在这个年龄才开始上三年级,一定是班上最大的学生,”主人说,“你要赢得同学们的尊重,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最好的学生。明白吗?”“明白,先森!”“坐下,我的好伙计。”乌古坐在了离主人最远的椅子上,很不自在地把双脚并拢。他更喜欢站着。
“关于我们的土地,他们教给你的一切都有两种答案:真实的答案和考试及格所要求的答案。你必须读书,知道两种答案。我会给你书,非常好的书。”主人呷了一口茶。“他们将教给你说,是一个叫芒戈·帕克的白人发现了尼日尔河。胡说八道。远在芒戈·帕克的爷爷出生之前,我们的人民就在尼日尔河里打鱼了。但在考试的时候,你只能写是芒戈·帕克发现了尼日尔河。”“是,先森。”乌古多希望这个叫芒戈·帕克的人没有给主人带来这么大的不愉快。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什么,先森?”“唱首歌给我听。”“先森?”“唱首歌。你会唱什么歌?唱吧!”主人一把扯下眼镜。他双眉紧锁,表情严肃。乌古唱起他在父亲的农田里学会的一首老歌。他的心怦怦地敲打着胸膛,疼极了。“Nzogbonzogbuenyimbaenyi(踩呀,踩呀,巨大的象)……”刚开始乌古的声音很低,但主人用笔敲着桌子说:“大声点!”于是他提高了声音,主人还是一个劲地说:“大声点!”直到他扯着嗓子尖叫,主人才满意。乌古反复唱了几遍之后,主人让他停下来。“唱得好,唱得好。”他说,“你会泡茶吗?”“不会,先森。但是我学得很快。”乌古回答。唱歌释放出了他心里郁积的某种情绪,现在他呼吸轻快,心脏也不怦怦乱跳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主人非常疯狂。
“我基本上都在员工俱乐部吃饭。现在既然你来了,我想我得多带点食物回家。”“先森,我会做饭。”“你做饭?”乌古点点头。很多个夜晚,他曾在一旁看着母亲做饭。他为母亲生火,火快熄的时候会用扇子扇。他削掉山药和木薯的皮,把它们捣碎,吹掉稻米里的谷壳,拣出豆子里的象鼻虫,剥开洋葱,磨碎胡椒。母亲犯病咳嗽的时候,他常常希望做饭的是他,而不是阿努利卡。阿努利卡对他说过,他花了太多的时间跟做饭的女人混在一起,再这样下去,他恐怕长不出胡子来。
“那好,你可以给自己做饭,”主人说,“你需要什么,列一张单子。”“是,先森。”“你不知道怎么去农贸市场,对吧?我会叫乔莫领你去。”“谁是乔莫,先森?”“乔莫收拾庭院。他每周来三次,是个有趣的人,我见过他对着巴豆说话。”主人顿了一下,“反正他明天会来。”之后,乌古列了一张食品单,交给了主人。
主人盯着单子看了一会儿。“了不起的组合,”主人用英语说,“我猜学校的老师会教你多用一些元音字母。”乌古不喜欢主人忍不住想笑的表情。“我们还需要一些木料,先森。”他说。
“木料?”“用来放您的书,先森。这样我才能把它们归整好。”“哦,对,是书架。我想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多摆几个书架,也许走廊里可以试一试。我会去找工程部的人。”“好的,先森。”“奥登尼博。叫我奥登尼博。”乌古疑惑地盯着主人。“先森?”“我不叫‘先森’。叫我奥登尼博。”“是,先森。”“奥登尼博是我一辈子的名字。‘先生’这个叫法变幻无常。明天‘先生’可能就是你。”“是,先森—奥登尼博。”乌古其实更喜欢“先森”这个称呼,叫起来干脆有力。几天后,工程部来了两个人,在走廊里装书架。乌古告诉他们,必须等先森回来,他自己不会在这张打字机打印了字的白纸上签字。他说“先森”两个字的时候,充满了自豪。
“他是乡下来的男仆。”一个工人不屑地说。乌古盯着这个人的脸,低声诅咒急性痢疾永远缠着他和他的子孙后代。他摆放着主人的书,在心里发誓说一定要学会在表格上签字,这些话差点脱口而出。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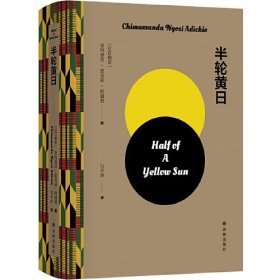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