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流美学(日本美学十八家译丛)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35.43 4.5折 ¥ 78 全新
库存21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日】冈崎义惠
出版社上海译文
ISBN9787532794560
出版时间2024-04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32037052
上书时间2024-10-15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冈崎义惠(1892-1982)日本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出生于高知县,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东北帝国大学教授。
倡导“日本文艺学”并致力于使其体系化,同时立足于日本古今文学史,研究日本审美传统,形成一系列独特的美学主张。
主要著作有《日本文艺学》《艺术论的探求》《风流的思想》《文艺学概论》《美的传统》《日本古典的美》《近代文艺的研究》《史的文艺学的树立》等。\"
目录
\"【目录】
译本序 于不风流中见风流
一、风流的原义
二、平安时代的风流
三、中世“过差”与“婆娑罗”的“风流”
四、茶道的“风流”与“数奇”
五、花道的风流
六、香道的风流
七、一休宗纯与五山禅林之“风流”
八、俳谐的风雅与风流
九、画论中的风流
十、近世小说中的风流
十一、明治大正小说中的风流
十二、子规的风流
十三、漱石的风流观
十四、明治以后的风流论
后记
译后记
\"
内容摘要
\"【内容简介】:《风流美学》是日本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冈崎义惠关于美学的重要著作。
《风流美学》介绍了日本自古以来风流思想出现的脉络及其历史价值,阐释了近代以来在西洋影响下日本风流呈现出的新世相,并通过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等日本文学大家的风流思想加以具体分析。如夏目漱石的风流思想是西洋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思想结合之下形成的“则天去私”思想的一部分,西洋教养在其精神构造中影响深广,昭示了昭和大正时代新风流的特色。而森鸥外的风流思想更多盘踞于东洋精神之上,倾向于将一切包纳在人的浑融精神之中,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美等。《风流美学》厘清“风流”的原意以及其与“风雅”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并对“风流”进入日本后,在平安时代、中世等不同时期的美学特性及发展演变加以缕析,对风流在茶道、花道等不同艺道乃至日常生活之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论述,更深入作家作品,分析“风流”在文学中的不同呈现。可以说,《风流美学》一书全面详尽展现了日本“风流美学”的样貌,并在与中国“风流”、西方美学的相关概念的比较中,确立了日本“风流美学”的民族特性。\"
精彩内容
\"【精彩书摘】漱石虽说并不属于以“风流”思想为中心发展其艺术观的作家,但漱石“则天去私”的艺术观的确立,“风流”却是参与其中并占据着重要地位的。
我始终认为,若将《草枕》的艺术观凝练出来,那其后“则天去私”说的成立也就变得顺乎其然了。——忘我,而后融入绝对的世界,去象征地描绘那无我的恍惚之境,描绘处于无我之境并与之相融合的对象,艺术由此而生。这样的艺术是纯粹的观照的世界,同时,它作为被观照的事物又足可让无法被观照的绝对事物得以清晰呈现,是象征的世界。艺术正因这样的象征作用表现出其脱俗性,它具备将满心自我的人引入无我之境的感化力。——漱石若能将《草枕》中这一基于精神性的艺术观加以充分发挥,或可确立一种带有东洋宗教色彩的精神主义艺术观,然而漱石反而选择了克服《草枕》的艺术观,并因对道德性与科学性的顾虑而逐渐深入其中,最终形成了“则天去私”这样一种难解的艺术观。《草枕》的美学,其中诗性的正义论与余裕派小说论足可克服伦理性、科学性的理论。《草枕》的美学因过度局限于感觉美的层面而具有相当的缺陷,但在余裕派小说论(以及写生文论)中,漱石着意将真与善纳入了非人情的观照之内,同时又为其确立了禅宗的宗教背景。而写生文论则将谐趣的美与温情乃至“物哀”之美融入了其审美观照。由此,《草枕》的精神性方得以完备。
尽管如此,漱石却并未向着将《草枕》美学、余裕派小说论以及写生文说相统一而后对“则天去私”艺术论加以体系化的方向进展下去,而是巧妙地引入了西洋风的写实文学、情操文学对立论,以及禅宗精神与儒教道义观,最终呈现出来的,与其说是与《草枕》精神相融合的审美态度,毋宁说是与其相对立的艺术观念。由此,《草枕》的美学发展,显示出了与作为小说论的“则天去私”说全无关联的形态,也正如晚年漱石思想中所展现的那样。“则天去私”的小说论毋宁说是与《草枕》恰好相对的、具有西方写实文学与人道主义倾向的艺术论,是漱石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却反被西方近代小说所影响的一次适得其反的反影响。
自《草枕》而至晚年的汉诗创作,漱石对“风流”的憧憬是一以贯之的,其作为东洋艺术观的中心地带,或可成为“则天去私”的中枢轴般的存在,然而作为小说论的“则天去私”,却奇妙地与之毫无关联,毋宁说与之呈现出了相背反的状态,这实在是有趣。若将惯来作为《明暗》世界之延展的“则天去私”视作风流的艺术,恐怕许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从这个意义上说,“则天去私”实际上是一条被西方近代小说的黄尘蒙蔽的道路。无论漱石于“则天去私”说中完成了怎样的艺术论,想来都与漱石所憧憬的“风流”观无法融合吧,这样的设想必定是成立的,这实际上也正是内在于漱石的最大矛盾。
对于写实文学的“则天去私”,我们或可通过自然主义系统的西方艺术论窥其全貌,若是劝惩层面的“则天去私”,其或许与马琴亦相去不远,唯独《草枕》以来的风流观,我们只有潜入漱石内心深处方可知其底奥,那是一种以全然忘我的热情阐说生命救赎的观念。而且因其并无处于“则天去私”艺术论中心的自觉,这样的“则天去私”说中总带着一股半生不熟的意味,也不免有被视作逍遥“没理想论”之复踏的风险。
我曾专注于漱石艺术观的研究,现仔细吟味其风流观,方觉漱石的风流观在其“则天去私”的艺术观主道中似乎占据着一席之地。
其实,漱石从很早开始就对“风流”抱有浓厚的兴趣。明治二十二年(二十三岁)五月,在为正冈子规《七草集》所写的评论文中写道:“吾天资陋劣,加之疏懒成性,龌龊没于红尘里,风流韵事荡然一扫,愧于吾兄者多矣。”以此褒美子规的风流,并写下了汉诗一首:“江东避俗养天真,一代风流饯逝春。谁知今日惜花客,却是当年剑舞人。”(十四卷,四三五、四三六页)这是他以“漱石”为号之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漱石在风流世界中的启程之作,也是漱石风流观的出发点。
同年九月完稿的《木屑录》是漱石游历房总之时的纪行文,其中漱石有记:“同游之士合余五人,无解风流韵事者,或被酒大呼,或健啖警侍食者,浴后辄围棋斗牌以消闲,余独冥思遐搜,时或呻吟,为甚苦之状。”(十四卷,四四一页)由此我们不难想见离群独处的青年漱石风流人的风姿。《木屑录》是一部充斥着中国风的风流韵事的纪行文,如序言开头所说,漱石是受到了少时爱读的唐宋文学的影响,这使得漱石的“风流”带上了中国式风流的基调。漱石当时迫于课业压力在学习英语英学,一时忘记了这种带有“东洋风”的“风流韵事”,但在与子规相交之后,在子规的影响下又重燃了对东洋诗境的热情。然而,与子规在《七草集》中尝试汉文、汉诗、和歌、俳句、谣曲、论文、拟古小说等各种传统文类相对地,漱石在这方面并没有花费过多心思,而是只以汉诗文踵迹子规之后。
当时的漱石,拥有着对汉诗的兴趣,并由此催发了对俳句的热情,他确实是优游于风流的世界并坚守着东洋的诗的传统。然而这样的蓬莱仙境很快就被现实的狂涛吞没殆尽。友人与兄长罹病,自身同样病弱不堪,加之落第,数年后又患上了肺病。“仙人堕俗界,遂不免喜悲。啼血又吐血,憔悴怜君姿。漱石又枕石,固陋欢吾痴。”(明治二十三年八月末写给子规的书信)这首汉诗,实为现实的写照。在二十三年八月九日写给子规的书信中,漱石吐露了内心极端的厌世情绪,他为厌倦浮世却又无法自杀的自己感到羞耻。在这封书信中,漱石写到了自己因眼病放弃学业后漫漫夏日难熬的处境,同时也不嫌冗余地描绘着庭中各色风物。观此书信,我们不难感知其中那无法专注于风流雅事的浮世苦痛与在苦痛中仍不忘追寻风流的情绪错综,这也成为后来漱石则天去私之风流确立的出发点。
这个时代的“风流”,尚未脱出古风的传统世界,仍然是“看帘外海棠而生惜花之情”的风流。漱石也没有摆脱“哀”、“趣”等平安王朝时代的趣味。他也会创作一些拟古文,不过比之和歌物语,漱石更倾心于汉诗与俳句的意趣,但不管怎么说,此时漱石的审美意识尚是传统的。这也并无难以理解之处。明治二十二、三年,是红叶、露伴等人的新小说初露头角的时代,若说最具西洋风的作品,当属是鸥外的《于母影》《舞姬》等了。但纵然是这样的新文学,也多是参杂着汉文调的拟古文,不过是强行披上了西洋风的外衣而已。写下《浮云》的二叶亭亦是如此。子规也尚未找到能够超脱传统风流的风流之路。
于漱石而言,因与子规交游而触发的风流之心,自青年时代而至明治三十三年留学海外一直都未曾断绝,直到明治三十六年(子规辞世的次年)一月归国,漱石开始以英文学者的姿态出现在日本文坛。读漱石全集便知,在明治三十三年漱石写下无题汉诗“君病风流谢俗粉,吾愚牢落失鸿群。磨瓦未彻古人句,呕血始看才子文。陌柳映衣征意动,馆灯照鬓客愁分。诗成投笔蹒跚起,此去西天多白云”之后,此后的十年间漱石便再未写过一首汉诗。他的俳句创作也是如此,在明治三十二年之前,每年都有大量的俳句问世,但到明治三十三年之后便数量锐减了。应该说,以留学海外及子规之死为转折点,漱石的风流世界也退潮了,他开始转向了西方文艺的研究与西方式小说的创作。事实上漱石最早是对建筑颇感兴趣的,后因折服于友人米山的高谈阔论而期望成为文学家,但他并不想进入汉文科和国文科,而是选择了英文科,他说:“我希望能够通达英语与英语文学,以外国语写出足以震撼西洋人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谈话《处女作追怀谈》十八卷,六七四页)可见,与子规贬抑南蛮文章而尊崇自国文学相对地,漱石似乎并未肯定自国文学的价值,而是为洋书着迷,虽说他已经放弃了成为“洋文学队长”的念头,但他并没有放弃西洋文学而追捧自国文学,他还是期待着未来能够创作出堪与西洋文学相比肩的作品,他怀着强烈的通过学习西方文学样式而使日本文学具备世界性的愿望。
然而,漱石通过在英国的生活深刻意识到让文学实现外国化的困难性,而且在此期间,风流的思想在漱石的内心其实并未绝迹,而是不时地点缀在漱石的作品之中。无论是在鉴赏西方文艺的时候,还是进行西洋风物批判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在风流世界中驰骋的漱石的思想。
漱石特别在《文学论》中指摘了英国人对自然之美的漠不关心,他例举道,英国人无法理解见雪而心悦、见月而生怜的心境;当他们看到庭中山石时会将其移走;当他们被问到路旁松树价值几何时,回答的不是其作为庭树的价值,而是作为木材的价格;在苏格兰宏伟的宅邸,在苹果园中的小径上,看到郁郁苔痕,感叹其古雅风味时,他们却会命园丁悉数铲去。(十一卷,三四八页)漱石在其中虽未用“风流”一语,但仍处处流露着东洋风流的韵致。当然,漱石也并不否认西方存在着与风流相类的审美意识,但他认为那与日本相比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主张以日本人的眼与心去观照西洋文艺的漱石,唯独站在“风流”的立场上批判了西洋。(类似的观念还可见于谈话录《英国的园艺》第十八卷,五四八页)事实上,这样的主张早在漱石学生时代的论文中就已初现端倪了。他认为,“英国诗人对天地山川的观念”正如英国自然派诗人所论述的那样,而漱石对自然之爱的兴味,是在东洋风流的滋养之中生长而成,这一点即使是在他用外文横写的文章中也不难发现。其中,对于彭斯的水鸟诗,漱石认为其所流露出的感情深笃,他认为,世上有人看到动物而产生食欲,也虐待动物成性之人,“他们不仅是风流的罪人,也是‘彭斯’的罪人。”(第十四卷,一九五页)漱石在子规去世之后便甚少创作汉诗与俳句了,然而,“风流”作为子规的代表,也作为对子规追慕之情的寄托,在漱石后来所写的小说之中也以各种不同的形态出现。漱石初期浪漫的、梦幻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一些风流的意味,但像《幻影之盾》《韭露行》这样的作品中所展现的,更确切地说是西洋式的风流,因其带着明显的西洋的风调,能不能将其视作真正的风流也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西洋式的风流是以“爱”、“想象”这样西洋式的美为中心的,与东洋式的飘渺空灵之美颇为不同,因为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生现实生活的拘泥。相比之下,如《一夜》《草枕》,以“非人情”之美为生命,本质上显示着一种东洋风流的极致状态。而《虞美人草》则是对西洋审美与东洋趣味的综合,但也因此而失却了浑然天成的兴味。《虞美人草》以俳句为中心的构想无疑是风流的,但决意以爱征服异性的藤尾作为西洋式的女性,其道义的精神却很难说是东洋式的,而且小说中也包含着西洋式的悲剧论。
漱石在《一夜》中虽未用“风流”一语而只使用了“雅”字,全篇却流贯着东洋风的风流。这部作品中尽是对梦与现实交缠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让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情调,其中既有与妖艳的感觉之美相伴而生的无形的快感,亦有伴随着否定一切合理性的超越而生发的神秘的氛围。这样的情调一经结合,便于刹那的印象中凝结出了一个永恒的世界,让人倍感空灵飘渺之况味。而《幻影之盾》的末尾也为读者描绘出了一个极具东洋风调的幻想的世界。《一夜》描写了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个夏夜里会谈的光景,人们或许也会去想三人间是否产生过三角的恋爱关系,但小说最终超越了人生戏剧化的纠葛,建筑起了一个清净的梦的国度。而漱石在小说中也不过是捕捉到了如同自然般存在着的三人人生中的刹那,这是艺术的、俳谐式的创作方式,这种将小说俳谐化的写作方法和态度与《草枕》几乎如出一辙这部作品从蓄须男人“许许多多美丽之人的许许多多美好的梦啊”这样的微吟写起,写另一个无须男人的反反复复絮语:“真是描绘也描绘不出的美啊。”作者认为他们是“脱口说出了从前就已意识到的禅语”。无须男子高声念诵着“写不出,画不成啊,是梦,怎么描绘得出”的话,桀桀大笑,回望着屋中的女子。在作品中,对“美好的梦”的追寻是三人生命一般的存在。三人交互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探寻着这“许许多多的梦”,在并这个过程中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感性之美。(因为于漱石而言,“美”就是感性的快感。)于是在各式各样的梦中,他们会不时踏入交织着人情美的“物哀”境界,脱离肉身,消散在超越的、禅的洒脱空气中。
细思《一夜》的立意便知,其构建的是一个诗性的、浪漫的“则天去私”的世界。其中所描绘的“空中独唱白雪吟”的境界,是一种小说的形式亦无法言明的奇妙世界。人生的真实,说到底并不是在恋爱悲剧的世界的沉浮,而是某个潇洒夏日的一夜清凉。而对梦与诗的追寻,至少可以成为这虚幻人生中唯一的热情所在,也让一切在夜深之时、睡梦之中进入一种“太平”之境。小说中便有这样一段对三人入睡之后的叙述:“忘尽所有,女子忘记了她美丽的眼与美丽的发,蓄须的男子忘记了他的胡须,无须的男子也忘记了他没有胡须的事情,他们越发地感受到了太平。”或许,唯有这样的“忘我”,才是真正的“去私”;唯有在绝对的无中做个太平的梦,才是通向“则天”之所的路径。三人醒时的种种风流——那所有充溢着感性之美与雅趣的梦——都是通向最后的忘我之境的途径,或者说,都不过是在忘我之境浮现出的一场梦。而对一刻梦境的描写也并不是要将人生的全部加诸其上。这样想来,《一夜》正是漱石“则天去私”思想在一个侧面的呈现。其正是以刹那的感觉去象征人生,并在绝对的“无”中主张着“则天去私”的风流。
即使在《一夜》之外,“风流”的气息也仍然是漱石在其初期浪漫主义时代所创作的小说的一大特色。现以漱石对“风流”一词的使用为线索对其加以简单论述。《我是猫》一书是围绕着苦沙弥周围的丑恶世界发酵而起的嘲笑与谐谑,更大程度上表现的是一种与“风流”相抵牾的东西。也就是说,其中更多是风流的缺乏,当然这也在更深的层面上表达了一种对风流的尊崇。就像迷亭说的:“午睡之事出现在中国诗中的确风流,可像苦沙弥那样把它当作日课去做,就不免俗气咯。”(一卷、二六八页)再如猫曾嘲讽过名为落云馆的私立中学却未必有风流君子。(同,三五七·三五八页)而面对妻子和侄女对苦沙弥买来的德利的嘲笑,苦沙弥也称之为无风流。(同,五一二页)诸如此类,都可以说是以诙谐的姿态俯瞰无风流者聚合的世界的一种风流。小说还写了小偷入户时苦沙弥一家不雅的睡姿,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春日的灯火当真别有一番情致,在这天真烂漫而又极度缺乏风流的光景背后,那令人神迷的灯火光辉似在提醒人珍惜这良夜。”(同,二一五页)可见,即使是在无风流中,也有那温软风流的灯火光辉,这也是此作中对风流的部分表现。
阅读《我是猫》,总能让人感受到其间萦绕着的“寂”的“风流”况味。事实上,这部作品不乏嘲讽“寂”,苦于“寂”,无法安住于“寂”之美的描写,在这个意义上,它似乎继承了反风流的厌世观的血脉,具有悲剧作品或披露小说的意味,但在那高度诙谐的空气中,我们仍然能够体味道其对风流幽微的憧憬。而这种幽默作为一种美,应该说也是从属于“风流”的。为了表现出这种极具吸引力的谐谑与讽刺挖苦,小说中能够达到风流之境的幽默其实是极为微弱的,但它仍然可说是后来漱石则天去私思想得以成熟的前奏。
不过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看,最能代表漱石这一时期的“风流”的,仍属《草枕》。这部作品中几乎不再表现“侘”、“寂”的风流,而是以感觉美的风流与超脱美的风流创造了一个风流的世界。“我是画工,是个只对作画工感兴趣的男人,纵使身陷人情世界,也要比不风流的东西边邻人要高尚。”(三卷,一七三页)这可说是对《草枕》的世界就是风流世界的宣言。而且这个风流世界正如画家所言,是一个充溢着趣味与美的所在。\"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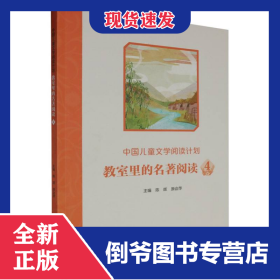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