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35.63 4.6折 ¥ 78 全新
库存2件
作者(美)琼·柯普洁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2182862
出版时间2022-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31396696
上书时间2024-10-13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琼·柯普洁(Joan Copjec),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媒体专业教授,重要的精神分析杂志《Umbr(a)》的创办人。她也是多部著作的作者和编者,包括《想象并无女人:伦理与升华》(Imagine There’s No Woman: Ethics and Sublimation)、《假定主体》(Supposing the Subject)等。她近期新的研究方向为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与中世纪伊斯兰哲学。
◎译者简介
王若千,曾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求学,关注左翼政治、艺术史和精神分析。
目录
总序 | 重拾拜德雅之学
中译本序 | 偶然性与无意识(致我的中国读者们)
致谢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1 导论:结构不上街
2 精神矫正的主体:电影理论和拉康的接受状况
3 切割
4 服装化的超我
5 吸血鬼、哺乳与焦虑
6 无能的大他者:歇斯底里与美国民主
7 密室或孤寂的房间:黑色电影中的私密空间
8 性与理性的安乐死
索引
内容摘要
本书是美国重要的文化理论家、拉康派批评家琼?柯普洁第一本专著,她运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从电影、哲学、文学、摄影等多个角度,对弥散在人文领域中普遍的“福柯幽灵”发起了雄辩的声讨。拉康和福柯虽同被视为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关键人物,但他们思想中的隐含分歧却将我们导向对诸多文化现象截然不同的理解与反思。
在书中,作者不仅尝试为精神分析重新夺回对“性”“凝视”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解释权,澄清语言和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还将展示精神分析对历史的独特见解:“主体是没有满足历史需求的历史产物。”作者主张,文化批评的使命在于读懂欲望,即文化表述中那些无法言说的部分。
主编推荐
★一场在雅克·拉康(精神分析)和米歇尔·福柯(历史主义)之间的理论碰撞,一次对历史主义的深刻批判。在“如何处理欲望?”这一问题上,精神分析和历史主义分道扬镳。
★犹如亲临拉康的讲课现场,柯普洁娴熟地使用拉康的诸多关键概念去讨论一系列议题:亨利·柏格森、功利主义、吸血鬼、侦探小说和黑色电影、朱迪斯·巴特勒……她提出充分的理由向我们证明,在对历史过程以及生成原理的解释上,拉康的思考模式具有一种优越性。
★通过促使文化分析者读懂欲望,读出文化叙述中无法发声之物,一种新型的文化批评呼之欲出。
精彩内容
偶然性与无意识(致我的中国读者们)听闻我的第一本专著即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愉快且荣幸。 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喜讯令我感到几分惊讶,正如不久之前,一则网上的新闻故事带给我的。 这则消息有关一群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每周在Zoom上聚会,讨论18世纪塞缪尔?理查逊(SamuelRichardson)那本整整1500页的小说《克拉丽莎:又名一个年轻小姐的故事》(Clarissa:orTheHistoryofaYoungLady),以此来纾解当下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隔离而带来的苦闷。“真够神奇的”,看到这则消息时我暗自思忖。 这本小说的完整版本极少被人阅读,取代它的则是一个常见于大学文学课程的、 大幅缩写的版本。 我无意于将本书与理查逊这本极为重要的小说相提并论,我只是讶异于支配着种种事物出现、 消失又重现的神秘节奏。 从未有人会预料到这部小说将与这群知识分子产生一种特殊的关联,后者正苦于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种种社交退避(socialwithdrawals)的症状。 似乎突然之间这部小说又变得重要了,这佐证了偶然性的本体事实(ontologicalfactofcontingency)。
按照宽泛的学术发表标准,这本书在1994年的首次出版是成功的。 它即刻就被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重印了,随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接着被Verso出版社纳入“激进思想家”(Radical?inkers)系列中再版。 然而,尽管本书的反响颇有热度,我亦觉察到一股寒意——甚至在它出版之前。 本书第1章作为论文首次提交于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法国拉康派电影理论的美国接受”(Th?eU.S.ReceptionofFrenchLacanianFilm?Theory)。 我论文的评议人雷蒙?贝洛(RaymondBellour)对我的论点提出了充满敌意的回应,在当时甚至引发了一场小型丑闻。此后,当会议论文被结集成书时,贝洛决定不再提交他的回应用于公开发表,相反,他写信给会议组织方来说明他拒绝提交的种种理由。 他写到,没有必要给我的论文一个回应,因为它与会议所宣称的主题以及他的期待并不“切合”(staywithinthelines)。 会议的组织方《框外》(HorsCadre)杂志并没有忽视贝洛对我“不符合游戏规则”的指责中存在的反讽意味,他们将这封信公开在会议文集中。显然,在框架外进行思考是不被允许的。 美国电影理论家托德?麦高恩(ToddMcGowan)也没有忽视这其中的反讽,他在《电影理论与“游戏规则”》一书中提到了这个我称之为“小型丑闻”的插曲,通过将其重塑为电影理论中的一个“创伤”,他强调了它所暗含的(学术)重要性。
本书最后一章也经历了一种相似的遭遇。这篇文章作为一次对精神分析性别差异学说的严肃重访而受到欢迎,然而一种沉默却扼杀了我论点的后续影响。 这篇文章的拥趸之一,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i?ek)第一个指出了这种沉默:“这篇有关拉康派性别差异理念的哲学基础与后果的论文,在众多对拉康的攻击中被悄悄回避了。”齐泽克始终拥护我的论点,同时他也采用“创伤性的”一词来指涉女性主义者们的缄默。我们本来期待着与她们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
如果没有激起一种防御的话,我在本书中的许多论点至少也该触发一场学术上的争论,不过没有必要继续纠结于学界对本书的这种古怪而严重的“忽视”。毕竟,我的观点也没有完全被无视,不少才思敏捷的学者极其认真地对待它们,并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及变化(twists)——这些都是我未曾设想并十分钦佩的。同时我也理解,虽然我严厉地在本书中批评了历史主义(historicism)这一在我写作之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方法,但仅凭这些并不可能击倒这位强大的对手。在大多数人眼中,历史主义是对思想的救赎;而在我看来,它所及之地一片荒芜。人们不应当天真地踏入这些战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某些间歇性的“忽视”,正因为它们带给我“创伤”这一外号。当我们用创伤来指涉某个事物——或某人,如在此语境中——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精神分析理论在创伤的问题上付诸了大量的笔墨。我所获得的标签给了我一种新的动力来回顾这个已被充分研究但依旧紧迫的概念。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创伤命名了一种无能(inability):无能去转化或消解某些事件,无能将某个事物纳入意识的系统当中。从这个简要的定义出发,许多问题涌现而出,尽管在此我们只能提到其中的一些。 如果引发创伤之物存在于意识的外部,那么它何以困扰——或者,更确切地说:创伤化——意识呢? 为何意识不简单地将其忽略或无视,也就是“不被创伤化”(untraumatized)呢? 这必然是由于这无法被消解的事物并不单纯处在意识之外,而是紧密地与后者相联系。创伤既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结构性的,这个事实也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从时间上,我们所谓的创伤性时刻就是指有些事情,它们颠倒了所有在它们发生之前的事。革命就是创伤性的事件,因为它们在空间上破坏了正在运行的结构:结构突然间无法再像往常那样延续了。 然而,创伤并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有着明晰的立场:主体本身正是被一个创伤所构成的,或者说,主体本身是像创伤那样被构成起来的。性存有(sexuality)并不是主体性的次级现象,而是决定主体与其自身关系的、起源性的非共时性(originaryasynchronicity)。
尽管这一对创伤的双重定义广泛为人所接受,却未曾有一种持续的思考来尝试把握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不过,近来我意识到另一个弗洛伊德的概念,“无意识情感”(unconsciousaffect),或许能阐明这一点——尽管这个我寻求启迪的概念有可能使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因为很少能想到一个比它更自我反噬的概念。 一种不能感受其自身的感觉? 这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参加过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研讨班,而弗洛伊德的读者如果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OntheSoul)的话,便不会看不到精神分析之父与这位古希腊哲人之间令人震惊的共通性。在此背景下,无意识情感所提出的问题(“怎么可能会有一种不能被感受到的感觉呢? ”),在亚里士多德提过的一个问题中产生了回响:为什么会有没有感官效应的感觉呢?(whyistherenosensationofthesenses?)而亚里士多德的作答同时也对应着弗洛伊德的问题:“可燃的事物……从来不会自燃,而是需要一个有着点燃……力量的中介物,否则它就会自己燃烧起来,而不再需要一簇将它点燃的实际的火。”我认为我们最好将无意识情感理解为主体对她自身他者性——也就是性存有之创口——的一种感受性(receptivity)、一种创伤性质的开放性。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可能换一种表述:无意识情感就是被他者性所影响的能力(thecapacitytobeaffected)。然而,若不是遇到了某些其他引起它的事物或人,无意识情感究其本身而言是某种麻痹或者说麻木状态(anesthesia)。正如弗洛伊德的说法所暗示的,无意识情感并不只是一种不能被感受到的感觉(notfeltfeeling),而是一种对无的感受(feelingnothing)。 或者,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提出的,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一无所知(innocence)或缺乏感受,而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我们或可称为空白的感觉。为何做出这个区分如此重要呢? 它让我们思考了我们没有它便不能思考的东西吗?承认一种空白的感觉,就等于承认了对无的感受,或者说对非-存有(non-being)的感受,也就是对潜在性(potentiality)之非-存有的感受。
我希望可以在未来对这一点展开更多的探讨。不过,我先在这篇序言里,写下这些原初的想法以展望这个尚在萌芽中的写作计划。然而,这些原初的想法也意味着反思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要点。无意识情感对理解主体的创伤性结构至关重要,尽管每个主体都存在于历史之中。因此,创伤的双重定义在时间中得以实现:被(他者性)影响的能力遇到了造成精神和社会巨变的一些事件。我同时想指出,这种双重定义也解释了书写性文本与艺术作品的兴衰变迁。面对一个文本时无法解释的沉默,或许证明的并不是一种拒斥,而是一种开放性或一种准备状态(preparedness),它等待着某种历史性的情景,来开启对自身的新的使用或解读。
最后,本书就如过去我曾写过的每一本书一样,是带着对我的丈夫,迈克尔?索尔金(MichaelSorkin)深切的爱写就的——他是一位曾投入大量时间在中国设计了不少非凡作品的建筑师。我将这个译本献给对他的记忆。
◎精彩论述选摘《导论:结构不上街》我所要批判的观点并非贯穿福柯的全部著作,而仅局限于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性史》(TheHistoryofSexuality),以及1970年代中晚期的论文和访谈,在这段时期,他对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发生了立场上的转变。像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他在一开始根据结构主义所定符号结构和精神分析所定义的精神结构来剖析社会事实,但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他不仅抛弃了这两个学科,甚至还激烈地与之相对立。
尽管关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福柯主义广受推崇,因为它被认为必要地纠正了那些更加天真地将这两项当作独立实体(discreteentities)来处理的政治理论,但我们则要说,将社会简化为这些关系是成问题的。福柯反对有些社会学理论,它们试图借助对权力系统的描述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认为权力系统从外部介入并歪曲了这些现象;而福柯则认为,权力体制是内在地透过现象本身而运作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福柯未能完成他所宣称的使命呢?正是因为他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去提出一个“超越”(transcends)他所分析的权力体制的原理或主体。他正确且强烈地相信权力体制运作的原理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元原理(metaprinciple),一个附加在所有其他观察之上的逻辑观察(logicalobservation),人们可能会通过构想出一个特殊的体制来组织、囊括或理解其他的那些观察。相对于权力的体制,统摄这个体制的原理并不占据一个不同的、更高的位置。福柯并不愿到某些外部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原理,并最终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放弃去定义这个他曾经试图理解的事物。
你们反对结构主义是对的,你们可以抱怨它所勾勒出的不过是一些僵死的关系。因此,你们宣称结构不会上街也是对的——但不是出于你们所想的那些理由。所以关键不在于改变你们的分析模式,将结构带上大街,将它们理解为根植或内在于社会现实中的。关键在于从最初的模式所教给我们的东西中汲取教诲:结构不会——也不应该——上街。它们并不处在构成我们日常现实的那些关系当中,相反,它们属于真实界的秩序。
当拉康强调我们必须按照字面(literally)对待欲望之时,我们便能理解他是在教导我们如何避免落入历史主义思维的陷阱。说欲望必须按照字面来对待,意味着欲望必须被发声(articulated),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想象登载在言说的单一表面之上某种事物,而这也同时意味着欲望是无法发声的(inarticulable)。因为如果被按照字面来对待的不是言词而是欲望,这就必然意味着欲望能够以否定的方式(negatively)在言说中登载自身,也就是说,言说和欲望的关系或者社会表面和欲望的关系是一种否定性关系。
《服装化的超我》精神分析并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揭示之前看来似乎难以解开的主体的秘密;相反,它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弄清的真相,主体并没有什么隐秘的知识,或者借用那句著名的黑格尔式俏皮话:埃及人的种种秘密对他们自己而言也是秘密。
一旦“人”被开始赋予一种功能性的定义,旧有的服装体制便土崩瓦解,而人也随之服从于新的服装体制。男性们的服装差异被抹除了,而所有的阶级都接受了工作制服和风格的简化。平等主义决定了今天的政治日程,并允许人们不再凭借出身而是凭借自己的工作来定位自身,而衣着上的平均化和去标签化也正是对这一点的佐证。
拉康关于伦理的研讨班让我们认识到,在功利主义的命题“功用是令人愉快的”之下潜藏着第二个命题:愉快感具有功用性。正是因为它设想可以将愉快用来服务于一种普遍的善和社会整体,功利主义变成了(1)一个很大程度上的技术问题,并(2)富有扩张性。
精神分析反对这种伦理模型,这根源于它对作为社会基石的乱伦禁忌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 并不像功利主义那样,为被禁止的愉快附加了一系列的犒赏——扩大了的亲属关系、女人们、财产、贸易渠道、住房单位(Unitéd’Habitations)、新定居点(Seidlungen),以及幸福本身——精神分析将禁令从任何愉快的承诺中剥离出来,彻底清理了伦理之域,将所有好的事物都一扫而空。 精神分析的禁令不以奖励作为牺牲的条件,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它。因而,愉快在保障人们服从道德律法的问题上毫无用处。
克雷宏波明确知道哪种衣服是大他者所偏好的:它通常是丝质的,但这不是出于任何那些丝织物所固有的“内涵”价值,而是因为它的僵硬(stiffness)。僵硬、坚固,这些才是一直被欲求的特质。克雷宏波曾经写下他对北非人的倾慕,就因为他们在清洗衣服之后将它们随意地放置,任由它们变得风干而僵硬。这种倾慕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他的照片中,因为我们从来看不到有哪件衣服勾勒或显现出身体的轮廓,也没有哪件衣服在精细地润饰着它的穿着者并因此具有符号上的色情意味,相反在他的镜头下,这种衣料最大的特征正在于它那僵硬的构造。
《无能的大他者:歇斯底里与美国民主》让我们再一次援引拉康的公式:爱是一个人给出他/她没有的东西。不过,这一次让我们把视角放在回顾需求(need)、 要求(demand)和欲望这三者的差异上。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美国的解决方案是歇斯底里式的:它选出了一位明摆着并不可靠的主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称职的主人。若仔细观察,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障碍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解决:美国爱他们的主人们,不仅不顾忌他们的虚弱,而且恰恰因为他们的虚弱。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以多元主义(pluralism)为特征的美国民主制度有赖于我们对一位无能的(unverm?gender)大他者的忠诚。
在这里读者可能已经认出了我们此前所说的无能的大他者,理想父亲就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amanwithoutmeans)。成为欲望主人——也就是理想父亲被假定该有的样子——的唯一途径,要不是变得无能,要不就是死去。这位父亲所建构的兄弟社会(fraternity)同样也是无能的,避免兄弟间的纷争所需的禁令让它瘫痪了。詹姆斯?乔伊斯的《柏林都人》(Dubliners)是文学上最佳的例证。语言、国家与宗教。三位理想父亲,一个禁令的泥淖。这样一个社会无法永远持续。 最终,理想父亲的律法被废止,暴虐的原父归来。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着手接管。
现代权力的杰出形式似乎就是“现代神经质”(modernnervousness)的来源。除此之外,随着那个“标记了确定性的地方”被抹除,享乐爆发,如果不是酿成了更多的不满的话,民主制度至少也是为了承认矛盾缓和的不可能性而设的。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言,“各种性需求不可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它们将他们分开了。
相关推荐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保定
¥ 45.24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济宁
¥ 27.01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烟台
¥ 44.4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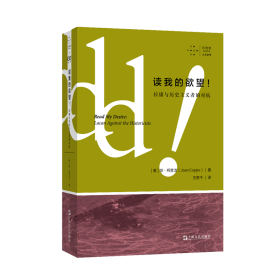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无锡
¥ 36.66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天津
¥ 49.92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保定
¥ 45.24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九品北京
¥ 36.85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九品北京
¥ 36.77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成都
¥ 42.30
-

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
全新保定
¥ 42.90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