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19.46 4.0折 ¥ 49 全新
库存61件
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译者:陈小慰
出版社上海译文
ISBN9787532776337
出版时间2017-12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9元
货号30034021
上书时间2024-10-13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文学奖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奖励和荣誉,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国内外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
自从1969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之后,她的作品频频获奖,这也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女仆的故事》(1985)、《猫眼》(1988)、《别名格雷斯》(1996)曾三次获得布克奖提名,最后凭借第十部小说《盲刺客》摘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的桂冠。
阿特伍德的影响不仅跨越了国界,也跨越了文学领域。她一直十分关注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和加拿大日益美国化的倾向;为抗拒这种倾向,她大力支持以推进独立的加拿大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阿南西出版社,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她帮助成立了加拿大作家协会,并曾任该作协的主席,还担任过国际笔会加拿大中心的主席。此外,她在《纽约人》等多种国际知名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短篇小说、评论等;她还应邀在美、英、德、澳、俄等国朗诵和演讲,扩大加拿大的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她开始关注另一领域——环境保护,显示了很强的生态意识,并因这方面的创作、论述和所采取的行动而获得环境保护和社会活动方面的荣誉和奖励。同时,她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政治:如反对美加自由贸易法案、为“大赦国际”组织的斗争在加拿大开辟阵地,等等。总之,在过去的约30年中,她一直以加拿大文学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被列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百位加拿大人”的第五位。
目录
夜……001
采购……005
夜……039
等待室……045
午休……075
一家人……087
夜……115
产日……123夜 ……163
安魂经卷……171
夜……221
荡妇俱乐部……229
夜……297
挽救……305
夜……331
史料……339
内容摘要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女性并非这场浩劫中唯一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精彩内容
第一章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育馆。那里从前曾举行过比赛,为此,光亮可鉴的木地板上到处画着直的和圆的线条;篮球架上的篮筐还在,但网早已脱落。馆内四周是一溜供观众坐的看台。我想我仍可以隐隐约约,如某种残留影像一般,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用的香水味。先是电影上才能见到的穿呢裙的女生,然后是穿超短裙的,接着是穿裤子的,再后来就是只戴一只耳环、剪刺猬头并染成绿色的。这儿想必也曾举行过舞会。你听,乐声回旋萦绕,各种无人倾听的声音交叠糅杂在一起,一种风格重复着另一种风格。隐约的鼓点,悲苦的低泣,绵纸做的花环,硬纸板做的魔鬼面具,还有一个旋转的反射镜球,在舞者身上洒下片片雪花般柔软的亮光。
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种企盼我记忆犹新。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它永远无法像在停车场上,或是电视厅内那搂着我们的腰背或身上其他地方的双手一样近在眼前、可感可触——声音已经关小,惟有画面在血脉偾张、蠢蠢欲动的肉体前闪现。
那时,我们渴求未来。这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究竟从何而来?它弥漫在空气中,即使当我们躺在排列成行的简易行军床上——相互间隔开着使我们无法交谈,只有一心强迫自己入睡的时候,回想起来,它仍在空气中挥之不去。我们用的是绒布床单,就像孩子们用的那种,还有年代久远的军用毯,上面可见“美国”的字样。我们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脚后面的小凳上。屋内灯光已经调暗,但没有完全关掉。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
不过她们没有枪,即使是她们也未能得到足够的信任配以枪支。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他们既使我们感到害怕,同时也令我们心猿意马,产生其他一些感觉。但愿他们能转过身来看我们一眼。但愿能与他们交谈。要真能如愿,我们想,相互就可以做些交换,达成什么交易买卖的也说不准,毕竟我们还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们常这么想入非非。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几乎不出声地低语。趁嬷嬷们没留意的时候,我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伸出手臂,越过床与床之间的空隔,相互碰碰对方的手。我们还学会了解读唇语,平躺在床上,半侧着头,注视对方的嘴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互通姓名,并一床一床地传过去: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
2采购第二章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抬头望去,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由于盖上石膏,看起来像是一张脸被挖去了眼睛。过去那个位置一定是装枝形吊灯的,但现在屋内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都拿走了。
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窗下的窗座上放着一张垫子。当窗子微微开启——它只能开这么点——徐风飘进,窗帘轻舞,我便会坐在椅子或窗座上,双手交握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也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光亮耀眼的细木条地板上,我能闻出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张碎布拼成的椭圆形小地毯。这是他们喜欢的格调:既带民间工艺色彩,又古色古香。这都是女人们在闲暇时利用无用的碎布头拼缀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勤俭节约,吃穿不缺。我并没有被浪费。可为何我仍觉得缺少什么?
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加了框却没装玻璃的装饰画,是一幅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花还是允许有的。但我想,不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画,同样的椅子,同样的白色窗帘?由政府统一分发?
丽迪亚嬷嬷曾说,就当作是在军队里服役好了。
一张床。单人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上套着白色的植绒床罩。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我明白为何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没装玻璃,为何窗子只能稍稍开启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其实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们会逃走。逃不了多远的。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会用其他方式逃避,那些你可以用来划开血管的东西,例如锋利的碎玻璃。
不管怎样,避开这些细节不谈,这里就像是一间为无足轻重的访客准备的大学客房,或是像从前供境况窘迫的女子居住的寄宿宿舍。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对我们中间还谈得上有什么境况的人而言,其境况确已陷入窘迫。
不过,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我伸出手,放到阳光下。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她向来对非此即彼情有独钟。
计时的铃声响起来了。这里的时间是用铃声来计算的。过去,修道院也曾如此,而且修道院也一样几乎没有镜子。
我从椅子中站起,双脚迈进阳光里。我穿着一双红鞋,平跟的,但不是为了跳舞,而是为保护脊椎。同样是红色的手套放在床上。我拿起手套,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仔细戴上。除了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裙子长及脚踝,宽宽大大的,在乳房上方抵肩处打着褶皱,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我穿红色向来难看,这颜色根本不适合我。我拿起采购篮,挎在手臂上准备出门。
房门没上锁——我不说我的房间,我不愿这么说。事实上,它连关都关不紧。我走进地板光滑的过道,过道中间铺着一条窄长的灰粉色地毯。这条地毯如同林中小路,又像是王室专用地毯,它替我引路,为我开道。
地毯在前楼梯口处折了个弯,沿梯而下,而我也顺着它一手扶着扶栏下楼去了。不知被多少只手摩擦得温暖发亮的扶栏是由一根完整无缺的树干制成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整座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为一个大富豪家族建造的宅屋。走廊里,一台落地式大摆钟正一左一右地摆动着,旁边一扇门通往舒适温馨的前起居室,里面夹杂着肉欲的气息与暗示。我从未在这个起居室里坐过,只在里面站过或跪过。走廊的尽头便是前门,门上方的扇形气窗是彩色玻璃的,上面绘着红色和蓝色的花朵。
走廊的墙上还留有一面镜子。当我下楼时,只要我侧过头顺着裹着脸部的双翼头巾的边缝望去,便可见到这面镜子。这是一面窗间镜,圆圆的凸出来,活像一只鱼眼睛,而我在里面的样子就像一个变形的影子,一个拙劣的仿制品,或是一个披着红色斗篷的童话人物,正缓缓而下,走向漫不经心、同时危机四伏的一刻。一个浸在鲜血里的修女。
楼梯底下有个挂帽子和伞的架子,弯木制的,长而浑圆的木杆在顶部稍稍弯成钩子的形状,宛若蕨类植物向外撑开的枝叶。上面挂着几把伞:黑色的那把是大主教的,蓝色的是他夫人的,而红色的则属我专用。我没去动它,因为我早已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是一片阳光明媚。我不知道大主教夫人是否在起居室里,她并非总是坐着。有时我可以听到她来回走动的声音,一脚轻一脚重,还有她的拐杖轻敲在灰粉色地毯上的嗒嗒声响。
我沿着走廊经过起居室和饭厅门口,来到门厅的另一头,开门进了厨房。这里面不再有家具上光剂的味道。丽塔正站在桌旁,桌面是白色搪瓷的,一些地方掉了瓷。她和往常一样穿着马大服,暗绿颜色,好像从前外科大夫的褂子。那衣服在长度、样式和遮密程度上都与我的相差无几,但外面多套了一件围裙,也不像我们需戴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丽塔只在出门时蒙上面纱,其实没有人会多在乎谁看到了马大的脸孔。丽塔把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褐色的手臂。她正在做面包,这会儿正把面团甩在桌上,最后揉几下,然后做成需要的形状。
丽塔见到我点了点头,很难说她是在向我致意还是仅仅表示看到我了。接着,她把沾满面粉的手往围裙上擦了擦,便到抽屉里找代价券的本子。她皱着眉,撕下三张给我。而我在想,假如她肯笑一笑,那副面容一定很慈祥。但她皱眉头并不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她只是不喜欢红衣服及其所代表的含义罢了。在她看来,身着红色的我也许会像传染病或厄运一样殃及他人。
有时我会站在关上的门外偷听,这种事要是放在过去我决不会干。我不敢长时间偷听,生怕被人逮个正着。有一次我听到丽塔对卡拉说,她可不会这样作践自己。
没人强迫你,卡拉说,不管怎么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宁愿去隔离营,丽塔说,可以选择的。
同那些坏女人呆在一道,最后饿死?天知道还有什么下场。你才不会那么做呢!卡拉又说。
那会儿,她们正边聊天边剥豆荚,即便是隔着那几乎紧闭的房门,豆粒落入铁碗时清脆的声响依然清晰可闻。接着只听丽塔嘟囔了一声或是叹了口气,不知是同意还是反对。
不管怎么说,她们这么做是为了我们大家,卡拉又接下去说,起码话是这么说的。假如我再年轻十岁,假如我还没结扎,可能我也会那么做,其实并不是太坏嘛,毕竟不是什么苦力活。
反正幸亏是她不是我,丽塔正说着,我推门进去了。霎时间,两人脸上显出一副难堪的表情,那副模样就像是女人们在别人背后飞短流长,却发现被当事人听了去一样,但与此同时,也流露出一丝不以为然的样子,似乎她们有权利这么做。后来那一整天,卡拉对我比平时客气多了,丽塔则更阴沉着脸。
今天,无论丽塔如何拉长着脸,紧绷着嘴,我还是想留在厨房里。再过一会儿,卡拉也许就会从房子里别的什么地方带着柠檬油和除尘器进来,而丽塔会去煮咖啡——在大主教们的家里还是能喝到纯正咖啡的——而我们便会坐在丽塔的桌旁聊天,虽然那桌子并非真正属于丽塔,就像我的桌子也并不属于我一样。我们的话题一般都是关于小病小痛什么的,脚痛啊,背痛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像顽皮孩子一样给我们添的种种小乱子。我们不时和着对方的话语颔首示意,表示赞同,是的,是的,一切我们都心领神会。我们会互相交流治病良方,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遭受的各种病痛。我们语气温和地相互诉苦,声音轻柔低沉,带着一丝哀怨,就像鸽子在屋檐下的泥巢里呢喃低语。我们有时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或者用一种偶尔从老人们那里还可以听到的奇怪说法:我听出你是哪儿人了。好像声音本身就是个远道而来的游客。可能真是如此,就是如此。
过去我何其鄙视这样的谈话,如今却对它求之不得。至少它是交谈,是一种交流。
有时,我们也嚼嚼舌根。马大们知道许多事情,她们常聚在一起聊天,将各种小道消息从一家搬到另一家。毫无疑问,她们也像我一样常常隔门偷听,并具有眼观六路的本领,不用看便能把一切尽收眼底。有时我能从她们的窃窃私语里捕捉到只言片语。诸如:知道吗,是个死胎哎。或者:用毛衣针刺的,正对着她的肚子,一定是嫉妒昏了头才干出这种事。要么就是些令人神往的奇闻逸事:她用的是洁厕水,简直神了,你们可能会想他怎么会尝不出来?他一定是烂醉了;不过到头来她还是被发现了。
有时我会帮丽塔做面包,将手插到柔软、温暖并富有弹性的面团中去,体会那种如触摸肌肤般的感觉。我渴望触摸除了布料和木头之外的东西,我对触摸这一动作如饥似渴。
但即使我开口要求,即使我不顾体面,低声下气,丽塔也决不肯让我碰她一下。简直像惊弓之鸟。马大们是不可向我们这类人表示亲善的。
亲善是指情同兄弟。这是卢克告诉我的。他说找不到与情同姐妹相对应的词,只能用拉丁语sororize(结为姐妹)这个词了。他喜欢对此类细节探本求源,如词语的派生、稀奇的用法等。我常笑他迂腐。
我从丽塔伸过来的手中接过代价券,上面画着用它们可换得的物品:一打鸡蛋、一块乳酪,还有一块褐色的东西,想必是牛排吧。我收起代价券,放在袖口带拉链的袋子里,那里还放着我的通行证。
“告诉他们,蛋要新鲜的,”丽塔说,“别像上次那样。另外,告诉他们,鸡必须是童子鸡,不要母鸡。告诉他们这东西是给谁买的,那样他们就不敢瞎对付一气了。”“好吧,”我回答道。我板着脸没笑。干吗要去讨好她呢?
第三章我从后门出去,走进面积很大、干净整洁的花园。园子中央有块草坪和一棵柳树,柳絮正漫天飞舞。草坪边上围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黄水仙花期将尽,郁金香正竞相绽放,流芳吐艳。鲜红的郁金香茎部呈暗红色,似乎被砍断后正在愈合的伤口。
这座花园是大主教夫人的领地。我透过屋里的防碎玻璃窗,常看见她在花园里,双膝跪在垫子上,头戴花园里摆弄花草时用的宽大草帽,脸上遮盖着浅蓝色面纱。她身旁搁着一只篮子,里面装着大剪刀和几条系花用的细绳。吃力的挖土任务通常由一位分配给大主教的卫士完成,大主教夫人则在一旁用拐杖朝他指手画脚。许多夫人都有类似的花园,这里是她们发号施令、呵护操心的地方。
我也曾有个自己的园子。那新翻过的泥土的清香,那圆圆的植物球茎捧在手心的饱满感觉,还有那种子漏过指缝干爽宜人的沙沙声响,这一切我都记忆犹新。那样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有时大主教夫人会让人搬出椅子,在花园里坐坐。远远望去,显得无比静谧、安宁。
她这会儿不在花园里,我开始猜想她会在哪儿,我可不愿冷不防地撞见她。也许她正在起居室里做针线活,患关节炎的左脚搁在脚凳上;也许她正为在前线作战的天使军士兵织围巾,我很怀疑她织的围巾在士兵们那儿能否派上用场,不管怎么说,它们实在是太过精美了。她看不上其他夫人织的十字和星形图案,嫌它们太过简单。她织的围巾两端不是杉树,就是飞鹰,要不就是样子呆板的人形图样,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的围巾适合给孩子用,对大人根本不合适。
有时我想这些围巾压根儿没送到天使军士兵手里,而是拆了,绕成线团,重新再织。或许这纯粹是为了让夫人们有事可干,让她们有目标感,不至于成天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我羡慕大主教夫人的编织活,生活中能有些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小目标是多么令人惬意啊!
她究竟嫉妒我什么?
不到迫不得已,她从不开口对我说话。对她来说,我是个奇耻大辱,却又必不可少。
五星期前,我到这儿上任时,我们初次对视而立。我前任那家的卫士送我到前门。头几天会允许我们走前门,往后就该走后门了。不过事情来得太快,一切尚未确定下来,谁也不能肯定我们的确切身份。过一阵子就会定下来了,要么都走前门,要么都走后门。
丽迪亚嬷嬷说她极力赞成走前门,她说,你们的工作可是功德无量、无上荣光的。
卫士替我摁了门铃,铃声未落,就有人从里面开了门,一定是早已守候在门后了。我本以为开门的是个马大,但眼前分明是穿着粉蓝色长袍的夫人。
这么说你就是新来的,她说。她并未侧开身子让我进去,就这么把我堵在门口,这是要让我明白,未经她的允许不准进门。直至现在,我们为了占据诸如此类的小小上风,还是各不相让,互相较劲。
是的,我回答。
放在门廊上吧,她对帮我提包的卫士说。红色的塑料包不大,另一个包里装着过冬的披风和厚衣裙,过些日子才会送来。
卫士放下包,朝她致了礼,接着脚步声在我身后响起,在走道上渐渐远去了。随着大门喀嗒一声关起,我顿时感到失去了一只保护我的臂膀,在陌生的门槛前备感孤单。
她就这么等着,直到车子发动,开走。我低着头,没看她的脸,但从目光所及之处可以见到她粉蓝长袍下臃肿的腰身,搭在象牙拐杖顶上的左手,以及无名指上一粒粒硕大的钻石。那一度纤细优美的手指仍然保养得很好,关节突出的手指上指甲修成柔和的弧形,在无名指上仿佛一道嘲讽的微笑,一个取笑她的东西。
你可以进来了,她说着,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朝门厅里走。把门关上。
我把红色的行李包提进去,这显然是她的意思,然后关上门。我一声不吭。丽迪亚嬷嬷说过,除非是非答不可的问题,最好保持沉默。尽量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她说话时,两手紧紧地绞在一起,脸上现出紧张不安、卑躬恳求的微笑。她们也不容易。
进来,大主教夫人说。我走进起居室,她已经坐在椅子上,左脚搁在脚凳上,那里铺着一块针绣垫。篮里装着玫瑰。她的编织活摞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上面还穿着针。
我双手交叉站在她面前。原来如此,她开了口。边说边夹起一支烟,用嘴衔着,点上火。她的嘴唇薄薄的,抿着时,周围现出许多细小的直纹,过去在唇膏广告上常可见到。打火机是象牙色的,香烟肯定是从黑市弄来的,这个想法带给我希望。即便眼下不再有现钞流通,黑市照有不误。只要黑市长盛不衰,就总有东西可以交换。这么说她并不恪守那些清规戒律。可我又有什么能与人交换呢?
我如饥似渴地盯着那支烟。对我而言,烟同酒和咖啡一样是绝对不能碰的。
那么老,连他的脸长得什么样都看不出来了,夫人说。
是的,夫人。我答道。
她发出一种近似笑声的声音,接着就咳起来。他不走运,她说。这是你的第二家吧?
第三家,夫人。我答道。
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事,她说着,又带着咳声笑起来。你可以坐下,平常是不准许的,今天就破个戒,下不为例。
我挨着一张硬背椅子边上坐下。我不想东张西望,不想让她觉得我对她有欠恭敬。所以,在我右侧的大理石壁炉,上面挂的镜子,以及屋里的一束束花,都只是在眼角一扫而过,隐隐约约的一团。反正以后要看有的是时间。
现在她的脸和我的在同一位置上了。我觉得她很面熟,至少某个地方似曾相识。一缕头发从她的面纱下露出,色泽依然金黄,当时我以为她也许染过发,染发剂同样可以从黑市弄到。但现在我知道那是天然的金发。她的眉毛修成细细拱起的两道,使她看上去总显得诧异、愤怒或是好奇,一副受惊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可是眉毛下面的眼睫毛却满是倦容。眼睛则又不同,蓝得像阳光耀眼的仲夏天空,带着不容分说的敌意,蓝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鼻子从前可以称得上小巧玲珑,如今在那张脸上则显得太小,不成比例。她脸不胖但挺大,嘴角边有两道皱纹,下巴紧绷着像握紧的拳头。
你离我远点,越远越好,她说。我猜你对我一定也这么想。
我没有回答,答是吧对她不敬,答不是吧又顶撞了她。
我知道你不蠢,她接着又说。她吸了口烟又吐出来。我看了你的档案,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一笔生意场上的交易。不过你可听清了,谁要找我麻烦,我就找谁麻烦,明白吗?
明白了,夫人,我答道。
相关推荐
-

使女的故事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九品北京
¥ 20.00
-

使女的故事 9787532776337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全新上海
¥ 34.5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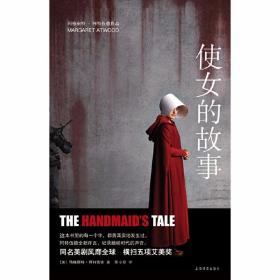
使女的故事 9787532776337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全新杭州
¥ 34.5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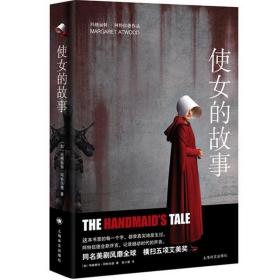
使女的故事 9787532776337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全新杭州
¥ 34.50
-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北京
¥ 24.84
-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太原
¥ 27.56
-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嘉兴
¥ 22.70
-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广州
¥ 18.36
-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广州
¥ 19.9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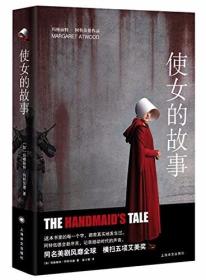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
全新南京
¥ 36.26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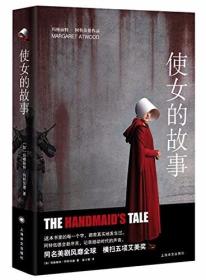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