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河流
①全新正版,现货速发,7天无理由退换货②天津、成都、无锡、广东等多仓就近发货,订单最迟48小时内发出③无法指定快递④可开电子发票,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24.87 4.4折 ¥ 56 全新
库存2件
浙江嘉兴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高领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21212648
出版时间2022-0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6元
货号31364878
上书时间2024-10-12
- 在售商品 暂无
- 平均发货时间 17小时
- 好评率 暂无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高领,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现就职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从事编辑、编剧工作20余年。90年代曾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发表中篇小说《敖包山庄》《黄昏》《敞开回家的路》等。编剧作品有电视连续剧《苍天》《谁来守护正义》《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其中《苍天》获“飞天”特别奖,全国政法题材影视剧二等奖,建国70周年70部优秀政法题材影视剧作品。近年致力法律文化研究与编簒工作。
目录
《一个人的河流》无目录
内容摘要
这是一个奇葩的人。他从不顾忌别人的攻击,同时还很任性,一句感激的话就能让他泪流满面。
他活在这条河上,死了也没离开那些风浪。他近乎传奇的一生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好的命运不仅仅属于聪明的人,愚笨的人也有走得通的路。
精彩内容
一
她从水里游过来,像一条鱼。“这孩子处于巅峰状态了。”赵涵波说。“太丢丑了。”孩子说。孩子爬上岸抖搂着身上的水滴。“不,你是一颗定时炸弹,到时,你就会爆炸,炸翻这条河上所有参赛的人。”赵涵波说。“没有……”孩子说。孩子不好意思起来。“你是的,你是一颗定时炸弹,现在没爆炸,但总有一天会爆炸。太动人心魄了。你不像那些游泳的人。他们只是镀镀金!不、不,你不会这样的。他们在瓜分你的智慧,瓜分,你知道吗?你和他们比赛,他们偷偷向你学习,参赛是手段,偷偷学习是目的,我知道。你多大年纪了?”赵涵波说。“十六。”赵涵波刮目相看了。“真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他盯着她看。“干吗不告诉我呢?你是一个游泳的天才,你岂止是一个运动员?”赵涵波说。“我得天天做作业。”孩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卜爱红。”“卜(不)爱红?这名字太有意思了,爱武。不过没关系。你会成为一位游泳健将的。喜欢垂钓吗?”卜爱红乐了。“你喜欢垂钓?”赵涵波取起垂在河里的渔竿,自我欣赏般,“上面是钓线,系在钓线上的是红丝条,红丝条系在钓线上面,钓线上红红绿绿的,一条条丝线系在竿子上,干什么?迷惑鱼!太有意思了。哈哈!坐在岸上,你像一个神仙,超凡脱俗的神仙,干什么?等鱼上钩。你是一个济世安民的人吗?是的,我是;你是一条河流的老大吗?不,岂止是老大,我是河,河里的波浪,是河中的河。我静观鱼的变化。我独独瞅着河里的波浪。手里的渔竿让我觉察到河,像大夫手指上觉察到病人的脉搏、了解病人的病情。我要起竿了,我钓到的岂止是一条大鱼,钓到的是一条河。你看看……”他伸出手。“我的手温与渔竿是绝缘的,我不让它觉察到我手上的温度,不,不能让觉察到。‘咔嚓!’鱼在咬钩了!我干什么?我就握紧竿子。可见光,可见光你知道吗?从水面望去有一层光,它在微微波动的细浪里,是可见光——只有长久垂钓的人才能看到,它隐藏在细细的波浪里——鱼从可见光里上来了。可乐了,鬼头鬼脑。你像一个老迈的人,你悄悄地往起收渔竿,水波连绵起伏,简直像一幅画,它就在那画里面。岸上是凉风飕飕的,你坐着,它鬼头鬼脑以为你不知道,你简直像一个聋子,闭着眼装着什么也听不见,看不到,只用脑子感受着可见光以及里面游来游去的鱼,杀戮!对!这是杀戮!它像麋鹿东撞西撞在水里。鹿死谁手这个词说得太好了!不知道吧?它就如鹿死在你手。水面是黑麻麻的黑,肉眼是不好分辨的。你慢慢地收竿。因为它上钩了,你要迷惑它。那个慢简直像慢镜头里的人物游动,你慢慢悠悠收竿,因为它要上钩了,噌!你‘噌’的一下收起竿!它傻了。它使劲在空中扑腾!有什么用?它脱离水什么也不是!它是你的了!你这时就这么说。你开始排险,一点点排险,把失误排到最小,‘噼啪!’它跃在空中了。千分点,一千分之一点,你就这么说,按一千分之一点失误捕它。没有多少余地。你收竿。你成功了!”赵涵波说。赵涵波手舞足蹈的。
“不行,我得练习游泳了。”卜爱红说。赵涵波愣住。“你住哪儿?”“岸那边。”赵涵波摇摇头。“我住在那边的那边,我怎么没见过你?”“我知道你,你是一个怕人打扰的人,我也知道你没有正式职业,你,你的职业就是钓鱼,从我见到这条河我就见你在河岸,你说你是河、河岸,我也这么认为。你不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人。你有学问,对吧?我看到你有很多书,全是关于河的书。你有很多渔竿、渔网,它们全在你的房屋和房屋的走廊里,那里全放着钓鱼的工具。那里还有你喜欢的书。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要看看它们,我看见它们,那些钓鱼工具,呵呵,群英会似的。你是这条河上的杀手!他们太烧包了!我不喜欢艄公呀、河上的商人呀,他们只会划船、买卖。他们没法和你比。我不喜欢。我常听见你吹唢呐。你坐在河上,脱了衣服,让渔竿在水里摆动垂钓,你坐下吹唢呐,你比那些有权势的人令我尊敬。”卜爱红说。
赵涵波摇摇头。“我不喜欢忧忧伤伤的人。”有什么用呢?尤其是你坐在水岸上垂钓,你像一个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你忘记了你记忆中的一切,人生就应该这样。人生就是这样演绎着自己。“望着你的项背,我的敬佩油然而生。我只是一个坐在象牙塔里胡思乱想的孩子,现在我该走了。”卜爱红说。
赵涵波有点抒情意味地望着走了的卜爱红。他不再思量水波是怎么波动的,波动的水流里垂钓的垂线是怎么摆动的,他在思量刚才与十六岁的卜爱红的对话。她应该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垂钓手。他的全部家当,或者说他的全部财产,这些大大小小的渔竿、渔网,加起来,不如她的一身蓝色泳装值钱。它进入水里,在细细的波浪里形成优美的线条,远比他众多渔竿垂落在水里好看。“不过这一点我很认可,也很知足。我喜欢垂钓,胜过喜欢我的双眼。”赵涵波说。这孩子太特殊了。她倏地站在你面前,如一条鱼倏地跃出水面。尤其她的线条,穿着蓝色泳装形成的线条,简直是河流的波纹,再没有像她游动在水浪里那么和谐的了。今天竟遇着卜爱红。今天竟与卜爱红说了那么多话。赵涵波双手握着渔竿蹲在河上。他知足了。
每天哨鸽一飞过酱色的天空,赵涵波就到了河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渔竿、鱼饵、渔网及兜鱼的袋子放下,然后拿起渔竿用下颌顶着渔竿的头,把饵挂在钩上,然后,刷地甩开渔竿,直到它忽忽悠悠落在河面,潜入水里,然后穿着橡胶水裤,哗哗地走在水里,把渔网布置在河里。在人声嘈杂中垂钓是一种极不合理的钓法,即使最老辣的垂钓者,也不会在人声嘈杂中垂钓。他在河上一蹲就是一天,他专门等人空河静时候下网、垂钓。有时候,他要抽一支烟。那是要在天空飘过一朵云的时候,因为云朵能遮住他下的网和垂钓的渔竿。晴天他抽烟,口里吐出的烟云会在河面形成雾影,河里极其敏感的鱼虾见了雾影要立刻逃跑。他下的渔网和渔竿在云影中是极其隐蔽的。他在云朵飘过时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平常人看来,这个样子是最凄怆的,但在他看来是最快乐的时候。他的渔竿上系有羽毛,鹲鸟的羽毛是最轻的,也是最容易觉察到水里的波动的,他常系上鹲鸟的羽毛。在鹲鸟羽毛下的丝线上,蚂蚱被拖在另一头了。溜边是什么也不系的,看到这些,他激动得眼泪汪汪的。“这是多么好的一副渔具!渔网也多么精致。这样的渔具钓不上鱼那简直是说不过去的一件事。”他说。他双目瞪着盯定河面。风平浪静,没有鱼群来了,他就款步走去,极具大将风度去晾网,网晾上以后,他就过去坐下。他的垂钓具体而微。他喜欢用蚂蚱做诱饵。像一个拾荒的人,他天天在洼地寻找、发掘蚂蚱,然后用来做垂钓的诱饵。“是的!又怎么?”他说,“我酷爱钓鱼嘛!”一个不安静的人垂钓是要被人谴责的,至少在他这里是这样。风在竿上打呼哨,我自岿然不动。一个垂钓的人必须具备定力。他最反感把渔网、渔竿随地抛掷。那是对渔具的极大亵渎。任何一件渔具都具有生命。所以,他每天如一个负荆的人,背着渔具,如背负众多生命走着。哪怕一丝网乱了,他也要捋直再走。他爱惜每件渔竿、渔网。不工作了,他就用藤条把它们缠起来,如一个个婴儿包在襁褓里以保护它们。他的渔竿用的是湘妃竹。“你能懈怠?用着这样的渔竿工作你能懈怠?”他说。他天天给它们潲水,它们和人一样需要饮水,在网晒久后,他就给上面潲水。这是必须做的。他的网真的很神奇,在阳光中竟出现了七色彩虹。“这是因为给网上潲了水。”每次看见七彩虹他都在肯定他工作后要高声喊叫起来:“太好啦!”湘妃竹唤起他一种崇敬感。平日他扛着它,他总让它磨着自己的颈项。这样他就感到安心,愉悦。
今天他遇到了卜爱红。起初,他不以为意。干吗这样呢?他不是天天要遇着一些人从河岸走过吗?可看见她凝视他的网,嘴唇微微动,他注意了。那孩子耐心地一点点地看他的渔具,垂钓,鹲鸟羽毛,渔竿通往河面的垂线,他注意到她的严肃与庄重。她一边观察,一边默念着:渔竿,湘妃竹,鹲鸟羽毛……她目光游动,手眼通天。“天性!这是天性!”他说。他看到了孩子和他具有一样的天性。他痛心现在的孩子天天贪玩,不上进。这样下去会毁了一代人的!怎么能使他们走上正路呢?这是他常考虑的问题。这就好了,这孩子热爱一行,而且专注。不管干什么,只要专注就行,包括垂钓。卜爱红走后,他一直在冥想。不能视而不见。一个人的专注是难能可贵的。“我是需要一个助手。那些孩子天天跳着脚闹,父母像一个听差,有什么用呢?我是需要一个助手了。”赵涵波说。
赵涵波开始垂钓了。他一开始垂钓就旁若无人了。一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一根渔竿,一张渔网,拥有一条河。他从小就喜欢钓鱼。可那时他不会钓鱼。他常放冷枪似的撒网,垂钓。他现在是一个垂钓老手了。他每天像一个赌棍一样不动声色蹲在河上垂钓。他的悟性极高,让那些一生都在河上捕获的人甘拜下风。他们常让他“狠劲地刮鼻子”。他最无聊的时候就蹲在河上吹唢呐。他像一个号手,可以河上飞舞的蜻蜓、蝴蝶士兵似的吹来,也士兵似的赶走。
“我是该有一个伴儿了。”他说。
二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黑暗中的水流,并且可以说喜欢上了黑暗中的水流,黑暗中的光波、浪声,以及恍恍惚惚的天际边的月亮。它们让他有一种“别有一番情趣”的感受。在黑暗中垂钓,他能一下认出哪是一条漩流,哪是一道光波,河道的走向,漩涡里响动是哪里来的风。“在黑暗中垂钓是我摈弃尘世的绝好时机。”他说。前脚踏入月光,后脚拖入黑暗里——他从不沮丧——左手在月光里摆动,右手则摆动在夜色里。他像一个还债的人,夜夜守在河上,如挨了一日少一日,偿还了一日少一日,几十年如一日,就这么蹲守在河岸。傍晚,他可以看见西天的火烧云舔着天空,入夜,他可见急变的天气里云雾从河上升腾,淹没了整个河流。他可以聆听到夜里的声音。他聆听着,如一个恋栈的人,舍不得自己的岗位,侧头认真听着河上的奇特声音。他甚至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在白天人的时间多是浪费了,只有黑夜才是属于一个人的。黑暗中一个人蹲着,如果面前是一条河,河成了人的了;面前是一座山,山成了人的一部分了。在黑夜里,人完全垄断了黑夜,黑夜是一个命题,它满载着你过去的思想,你能想见的,你视线范围内的,都属于你。那孩子让他喜欢,就因为她有着黑夜般的宁静。她静静地游泳,游泳完了静静地上岸,穿衣,走掉,静得像一只猫。挨着肩和你站着,他“嗷嗷”叫喊,他最反感这样的人了。一个人能够坐在岸上,泰然自若,一坐一天,一声不吭,那是最让他尊敬的人。他喜欢寂寞,也喜欢享受这种寂寞的人。天上下雨了,我自岿然不动;人们蜚短流长了——有时吵闹沸沸扬扬——我充耳不闻。“说话有用吗?”他说。他看到吵嚷的人——有时吵嚷得面红耳赤——深感悱恻。
“属于白天的人。”他说。
因为没有丁点兴趣,在人们感兴趣的事里面,所以他总是低垂着头或高昂着头不看人走。他像一只斑鸠不熟悉人的话一样,对别人的议论充耳不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他对哪里有鱼,哪里有多少河汊,每道河汊可生存多少鱼虾,这些鱼虾可居住多久,多少鱼虾产卵后要转移,河汊生长的鱼虾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了如指掌。他站在河岸可一站一天。他像一个思想家一样,观察阳光照射在河面的情景,大雨飞溅在波浪上,他说他可闻到河水的馥香,闻到河水的馥香就心跳,仿佛恋人见到心仪之人。平日没事,他就在自己撑起的吊床上晃荡,他享受这份独处。他像一个操盘手一样,闭上眼——河完全在他掌控中——貌似睡觉。
“真得!”他说。
今天早晨,他遇见了何必明。在他系好网绳后抹嘴巴、一回头间,他看见了何必明。这条河上,他还是第一次遇见和他一样宁静的人。何必明不紧不慢——他是河岸上的凿石人——凿石,一下一下,他用眼睛看他,他边撒网边用眼睛看他,他只笑笑,并没说话(说话他就反感了),仿佛在说:我在这儿凿石不会影响你网鱼吧?
“你在干什么?”他问。是他先开的口。
何必明笑了。他没答。
“我在问,你来河上干什么?”他又问。他停下手里的工作。“问我吗?是,我在这儿干活儿。”他说。是要垂钓吗?抑或是经过这里?他不能确定。何必明直挺挺站着,仿佛被他问傻了,用疑惑的,不,胆怯的目光看着他。他喜欢这个样子。当他坐下来垂钓,他走了。他一个人去码那些凿出的石头。他不紧不慢,把一些石头码起来,又去另一处背石头,然后过来又码着。他一上午默默不吭背石头,码石头,直到太阳照射在被他码起的那道石墙上,才向夕阳落去的村庄走去。
“这是一个安静的人。”赵涵波说。他给他在心里留了那么一点位置。 当然是垂钓以外的空余的地方了。
一个有成就的人绝不会夸夸其谈。了解一条河流需要时间。了解那些石头也一样。赵涵波坐下吸烟。一条河有多少漩流,它们将会流向哪个方向,最后可以延伸到什么地方,重要的是它们下面潜藏有多少鱼群,这些鱼群的活动范围有多大,什么时候浮出水面,多大程度,垂钓是最需要掌握鱼群浮上水面的时间与尺度的,这也是垂钓最难把握的,但又必须要把握,鱼群与水波形成怎样的关系,在什么水波下鱼群会大胆地游动出没,什么水波中它们会谨小慎微,甚至逃走……一个好的垂钓者还必须具备好的嗅觉:什么腥味会出现什么样的鱼群,哪些腥味是哪些鱼群散发出来的,一个垂钓手能从几公里外飘来的鱼腥味判断出它们会在什么时辰到来……赵涵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的高超技艺是他多年持之以恒训练出来的。他对要求与他合作的人一概拒绝。诸如钓鱼协会、河道治理委员会、鱼类养殖协会……他喜欢一个人工作。在他垂钓的河上,常常聚集许多垂钓者。因为跟着他下网,总可以有很大的收获。他蹲在河岸的姿势、如何撒网、怎么下落渔竿,都成了那些垂钓者模仿的对象。只要他一动不动坐岸上垂钓,河岸所有的人都与他如此一样的坐姿、垂钓,一声不吭。关键是学习他总可以奏效。他的判断,成了所有人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总是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巨匠!真是一个垂钓的巨匠!”人们说。
他生来就像不能于人群居住,觉得在村庄或城镇居住的人简直不可思议。就是在他居住的河岸的土屋,他也是深居简出,对那些热闹欢腾之事索然寡味,他认为真正有思想的人是需要从人群“择离”出来独居的。“只有独处的人才能完成那些彪炳青史的事嘛!”他说。他几乎没有朋友。他觉得人应该按说话多寡分为三六九等,一个多干少说的人的头脑可以抵过十个、一百个人的头脑,他是芸芸众生的头脑,是人中的灵魂。过去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纯属胡说八道,智慧少语的人属典藏,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的人只适于奔窜。他甚至认为应该让人分类居住,把“没头脑”的人分居一起,把“有头脑”的独居者分居一起,不仅是人类,在自然界亦如此——越是没头脑的动物越喜欢群居,而那些越是大的、有作为的“有头脑”的动物越喜欢独居。
与他相比,他的同行们就显得粗鄙肤浅多了。他们垂钓总是相互交谈,交头接耳,这是他最看不上的。就连他们拿渔竿的笨拙样,都是他不屑的。但他从不指责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造化。”他说。他从不指责别人,也很少听别人指手画脚什么的给他“指点迷津”——倒不是因为他技艺精湛,是他对别人的指责从来充耳不闻。那些钓着一条鱼就欣喜若狂、自鸣得意者,他不嘲笑他们,但从不关注。那些人是不自信的。他们来到河上,他没有来,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来早了;他们坐下垂钓,见他没落座,他们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坐错了地方。他姗姗来迟,成了别人要模仿的。他的渔竿长短,成了别人渔具尺寸的标准。大家毫无怨言地容忍着他这种嘲弄——要知道有人在这之前是天不亮就来到了河边,整整早他两个时辰。他什么时候垂钓、垂钓有多久了,人们记不得了,因为他一天到晚蹲在河边,一动不动,给人的印象他是生在河上的,是河的一部分。有人大胆地问:“你来河上垂钓多久了?”他的回答是:“我不记得,我也从不去记它。”至于怎么钓鱼,在哪个方位钓鱼,钓到鱼后怎么办,他倒可以与他们交流。他说:“我可以与你们交流怎么钓鱼,但不交流感受。”感受是什么?绣花女拿捏花针,是感受;一个人品味饭食的味道,是感受;把渔线垂入河里,渔线像静脉流过他的手掌,是感受,这不懂能胡吹?他从一开始就说,他最终要把他垂钓的全部知识告诉人们,但现在不是时候。过早地得到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就等于开门揖盗——把自己原来的一点知识也破坏掉了。怎么解释他竿竿不落空的垂钓技能呢?或许是经验,或许是天生的智慧?但说他会把它们留给后人。至于怎么留,什么时候——“也许他宽衣睡觉,吹着呼噜中吧。”人们说。
在他一次谈话中,他说,他不相信一个人有多大能力,但他说任何一次成功的垂钓都与智慧有关。他接着进一步解释道:这个智慧,在整个垂钓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整个垂钓中,河流、河流的走向,风速、在风速中形成的回流,月光、月光下河水的气温等因素,没有这些,没有这么一个综合考量,是不可能进行一次成功的垂钓的。人们说他的智慧是他的第二条河流,而且与他拥有的这条河一样真实、可靠、丰富,甚至比这条真实可靠的河流更富有灵动性,富有变数和感染力。与他坐在河边垂钓,鱼虾什么时候上钩,上钩后怎么样,上钩的鱼虾有多大,它将要进行怎样的抗争,最终结果如何,都在他的大脑里。也就是说,在他的计划和安排里,头一天的思考中。换句话说,今天垂钓是他昨天思考的结果,是他昨天、前天头脑中的复制品。他取出渔竿慢条斯理地系上诱饵,他心不在此,他望那河——河面被风拂动形成波纹——鱼群按他的计划按时来到他要求它们出现的范围。他一边系鱼食,一边观望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河流,他在计划着下一次垂钓的范围、时间与方向。他取出笔写着:“某月某日某时,在某条回流垂钓。气温:××。日光强度:××。风速:××。”他用这些记录垒建着他的高度。正因为这些记录,他从普通垂钓者中脱颖而出,甚至从河流突显出来,成为一条比河水更真实、可靠、丰富的河流。那些鱼群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改变着方向,这对他来说是挑战——可是“小儿科”——他在头一天就在那里下了网,头一天就做了判断——它们投入了“罗网”。“它们是不会向这个方向涌去,也不会跑得这么快,一切都是徒劳,谁控制着这条河流?”他说。他每天的垂钓记录不是拿来吃喝的。他对它们的来去了如指掌。
他每记录完一次垂钓活动,就满意地收起笔和本,叼上一支烟。他一边吸,一边观望河面。这时,河面十分开阔,光怪陆离,一切事物都在变。太阳落山时候,河面上的河藻是暗灰色的,太阳上来它们就变成了橙色、褐色——在太阳照射中,它们变成绿色、紫色、红色,变成一团雾,它们让人辨识不得。这时河藻的水波更是变幻莫测,变化多端。观看这些变化,对一般人来说,似乎没有意义,可对他来说就成为他垂钓的一部分了。他垂钓岂止垂钓一条鱼,一只虾,他垂钓这变化多端、五光十色的整个一条河流,甚至是对一条河的想象。他喜欢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我喜欢。”他说。一个人拥有一条严寒中的河流那简直是一个贵族。“那人居然麻木不仁。”他深表遗憾。他认为这是对垂钓的一个践踏。这是他的错处。不过他颠覆了垂钓人的传说。
赵涵波加快速度往家走。当太阳从河面浮出,也就是说,一直漂浮到那浪尖上,他就匆匆地回家。那里晾着他备用的渔网以及摆放着头一天夜里备好的鱼食,他要回去取它们。他的屋,在荒郊,离村庄一里多地。平日,屋子锁着,他回来,小心翼翼打开门。他要去查看那些挂在庭院木架上晒晾的网,他一条丝线一条丝线查看着,直到查看完毕,从网前走过——院里全是网和渔具——他慢慢地抬头看着那些渔网、渔具。他浏览一遍,把目光移去,光线从渔具隙缝射下来形成斑斓的颜色,他从斑斓色彩走过,那些渔具下,摆放着他养育的各种品种的鱼。他看到一些鱼十分放浪,从缸这头游到那头。这是他喜欢看到的。尤其是那些匪夷所思的光线照射在鱼脊上,似乎可以听到它们幸福的聒噪声。当确认鱼缸里的鱼没有变化,比如有一条鱼下了崽,有的鱼发情、怀孕,他便把目光移去右墙壁——上面挂着各类渔竿和各种垂钓的渔线——他看到光线从上面均匀地照亮所有的渔具、渔网,渔网晒得比较合适,便走去自己的卧室。他从河到家,从来目不旁视,心无旁骛,目光从河上移开,就盯着这些网、渔具了,除此视而不见。
赵涵波从没有能从他严肃的思想中跳出来,他盯视过这些渔具、渔网后,走到第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全是关于垂钓捕获的知识读物,它们从前面的壁柜一直堆到屋顶,整整一墙壁全是书柜,里面全摆放着垂钓、捕获的书籍。他可听到书籍号子般的吟唱。一本书被他看见,或者说一本书扑入他眼帘,所有的书如涸辙之鲋,叫嚷着,拥挤着,扑入他眼睛。他喜欢看到它们这个样子,喜欢它们号子般的叫声。另一面墙壁,陈设着鱼虾的样本,有从深水里打捞上的稀有鱼种,也有浅河湾捕获的少见鱼类,他把它们做成标本陈列。为防止腐变,他给洒了红药水。这些洒了红药水的标本,经阳光照射,如在涣涣水中了,有的快乐自如,有的患得患失,有的则哼哼唧唧如爬坡的老人,还可以看到他生气地狠命推搡挡他路的拥挤的路人。在两个房间中间,是一条通道,通道两侧,他养殖了各种水藻,它们与前面的渔具相映成趣。他睡觉的地方只那么一个角落,在角落摆着一张一坐上人就哼哼哧哧乱叫的床和一把三条腿椅子。一张条木桌子除供他天天坐在前面吃饭外,还兼做着他工作用的文案。赵涵波步履豪迈地走过通道。因为他为保持安静在通道上铺有地毯,即使他踩踏沉重,也没发出声响。从安静的走廊走到那座玻璃房里,他看到即使走开一天也是井然有序的渔具和标本,他研究摆放的风干鱼鳞没有被风吹凌乱,每只鱼盖骨都安静地立在温煦的阳光中。他习惯地坐下检视它们。当他确认一切都完整无缺,便挪动梯子,去取挂在墙壁的渔钩。这时一支渔竿掉了下来,他用手企图抓住,可惜出手晚了没有抓住,渔竿折断。“笨蛋!”他冲自己大声嚷道,“你在干什么?”他十分心疼地捧住渔竿,匆匆地向门外走去。“你在吗?”他大声喊。“出什么事了?”何必明从屋里面出来,“出什么事了?”赵涵波说:“快把胶带拿来!”从他的回话中,何必明听出这是他在自己埋怨自己。何必明摇摇头。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他忍不住要探个究竟。“对不起,赵老师,有什么事吗?”何必明话中明显带着自责。何必明与赵涵波居住三年,从来与赵涵波师生相称。赵涵波严肃地看着何必明裁剪胶带。“你太不小心了。”何必明责备赵涵波。说完,何必明像拿着一件珍贵的物件,双手捧着胶带递给赵涵波。何必明想继续这个话题聊下去,但从赵涵波的表情他看出没这种可能,他便嗫嚅着站在一旁,说了一句“以后得小心”,然后走开。当何必明转过身,也就是走了一步多一点,赵涵波把握着渔竿看着。赵涵波说:“是你动了我的渔竿吧?”何必明听到这么说,不由得停住,并转过身来。“您说什么,赵老师?”何必明明显提高了后边话的音调,带有一种质疑与不满。看他的样子,他要和他干仗,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脸都因气愤过度变红了。赵涵波见何必明盯着他看,摇摇头:“不是……你知道我是爱惜我的渔竿的。”何必明听完赵涵波这么说后,停顿了一下,是那种过度愤怒下听到认错的话后想要解释的停顿,何必明咽口唾沫,然后看看赵涵波,再没说什么,掉头走去。
何必明走后,赵涵波坐下来。他把渔竿放置一边,十分自责地叹着气。怎么才能使这个合住一个屋里的人珍惜他的渔具呢?他并不知道这些渔具的价值。他一定以为他是一个疯子,爱这些渔具超过爱自己。赵涵波捧着渔竿走去。
三赵涵波与何必明初次相识,是在河岸上。当时,赵涵波低头捕鱼,何必明在凿石。何必明凿石发出的“再一下、再一下”的声音,与河上波浪里的“哗——啦、哗——啦”发出的声音正好合拍:何必明凿石发出的“再一下、再一下”声刚结束,河里就发出“哗——啦、哗——啦”的波涛声,“再一下、再一下”与“哗——啦、哗——啦”此消彼长,彼此相衔,不绝于耳,把河岸上垂钓的赵涵波吸引了,赵涵波听得如痴如醉,心里痒痒的。这是凿石吗?这是波浪的声音。这是波浪声吗?
相关推荐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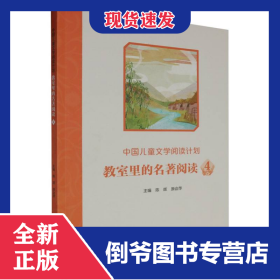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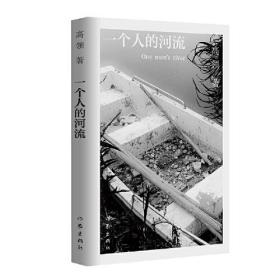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