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9787573906069
全新正版 可开票 支持7天无理由,不清楚的请咨询客服。
¥ 50.58 5.1折 ¥ 99.9 全新
库存126件
作者[美]阿图·葛文德
出版社浙江科技
ISBN9787573906069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99.9元
货号31751798
上书时间2024-01-24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作者简介
阿图·葛文德●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大力褒奖的医学工作者。《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榜单中仅有的医生,2014年《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哈佛医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项目负责人,《纽约客》等杂志的医学专栏作家。
●美国麦克阿瑟奖获得者,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得主,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得主,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
?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阿图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医生世家。作为印度新移民的后代,阿图成长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环境下,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在牛津大学攻读PPE专业(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的经历,对他在医学人文思想和社会支持方面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哈佛医学院就读期间,恰逢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他成为卫生保健部门中的一员。克林顿就职美国总统之后,他成为克林顿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顾问,指导由3个委员会组成的75人医疗小组,那年他只有27岁。
?影响世界的医生
完成学业后,阿图成为了外科医生,但是他不只将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手术台前。面对医疗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他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全球手术清单的研发和实施,呼吁医护人员使用简单、却被证明很有效的清单来改变工作方式。这个项目大大降低了手术中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在全球8个城市(其中既有印度德里,也有加拿大多伦多)执行、推广了这份清单后,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47?——比任何一种药物都管用。
阿图主动普及医学知识,对医疗体制进行思考与变革,他创造性的工作让他在2006年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2010年入选《时代周刊》“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是此份名单上仅有的医生。
?奥巴马医改的关键之笔阿图医生从1998年开始为《纽约客》撰写大量医疗观察类文章,见解深刻。2009年6月,阿图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成本的难题》(TheCostConundrum)探讨医疗费用问题。文中指出,美国的医疗服务及成本存在巨大的区域差距,而卫生保健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医生通过过度医疗提高收入。这篇文章成了医改的催化剂。奥巴马推荐政府官员务必阅读这篇文章,文中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国会立法者们经常引用的论据。
?来自金融大鳄的支票阿图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不仅触动了奥巴马,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大鳄查理·芒格的赞赏。看完这篇文章后,他立即给阿图寄上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巴菲特在知名财经频道CNBCSquawkBox节目上回忆起这件事:“……那是一篇伟大的文章,我的搭档查理·芒格坐下来,立即写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从来没有见过阿图,他们也从未有过任何信件往来,他只是将支票寄给了《纽约客》。他说:‘这篇文章对社会非常有用,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葛文德医生。’”而阿图确实也收到了这张支票,但他没有存入个人账户,而是捐给了其所在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外科和公共卫生部。
?医生中的作家除了医术精湛、主动参与公共事务,阿图在写作方面的成就更是耀眼,他的专栏文章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同时也斩获了众多文学奖项。他先后获得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2011年美国科学和自然写作奖等多个写作大奖。他出版过的4本书,其中3本都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入选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最好的告别》更是荣获2014年众多媒体大奖。
在美国,很多医学院里那些有志于当作家的医学生会被称为“阿图·葛文德”。
目录
总序 了不起的葛文德
楔子 当简单科学遇到复杂个体
第1部分 孰能无过
第1章 一把刀的修炼
我把手术刀放在病人皮肤上,划下第一刀。这种感受实在太奇特了,会让人欲罢不能,它混合了见血的亢奋、担心出错的焦虑和坚定不移的成功信念。
第2章 像机器一样精准
长久以来,西方医学界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近乎机器的完美。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要诀就是“多做”,连续不断地做,有朝一日自然会像庖丁解牛一样熟练而精准。
第3章 切烂的喉咙
我在她脖子上摸索着,寻找甲状软骨的突起,但只摸到一层层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该切下去吗?是横切还是纵切?我真痛恨自己。没有一个外科医师会犹豫不决,而我竟这般踌躇。
第4章 9 000个医生的嘉年华
主办单位安排了3间放映室,接连6天从早到晚播放手术视频,我看得目眩神迷。片中呈现了各种手术,有大胆的,有精细的,还有既简单又高明、令人拍案叫绝的处理方法。
第5章 好医生是怎么变坏的
曾经负责尽职的医生最终堕落的例子比比皆是。根据多项研究,医生酒精成瘾的问题并不会比一般人罕见。另外,由于更容易取得药物和麻醉药品,医生也更可能滥用药物。
第2部分 难解之谜
第6章 13号、星期五、月圆夜
我自认为是个头脑清楚、训练有素的医生,不会被这些迷信的念头击败,于是,我去了图书馆,想找出有关13号星期五的科学研究报告,看看这天是不是真的不吉利。
第7章 疼痛的迷雾
针对慢性疼痛的治疗,除了要完成详尽的身体检查,也要了解病人所在的社会环境中是否存在问题。慢性疼痛往往不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出了毛病,而是我们身体外部的问题造成的。
第8章 孕吐30周
安娜的情况越来越糟,但她完全不考虑人工流产,因为每天,护士都会推着B超机来到她床边,她能听到子宫里两颗小小的心脏在扑通扑通地跳着。这就够了,她决心奋战到底。
第9章 一说话就脸红的女主播
登上主播台后,她发现自己总会忍不住脸红,连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让她双颊绯红,比如播报时突然忘了词,或是发觉自己讲话速度太快,在那一刹那,她已满面通红。
第10章 吃个不停的人
医生详细地向威廉解说了胃绕道手术的原理,也坦白地告诉他,这种手术的死亡率约为千分之五。因为肥胖,威廉已经失去了工作、尊严和健康,他决定放手一搏,手术是他唯一的希望。
第3部分 世事难料
第11章 最后的一刀
今天,我们有电脑断层扫描、超声波等利器,病人去世时,我们早就知道死因了,尸体解剖等于多此一举。我本来是这么想的,然而,有一个病人改变了我的想法。
第12章 “死因未明”的8个婴儿
尽管尸体解剖报告单上写着“死因未明”,我们还是希望医生能找出比较充分的解释。30年过去了,那8个婴儿的猝死之谜的真相,似乎终于露出端倪。
第13章 医疗决定谁来做
你在生病的时候,必须做出明智的选择,知道什么时候该听别人的话,什么时候该坦率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即使选择不自己下决定,也应向医生问明清楚。
第14章 成功会有时
引起坏死性筋膜炎的细菌会长驱直入,侵入深层肌肤,随即在筋膜处大肆破坏,所有的软组织无一幸免。在刚发现的时候就进行彻底的清创手术,患者才有存活的机会。
内容摘要
新手医生阿图满怀抱负进入梦想中的白色巨塔,他将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试炼?硬着头皮开始拿起手术刀的他,将如何处理突如其来的变故?在错误切开病人气管的时候,他如何面对从手边一丝丝逝去的生命?在“成功是常态,失败就是一条人命”的职业生涯中,在每一个或者温暖或惊悚的病例故事背后,都是生与死的殊死较量。
本书精选了14个主题,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医生所面对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做抉择时需要考虑的复杂因素。一个个医学现象背后,是外科医生群体的自我审视与修炼。
适合医疗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阅读。
精彩内容
第3章切烂的喉咙我在她脖子上摸索着,寻找甲状软骨的突起,但只摸到一层层脂肪,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该切下去吗?是横切还是纵切?我真痛恨自己。没有一个外科医师会犹豫不决,而我竟这般踌躇。
致命的过失公众认为医疗过失是由某些医生的不称职造成的,律师和媒体也这样想,但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医疗过失其实经常发生,而且每个医生都有可能出现过失,只是我们很少能亲眼看到医疗过失的发生,因此常常产生误解。错误发生了,我们情愿认为它们是异常的。
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某个星期五的凌晨2点,我穿着手术服,戴着手套,划开一位少年肚子上的伤口——他在打架的时候被人在肚子上捅了一刀。这时,我的呼叫器响了。“外伤,3分钟!”手术室的护士大声读出我的呼叫器上显示的内容。这意味着救护车即将送来另一位外伤病人。作为在急诊室值班的外科住院医生,病人送来时我一定要到场查看。我离开手术台,脱下手术服。另外两位外科医生——主治医生本森和总住院医生继续处理手术台上病人肚子上的伤口。这两人本该来监督指导我处理那位将被送来的外伤病人,但他们现在走不开。本森今年42岁,看起来冷冰冰的,当我走向门口时,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说:“如果你遇到任何麻烦,就呼叫我们,我们两个中会有一个抽身去帮你的。”我还真遇到麻烦了。在叙述这个故事时,为了保护病人、同事还有我自己,我修改了一些细节(包括当事人的姓名),但我会尽可能忠于事实。
急诊室在手术室的上一层,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上去。我到的时候,急诊室的护士刚好把病人推了进来。病人是位30多岁的女性,体重超过了90千克,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推车上,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不断有血从鼻孔中流出。
护士直接将她推入1号手术室。这间手术室贴着绿色的瓷砖,设备齐全,也有足够大的空间来操作移动型X线检测仪。我们把她抬到床上,然后进行检查。一个护士剪开她的衣服,另一个检查她的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数据,第三个护士在她的右臂上扎入粗针头,为她输液。一个外科实习医生将导尿管插入她的膀胱。今晚急诊室中的主治医生是亚瑟,他50多岁,看起来干瘦、憔悴,颇像电影《断头谷》(SleepyHollow)中的纽约警探克瑞恩。他双手交叉,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表示我应该赶紧动手了。
在医院里,住院医生大都会处理一些即时性的任务,而且总是有主治医生在一旁监督指导。那晚,亚瑟是主治医生,病人的一切处理措施都由他负责,我照做就好。不过,他不是外科医生,因此由我来做外科手术。
“什么状况?”我问。
救护人员迅速报告着细节:“女性,姓名不详,因车辆超速而翻车;身体从车内弹出;对疼痛没有反应;脉搏100次/分钟,血压100/60毫米汞柱,呼吸速率每分钟 30次……”他一边说,我一边检查病人的伤势。处理外伤病人的第一步,就是确认病人是否呼吸困难。这位女性呼吸急促而微弱,血氧饱和度只有90%,而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
“她的血氧饱和度太低了。”我没精打采地说。所有的住院医生在医院待上3个月以后,语气都会是这样的。我用手指查清她的喉咙里没有会导致呼吸不顺畅的异物,用听诊器确认了她的两肺没有萎陷,然后给她戴上氧气罩,用力挤压气囊(一个有单向阀的气球,每次挤压后都有1升的氧气进入病人的呼吸道)。大概 1分钟后,她的血氧饱和度上升到了98%,看来她需要我们的帮助才能正常呼吸。“为她插管吧。”我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将导管穿过她的声带,插入她的气管,为她装上呼吸机,以确保她呼吸顺畅。
主治医生亚瑟想为病人做插管手术。他拿起3号喉镜,把弯弯的、很像鞋拔的刀片插入病人喉咙,直至喉头。然后他抬升喉镜手柄,压住病人的舌头,撑开嘴巴和喉咙,露出声带。病人没有抽搐或恶心,表现得很镇静。
“抽吸器,”他说,“我什么也看不到。”他吸出了一杯的血块,然后拿起一条气管内膜导管,试图把管子顺着声带插进去。1分钟后,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
护士说:“已经降到70%了。”亚瑟不停地和管子做斗争,试图将它插进去。这时,病人的嘴唇开始发紫了。
“60%!”护士说。
亚瑟把病人嘴里的东西都拔了出来,然后又把氧气罩戴回病人脸上。血氧饱和度测量计的绿色显示灯一直徘徊在60%,然后又逐渐上升到97%。几分钟之后,他把面罩拿开,再次试图把导管插进去,血氧饱和度又降到了60%。他又拔出导管,把面罩戴到病人的脸上,血氧饱和度回到了95%。
当导管实在插不进去的时候,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特别技术专家。“去请麻醉科医生。”征得亚瑟的同意后,我说道。同时,我继续按照外伤病人的处理原则全面检查病人身体,给病人输液,填写检验单和X线检查单。这些只需花5分钟。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降到了92%,这不正常,因为病人使用了氧气罩。我问护士:“氧气开到最大了吗?”“开到最大了。”她回答。
我再次用听诊器检查病人的肺部,没有萎陷迹象。“我们还是给她插管吧。”亚瑟说。他把病人的氧气罩移开,打算再试一次。
我心想,病人呼吸道阻塞是因为声带肿胀或出血,导管是不可能插进去了。那她活命的机会只有一个,就是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在她脖子上开个小洞,然后把呼吸管从小洞插入她的气管。
如果我想得足够长远的话,我就应该明白自己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做紧急气管切开术。作为手术室内的外科医生之一,我的经验是比其他人丰富些,但这不代表我能胜任这个手术。我只是在六七次气管切开术中担任过助手而已,而且手术大多是紧急情况,所以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去操作。我唯一一次自己练习气管切开术,还是在山羊身上做的。
这种时候我应该马上呼叫本森医生来帮忙,我应该把一切工具器械准备好——照明设备、抽吸器、无菌器械等,我该请亚瑟稍等一下,等支援的医生来了再说。我甚至应该在之前就意识到病人的呼吸道已经完全阻塞了,然后我也许该趁情况还比较稳定,还有时间慢慢来的时候拿起手术刀为病人做气管切开术。但是,也许是因为过于自信、心神不宁、患得患失,或是根本没弄清状况或其他什么原因,我错失了机会。
亚瑟一心想把管子插进病人的声带。当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再次降到60%的时候,他停下手,把面罩扣了回去。我们盯着测量计,然而数字没有回升,她的嘴唇仍然发紫。亚瑟努力挤压气囊,想把更多的氧气送进去。
“氧气进不去了。”他说。
我这才醒悟过来,这简直太糟糕了。“呼吸道堵住了。准备做紧急气管切开术!灯!叫25房的本森医生过来!”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告诉护士把手术服和手套拿来,然后从架子上拿了消毒药水抹在病人的脖子上。一个护士准备好一套无菌铺单和手术所需器械。我穿上无菌手术服,戴上一副新手套,心里反复回想要如何去操作。我告诉自己,这很简单,真的不用紧张:在喉结处有一个小小的间隙,这里有一层薄薄的纤维组织,也就是环甲膜。切开它,你就进入气管了。然后把一条10厘米长的塑胶管插进去,连接起氧气筒和呼吸机,就OK了。但这只是理论。
我把铺单铺在病人身上,把脖子露了出来。我在她的脖子上摸来摸去,想从厚厚的脂肪中找到下刀的地方。
“我需要再亮一点儿。”我说。立刻就有人出去找照明灯了。
“有没有人去叫本森来?”我不太有底气地问道。
“他还在忙。”有个护士回答。
没有时间再等了。缺氧4分钟,病人即便没死,脑部也会因此受到永久性损伤。最后,我拿起手术刀切了下去。我在病人的脖子中央由左至右切了一条7厘米左右长的刀口,实习医生用拉钩撑开伤口,我用剪刀将切口剪得更深一些。虽然没有大出血,但血已淹没了伤口,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叫人把抽吸器拿来,但是抽吸器这会儿不工作了——由于之前使用时血液中有许多组织碎片,导管被堵住了。
“拿些新导管来!”我喊道,“灯怎么还没拿来?!”医院勤务工终于推来一台高架照明灯,可还是太暗。要是有强光手电筒就好了,我想。
我把血抽吸干后,用指尖去摸索伤口。这回我觉得我找到了环甲膜。但我还是不敢完全肯定。
这时,满头白发、经验丰富的麻醉师老本进来了。亚瑟迅速向他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退开一步让他接手。
我像拿笔一样拿着手术刀,想着就从这里切吧,然后使劲一切,突然感到手下一空,我切了一个2.5厘米长的开口。我把食指放进去时,感觉自己好像打开了一个空间,但是我预期的空气流动的声音在哪里?切口够不够深呢?切对地方了吗?
“我想我已经进去了。”我说这话是为了鼓励自己,也让大家放松一下。
“希望如此,”老本说,“她的时间不多了。”我拿起气切管又扭又转,最后强塞了进去。这时,本森赶到了。他探过头来一看,问:“气切管插进去了吗?”“我想是进去了。”我答道。我们把氧气罩与气切管的一端相连。结果,气囊一压,空气就从伤口漏了出来。本森飞快地戴上手套,穿上无菌衣。
他问道:“呼吸道阻塞多久了?”“不知道,大概 3分钟吧。”本森面色凝重,因为他只剩1分钟可以扭转乾坤。他接过手,两三下就把气切管拔出来,一看伤口,叫道:“天啊,真是惨不忍睹,都被你切烂了,我都不知道你切的位置对不对。把灯调亮一些!抽吸器呢?”助手把新的抽吸管递给他。他迅速将伤口清理干净,然后进行下一步。
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太低,血氧饱和计已经测不到了;心跳速率也越来越慢,一开始是每分钟 60多次,现在只有每分钟 40多次;脉搏也完全测不到了。我双手叠在一起放在她的胸部下半段,手肘打直,俯身,帮她做心脏复苏术。
本森抬起头来,对老本说:“我没能及时挽救她的呼吸道。你从上面再试一次吧。”言外之意就是说,因为我的过失,事情被搞砸了。我很难过,只能低着头专心做心脏复苏术,不敢看其他人。我心想,再试一次气管插管又有什么用呢?只能是做无用功,这回真的没救了。
之后,我突然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老本说:“我插进去了!”他用儿科的小号气管内管完成了这个手术。由于人工换气成功,不到30秒,病人的心跳就恢复正常了,血氧饱和度上升到97%。在场的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本森向我交代了一下之后的步骤就回手术室了,那个肚子被捅了一刀的少年还在手术台上等着他。
我们确认了这位病人的身份资料(在讲述中我会用“威廉姆斯”指代她)。救护人员把她送来的时候,她体内的酒精浓度已经超过法定标准上限3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失去了意识。当天晚上,本森和外科总住院医生妮可把她推到手术室,重新做了一次气管切开术。
本森从手术室出来后向病人家属解释,她被送来的时候情况十分严重,呼吸道堵塞,呼吸困难,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救回来。尽管如此,她的脑部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缺氧的状态,因此不知道脑部功能有没有受损。家属静静地听他说着,没有任何异议,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待。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桩外科事故: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手术时把一支很大的金属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肚子里,结果病人的肠子和膀胱都被刺破了;另一位肿瘤外科医生为一位女病人做乳房切片检查,但搞错了地方,使其癌症诊断拖延了数月;还有一位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碰到了一位腹部剧痛的病人,他没做电脑断层扫描就认定病人患有胆结石,18小时后,扫描结果显示是病人的腹部主动脉瘤破裂,没多久,病人就死了。
你可能会说,怎么会有医生犯下这种大错?他们必须为所犯下的过错受到惩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因为医疗过失,医生可能要面对医疗官司、媒体曝光、停职处分,或是被解雇的命运。做错了事就要接受处罚,这固然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现实生活并非这么简单。在医生这个行当中,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医生都可能犯下可怕的错误。想想我刚才描述的实例吧。这些实例来自我询问的一些我认为值得尊敬的外科医生,他们都是从顶尖的医学院毕业的。上述实例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所犯的错误。每一个人都犯过。
亡羊补牢1991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发表了一系列以医疗事故为研究课题的重量级报告——“哈佛医疗执业研究”项目(HarvardMedicalPracticeStudy),研究对象为纽约州的30000多家医院和诊所。研究发现,将近4%的住院病人因为并发症而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残疾甚至死亡,而这些并发症中有2/3是后期护理不当引起的,1/4则确定是由医生的医疗过失所致。据统计,美国每年至少有44000名病人死于医疗过失。
你也许会认为,治疗不当的例子只集中在少数差医生身上,但事实上,大多数外科医生在行医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而在医院照顾病人的临床医生,每年都可能犯下重大错误。每次媒体大幅报道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的时候,医生很少会感到愤慨。他们通常会想:我也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如何避免差医生伤害病人,而是如何保证好医生不去伤害病人。即使可以打医疗官司也于事无补。哈佛法学教授特洛严·布伦南(TroyenBrennan)指出,医疗过失的发生率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那些提出医疗过失诉讼的病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确实是医疗过失的受害人。而医疗官司最终能否打赢,主要取决于原告病人的状况有多惨,而并非这个结果是不是由医疗过失所造成的。
有关医疗官司,更深一层的问题是,若把过失放大化,将其视为不可的问题,那么医生当然会拒绝公开承认和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扭曲的制度造成了医生和病人间的敌对关系。错误发生时,医生几乎不可能坦诚地把错误告诉病人。医院的法律顾问会警告医生,虽然按规定他们必须告诉病人出了什么问题,哪里受了伤,但在言语中不可以暗示在治疗中存在医疗过失。否则,这种“自白”会让病人一口咬定一切后果都是医生造成的,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最多,医生只能说:“我们很遗憾。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医生们坦率地讨论自己的过失,它被称为“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简称为M&M,几乎所有的教学医院每周都会开一次这样的会议。美国大多数州明文规定司法机关不得调阅这种病例讨论会的记录,尽管如此,还是经常有人施压,希望这种会议记录能够被公之于众。外科医生特别重视这种讨论会,在这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认真检讨错误,裁定责任归属,同时进行反思,看看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在我们医院,每星期二下午5点都会召开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所有的外科医生和实习的医学院学生都必须参加,因此出席人数常有近百人。主任外科医生收集了每一个案例的相关治疗信息,包括心脏、血管、外伤等各方面,走上讲台进行报告。
这里有一些病例单,上面列的都是从日常治疗中挑出的典型案例:68岁男性,心脏瓣膜手术后失血过多死亡;47岁女性,左腿动脉旁路术后出现感染,不得不再次手术;44岁女性,胆囊手术后胆汁渗漏;3个病人术后大出血,再次手术;63岁男性,心脏绕道手术后心搏骤停;66岁女性,腹部伤口缝合处的线突然断裂,肠子差点儿漏了出来;还有前面描述的事故——发生车祸、气切失败的威廉姆斯这个惨痛的经验也被列入会议的讨论范围。
轮到这个病例的讨论时,外科总住院医生妮可上台讲述经过:“34岁女性,酒醉驾车,车速过快而翻覆。抵达急诊室时,昏迷指数7分。”(昏迷指数用来评估头部外伤的严重性或昏迷的程度,7分属于昏迷。)接着她又说:“可能是由于呼吸道阻塞,急诊插管数次,没有成功,后来进行气管切开术,也没有成功。”妮可继续报告:“病人心搏骤停,于是为她实施心脏复苏术。麻醉科医生后来用儿科用的气管内管插管成功,病人情况因而稳定下来。”大家心照不宣,威廉姆斯想必是因为脑部缺氧才会出现心搏骤停,这时很容易出现中风或者更糟的状况。随后,妮可阐述了事件的结果:“她的后期检查结果显示,没有脑部永久受损的迹象,也没有其他后遗症。”是的,就我了解到的情况,出院回家后她脖子上的伤口也结痂了。她的家人如释重负,我也是。
负责报告下一个病例的总医生还没登场,第一排突然传来大声斥责的声音:“什么意思?!‘气管切开术没有成功?’”我的双颊火辣辣的,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个病人是我负责的。”本森从前排挺身而出,一句话道尽了外科文化。出现差错时
相关推荐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真相
全新北京
¥ 18.01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真相
全新保定
¥ 18.96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真相
全新保定
¥ 18.34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真相
八五品德州
¥ 2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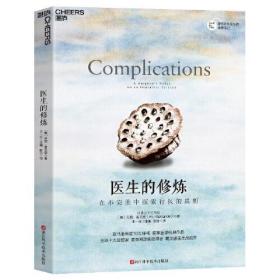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全新成都
¥ 57.45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八五品成都
¥ 30.92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九五品成都
¥ 32.54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八五品成都
¥ 31.07
-

医生的修炼: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九五品成都
¥ 32.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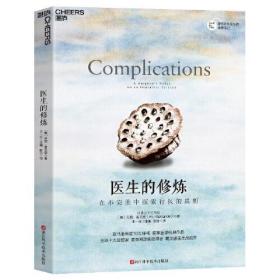
医生的修炼 在不完美中探索行医的真相
全新北京
¥ 68.11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