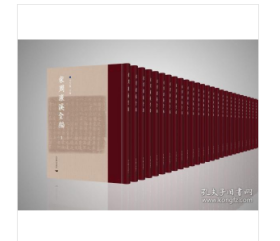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
¥ 134350 8.0折 ¥ 168000 全新
仅1件
作者金生杨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ISBN9787540259754
出版时间2020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其他
定价168000元
上书时间2022-04-01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
周敦頤(一〇一六-一〇七三)原名惇實,字茂叔,宋道州營道(今湖南省零陵縣)人。避宋英宗舊諱宗實改名惇頤。因南宋光宗諱惇,後世通常作敦頤。周敦頤位居『北宋五子』之首,清康熙帝曾稱之爲『有宋理學之宗祖』,開啓心性義理之學,其功甚偉。經南宋張栻、朱熹等的宣揚,特别是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賜謚曰元,淳祐初元(一二四一)詔從祀于學,封舂陵伯,周敦頤的影響便廣及于中華文化圈了。
周敦頤著作不多,却因影響日著,内容簡潔,流傳甚廣。其原著《太極圖》《太極圖説》《通書》及少量詩文而已。南宋時人開始將周氏年譜、家譜,特别是其當時及後世的有關詩文附録于前後;明時更附編《遺芳集》,另辟爲地志,稱《濂溪志》。至清,又有祠志、家譜等類,形式更爲多樣。其《太極圖》《太極圖説》《通書》有單傳者,更多爲易學、性理書所收録,成爲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宋元本源流
潘興嗣《濂溪先生墓志銘》稱其『尤善談名理,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説》《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周敦頤生前,並未將其著述結集、刊刻,僅將所著《愛蓮説》《拙賦》刻石,『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
周敦頤去逝後,其子周壽、周燾邀約蘇軾、黄庭堅等贊述其學術事跡。其家長期保存周氏著作傳本,在南宋時逐漸爲地方官員及學者所知,並傳刻開來。祁寬、曾迪、林栗、朱熹等皆得其家傳本,曾、林更刻而廣之,朱熹亦嘗據以校勘。
程門侯仲良、尹焞、高元舉、朱震、祈寬等則相互傳藏其著作。紹興十四年(一一四四),尹焞門人祈寬《通書後跋》清晰地梳理了《通書》傳藏的源流情况:『《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于程門侯師聖,傳之荊門高元舉、朱子發。寛初得于髙,後得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于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祈寬所見有程門傳本、周氏家藏本。兩本相校,家藏本無《太極圖》,其他舛錯僅三十六字而已。程門傳本又分爲侯師聖傳本、尹焞傳本。朱震嘗訪得侯師聖傳本,録周氏《太極圖説》于《漢上易傳》中,于紹興四年甲寅(一一三四)經筵進呈,開啓易書中録解《太極圖説》的先河。尹焞嘗手書《通書》中言粘之屋壁以自警戒。時紫芝嘗見而注之。朱熹稱:『時紫芝亦曾見尹和靖來,嘗注《太極圖》。不知何故,渠當時所傳圖本,第一個圈子内誤有一點。紫芝于是從此起意,謂太極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凡百説話。』時紫芝所見尹和靖傳《太極圖》與他本不同,其首圈中多一點。時紫芝,南宋建炎、紹興時人,生平事跡不詳,汪應辰嘗薦之曰:『臣伏見左朝散郎時紫芝問學淹貫,而耽玩數象,用意詳密。著《曆書》五十卷,辨析異同,推究微隱,多先儒所未到。士人之明曆學者,少見其比。』祁寬跋文中還解釋了《通書》得名之由,以爲『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朱熹《通書後跋》則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説》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説,實相表裏。』此忽周氏家藏本不論,未爲妥當。
入南宋後,胡安國、胡宏、林栗、朱熹、張栻等人開始整理、刊行周氏著述,而又以朱熹用力最巨。胡宏《通書序略》:『《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敘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胡宏爲胡安國之少子,師事二程弟子楊時、侯仲良,其言《通書》四十章,又論及《太極圖》源流,均可見胡氏長沙傳本即源出于程門傳本。胡銓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五月丙子《道州先生祠記》稱:『舂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兹土。(紹興二年)壬子(一一三二)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舂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録》,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説,味于其所不味。』就此看來,正是胡安國免官歸居舂陵,關注周敦頤遺事,促成其子胡宏整理《通書》而序刻之。朱熹《太極圖通書後序》則認爲胡宏有篡亂之嫌,批評道:『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于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可見胡氏調整程門所傳舊本篇章次第,删除章目,而代之以『周子曰』,已成爲一個新的傳本。
紹興年間曾迪刻濂溪集于永州。曾迪爲三孔外族,出任永州通判,因慕濂溪,據其《拙賦》而築拙堂,請叔父曾幾爲作《永州倅廳拙堂記》,記署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曾迪紹興二十八年(一一五八)正月十五上元日《拙堂留題》則稱:『迪爲兒童時,先公尚書嘗以外祖孔公司封郎中《邵州新遷學記》,及舅氏舍人《祭濂溪先生文》示迪,令熟讀之。……迪以紹興丁未來倅零陵,適繼先生遺躅于九十二年之後。暇日得清獻詩于廳事壁間,已而得釋菜祝文于邵,又得《通書》《太極圖》《拙賦》與夫《墓銘》于先生之家。……迪既刊先生之文,以廣其傳,又以先生事實及諸公詩文附其後,將與同志共進此道,其庶幾乎不墜先公之訓云。』按紹興有七年丁巳(一一三七)、十七年丁卯(一一四七)、二十七年丁丑(一一五七),未有丁未者。據記署時,則當爲丁丑之訛。因此,曾迪刻濂溪集就在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與周敦頤嘉祐八年(一〇六三)移通判永州、治平四年(一〇六七)秋攝邵州事,在永三年,相去正在九十二年之間。蓋周敦頤于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始至永州故。
乾道初年,林栗以左承議郎權發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至九江,武學博士朱熹以書請祠周敦頤于學。『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像與其遺文,並《通書》《拙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鏨諸板,而繪事于學宫,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據此,知周敦頤曾孫直卿家傳《通書》《拙賦》等遺文,而林栗據此刻本以傳。是當即朱熹所言九江本者,時在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二月前。林栗刻九江本,朱熹曾得而校勘,似與原傳本不同。故朱熹延平本《通書後記》稱:『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舊本最引人關注的是其《太極圖説》首句爲『無極而生太極』。
紹興二十二年(一一五二),朱熹得周敦頤《通書》而伏讀之。朱熹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回顧道:『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説之一二。』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朱熹始從李侗學。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五月,以濂學請益問難。《延平答問》上:『五月八日書云:「承惠示濂溪遺文與潁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全本,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嘗愛黄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佳。胸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進。愿更存養如此。』李侗曾見《通書》,可見《通書》在程門傳播比較廣;而所見不全,則可見其影響比較有限。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二月,朱熹與李侗論學,討論《太極圖説》,解『太極動而生陽』爲『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乾道元年(一一六五),朱熹則以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祠周敦臣于學宫,請求左承議郎權發遺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林栗祠周敦頤于江州學宫。在研讀濂溪著述的同時,朱熹也特别重視校勘整理,以成善本。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朱熹編訂《通書》,由湖南帥劉珙刻印于長沙,是爲長沙本。其《太極圖通書後序》云:『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朱熹所搜周氏著述各傳本,包括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舂陵即道州,與零陵一道,皆周敦頤故鄉所在地。九江則爲周敦頤卜居終老之地。舂陵本即胡宏刻本,葉重開嘗重加補正刊行。其《舂陵續編序》稱:『舂陵本最先出,板浸漫滅。重開既白諸郡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並以南軒、晦庵二先生《太極圖説》,復鋟木郡齋矣。』零陵本即曾迪所編刻者,九江則爲林栗所刻者,皆得之周氏後裔所傳。朱熹首次編校,定爲朱氏長沙本。此本一依程門傳本順序,列《太極圖》于《通書》之後,又沿襲了胡宏所更定的《通書》章次及削去原書章目而代之以『周子曰』。朱熹反思道:『諸本皆附(《太極圖》)于《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輙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于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
乾道五年(一一六九),朱熹覆校舊編《通書》,六月二十三日撰《太極通書後序》,是爲建安本。朱熹更定書名爲《太極通書》,置《太極圖説》于篇端,復《通書》章次之舊,删定潘興嗣、蒲宗孟、孔文仲、黄庭堅等人所記周氏行事之重複,合定爲《濂溪先生事狀》一篇。『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説矣。至于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此外,還列舉程氏及門人之言有顯然承用周敦頤之説者,以爲周程授受之證。『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至于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見矣。』朱熹删除潘興嗣、蒲宗孟、黄庭堅等人所記周敦頤行實,而重新寫就《濂溪先生事狀》,已然纂改故書。據朱熹言,他所見『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可見,當時各傳本,實爲周敦頤全集本,並非僅有《通書》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據朱熹言,當時還有周敦頤《易説》傳本,但朱氏以爲非周敦頤精要微言,定其爲僞,而不多論。『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説》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葺緒餘,與《圖説》《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朱熹所謂『舍法時』,指王安石開始推行的三舍法取士,至宣和三年(一一二一)詔罷。
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張栻據朱熹所定建安本,重刻于嚴陵學官。其後跋稱:『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學官,以示多士。』
朱熹于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完成《太極解義》,寄與張栻、吕祖謙討論。張栻亦爲之作解,著成《太極圖解》,乾道八年(一一七二),被人在江西高安刊行。朱熹認爲『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吕祖謙更稱『俟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學者據宋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三《諸儒太極類説》之《南軒文集並語録答問》所録『解義初本』『圖解初本』,基本復原了張栻《太極圖解》初本,是則並未如朱熹、吕祖謙所願,毀板不傳。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四月,朱熹在與張栻、吕祖謙討論的基礎上,修訂定稿《太極解義》,並寫作《太極解義注後記》,但未公之于世。與此差不多同時,在朱、吕的交流切磋下,張栻對其《太極圖解》作了較爲系統地修訂,形成了『正本』《太極解義》。學者也對此進行了輯佚,但所附前後序則雜有定本之嫌。據宋刻《濂溪集》,其《太極圖解後序》署作『癸巳中夏廣漢張栻書』,是其書序定于乾道九年(一一七三)五月仲夏,顯爲定本。所以尤袤《遂初堂書目》、趙希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著録了《南軒太極圖解》《張子太極解義》兩種不同的版本。
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十一月,宋孝宗因不滿《文海》,而令秘書郎吕祖謙重編《宋文鑑》。淳熙六年(一一七九)編成,周必大奉旨撰序繳進。吕祖謙將周惇熙《太極圖説》一文收録其中。
婺源縣宰張漢印刻《通書》。朱熹淳熙六年(一一七九)正月初一《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黄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字爲字,爲出于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方將並附其説于書後,以證黄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
在編定長沙本、建安本後,朱熹又意外地得到九江故家傳本《太極通書》,而爲臨汀楊方所得,故又稱之爲『臨汀楊方本』。『臨汀楊方本』既屬九江周氏家藏本系統,故與程門傳本系統有别。于是朱熹復據楊方本校建安本,發現不同之處凡十九條,而互有得失,于是對周氏重加刊定。淳熙六年(一一七九)四月間,爲延平本《通書後記》稱:『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凡十有九條。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朱熹所謂延平本,學者或以爲即建安本的另爲刊刻者,或以爲非其校刻者。按,朱熹反復校刊《通書》,當以自己校刻成果爲據,再補校新本,故延平本當是遵從朱熹校刻者方是。而此又據臨汀楊方所得九江故家傳再校,得十九條異同,作跋而記録之。
淳熙六年(一一七九),朱熹于南康軍任上,因與周敦頤讀書處鄰近,『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撰《再定太極通書後序》,五月『鋟板學宫,以與同志之士共焉』。朱熹因四事而重訂:一則『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即延平校本所得不同者十九條;再則『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説有失其本意者』,乃得何棄仲《營道齋詩並序》、《與仲章姪手帖》鄒旉跋文、張栻跋文,而反思濂溪之名義,一改以前遵蘇軾、黄庭堅清廉之説,定爲據營道故溪命名,以示不忘其本之意;三則『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是乃反思之前編纂筆削遺漏之作;四則『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是據張詠語而反思周氏學術之傳。于是藉假守南康之際,『别加是下,以補其闕』,鋟板南康學官,是爲南康本。『右《周子太極圖》並《説》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此次校訂,朱熹還對周敦頤《易説》再作考論:『先生《易説》久已不傳于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説》,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詞説》,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决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説》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于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于何時爾。』乾道五年(一一六九),朱熹以世傳《易説》爲『舍法時舉子綴葺緒餘』而成,非周氏書;此經再考,得其一爲《卦説》,乃陳瓘所著,今陳氏《了齋易説》仍傳于世;一爲《繫辭説》,乃佛老陳腐之談,與周敦頤説相去甚遠,『决非先生所爲可知矣』。因此,朱熹仍以世傳者爲僞。此外,朱熹更進一步討論周氏《易説》大旨,以爲『《易説》既依經以解義』,即據經文,逐卦解説,與《通書》『通論其大旨而不繫于經者』相表裏。惟《通書》可説,而《易説》不得而見,朱熹僅爲邏輯推論而已,未必是實。朱熹還將濂溪遺文遺事編訂成册,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道:『《濂溪遺文遺事》一卷,侍講朱熹集次于南康。』
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朱熹又對《通書》重加注釋,成爲其生平中對周敦頤著述的最後定稿。朱熹《通書後序》稱:『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説之一二。比年以来,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倐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朱熹正式刻印《太極西銘解》,其《題太極西銘解後》稱:『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文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由于朱熹此次注釋未對《通書》原文做任何改動,故可視此爲南康本的注釋本,而實爲一本。其注釋也一仍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定本。
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朱熹從洪邁處借得所修《國史》,其《濂溪傳》盡載《太極圖説》,是爲《國史》本《太極圖説》。朱熹道:『此説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深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可見,洪邁修《國史》,所據周敦頤《太極圖説》又别有所本,而與朱熹所見諸傳本不同。本年,朱熹『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括蒼道州知州葉重開以舂陵本爲底本,恢復被朱熹删節的『銘、碣、詩文附見諸舊袠者』,並廣泛搜集周氏其他著述資料,重新分類彙編爲《濂溪集》七卷,是爲周氏别集之始。其《舂陵續編序》詳言道:『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舂陵本最先岀,板浸漫滅。重開旣白諸郡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並以南軒、晦菴二先生《太極圖説》,復鋟木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間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録,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菴更定周子之書至于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諸舊袠者,悉從删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于求道。」重開應之曰:「晦菴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于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况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自遠而即近,由粗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畢録于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矣。』
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著録《濂溪集》兩本,而以有無《太極圖》爲關鍵:『《濂溪集》七卷,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也。……又本並《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状附焉。』陳氏所著録的兩本,與祁寬所言的程門傳本、周氏家藏本頗爲類似,惟稱全書七卷爲獨出。
宋趙希弁《讀書附志》著録有《濂溪先生大成集》七卷、《濂溪先生大全集》七卷兩種不同的版本。『始道守蕭一致刻先生遺文並附録七卷,名曰《大成集》。進士易統又刻于萍鄉,名曰《大全集》。然兩本俱有差誤,今並參校而藏之。』蕭一致刻本,乃其寧宗時任道州知州時所刻,含遺文、附録兩部分。《宋史·藝文志》亦有著録:『蕭一致《濂溪大成集》七卷。』事實上,此本源于度正所編。元黄瑞節稱:『朱子集次周子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其後朱門度正編《周子大成集》七卷,遺文增爲十九篇,《拙賦》《愛蓮説》《養心亭説》《題大林寺》等詩八首,先聖先師二祝文,《賀傅耆手謁》、《與傅耆手書》、《慰李大臨疏》,二家書,吉州彭推官應求《温泉寺詩序》。推官之子思永即明道婦翁也。遺事亦增爲十九條。今考其事,雜見于朱子《事狀》、《通書後録》,而其未及録者,摭取四事附此。』除蕭一致道州刻本外,連州教授、周敦頤後裔周梅叟增補而刻之連州本。方大琮稱:『梅叟闡明家學,以淑其鄉人,皆曰周氏有人矣。對策大廷,陛下拔之稠中,寘之甲科,又皆曰周氏復興矣。蓋自敦頤二子壽、燾好學承家,相繼登元豐、元祐進士第一,爲郎曹一,陞法從,其後浸微。梅叟乃能續響于百五六十年之後,不以高科自居,汲汲焉惟學不足是憂,惟羞先世是恐。掌泮連山,得熙寧中行部過郡之大雲留題,既刻于巖,又取《太極圖》《通書》《大成集》刊于學宫。』又稱周氏『惠新刻《大成集》,其遺文眎春陵本稍增』。清初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四著録:『宋板《濂溪大成集》二册。』進士易統所刻萍鄉本,時間約在紹定元年(一二二八)或稍前。是年二月甲子,萍鄉胡安之叔器《書萍鄉大全集後》有云:『易兄綸叟昆仲暇日攜所刻《周子大全集》見示,曰願有以志其後。』此《大全集》之編或與度正廣泛搜求周氏遺文有莫大關係。度正《書萍鄉大全集後》言周氏之學及學者習讀其書之要,以爲『學者苟能虛心一意,積其操存之實,極其涵養之功,優柔厭飫以求之,夫何難致之有』!其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六月二十八日《書文集目録後》則備言其求訪遺文遺事,補録其書的源委:『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傳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説》《同人説》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于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于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舉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于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傳伯成登第手謁》于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又于重慶之温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傳伯成手書。于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于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于謁、于疏又見其所以篤于朋友慶吊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象其一時切瑳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遊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録》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並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
相关推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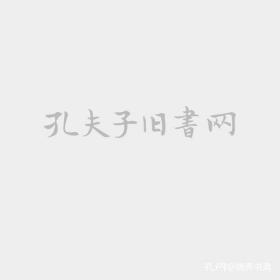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
全新北京
¥ 1092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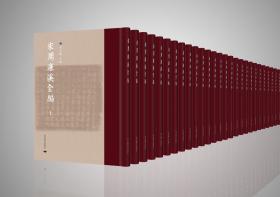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
全新北京
¥ 168000.00
-

宋周濂溪全编,全173册
全新成都
¥ 11424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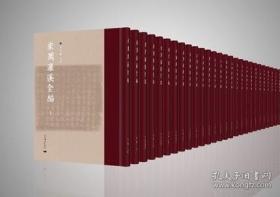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全173册)
全新北京
¥ 10907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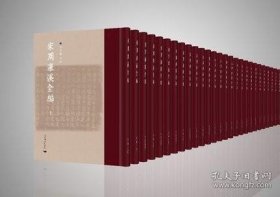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全173册 原箱装)
全新郑州
¥ 1090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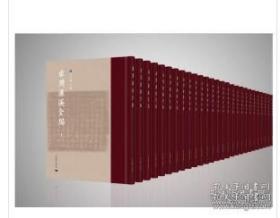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16开精装 全173册 )
全新
¥ 1343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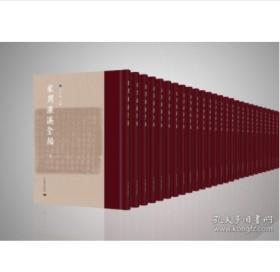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16开精装 全173册
全新杭州
¥ 13196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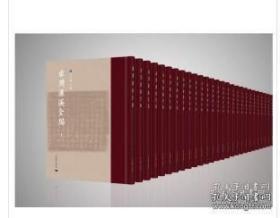
宋周濂溪全编(16开精装 全173册 )
全新杭州
¥ 131960.00
-

【全新正版】宋周濂溪全编(全173册 原箱装)
全新郑州
¥ 109000.00
-

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
九品无锡
¥ 145.00
— 没有更多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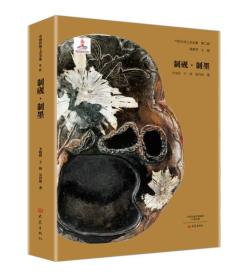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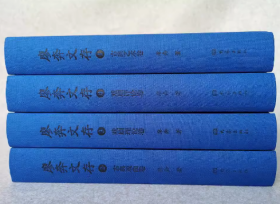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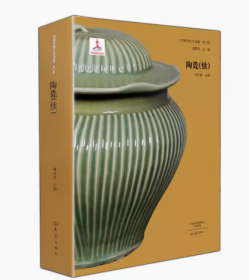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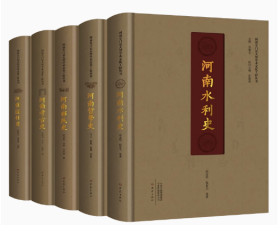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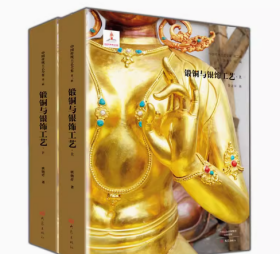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